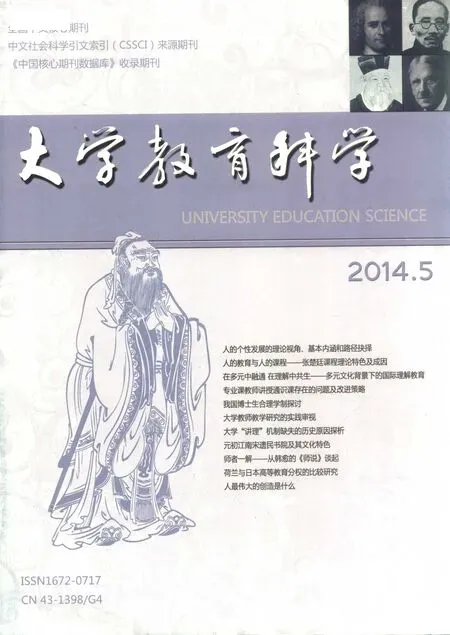人最偉大的創造是什么
□ 張楚廷
我曾問一位院士、大學者:“牛頓和愛迪生,誰更偉大?”我得到的回答是:“都偉大”。顯然,這是回避了那個“更”字。還是同一位學者,幾天之后對我說:“還是牛頓更偉大。”第一次的回答顯然不像第二次那樣作過了較為仔細的比較。
當我再問“牛頓和亞里士多德,誰更偉大”的時候,同一位學者作出了更肯定的回答:“亞里士多德”。牛頓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今天都還是大學生們所必修的,然而,牛頓的力學和微積分在表達方式上發生了深刻且實質性的變化,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則仍然原原本本地擺在大學生面前。
牛頓是偉大的科學家、數學家,亞里士多德是偉大的哲學家。牛頓也是哲學家,但確切地說,他是自然哲學家,跟亞里士多德還是有所不同。牛頓的代表作之一叫《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而亞里士多德的經典之一名為《形而上學》。這大概都堪稱偉大的著作,然而在意義上又是有所不同的。
上面是指人物與人物的比較,就內容而言,這種比較是否表明了哲學家更偉大的觀點呢?
哲學確實代表了人類智慧,人類智慧孕育了哲學,被孕育出來的哲學,又孕育了一代一代人,他們若有哲學的習得,必走向更高的智慧,哲學本因智慧而生,故必給人以智慧;愛智的人必愛哲學;愛哲學者必愛智。有的人自覺地愛著,有的人不自覺地愛著。只要愛著,無論自覺與否,必走向智慧。
哲學畢竟是人的創造,偉大的創造。是否人之最偉大的創造呢?有比它更偉大的嗎?
杜威所說的三段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我們引述如下:
——“哲學甚至可以解釋為教育的一般理論。”[1](P347)
——“教育乃是使哲學上的分歧具體化并受到檢驗的實驗室。”[1](P38)
——“歐洲哲學是在教育問題的直接壓力下(在雅典人中)起源的,這一點使我們有所啟示。”[1](P348-349)
杜威以歐洲、以希臘為例,說明哲學起源于教育。更具體地說,希臘哲學的產生與那些圣哲們創辦學園有關,即與學校、與教育直接相關,教育催生了哲學。
在我們中國也如此。孔孟等圣哲也是在創辦教育的過程中生成了他們的哲學。
為什么教育能催生出哲學呢?因為若要真正理解教育,必理解人;而若要真正理解人,必問“人是什么”,這便是哲學的第一問。首先是教育的第一問,而這個第一問也瞬即成了哲學的第一問。教育最早出現在哪里,哲學就有可能最先出現在哪里。事實能夠證明這一點,邏輯也能說明這一點。
當我們再進一步問“人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的時候,就會想到大自然,想到宇宙。于是“宇宙是什么”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了,出現在哲學里。這是哲學中的宏觀問題,而“人是什么”則是哲學的微觀問題。人們往往是在微觀與宏觀之間來回進行思考的,微觀問題的意義一點也不亞于宏觀問題。誰能說基本粒子的研究沒有對物質世界整體的研究那樣更有意義呢?
我們已經提到過,就起源問題而言,對于宇宙,自康德以來到近代科學,已作出了相當圓滿的回答;而對于人這樣一個“小宇宙”所隱藏的秘密,卻遠沒有弄得很明白。科學不會停止對大宇宙的研究,當然也不會停止對“小宇宙”的研究;然而,哲學將更多地傾向于對“小宇宙”的研究。卡西爾就是走在這個龐大研究隊伍行列中的一位,并且是特別杰出的一位。
希格斯或許終結了物質起源的研究,但誰能終結精神起源的研究呢?誰能終結意識起源的研究呢?現在還沒有跡象表明這樣的研究者是存在的。筆者相信,不存在這樣的終結者。會有深入者,擴充者,更杰出的洞察者,卻永遠不會有終結者。有誰能終結神奇?有誰能終結神秘和神圣?有誰能終結還將繼續的無數神話?
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繼續思考和研究“人是什么”,滿懷信心地深入下去,卻不能妄想終結這一問題。不少哲學家認為自己終結了哲學,這可能是一個誤會;如果認為自己終結了對人的研究,那將是更大的誤會。這種誤會更直接地終結了哲學家自身的哲學。終結的,終究是誤會,而不是哲學。
討論至此,我們已知哲學是人偉大的創造,卻不是最偉大的創造。在其壓力下產生了哲學的教育,無疑更偉大。教育是不是人最偉大的創造呢?
當然,教育是人偉大的創造,更偉大的創造,對此,已有了充分論證。如果認為它是人最偉大的創造,那么,所需特別集中說明的,是一個“最”字。
在人的創造之中,科學、哲學與藝術特別耀眼,特別集中地反映或代表了人的智慧,并且三者常常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人的創造到了頂點,都會與哲學和藝術行見面禮的,科學往往是跟隨藝術和哲學的,大凡杰出的科學家都明白這個道理,都有對藝術和哲學的獨特感受,以致情感至深。
盡管如此,這三個方面還不能算人最偉大的創造,任何創造都難以與人所創造出來的教育相比。我們需要進一步闡明:教育為何是人最偉大的創造?
人類有過了千百種不同類別的活動,從陸地到海洋,從海洋到天空,從航空到航天,從月球到外星。未來,人類還會有很多嘗試,令自己也難以想象的嘗試。從理論上講,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可是,這個限度在哪里,實際上說不清楚。
就已經歷過的活動來說,什么活動伴隨人的歷史最為悠久?哲學,兩三千年吧;宗教活動,最古老的也就只是一兩千年;科學活動,近代以來的三四百年,算上古代樸實的科學活動,最多也只有三千年左右;可能藝術活動最早,大約四萬年左右。
最為悠久的,正是教育。教育在廣義的文化之列,但不如直接說教育更為確切。教育已有了多久呢?人類有了多久,它就有多久。現在所知的數字是382萬年。教育伴隨人類至今,且必將伴隨人類至永遠。就歷史悠久而言,還有什么可與教育相比?
歷史最悠久必然是最偉大嗎?教育是人類創造中最悠久的,它因此而最偉大嗎?
教育還最為人之所需。最為所需就最偉大嗎?吃飯不也是最為人之所需嗎?一個人一日一月一年無教育,問題不算很大,但一天一周一月不吃飯,問題就很大了,吃飯因此而最偉大嗎?我們民間有一說:吃飯大死皇帝。開明的皇帝也明白,老百姓不能餓著了。但這是“大”,而并非偉大,更非最偉大。
衣食住行都很重要,很必要,但與很偉大在性質上還是有所不同。有了基本的衣食之后,人們就會開始尋求其他的創造,物質上的和精神上的創造。不過,教育作為人類活動與衣食住行一樣最需要,這一點仍不足以說明教育更偉大。
特別需要指出三點,首先是人因教育而成為人,人創造了教育,就是人創造了使自己成為人的偉大壯舉。人與其他生命體區別開來是從教育開始的。
第二,教育使人的繼續發展成為可能,使文化一代一代相傳、繼承,并在繼承中越來越富有知識、富有智慧,因而,人因教育而變得更強大、更偉大。
第三,教育是人的其他一切創造活動的前提,為其他一切創造活動提供條件。如今,一個人在學校度過的時光,至高中為12年,至本科16年,至研究生則是20年左右了。甚至,教育延至終身了,出現了所謂終身教育。
歷史更為悠久,更為人之所需,更能持久與人相伴,所有這些方面綜合起來,還不能說明教育是最偉大的嗎?還不能說明教育是人最偉大的創造嗎?
從布衣百姓到所有的大學問家,再到那些開明的政治家,其共同點或最大公約數,無論如何是對教育的虔誠。誰還敢在教育面前,在人類這一最偉大的創造面前懈怠呢?
我們的教育界曾流行一種說法,認為教育是社會經濟的產物,是社會政治的產物,是為統治集團服務的,因而,也受著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制約。你制約我,我就只好適應你,教育就去適應經濟發展,適應政治需要。這就叫做制約論、適應論,有制約論就必然有適應論,兩者相伴相隨。
然而,我們已有足夠的理由認為,教育是人的產物。經濟、政治等也是人的產物,但教育所具有的歷史與現實地位都是經濟、政治所無法比擬的。教育對經濟、政治有最直接、最重大的影響,經濟、政治也影響于教育,是相互影響,但并非對稱性影響,教育的影響是主導的;社會越發展越進步這種主導性作用越顯著。因此,教育是制約者而不應是被制約的;因而,開明的社會,應當去適應人的發展,而不是相反;故而,都應適應教育的發展。最靠近人自身的、最重要,因而,應處在主導的地位。
我們還可以從一個重要的方面來比較教育活動與其他活動在性質上的差別。
例如,自然科學研究活動,它是指向外在的,研究物質世界的,研究天地日月的。然而,教育是指向人的,是指向內在的,指向人的心靈世界。這是一外一內之別。
又如,藝術活動,它是表現于形的,當然,真正的藝術是通過形而表現無形,是由形至神的。然而,教育并不用于表現,而是直接指向人之無形、人之神的。
再如,經濟活動,無論是什么產業經濟,都是為了創造財富。直言之,都將指向更高利潤。然而,教育直接指向的是人的成長、人的精神財富的增長,這與利潤不直接相關。經濟也為人的生活之所需,為富裕之所需;教育則為人本身的美好之所需,富裕不等于美好。教育為經濟活動的更為有效提供條件,經濟也能讓人更美好,但若無精神上的美好,經濟可能產生的美好將不復存在。換言之,經濟之類給人帶來的是身外之物,教育給人帶來的是身內之物。
[1][美]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M].王承緒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