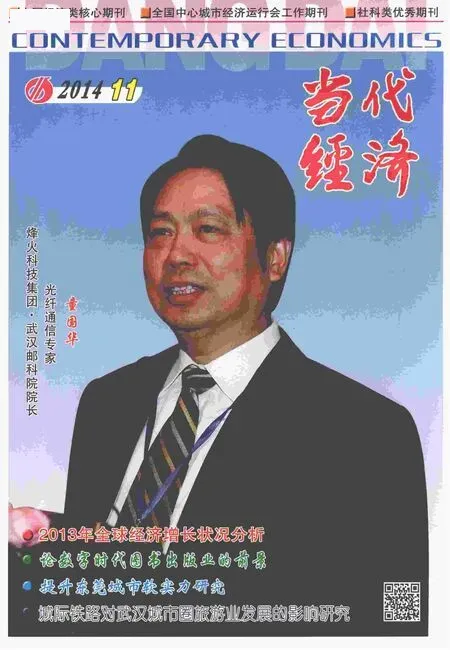論數(shù)字時(shí)代圖書出版業(yè)的前景
○陳蘭平
(湖北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 湖北 武漢 430070)
數(shù)字時(shí)代圖書出版業(yè)的前景,是當(dāng)今出版人無法回避并正在積極思考、努力探索的問題。耳熟能詳?shù)乃^出版業(yè)的“轉(zhuǎn)型升級”,說的就是這個(gè)問題。對此,筆者從以下幾個(gè)方面做些探討。
一、認(rèn)清形勢,堅(jiān)定信念
20世紀(jì)末和21世紀(jì)初,也就是二三十年的光陰,世界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jìn)步突飛猛進(jìn),十分幸運(yùn)的是,這個(gè)時(shí)期正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進(jìn)程同步,中國也從相對落后和貧窮的國度步入發(fā)展中國家的行列,尤其是通訊數(shù)字技術(shù)更是步入先進(jìn)國家陣營。這便是歷史,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隨著我國加入WTO,改革開放的大門打得越來越大,我國的各行各業(yè)由于其在政治或國民經(jīng)濟(jì)中的所處地位不同,有的行業(yè)處于世界競爭的前沿,因而較早適應(yīng)新的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有的行業(yè)由于受政策保護(hù),壟斷性較強(qiáng),其業(yè)內(nèi)外競爭相對較弱,圖書出版業(yè)便屬于此類。長期以來出版社是政府財(cái)政保障的事業(yè)單位,而由事業(yè)單位改制為企業(yè)性質(zhì),則是近幾年的事。伴隨數(shù)字時(shí)代的到來,首當(dāng)其沖的便是文化產(chǎn)業(yè),特別是圖書出版業(yè)。當(dāng)數(shù)字出版初露頭角并展示其便捷性時(shí),坊間便傳言紙質(zhì)圖書出版是夕陽產(chǎn)業(yè),離全面沒落不遠(yuǎn)了。一時(shí)間人云亦云,一般悲觀情緒迅速在出版界蔓延。毋庸諱言,面對數(shù)字時(shí)代的飛速到來,圖書出版業(yè)確實(shí)有些茫然失措,網(wǎng)上也有文從警示的角度說:傳統(tǒng)出版業(yè)是死循環(huán),做書是死,不做書也是死。對此筆者不敢茍同,畢竟出版行業(yè)不是一部被淘汰的機(jī)器。出版業(yè)的管理者,各出版單位的領(lǐng)導(dǎo)者,出版業(yè)的所有從業(yè)者,都決不是一部被淘汰機(jī)器上的不中用的零部件。中國的出版業(yè)是可以與時(shí)俱進(jìn)的,其從業(yè)者也是可以適應(yīng)形勢轉(zhuǎn)型升級的。不論時(shí)代如何進(jìn)步,淘汰的永遠(yuǎn)是落后的產(chǎn)品和技術(shù)。圖書出版業(yè)也是如此,它將會以自己獨(dú)特的方式來發(fā)展壯大。
第一,出版和數(shù)字出版的概念在本質(zhì)上的共同點(diǎn),就是把一份內(nèi)容變成多份內(nèi)容,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就是把一個(gè)人閱讀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變成多人閱讀,即重復(fù)閱讀。數(shù)字出版相對于傳統(tǒng)出版而言,只不過是載體不同而已。數(shù)字出版作為一種出版形式,也必須按出版的規(guī)律來辦,不能完全脫離出版管理而獨(dú)立地去從事數(shù)字出版。那些利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闖入出版界的科技公司,當(dāng)他們涉足出版業(yè)時(shí),如果不與傳統(tǒng)出版業(yè)聯(lián)手,數(shù)字出版就難成氣候。所以,他們做出版的方式多半是與傳統(tǒng)出版社合作,而不是完全游離于傳統(tǒng)出版社之外。數(shù)字出版比較發(fā)達(dá)的美國,初期也經(jīng)歷過此過程,后來數(shù)字出版終究還是與傳統(tǒng)出版走向融合,互相促進(jìn),共謀發(fā)展。
第二,從讀者的閱讀偏好來看,紙質(zhì)圖書的閱讀者不會消亡,傳統(tǒng)出版方式還必須存在。由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組織實(shí)施的第十次全國國民閱讀調(diào)查顯示,國民閱讀紙質(zhì)書和電子書的閱讀率雙升,網(wǎng)絡(luò)閱讀量增加但付費(fèi)意愿降低。調(diào)查還顯示,2012年,中國國民人均紙質(zhì)圖書閱讀量為4.39本,實(shí)現(xiàn)小幅增長,并連續(xù)7年保持穩(wěn)步提升。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郝振省認(rèn)為,圖書閱讀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隨著經(jīng)濟(jì)發(fā)展,國民對文化的追求產(chǎn)生變化,圖書購買力和數(shù)字化閱讀需求都相應(yīng)增長。不可否認(rèn),在電子設(shè)備上閱讀書籍的人越來越多,但還是有很多人堅(jiān)持購買紙質(zhì)圖書閱讀。為什么呢?因?yàn)榭措娮訒袝r(shí)會走神,但閱讀紙質(zhì)圖書會讓人擁有一種幸福感,在翻頁時(shí)有翻的樂趣,還有書的香氣。只有在翻閱紙質(zhì)圖書的時(shí)候,那些文字才有了溫度。再者,電子書沒法呈現(xiàn)紙質(zhì)圖書的裝幀美,也沒有紙質(zhì)圖書的質(zhì)感。最重要的一點(diǎn),紙質(zhì)圖書在閱讀時(shí)可用筆寫寫畫畫,一本書讀下來便有了閱讀者的個(gè)性和印記,也就變成了一本獨(dú)特的書。此外,紙質(zhì)圖書還具有收藏價(jià)值,可作為禮物送人。由此可見,紙質(zhì)圖書的需求是不會消失殆盡的,傳統(tǒng)出版業(yè)也不會消亡。
第三,一個(gè)民族的思想基礎(chǔ)和核心價(jià)值體系的建設(shè)離不開閱讀,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建設(shè)更離不開閱讀。“世界讀書日”(每年的4月23日)的確定,“全民閱讀活動”的推廣,“農(nóng)村書屋”的建設(shè),使得圖書出版業(yè)有了發(fā)展的空間。盡管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不愛讀紙質(zhì)圖書了,成天抱著手機(jī)上網(wǎng)閱讀,即便是乘坐地鐵類公共交通,甚至乘電梯,都習(xí)慣性地用手機(jī)上網(wǎng),但他們一定會回歸到對紙質(zhì)圖書的閱讀中來,因?yàn)槁殘龅男枰x升的需要、生活品質(zhì)的需要,以及深度交流的需要,紙質(zhì)圖書的閱讀會顯得更為重要。有人做過國人閱讀載體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如下:電子閱讀器占2.2%,手機(jī)占9%,上網(wǎng)在線占13.2%,下載打印占1.3%,紙質(zhì)圖書占74.3%。這組數(shù)據(jù)表明,紙質(zhì)圖書閱讀依然是最主要的。由此可見,圖書出版業(yè)的前景還算樂觀。
二、適應(yīng)形勢,盡快轉(zhuǎn)型
形勢的發(fā)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人們只能適應(yīng)形勢。電子時(shí)代是個(gè)大技術(shù)時(shí)代,網(wǎng)絡(luò)的應(yīng)用、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是電子時(shí)代的產(chǎn)物,各行各業(yè)都繞不過去。圖書出版行業(yè)身負(fù)信息傳播和積累文化的責(zé)任,當(dāng)然與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和數(shù)字技術(shù)密不可分。從五百里加急快馬送信,到電報(bào)、電話的應(yīng)用,再到QQ、微信時(shí)代,日新月異的發(fā)展使得地球人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傳統(tǒng)圖書出版業(yè)必須跟上時(shí)代,謀求轉(zhuǎn)型發(fā)展,只有這樣才能適應(yīng)新的形勢。
現(xiàn)在的出版社早已不完全是傳統(tǒng)的圖書出版社了。所謂傳統(tǒng),是個(gè)籠統(tǒng)的概念,而一個(gè)時(shí)代的到來,不是像元旦來臨那樣可以倒數(shù)讀秒的,它是漸變的。20世紀(jì)90年代之前可以說是處于傳統(tǒng)出版時(shí)代。1978年,全國只有105家出版社,每年出書1.5萬種,37.7億冊,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盡管出版社數(shù)量不斷增加,但出書總量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讀者的閱讀要求。這段時(shí)間,就是出版業(yè)的黃金時(shí)代,也是所謂傳統(tǒng)出版時(shí)代。
20世紀(jì)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jìn)入21世紀(jì)后,全國有出版社572家(2004年),年出書21萬種,64億冊。出版競爭日益激烈,各出版社的生存環(huán)境頓感艱難,為了應(yīng)對當(dāng)時(shí)的環(huán)境,各出版單位的改革便提上日程。
近幾年來,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迅猛異常,網(wǎng)商電商呼風(fēng)喚雨,對出版業(yè)的沖擊力日漸顯現(xiàn)威力,出版業(yè)被擠壓得有些踹不過氣來。現(xiàn)在再次強(qiáng)力提出出版業(yè)的轉(zhuǎn)型,與上次的自覺不自覺的漸進(jìn)式轉(zhuǎn)變大不相同。因?yàn)檫@次面對的是數(shù)字出版,是網(wǎng)商和電商的沖擊,現(xiàn)實(shí)要求出版業(yè)要有迅速提升的轉(zhuǎn)型,慢慢來是不行了,因?yàn)樗牧魉倏炝耍绻俦人牧魉龠€要慢的話,那么這只船實(shí)際上是在后退,便有沉沒和淘汰的危險(xiǎn)。
面對出版業(yè)的現(xiàn)實(shí),首先要做好結(jié)構(gòu)優(yōu)化轉(zhuǎn)型,也就是由傳統(tǒng)紙質(zhì)出版產(chǎn)業(yè)向以數(shù)字化內(nèi)容、數(shù)字化生產(chǎn)和數(shù)字化傳輸為特征的戰(zhàn)略性出版業(yè)態(tài)的轉(zhuǎn)型,并用產(chǎn)業(yè)的合理布局來帶動轉(zhuǎn)型。對編輯人員而言,僅有市場意識和經(jīng)濟(jì)頭腦還不行,或者說還遠(yuǎn)遠(yuǎn)不夠,還應(yīng)有較強(qiáng)的信息收集、整理、過濾能力,選題策劃、創(chuàng)新能力,對作者的發(fā)現(xiàn)、挖掘、拓展及對其作品的壟斷能力;要搶占知識產(chǎn)品內(nèi)容的源頭,并作為社會活動家廣交朋友。這便是編輯人員在數(shù)字時(shí)代的轉(zhuǎn)型,即由追求利潤的原始驅(qū)動力的市場意識向智慧型轉(zhuǎn)變。當(dāng)然,編輯的轉(zhuǎn)型,要依賴于所在出版單位或所在出版集團(tuán)的整體轉(zhuǎn)型。要做“大出版”,就要做好相應(yīng)作品的全產(chǎn)業(yè)鏈的文化產(chǎn)品。出版單位(或集團(tuán))要做有影響力的、正能量的作者的經(jīng)紀(jì)人,同時(shí)授權(quán)編輯作為其經(jīng)紀(jì)人的代理人。建國以來出版業(yè)的發(fā)展壯大,使得很多出版社具備了一定的行業(yè)基礎(chǔ),有網(wǎng)商、電商不可比擬的強(qiáng)大的內(nèi)容優(yōu)勢,搶占源頭也好,相對壟斷也罷,這些出版社都有條件開展版權(quán)經(jīng)紀(jì)人和代理人的業(yè)務(wù)。做到這種境界,傳統(tǒng)出版就能優(yōu)雅地轉(zhuǎn)型升級,出版業(yè)也會由寒冬進(jìn)入暖春。
三、駕馭形勢,開創(chuàng)圖書出版的新局面
網(wǎng)絡(luò)運(yùn)營商如京東、當(dāng)當(dāng)進(jìn)軍圖書出版行業(yè),無疑對出版業(yè)造成很大沖擊。出版單位如何應(yīng)對此等局面呢?如何開創(chuàng)出版的新局面呢?第一,圖書出版業(yè)是由國家審批和控制的,從整體上講,出版權(quán)還是壟斷的。也正因?yàn)榇耍W(wǎng)商也好,電商也罷,他們進(jìn)入數(shù)字出版還得通過審批,在數(shù)字出版的內(nèi)容提供方面還有賴于出版單位。第二,許多網(wǎng)商和電商的“超低價(jià)”銷售圖書的模式很難盈利,不可能長期堅(jiān)持下去,所以低價(jià)銷售注定也是行不通的。第三,反過來出版社可以從網(wǎng)商和電商那兒學(xué)習(xí)新的操作模式,如“盛大文學(xué)”的全版權(quán)運(yùn)營模式(“全版權(quán)”是指一個(gè)產(chǎn)品的所有版權(quán),包括網(wǎng)上的電子版權(quán),線下的出版權(quán),手機(jī)上的電子版權(quán),影視和游戲改編權(quán),以及一系列衍生產(chǎn)品的版權(quán)等。盛大文學(xué)全版權(quán)運(yùn)營包含兩部分,即版權(quán)的生產(chǎn)和分銷。版權(quán)的生產(chǎn)在盛大文學(xué)的七大原創(chuàng)文學(xué)網(wǎng)站上完成;版權(quán)的分銷,則是與其他內(nèi)容生產(chǎn)商協(xié)作完成)及“騰訊文學(xué)”模式(即為讀者提供圖書在線閱讀,包括女生原創(chuàng)小說,男生原創(chuàng)小說;出版暢銷圖書,包括都市、言情、青春、玄幻、修真、歷史等熱門種類。同時(shí),也為熱愛文學(xué)寫作的網(wǎng)友提供在線創(chuàng)作、宣傳和銷售的綜合原創(chuàng)文學(xué)平臺)。出版單位可以學(xué)以致用,并利用自身的內(nèi)容優(yōu)勢資源做好這個(gè)板塊。再者,出版行業(yè)有規(guī)模宏大的發(fā)行機(jī)構(gòu)——“新華書店”,各出版單位還有自己的發(fā)行推廣人員,可以相對集中統(tǒng)一起來成立覆蓋全國的圖書銷售網(wǎng),既經(jīng)營實(shí)體書店,又經(jīng)營網(wǎng)絡(luò)銷售。各出版單位還可以搞自己的分眾營銷;各省市書店可以相對獨(dú)立,但又有大聯(lián)合,組成全國的圖書大物流,并可兼營其他物流業(yè);出版業(yè)還可與現(xiàn)有的網(wǎng)絡(luò)運(yùn)營商、電商聯(lián)合發(fā)展,把競爭變成合作,也是可行的。
如此大手筆,當(dāng)然不是單體出版單位可以辦到的,只有出版行業(yè)達(dá)成共識,充分利用好現(xiàn)有政策,大團(tuán)結(jié)、大融合,才能化被動為主動,掌控局面,駕馭形勢,再造出版業(yè)的輝煌。
[1]閻曉宏:關(guān)于出版、數(shù)字出版與版權(quán)的幾個(gè)問題[N].中國新聞出版報(bào),2013-02-21.
[2]朱永新:全面閱讀應(yīng)成為國家戰(zhàn)略[N].光明日報(bào),2013-04-21.
[3]范衛(wèi)平:新聞出版業(yè)轉(zhuǎn)型發(fā)展的三個(gè)問題[J].中國出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