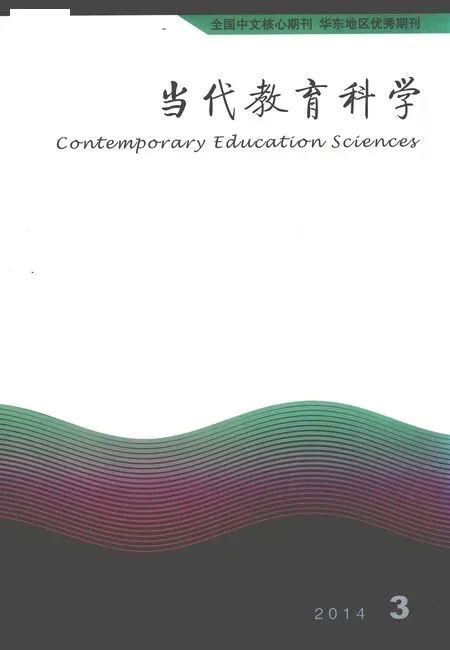美國城途市徑化、進內程容中及公啟民示教育的
● 李朝陽 周菲菲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城市化崛起中,人口的快速增長和社會分化加大了社會關系的松散,削弱了長期認同的模式。人們不再了解自己的鄰居和其他社區的成員。社會關系變得更加冷淡,異質性帶來不斷增強的流動性和不穩定性,個體依附于各種交叉卻沒有關聯的社會群體,成員具有強烈的不安全感。[1]有一個因素涉及到擔心移民作為長期公民的問題:把學校教育視為文化適應的一種工具,也是促使年輕移民遵守美國價值觀的一種方式,并以這種方式使移民成為更有效率的工人,也減少了他們對鄰居的威脅。于是美國通過公民教育,從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教育公民。
一、美國公民教育的途徑
(一)建立街坊文教館
為使窮人和富人在一個相互依存的社區和睦相處,進步主義改革者在城市貧窮地區建立社會服務場所——街坊文教館,給城市貧困人群提供教育與娛樂,志愿的中產階級人士希望緩解自己低收入鄰居的貧困,與他們共享文化和知識。其中,芝加哥的赫爾會所是最大最有影響力的街坊文教館之一。
1889年亞當斯(Jane Addams)創辦赫爾會所。它在建立之初的主要目的是向鄰近地區的工人階級(主要是新來的歐洲移民)提供社會和教育機會。志愿者提供文學、歷史和家政課(比如縫紉),舉辦免費開放的音樂會,也就當前問題舉行自由演講。赫爾會所對不同族裔平等相待,不會歧視移民的民族、語言、信仰與傳統。赫爾會所第一年就吸引了50000人。許多女志愿者后來成為杰出的有影響力的改革者。會所起初沒有真正的醫生,亞當斯自愿擔任隨叫隨到的醫生。救出受到忽視的嬰兒,護理病人,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會所也提出移民政策與衛生保健的改革問題。在街道設立市公共娛樂場、市民體育館,推動教育改革,調查工作、居住與衛生條件。她們也對職業安全與健康、移民權利、養老金等立法產生影響。
為改善移民生活,赫爾會所為他們供應“語言訓練、職業技術、家庭生活、文化博覽與公民課程”。[2]為在日益發展的印刷術行業中及時抓住就業機會,會所還提供裝訂術課程。亞當斯認識到社區也能從舞臺劇中獲益,于是1899年建立一個業余劇團。鄰里希臘人用自己的語言表演了古代經典戲劇,歐洲移民的子女演出莎士比亞。禮堂里洋溢著多民族人群的快樂。會所的勝利使此團體被稱為“霍爾斯特德大街偉大的女士們”。赫爾會所的目標正如它的章程所言:為更高的市民和社會生活提供一個中心;建立和維持教育與慈善事業;調查和改善芝加哥工業區的條件。到1900年美國已有街坊文教館一百多個,1910年超過四百個,街坊文教館成為美國城市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征[3]。赫爾會所創新性的社會、教育和藝術計劃成為運動的旗手。
(二)開辦慈善幼兒園
城市化對婦女的社會角色產生重大影響,一些婦女走出家庭,走向工作崗位,大量兒童由誰照顧和教育成了一個問題,這時幼兒園就“站”出來,擔任這個角色。正如一個公民團體宣稱:“像在這樣的工業城市,我們認為盡可能早的開始兒童的心智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們祈求您,可敬的董事會,繼續幼兒園吧!我們已準備在需要它們的地方建立幼兒園。”[4]教導貧困兒童正確的行為和合乎體統的道德。
有教育者在1870年之前就指出兒童需要學習共同的東西:公民身份、道德、交流和思維的要素。1880年肖(Quincy Shaw)幫助建立三個幼兒園班級,起初它們是慈善幼兒園,幼兒園班級為22個月大到5歲之間的孩子服務。滿足物質需要是第一位的:孩子每天要洗臉,把衣服弄干凈,提供牛奶和面包。一位觀察者曾這樣描述幼兒園的教室:溫暖而愉快,墻上掛著明亮的照片,一個黑板上是一群漂浮在靜靜水面上的天鵝蠟筆畫,另一個黑板上是簡單歌曲的歌詞與含義,在房間一側架子上是一堆玩具娃娃,每個孩子的珍寶零星分散,都放在小手容易夠到的地方。[5]移民貧民區中心的班級活動對孩子有益處。他們行進中唱著“小小鳥”,他們懂得木球來自于參天大樹,漫步于綠色田野,談論著褪色柳和太陽。
(三)設立公民服務屋
1901年肖創辦公民服務屋,這種慈善事業主要從事移民的社會團體活動。在羅馬尼亞移民布盧姆菲爾德(Meyer Bloomfield)的領導下,公民服務屋的安置工作開拓了成年公民身份和美國化的活動。在布盧姆菲爾德的催促下,肖同意贊助職業信息局變成公民服務屋的一個組成部分。職業局對波士頓的職業教育起到重要作用。隨著職業指導從慈善的公民服務屋移到公立學校,安置變成首當其沖的問題,尤其是教育軌道的安置。職業指導幫助家長對子女未來的職業和社會角色做出選擇。
(四)推行夜校教育
面對眾多年輕人白天從事工作,錯過在日校學習時間,馬薩諸塞州轉向夜校,向移民傳授基本的英語讀寫能力,降低國外出生的英語文盲率。夜校使用小學日校教材。立法不僅要求向入夜校者征收出勤押金,還規定入學者的證明與找工作的資格相聯系,如果雇傭了既無英語讀寫能力又無入學證明的人,雇主將受到罰款。這使得夜校從自愿變成強制性,逐步使夜校體制系統化。立法加大了學生的規模與異質性,這有助于塑造公民教育的新內涵。
但學生經過白天勞動再接受夜校教育的話,容易產生疲勞。為克服這個問題,夜校改革教學方法,招入經驗豐富的教師,行為教學加大啟發式的討論與閱讀,調動班級的學習積極性,讓學生感到參加夜校是出于自愿的。還專門為不說英語者的讀物代替小學教材。巴利埃特(Thomas Balliet)督學指出自從成熟的青年男女成為夜校學生之后,要廣泛使用奧布賴恩(Sara O'Brien)的讀本——《外國人的英語》。巴利埃特認為兒童讀物的課程內容不能吸引他們。而此書中課程涉及的是成熟思想的內在興趣,它以正確次序為課堂重現了確切問題。學生不需要閱讀玩具娃娃或學習兒童詞匯就能得到有益知識。1908年勞倫斯學校委員會分發的《非英語夜校生的教學大綱》揭示了如何按性別、國籍、一般智力組織學生。對那些不知道如何教授外國出生者的教師來說,這些讀本提出明確忠告。
夜校變成了個人得到權利的機構,也讓個體知道了如何成為公民。教科書闡述了政府的操作及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系,詳細解釋必需的程序以了解自身的入籍文件。1907年波士頓建立一個特殊委員會,專門為夜校制定公民基礎讀物,讀物聲稱,一旦外國出生者掌握美國語言,就獲得了公民的高尚理想。到20世紀初語言僅是教授適當行為和美國理想的第一步。行為準則取代了讀寫能力和道德價值觀的灌輸,成為定義公民教育的元素。
(五)開辦晚間社會中心
晚間社會中心是開展公民教育的又一種途徑。這種途徑的思想是運用社區觀念把個體融于和諧的公民。城市發展在提供更多自由和選擇的同時,也要承擔社會的分離和孤立[6]。晚間社會中心認為,居住在人口密集的異質性城市,鄰居之間的關系限制了群體身份、相互合作。與鄉村學校學區相比,城里人的社會生活很難組織好。于是城市學校學區使用已有的設施加強與社區的聯系,學校將廣泛運用這些概念——學校走進社區、延展學校課堂之外的職責、同化外國出生者。友好、團結及公民參與成為社會中心的期盼,社會中心運動表明了改革城市公共教育的主題。它將促進社區利益、和諧相處的精神與來到城市之前所了解的民主,從而使公民身份表現出新的涵義。
二、美國公民教育的內容
(一)美國歷史
為了保障移民的忠誠,馬薩諸塞州立法機構在公立學校的必修課程中添加美國歷史。1892年斯普林菲爾德的學校督學提出,如果讓外國人的孩子變成美國忠誠的公民看做公立學校的功能之一,學習美國歷史則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最佳途徑。這強化了課程中美國歷史的重要性,學校的歷史課本補充了戰爭的編年史與政府當局關于社會生活的談論。
巴利埃特指出公立日校變成使外來兒童美國化的最佳手段,公立夜校也應成為兒童家長美國化的機構,傳授美國歷史與政府規則。學校給城市居民輸送美國生活理想。正是美國歷史對智力培養與公民教育的啟迪,美國歷史日益受到重視。在日校這顯示了美國歷史的地位與公民課程的出現。這是一種提高群體忠誠與灌入民族自豪感的方法。目的是讓學生能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可以知道過去的奮斗與英雄精神,是它們帶來了目前的光榮傳統,他們最終可以體會到和平的神圣、當今的昌盛和舒適以及他們自己未來的責任。[7]
(二)傳記
傳記教學和美國歷史密切相關。傳記是融合歷史和公民的一個方式,歷史變成一個追溯當代現象源頭與發展的手段。演化與相似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達爾文論對歷史學家產生的影響。在學校教材中,傳記對兒童來講成為一種指示:兒童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成功的機遇在于他們自身的行動。在這個方面公民學被引入公立學校課程就是一個明顯表現。
(三)美國精神
1892年全國教育協會報道指出,在整個北美大陸有一種愛國的美國主義精神復興。這是多方因素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愛國教師開展明智的工作。公立學校中新美國主義精神是最積極的。曼認為學校在公民之間建立了社區意識。到世紀之交民主和公共教育之間的紐帶已成為一種信仰,早期改革者呼吁學校通過灌輸共同的道德價值觀和基本的智力技能去解決社會問題。他們對學校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憂喜參半,但他們仍保持樂觀,認為學校將依賴家庭和社區之外傳授的價值觀念。在城市和新近到達的移民之間,敵對環境被視為是暫時的可隨時改變的。
三、結論與啟示
城市化中公民教育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如果只是孤立探討公民教育,而沒有考慮到相互作用的環境是不能解決公民教育問題的。公民教育的問題在于城市發展和變化的政治經濟學。公民教育的政治經濟學的要素是城市本身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層面,以及提供人們和關系獨特的空間結構的基本過程。正如新城市社會學所述,空間是深刻的政治,隨著時間推移,空間在政治上已變得更加強大。而在較大的城市環境中,教育不會以任何重要方式獨立于政治力量而運作。單個城市最終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它們都被捕捉在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的大網之內。因此理解塑造公民教育的社會和經濟力量至關重要。
當前我國也在推行城鎮化建設,通過對美國公民教育的途徑與內容的分析,對我國公民教育的啟示是:
(一)推行夜校運動
隨著我國大量人口涌進城市,要建立夜校,開展夜校教育,打發農民工的閑暇時光,充實他們的思想,為農民工提供工作、生活、休閑與公民權利的指示。在貧窮和人口稠密地區,夜校教育應把重點放置在教育管理、采用統一課程和教學標準、認證程序和更有效地生產使用上。將效率、規律性和標準化作為層次結構中的目標。讓流動人口熟悉所居住的城市文化、城市精神、城市領導、城市機構的程序等。把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二)建立公民的社會服務場所
以社區為中心設立街坊文教館,建立街坊文教館學校,為社區居民及其子女提供早期教育、青少年問題的預防和干預等一系列服務。設立社區晚間活動中心與公民會所,發揮公民俱樂部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加強對公民身份、行為準則、道德價值、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解讀。
(三)注重我國傳統文化與歷史
城鎮化的發展使人們物質生活條件發生了改變,出現追風物質主義。而美國公民教育中注重美國歷史和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復興美國精神。為此,我國在公民教育過程中要注重我國傳統文化與歷史的教育,開展名人傳記的閱讀運動。注重公民教育中待人接物、人際關系的原則,提高公民素質、公民心理、公民文化,注重在精神與思想意識領域開展公民教育。
[1]Louis Wirth.Urbanism as Way of Lif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1):1.
[2]厄本.美國教育:一部歷史檔案[M].周晟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271.
[3]克雷明.美國教育史:城市化時期的歷程,1876-1980[M].朱旭東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89.
[4]Marvin Lazerson.Urban Reform and the Schools.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71,(2):134.
[5][7]Marvin Lazerson.Origins of the Urban School.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54.232-233.
[6]John Rury.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