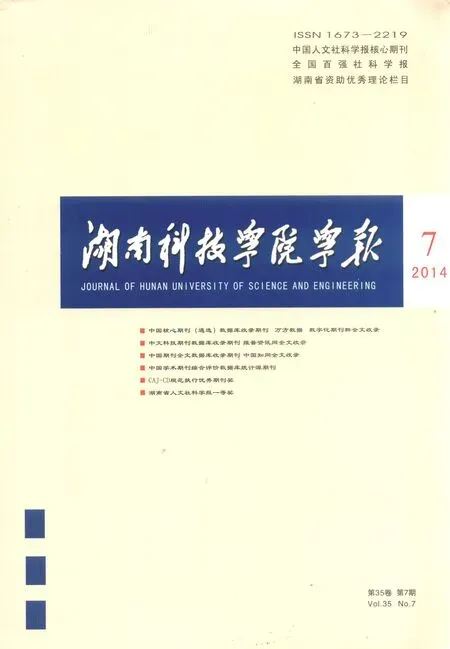舜文化與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
陳仲庚
(湖南科技學院,湖南 永州 425199)
舜文化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源遠流長,涉及方方面面,而要找到其最早的源頭,需要確定一個點,這個點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可以有多個,如被稱為中國文藝理論開山之作的“詩言志”,在《尚書》中托言帝舜,因而可視為舜文化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最早源頭。中國文學在幾千年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以言志抒情為主要特征的詩歌一直占據著正統地位,不能不說與“詩言志”的理論有著深刻的聯系。但“詩言志”畢竟只是一種理論性表述,缺乏創作的典范性意義,而要找到創作與理論相結合的點,《南風》之詩和舜歌《南風》之事是一個很好的范例。結合《南風》之詩和舜歌《南風》之事進行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它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形成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一 開創了中國文學的“觀風”傳統
舜歌《南風》之事,在中國先秦時代有著廣泛的影響,先秦兩漢的諸多典籍均對此事有著大同小異的記載,如《史記·樂書》云:
故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
另外,在《禮記·樂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尸子·綽子》、《韓詩外傳》卷四、《淮南子》之《詮言訓》和《泰族訓》、《新語·無為》、《說苑·建本》、《越絕書》卷十三等文獻中均有記載,其影響可見一斑。那么,《南風》之詩究竟是一首怎樣的詩呢?《孔子家語·辯樂解》云:
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之詩是否真為舜帝所“造”,這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這里不想糾纏其詩的真偽,更不想糾纏其作者的真偽,需要強調的只是:舜文化作為一個文化代碼,它在中國歷史和文化史上是一個真實的存在,并曾經起過核心價值的作用。因此,舜歌《南風》不管其事其詩的真實程度如何,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所產生的作用則是真實的,我們完全可以將它作為舜文化的內涵進行解讀。
分析《南風》之詩和舜歌《南風》之事,有兩個問題必須首先理清楚:其一,《南風》之詩為什么是“生長之音”;其二,“樂”為什么能“與天地同意”。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必須先追索一下“以音律省土風”的古老傳統,而這一傳統又與有虞氏的世職有著密切的關系。
所謂“以音律省土風”,乃是華夏先民長期運用的一種測量風氣、物候的獨特方法,與當時的天文、歷法、農業生產及生活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在早期的典籍中不乏記載。如《左傳·昭公二十年》曰:“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呂氏春秋·察傳》亦云:“夔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從這種記載中不難看出,古人認為音律、樂聲與“風”及國家的治理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以音律來辨別四方或八方之風,在當時是被廣泛尊信的一種專門技術,這門技術被后人稱作候氣法。馮時總結說:“候氣法是一種以律呂測氣定候的方法,它的起源相當古老,惜其術絕來既久。”[1]在《后漢書·律歷志》中還有關于候氣法具體操作的記載,但它是否與上古的法則一致,研究者一直表示懷疑。
候氣法的具體操作方法怎樣我們已經無法考證了,但“以音律省土風”的技術和傳統確實存在過,這是毋庸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技術和傳統最早是由有虞氏家族掌握和繼承的。《國語·鄭語》云: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為王公侯伯。
虞幕為有虞氏初祖,執掌樂官。《左傳》昭公八年言:“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有虞氏家族執掌樂官之職從初祖虞幕一直到虞舜之父瞽瞍,世代均能忠于職守,未有過失。那么,虞幕“聽協風”與“成樂生物”又有什么關聯呢?我們可以看看韋昭的注解:“協,和也,言能聽知和風,因時順氣,以成育萬物,使之樂生。”也就是說,當時的所謂樂官,其職守不僅僅是精通音樂,還要能從音律中聽出和風的到來,預測季節的變化,以使天下民人不誤農時,助生萬物,達到“解吾民之慍”、“阜吾民之財”的目的。誠如是,虞幕的“聽協風”,才能與夏禹的“單平水土”、商契的“和合五教”、周棄的“播殖百谷蔬”相提并論,成為“天地之大功”。
最早的“聽協風”主要是指自然之風,但因自然之風與“成育萬物”相聯系,與“物阜民豐”相統一;而“物阜民豐”與否又與國家的治亂相聯系,治與亂的征兆需要從“民風”中觀察。因此,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說,“協風”與“民風”必須同時關注,這恐怕也是《詩經》稱各國的民歌為“風”的緣由。
舜歌《南風》本來是將“聽協風”與“觀民風”結合在一起的,但到后來,“聽風”的技術失傳,只有“觀風”的傳統延續下來了。
學者們一般都認為“觀風”的傳統源于孔子,其《論語·陽貨》云: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這里所說的“觀”,一般都解釋為“觀風俗之盛衰”(何晏《論語集解》引鄭玄注),如趙孟頫《薛昂夫詩集敘》稱:“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當然,“觀民風”還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考見政治上的得失及其原因,所以班固《漢書·藝文志》說:“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一觀點后人多有贊同。如劉知幾《史通·載文》云:
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
白居易《采詩以補察時政》云:
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
由詩觀風,進而“察興亡”,聞“王政之得失”,才是“觀”的真正目的。治理國家的人通過詩來“觀民風”、“世道”,掌握國情民俗和政治上的興廢得失及其原因,從而調整政策,緩和社會矛盾,引導社會順利發展,這就是通過“觀風”而經國治世的一般原理。而“觀風”之所以能夠“察興亡”、“知得失”,是因為“風”中真實寄寓或記錄了“興亡”、“得失”的實情,如果缺失這種“實情”的寄寓或記錄,“王者”既無由“察”更無由“知”,由詩“觀風”便也無從談起。因此,就“觀風”的傳統而言,孔子的提倡與其說是“源”,不如說是“流”,因為孔子至多是一種發現或認識,他看到了詩中確實有“風俗民情”可“觀”,所以才加以提倡的;而且,這一傳統在孔子之前就已經流傳了多少年,他只是“述而不作”,從理論上加以總結而已。
因此,舜歌《南風》,不僅在詩中真實記錄了風俗民情,也寄寓了自己從“風”中所體察到的風俗民情。作為一個“圣者”和“王者”,他的實踐就是一個最高、最好的典范,后人在理論和實踐上仿效的同時,也就形成了傳之久遠的“觀風”傳統。
二 開創了中國文學的“教化”傳統
與“觀風”相聯系的是中國文學的“教化”傳統,因為“察風俗之邪正”絕不只是消極被動的“察”,還包括積極主動的“教”;而且,“風”的本義上也包含有“教”的意思。《毛詩序》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按照《毛詩序》作者的解釋,“風”包含有“教”的意思,但與“教”又是有所區別的,“風”是“諷喻”,也就是用形象化的手段來打動人,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這一傳統舜帝曾有過更為明確的提倡,《尚書·堯典》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在這里,舜帝命樂官夔典樂,明確提出要用詩樂來教育貴胄子弟,將他們培養成具有“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等品格的人,這無疑是適應當時社會需要的高素質人才。舜帝的這一段話,前半部分是直接對樂官夔說的,夔的職責就是“教胄子”,所以只提出了對貴胄子弟的人格要求;后半部分則是針對整個天下說的,要做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以達到“神人以和”的目的。從“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的要求中不難看出,這不僅僅是指詩歌音樂的和諧,而是要以和諧的詩歌音樂來感化人教育人,使全社會的人都能夠和諧相處、“無相奪倫”,這不僅能夠做到人類自身的和諧,還能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神人以和”意即“天人和諧”,“神”可以代表天地自然。正因為詩歌音樂的教育感化作用有如此之大,所以《毛詩序》的作者才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其實是對舜帝以降歷代先王以詩教化亦即文學教化傳統的一個總結。
“教化”是從文學的社會作用而言的,而事實上,文學的社會作用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而要讓文學真正起到積極的“教化”作用,就必須從內容上提出要求,這就是所謂的“文以明道”或“文以載道”。這個“道”,就是儒家提倡的“堯舜之道”或“孔孟之道”。
從文學史來看,最早提出“明道”觀的是劉勰,他在《文心雕龍》的開篇就說: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由道而圣,由圣而文,文是道之文,圣以文明道。劉勰的這一觀點,清人紀昀曾作了這樣的評點:“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源于道,明其本然。”從文學的社會職能說,理所當然應該“載道”;從文學的起源來說,“文”本來就是從“道”中流出的。因此,在劉勰看來,無“道”不成“文”,“道”因文而“明”,“文”因道而“用”。“道”與“文”的關系,相當于當代的文學理論所說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容。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劉勰的“明道”說雖然不無偏頗,但它確實為后世的“文以載道”而實現教化的理論奠定了基礎。
劉勰之后,在詩文領域提倡“文以明道”的代不乏人,譬如,唐代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宋代柳開、歐陽修等人所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到了明清之際,則又有李贄、湯顯祖、李漁等人強調戲曲的教化功用;有意味的是,小說、戲曲雖不為當時的正統文學觀念所認可,但它們卻同樣重視正統文學觀念所一直提倡的教化功能。這說明,文學的教化功能不僅僅是封建統治者或正統文學所需要的,所教化的對象也不僅僅是“胄子”,而是它本身確實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并已成為古代文人的自覺意識和全社會各個階層的一種“教育”需要。因此,凡是對于社會歷史進步和文化教育需要有一定責任感的作家、理論家,總是自覺地提倡文學的教化功能。李贄、湯顯祖等人大力提倡小說、戲曲的教化功用,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人重視詩文的教化功用,盡管他們的思想態度、政治觀點與正統社會格格不入,但在文學的教化觀上卻與正統社會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這只能說明,文學教化觀本身就包含了一定的歷史進步意義。這種進步意義是它得以貫穿中國古代文論史和文學史始終、并進而成為中國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學優良傳統的真正原因所在。這一優良傳統使源遠流長的古代文學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發揮了巨大的進步作用。
那么,文學教化觀的歷史進步意義體現哪里?主要就體現在它的“以人為本”或“以民為本”的思想中,而這一傳統的形成無疑是與舜文化相關的。舜帝所要求的“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這是要培養人的良好品性和健康人格;虞舜所關心的“解吾民之慍”和“阜吾民之財”,這是要解決民眾的生活需要。前者主要是解決人的精神需求,后者主要是解決人的物質需求。這二者的結合,才使得中國文學在物質生活方面有“風”可“觀”,在精神生活方面所“教”能“化”。正因為舜文化給中國文學提供了這樣的“影響因子”,所以后來的歷朝歷代才能夠“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從而形成源遠流長的文學“教化”傳統。
三 開創了中國文學的“美刺”傳統
“觀風”和“教化”的傳統主要是從文學的內容而言,而為了讓“風”表現得更真實,為了讓“教化”收到更好的功效,必須借助一個有效的表現手段,這個表現手段就是所謂的“美刺”。《史記·樂書》說:“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因此,“彈琴”、“歌詩”只是手段,目的是為了“天下治”;同樣,“觀風”和“教化”也是手段,目的也是為了“天下治”。“觀風”和“教化”為“天下治”服務,“美刺”則為“觀風”和“教化”服務。“美刺”作為文學表現手段,主要就是歌頌與批判,也就是通過歌頌美好事物和揭露批判丑惡事物而使“觀風”和“教化”達到更好的效果,最終達到“天下治”的目的。
“觀風”是為了了解天下的治與亂,“美刺”則是將天下治與亂的現狀及其態度寄寓在“風”中,這一傳統從虞舜開始,到《詩經》已初步形成。《魏風·葛履》云:“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大雅·節南山》云:“家父作誦,以究王讻。”此為刺。《大雅·菘高》云:“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為頌,即美。孔子在總結《詩經》的社會功用時,提出了“興、觀、群、怨”說,其中的“怨”,就是怨刺。《荀子·賦》中也有“天下不治,請陳詭詩”之說。這說明在先秦時代美刺傳統就已基本形成。
美刺傳統真正從理論上進行總結的是漢代。《毛詩序》云: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按照《毛詩序》的說法,“風”包含兩種意義:一是帝王的風化影響到下層百姓;一是下層百姓用詩歌來諷刺政治的得失,表達他們的思想感情。變風變雅之作,起于“王道衰,禮義廢,國異政,家殊俗”,在政治紛亂社會動蕩時期,詩歌尤其富有深刻的諷刺意義。所以“風”的意義,應該以諷刺為主,但它是一種委婉的諷諫,以使統治者能夠了解世道民情和王政得失。因此,這里所謂的“風”同“諷”,也就是“刺”。至于“頌”,或用來頌揚當代帝王的功績,或贊美帝王祖宗的功德,并以此昭告神明。因此,“頌”是歌頌,也就是“美”。《毛詩序》作為儒家詩論的經典文獻,以美刺論詩,揭示了詩歌的基本社會功能,從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這種美刺的表現手法,一直貫穿二千多年的傳統社會。
《毛詩序》之后,鄭玄進一步發展了“美刺”說,其《詩譜序》云:
論功頌德,所以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美刺”說中的“美”,只是《毛詩序》作者對《詩經》中《頌》詩的評論,這一類詩歌以歌頌周王朝統治者的“盛德”為主。但在后來的實際創作中,以歌頌帝王之德為主要內容的作品很少,除了為統治者“潤色鴻業”的漢代大賦是有較高價值的美頌文學之外,像一些宮廷御用文人為帝王歌功頌德的奉召應制之作,是沒有多少價值的。在社會上發揮實際功用的文學,是以“刺”,即揭露批判性的文學為主。在中國古代的文論中也特別重視“刺”,重視怨刺諷諫,傷時濟世。這恐怕與我國流行的藝術發生論也有關系。《禮記·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一直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的主要精神。似乎悲天憫人、傷時憂世的憂患意識是中華民族的天性,我國古代文學在關注現實、指涉人生時幾乎都帶有濃郁的憂患色彩,文學常常自覺地擔負起譏刺時政、感慨世道的“濟時”使命,以至于南宋劉克莊在《跋章仲山詩》中得出“詩非達官顯人所能為”的結論。詩歌乃至整個文學就是窮而在下的文人言說政治現實、時事人生的窗口。
《詩經》的諷諫精神,再加上漢樂府直面現實的文學傳統,在經過《毛詩序》作者等漢代文論家大力倡導之后,在后來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中均得到了發揚。反映在文學理論上,要求文學譏諷時世、補闕時政、關注民生,成為一種理論的自覺。如唐代詩人陳子昂批評齊梁間的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要求文學有“興寄”,寄寓深沉的人生感慨。李白在《古風·第一》中批評建安以后徒尚文采的創作傾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慨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并立志要繼承《詩經》和楚騷直面現實、關注社會的文學精神。陳子昂、李白革除南朝以來浮糜輕艷的文風和局促于個人狹小天地的創作風氣,溯風雅諷諫精神,為文學創作指明了通向現實人生和廣闊社會的正確途徑。杜甫的詩歌創作和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運動踐履了這條通途。杜甫以如椽巨筆“辨人事”、“明是非”、“存褒貶”,描寫廣闊的時代風云,反映深重的社會人生苦難,后人將他的詩歌概括為“詩史”精神。晚唐孟棨《本事詩》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斯言一出,便得到后人的普遍認可。此后,“詩史”成為詩歌理論的一個標范,不僅用來稱道杜詩,而且像陸游、文天祥、謝皋以至近代金和、鄭珍等人記一代之實的詩均被譽為“詩史”。“詩史”說非常切實地揭明了文學貼近現實、關注時代政事、反映社會人生的特點。
需要說明的是,《南風》之詩和舜歌《南風》之事雖然并沒有直接開創出“美刺”傳統,但它卻為后世的文人和文學樹立了一個標尺,后世文人無論是從事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或是文學理論研究,似乎都忘不了一個共同的宗旨,那就是杜甫所說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堯舜時代,既是中國文人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也是用來衡量社會現實的標尺,合則“美”不合則“刺”。因此,舜文化對中國文學美刺傳統的形成和流傳,與其說是影響作用不如說是決定作用,因為就像今天的文學批評必須確定一定的標準一樣,沒有一定的標準文學批評便無從談起;同樣,沒有舜文化這一桿標尺,“美”與“刺”便失去了依據標準。
[1]馮時.殷卜辭四方風研究[J].考古學報,19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