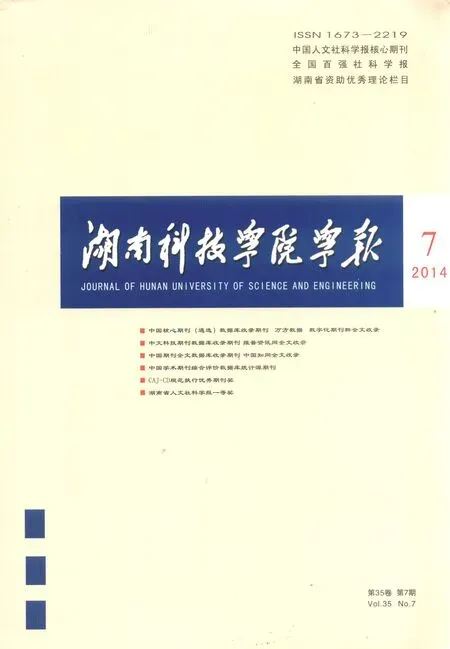小楷《九疑山賦》是柳公權真跡
孫吉升
(寧遠縣民政局,湖南 永州 425600)
1997年春,河南新鄉著名書法家馬慶才先生偶然得到一拓本:柳公權小楷《九疑山賦》,他經過兩年多的考證后,在《書法導報》上披露了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16年來,書法、文物、文學等界專家學者,艱辛探析,各抒己見,求真精神令人敬佩。論點很多,但歸納就是兩點:真品、贗品。說真者以書否文,說贗者以文否書。我在從事《湖南古縣·寧遠卷》編纂工作時,有幸涉及了這一課題,憑天時地利,考論點、查家譜、搜資料、請教專家。經過探析,認為贗品論據一一都能否定,真品論據個個令人信服,似能拂去拓本塵埃、顯現原貌。
一 名家觀點商榷
馬慶才先生說,《九疑山賦》是柳宗元作文。
柳宗元是散文大家,也是“辭賦麗手”,他的賦,沒有寄情山水的,或直抒胸臆、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柳宗元的代表作多在永州創作,但在永州涉及九疑山的詩文只有《與崔策登西山望九疑》一首,柳宗元的作品都由好友劉禹錫保存,并編成《柳河東集》,不可能漏掉《九疑山賦》這篇詩賦。柳宗元到過九疑山,但難以對九疑山研究得那么透徹。文章提及的十八個地名表明,不是九疑山人是不可能完全知曉的。柳宗元與柳公權不是好友。《九疑山賦》是844年書寫的,在柳宗元死后的21年后,柳公權如果還為他書寫,也只是寫墓志銘或行事。
周九疑先生說: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是宋人在《云笈七簽》中才出現。
唐朝司馬禎(646-735)人著《上清天宮地府圖經》,列出了三十六七十二洞天福地的詳細情況,三十六洞天中“第二十三,九疑山洞周回三千里,名曰朝真太虛天,在道州延唐縣,仙人嚴真青治之”。這說明是宋人轉載了唐人文章,不是宋人書中才出現。
周九疑先生說:“云閣兮白云齊”(拓本為飛,府志為齊。)是永福寺齊云閣建筑。永福寺是宋代僧人善義修建。已經死去的柳公權,不可能寫“齊云閣”。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載:永福寺居舜祠之右,舊名無為寺,又名報恩寺。相傳南齊(479-502)敕建。以衛舜祠,有斷碑可識。981年易今名。《玉琯巖無為洞圖》標有:玉琯巖、無為寺、看云閣。這個“看云閣”在南齊時就有了,文章寫的也可是唐朝的“看云閣”,不一定是宋代的“齊云閣”。文章表明,飛是寫云的動態,齊是寫云的靜態。這二字是寫云不是寫閣。拓本中“云閣兮白云飛”比志中“云閣兮白云齊”的確要好,漢武帝劉徹《秋風賦》開頭就唱“秋風起兮白云飛”,毛澤東《答友人》開篇就吟“九疑山上白云飛”。圣人們都用“白云飛”,“白云飛”比“白云齊”要好。
周九疑先生說:文先國提出的府志“有舜江則可浣可漱”不如拓本“有舜江則可枕可漱”之味無窮,卻不敢茍同,因為江水可浣可漱是合其水性的,可枕可漱就難以言通了。
周九疑先生是從水性而言,離開了文章的本意,文章寫的盡是九疑山道家仙人仙事,應從道家仙人典故來理解。宋道州司法參軍鄭舜卿在《永福禪寺記》中說:“衡山多古佛剎,華山、武夷、九疑是神仙窟”。《世說新語·排調》說:“孫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后以漱石枕流或枕流漱石指士大夫的隱居生活。府志“有舜江則可浣可漱”是寫水性,拓本“有舜江則可枕可漱”是寫仙事。
趙衛平先生說:“天下一景,湖南九疑”。僅此兩句,便可斷定此文作者年代……湖南一詞,是宋代行政地名。如果唐人所寫,“湖南九疑”當寫“江南九疑”。
《湖南省志·地理志》載:764年置湖南觀察使,湖南之名自此始。《舊唐書》韋貫之傳,任過湖南觀察使。“湖南九疑”比“道州九疑”名氣要大,比“江南九疑”表述要準。
趙衛平先生說:寧遠的“九疑水始稱瀟水,瀟江,也是宋代才見于記載。
《辭海》上說,“瀟水:源出九疑山,北流零陵入湘江。古以此水與其上游之沱水并稱營水。唐人始稱瀟水。柳宗元《愚溪詩序》、呂溫《道州秋夜南樓即事》皆稱瀟水。”
趙衛平先生說:元結作《九疑山圖記》諸文,未見“碧虛巖”,只有宋代蔣之奇作《碧虛巖銘》才出現。又說舍人李嶠(名挺祖)受郡守之命,以郡守李襲之名義書寫玉琯巖碑銘題記。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說,元次山將“碧虛洞”改為“無為洞”,舍人李嶠在篆刻“無為洞”時又篆刻了“碧虛池”,舍人李嶠是唐代李嶠,不是宋代李挺祖。日本戶崎哲彥先生考證后說,李挺祖不是李嶠不容置疑。
趙衛平先生說:九峰齊高,三峰壓眾。九疑山有十二峰之說,唐代文獻無記載。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九疑山部》載,“舜峰即三峰石,在舜祠西十里,三峰鼎立,其下眾山環合……舜峰不列九峰之內,乃為九峰朝宗,特列入首。”三峰指的是三峰石,不是三個峰。
戶崎哲彥先生雖是日本教授,但對拓本印鑒、避諱、黃表卿年代考等都依據依典,這種認真態度令人敬佩。但戶崎哲彥先生是日本人,盡管認真,也會受到國界和文化的限制,難免有錯。如將拓本與府志對比時,閤、閣;領、嶺;箾,簫是通假字,而說是拓本之錯。他不知道從意境、典故考證,因而認為黃表卿是南宋人而認定拓本是贗品。這是可以理解的。
二 是唐文,不是宋文
文章是唐朝湖廣第一狀元李郃撰寫,不是南宋黃表卿撰寫。
文章藝術水平黃表卿難以達到。黃表卿(1178-1245)是寧遠縣禾亭高寨村人。家譜說是1191年進士(有誤,只13歲),授天河縣令,字號黃天河。因病歸家,因山瑤侵擾從由村遷居舂陵。《九疑山賦》氣勢磅礴,詞句優美,沒有出眾的文學修養是寫不出的。據樂雷發《送黃天河》詩,黃表卿中舉即在1228-1236年,此時黃表卿應是50-58歲。這就說明他的才華不會出眾。他因病歸鄉,因瑤侵遷移,家境、身體都讓他難以飽讀詩書。他家譜的藝文雜志上,沒有他的一詩一文,這也說明他的詩賦水平非常一般。如果他能寫出《九疑山賦》這樣的流芳之作,而為何不見其它一詩一文呢?文先國先生說,他是否見文未見拓本,改動幾字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此誤傳了。這讓我想到,黃表卿先住由村,由村是沐塘村的佃戶,離沐塘村近,有機會見到《九疑山賦》,又是黃姓,應深受黃庭堅“點鐵成金”觀點的影響,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
文章意境不是南宋國情。《九疑山賦》是一篇寫景、述史、用典、言情于一體的優美散文。先述舜事、道家仙人仙事、九疑美景。再寫九峰、二妃灑下西江之水之淚,染成千百畝淚竹的愛情故事,最后肯定九疑山是舜帝藏精之所、道家修煉仙境。從而達到歌頌國泰民安盛世和贊美九疑神奇的目的。靖康時,徽宗、欽宗被擄,國破家亡,民不聊生。仁人志士,崇尚的是救國救民,書寫的是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岳飛在《滿江紅》中高歌:“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辛棄疾在《鷓鴣天》中慟哭:“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文天祥在《過零丁洋》中怒吼:“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有南宋文人,都在抒發愛國之志,衛國之情。黃表卿的同鄉好友樂雷發在《烏烏歌》中吶喊:“莫讀書!莫讀書!惠施五車今何如?”、“好殺賊奴取金印,何用區區章句為”。全國上下都在憂國憂民,黃表卿敢寫修道成仙嗎?敢于藐視權臣的樂雷發不譴責嗎?自古文章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抗戰時期,毛澤東寫的是《論持久戰》;蔣介石喊的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抗戰守土之責”;文人騷客寫的、億萬人民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我們在太行山上》。就在今天,黨中央提出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全國上下,電視講夢、文章寫夢、人們追夢。
文章典故是唐代外丹人事。文章的十個典故,都是初唐前后道家仙人仙事。重道輕佛是唐太宗欽定的。唐統治者自詡老子后裔。太宗言:“今李家治國,李老在前。”道徒修煉分為外丹和內丹。唐道徒用礦石藥物煉成丸藥,服者喪身者眾。唐末宋初,道徒從長期的外丹修煉中醒悟過來,認識到服丹成仙之路走不通,但又沒有放棄成仙追求。于是回到了“元氣生萬物”這一基本教義上來。唐末宋初內丹興起。北宋道士、內丹代表人物張伯瑞著《悟真篇》,闡述了內丹修煉理論和功法。以內丹為成仙唯一途徑,并云“為仙須是為天仙,唯有金丹最為端”。自宋始,道徒采用的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化虛”內丹修煉法。文章寫外丹仙人仙事,說明這是唐文不是宋文。
文章意境符合唐朝盛世。文章表達的不是南宋衰微國情,而是唐朝太平盛世,也是李郃遵圣意、敬先祖的體現。
太宗自詡李耳后裔,尊重“李老”,尊重道教,遂成國意。
李郃家住沐塘村,距舜祠十里,生在家鄉,長在家鄉,對舜事、祖宗淵源十分清楚。《灌溪李氏族譜》載:“李氏十七世祖,耳公名聃,號伯陽,又名李老子、李老君、太上老君”……著《道德經》上下篇五千言,成為道教之宗”,沐塘始祖道辨公是李耳三十七代孫,李郃是李耳的五十三代孫。李郃撰寫《九疑山賦》是述舜事、尊皇意、敬祖宗,一舉三得。
文章藝術水平符合李郃生世。《九疑山賦》與名家詩賦比雖有差距,但不失為一篇流芳千古的優美詩篇。沒有良好教育,沒有飽讀詩書,沒有鶴立群首的天賦,是寫不出的。李郃三代書香世家。他曾祖飛龍衡州教授,祖父周廷劄授本路教授,父太淵本州教授,三代都是儒學世家,這為李郃營造了良好的教育學習環境,得以20歲在無數優秀人才中脫穎而出,以一詩一賦中狀元,展示了他非凡的文學藝術素養。
文章地名符合。文章涉及的18個地名中有16個可以在圖志中查到,只要閱讀九疑山圖志的便可知曉。而萬歲山、西江這兩個地名,只有沐塘村人才叫才會寫,別村人不會叫不會寫。
文章詞、典符合。李郃文章保存的很少,只有九篇,就連狀元及第的《觀民風賦》也已失傳。在這九篇文章中就有多處同詞語、同典故。如《詠石床石鑒》中的“麓床高接天”和《九疑山賦》中的“三麓床上丹煉九轉”的“麓床”;《游九疑黃庭觀》中的“神府枕疑川”和《九疑山賦》中“有舜江則可枕可漱”的“枕”,用的是同一典故——“枕流漱石”;《游九疑黃庭觀》中的“別有月帔上”與《九疑山賦》中“月帔兮明月上”的“月帔”。文章若不是出自同一人,不可能有這么巧合。
文章格式也能佐證。李郃是以《觀民風賦》和《早鶯求友詩》中狀元的。李郃用詩賦贊美家鄉,符合情理。
三 是真品,不是贗品
文章是唐朝李郃寫的,不是南宋黃表卿寫的。
同朝為官,關系很好。柳公權、李郃二人在 837年至860年,都在朝廷為官達 23年之久,關系很好。李郃 837年任吏部侍郎,屬宰相李德裕下屬;柳公權838年任工部侍郎,《舊唐書》說:“李德裕素待公權厚。”說明李郃、柳公權都屬李德裕部下或同黨,關系自然好。當時,上至天子、下到官僚,都想多得和得到柳公權墨寶,李郃請柳公權寫一幅贊美家鄉的字很合情理。
符合避諱。《九疑山賦》帖拓本有“世”、“民”各一處,均缺一筆,為唐太宗李世民避諱;有“境”三處、“貞”一處、“玄”一處,皆宋朝國諱,“境”為祖趙敬避諱,“貞”為仁宗趙禎避諱,“玄”為圣祖趙云朗避諱,拓本未避。
沒有如此水平的書匠。自唐以后,楷書趨向敗落,沒有能與柳公權相比者。按黃表卿生活區域看,當時的湖南九疑、廣西天河沒有如此水平的書匠,若有這種水平,還不自成一代大師嗎?
馬慶才先生收藏的拓本、上野精一先生拓本、尚古山房本一模一樣。文先國先生從文物的角度進行了比較,馬慶才先生的拓本比上野精一先生的清晰外,其它一模一樣。我們用電腦將二人拓本擴成相同尺寸,二者競能重合。我想至于清晰原因是因為馬慶才先生拓本早于上野精一拓本,這也符合邏輯。馬慶才先生的拓本是朝廷的,上野精一先生的是民間的,朝廷早于民間的符合情理。
鐫刻者符合。《九疑山賦》為邵建和鐫刻,邵建和是唐代碑刻名手。唐代很多書法都是邵建和所刻,且都和柳公權有關系。如:《苻璘碑》李宗閔撰文,柳公權書并篆額,邵建和鐫字;《吏部尚書馮宿碑》王起撰文,柳公權書并篆額;《玄秘塔碑》柳公權書,邵建和并其弟邵建初刻。1986年,在西安城墻東南角,出土的“大唐回元觀鐘樓銘并序”碑,令狐楚撰文,柳公權書,邵建和刊刻。邵建和為當時碑刻名家,與柳公權關系極為親密,具有高超鐫刻技藝的邵建和也能證明《九疑山賦》拓本為柳公權所書。
書法家一致看好。《九疑山賦》拓本重新面世后,引起了書法界的高度關注。對其藝術水平一致看好,說贗者都認為是難得的佳品、難得的范本。眾多書法家認為:“《九疑山賦》通篇六百零一字,字字用筆一絲不茍,肥瘦得體,血肉俱美,可以說是無筆不妙。”書法家趙思敬先生說:“柳氏諸書,應為極品,古今小字,當推第一。”《書法報》總編張鵬濤先生來寧遠講座,如數家珍地講述了柳公權《九疑山賦》拓本的來龍去脈。但也有書法家認為是贗品的,山東煙臺潘英琪先生讀到《中國文物報》馬慶才先生《再談柳公權小楷〈九疑山賦〉》,對報刊展示的“昌”、“皇”、“莫”、“左”、“其”、“日”、“月”、“然”、“知”、“會”十個字從筆勢、書寫規律進行了鑒定,認為拓本是贗品。潘先生是中國書法協會鑒定評估委員會委員,海內外頂禮膜拜的大書法家,潘先生的鑒定是權威性的。但我在數次拜讀了潘先生送給我的《潘英琪書畫藝術》一書后,對潘先生的認定有不同看法。其一,潘先生沒有見到全拓本,難免以點概全;其二,潘先生沒有分析文章意境、景點、典故,沒有考證文章作者與柳公權的關系,忽略了《九疑山賦》拓本創作的天然條件;其三,潘先生在《書·言志達情》一文中說:“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依不同的心態,書寫不同的內容,即使用同一種書體完成,也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鄭道昭書寫《論經書詩》時是分三次書丹上石,形成了前、中、后三部分書寫的差異較大,造成了一些書界朋友論其為三人書丹。”柳公權書寫《九疑山賦》與其它碑帖相比,心態不同,內容不同,時間也不同,有些差異純屬正常。
流傳范圍符合。拓本在河南發現,符合情理。因李郃在河南任過參軍。清代以來,國內國外,相傳為寶。拓本首頁“笪重光秘籍之印”、笪重光(1623-1692)明末清初書畫家,尾頁“劉墉”、“石庵之印”,石庵、劉墉(1719-1804)乾隆、嘉慶宰相書法家,說明得到了劉墉宰相的認可。同時說明了只有真品才能流入朝廷,贗品是無法流入朝廷的。日本朝日新聞社長上野精一先生幾次捐贈給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文物中,其中一次捐贈的文物藝術品130件藏品的117號藏品,則是《九疑山賦》拓本。這130件文物藝術品,均被列入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品目錄的重要文化財產。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與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盧浮宮等世界超級博物館齊名,收藏文化藝術品不僅數量非常巨大,而且非常嚴謹講究質量。上野精一先生,是現代日本收藏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也被日本近代文物藝術收藏界認定為一位極高品位的收藏家。民國時期上海尚古山房有過《九疑山賦》拓本面市,總發行上海新馬路尚古山房,分發行所奉天、南京、漢口尚古山房,印刷所上海尚古書局,博古書屋藏本,定價實洋兩角。從流傳的廣度、高度,可以看出,清末民初該拓本就已獲得很高層次的名家認可,已被視為真品,視為瑰寶。
結 論
《九疑山賦》拓本,是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湖廣第一位狀元道州延唐縣沐塘村人李郃撰文,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狀元、唐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寫,唐鐫刻大師邵建和鐫刻,是歌頌靈山仙境九疑山舜帝陵的“三絕”,不愧為千古絕唱,天下瑰寶。世上獨一無二的書法藝術,應為其戴上閃光的桂冠,列入國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