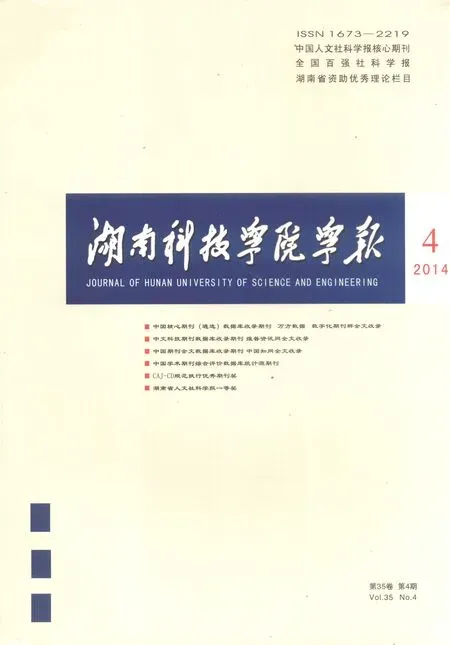史詩的儀式發生學新探——以苗族活態史詩《亞魯王》為例
蔡 熙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民族研究所,貴州 貴陽 550002)
對文藝發生學的研究由來已久。自古以來,關于文藝的起源問題眾說紛紜,如“靈感說”、“模仿說”、“勞動說”、“巫術說”、“心靈表現說”等。文藝起源諸說雖然各有其道理,但在我國學界居于主導地位的是文藝起源于勞動的觀點。雖然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從酒神狄奧尼索斯的祭祀儀式與悲劇的發生關系入手,提出了悲劇源于對酒神祭祀儀式的模仿,“借以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1]P19。但論者只知其“模仿說”卻淡忘了其影響深遠的“儀式說”。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指出,中國戲劇來自宗教性的巫舞,“靈(巫)之為職,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樂神,蓋后世史詩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2]P9。但文藝起源的儀式說,在我國應者寥寥。主要原因在于,儀式往往與宗教巫術難分難舍地糾結在一起,長期以來,人們把儀式展演當作一種封建迷信。在貴州麻山地區苗族的喪葬儀式上展演的活態史詩《亞魯王》為我們探討史詩的儀式起源問題提供了鮮活的例證,本文以《亞魯王》為例,對史詩的儀式發生學作一初步探討。
一 《亞魯王》對史詩發生學的挑戰
在民間流傳幾千年的苗族史詩《亞魯王》直到2009年紫云縣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中才意外現身,同年成為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的重點項目,并被文化部列為2009年中國文化的重大發現之一。2011年《亞魯王》榮列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2年2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并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六大學術事件,與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等事件相提并論。這部26000余行的史詩涉及古代人物10000余人,400余個古苗語地名,至今仍以口頭形態在貴州麻山苗族地區的3000多名歌師中口耳相傳。《亞魯王》的橫空出世對史詩的概念、史詩的發生學以及史詩的分類都提出了挑戰,這是目前史詩學界不能不回應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史詩究竟起源于何時,引發它起源的直接誘因是什么?這就是史詩發生學。談到史詩的發生學問題,人們一般認為,人類的史詩是從原始氏族社會解體到奴隸社會初期產生的,它代表了那個時期的文學成就。苗族史詩《亞魯王》直到21世紀的今天才被發現,至今還是活形態的史詩,依然在民間流傳。面對《亞魯王》,認為人類的史詩產生于原始氏族社會末期到奴隸社會初期的史詩起源理論,顯然不能自圓其說。《亞魯王》主要流傳于麻山地區的紫云縣,分散流傳于鄰近的羅甸縣、望謨縣、平塘縣,另外在貴陽、花溪、龍里、息烽、平壩、黔西、大方、織金、威寧、鎮寧、關嶺自治縣等西部苗族地區也有少量流傳。麻山地區深處高聳入云的喀斯特大山之中,地理位置偏遠荒僻,外人罕至,交流不便,信息閉塞,語言獨特,生活狀況十分原始,這為史詩《亞魯王》的傳承不衰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可見,只要存在特定的文化空間,活態的民間文化遺產就會代代相傳。
關于史詩的類型學問題,西方的史詩種類比較單一,史詩一般是指以英雄人物為中心的英雄史詩。就史詩的內容而言,在中國,除了英雄史詩以外,還有神話史詩、創世史詩、民族遷徙史詩。《亞魯王》兼具創世史詩、遷徙史詩和英雄史詩三個亞類型的特征,可以說是一部“復合型史詩”,《亞魯王》的發現豐富了世界史詩寶庫,為史詩的分類提供了當代的新案例。從文明形態來看,以跨海遠征作戰、海上漂流冒險為主要內容的荷馬史詩是海洋城邦類型的史詩,印度的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是森林史詩。我國北方著名的三大史詩《格薩爾》、《江格爾》與《瑪納斯》發端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土壤,屬于草原史詩。流傳于我國南方麻山地區的史詩表征的是山地文明形態,反映了苗族先民在高原山區創世、征戰、遷徙的生活歷程,屬于典型的山地史詩。史詩是人類社會和精神文化發展史上的普遍現象。在我國,由于史詩研究起步晚,甚至于史詩(epic)這一概念也是舶來品,再加上缺乏多民族的文學觀念,引發了長時間的我國有無史詩的爭論。事實上,我國不僅有史詩,而且擁有多種類型的史詩,是史詩的富國。史詩的發生學以及史詩的分類學唯有納入“儀式”的視角才能得到很好的說明。
二 史詩在儀式中發生
史詩是最古老的文學樣式。苗族活態史詩《亞魯王》唱述了古代苗族亞魯王國第17代國王兼軍事首領亞魯在頻繁的部落征戰和遷徙中創世、立國的坎坷發展歷程。當歷史的車輪輾轉到21世紀,工業化、城市化已經高度發達的今天,《亞魯王》作為苗族的“活態”文化大典,依然在麻山地區的民間傳唱。《亞魯王》為史詩起源于宗教祭祀儀式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
麻山地區苗族喪葬儀式的程序復雜多樣,耗費時間長。根據田野調查的情況,由于深處山地的苗族住地分散,支系眾多,各地的儀式的程序存在一定的差異,如紫云縣大營鄉巴茅村、宗地鄉大地壩村的喪葬儀式要經過凈身裝棺、停棺、牽馬走親戚、隔房家族的晚輩給亡人獻牲、孝子給摩公倒洗衣腳水洗腳、摩公唱念經詞、牽馬到砍馬場的喝酒儀式、牽馬到砍馬場、開馬路、眾親戚上祭、念唱砍馬經、為亡人宣告恩怨了結、牽魂回家、請吹打班子進砍馬場踩場、亡者的女兒和兒媳婦喂馬、用鞭炮驚嚇獻牲、砍馬師進入砍馬場地、砍馬抬杉樹下塘、獻牲、亡者的女兒送飯、摩公為亡人唱念開路的經詞、為亡人指路、燒掉亡者的不潔之物、出殯上山、下塘、掃家和解簸箕等28道程序。雖然各地的喪葬儀式程序有一定的差異,但從根本上來看是大同小異的,即這部26000余行的史詩圍繞核心人物亞魯王而展開,唱誦史詩《亞魯王》是葬禮的靈魂,它統領了其他所有的儀式程序。唱誦的內容,一般從亡者何時何地出生,到亡者的家庭成員,再到亡者的父輩、祖輩,一直追溯到亞魯王乃至最遠古的祖先,重點唱誦苗族先民在亞魯王的統領下創世、征戰和遷徙史的歷史,歷時9-10小時不等,企望通過這種反復唱誦的儀式過程,實現與祖先的對話,讓死者能夠回歸祖先的身邊。在種種儀式中,最重要的是兩種儀式,即開路儀式和砍馬儀式,下面分別展開探討。
(一)開路儀式
在麻山苗族地區,亡人過世后都要請當地的摩公(即在麻山苗族的喪葬儀式中主持巫祀儀式活動的歌師)到家中主持儀式為亡人開路。開路是麻山苗族喪葬儀式最重要的部分,意為給亡人指路,即請摩公給亡者指引一條回歸到祖先故地去的路。開路前,主人家要給亡人準備好五谷種、包晌午飯等。供飯時,主人家會抬來一頭豬和一條狗,放在棺材的大頭位置。
在開路儀式上,摩公要為亡人唱誦《開路經》,其中唱誦的亞魯王部分在凌晨兩點開始,歷時大概三個小時。其內容分為四個部分:(1)唱述宇宙和人類創世的由來。以創世神話為基本內容,以天地萬物、人類社會、文化起源及演進發展為敘述線索,主要神話有造天造地,造人,造山造丘陵、趕山平地、造太陽月亮、造嗩吶銅鼓、箭射日月、與雷公斗爭、洪水滔天、倆兄妹治人煙、蝴蝶找來谷種、螢火蟲帶來火、馬桑樹天梯等神話。(2)唱誦亞魯王的故事,重點唱誦亞魯王成長、創業、征戰和遷徙的故事,塑造了一位勤勞智慧、能力超凡、關愛民生的苗人首領形象。(3)殺雞開路。唱完最后一部分之后,摩公右手懷抱半大的子雞,左手執劍,把用來給亡人開路的雞在地上摔死,然后用竹子縱穿雞的身體,插在飯簍上給亡人,是謂“殺雞開路”。殺雞給亡人指路,首先將亡人送到東南方,然后再轉回到門口,接著送到西方。指路過程需要兩個多小時。(4)為亡人指明本家族先人所在的地方,自己的祖先是怎么來的,祖先遷徙來此定居的路線,怎么樣回到祖宗的故地。麻山苗人認為,亞魯是他們的祖先,是亞魯把苗人帶到這個地方來定居的,亡人要走的路,就是沿著亞魯遷徙的路線回到過去曾經生活過的東方老家。
在開路儀式中,對苗族祖先亞魯王的唱誦貫穿了整個喪葬儀式的始終。因為苗人自古以來具有追本溯源、慎終追遠、揚尚祖德的傳統。他們認為,只有靈魂得到妥善的安置,才能回歸到祖先的住地,與祖先的靈魂共同生活。麻山苗族濃郁的祖先崇拜意識表征了他們獨特的民族信仰、堅定的民族傳承性和強烈的精神回歸的生命意識。
(二)砍馬儀式
砍馬儀式可分四個階段。(1)砍馬前,摩公把懸掛在大門上方的糯米谷穗分發給主家的各女性,大孝子肩扛長梭標去屋外牽馬,從拴馬的地方把馬牽到大門,然后牽到拴馬的地方,如此反復三次。(2)供馬。到了砍馬場,馬的頭要朝向東南方,分到糯米谷穗的女性聚集過來,一邊哭泣一邊把手中的稻穗敬獻給馬。先由主家的摩公供馬,供馬時要敬三碗酒,供完后直接倒在馬的脖子上,摩公要喊到主家的祖先三輩。(3)念《砍馬經》,唱述砍馬的由來與歷史,指明馬如何到達祖先之地。馬背上馱著一系列帶領亡人靈魂回歸祖先之地的物件,其中包括酒瓶、葫蘆殼做成的水壺、六個竹筒(五個竹筒裝水,一個竹筒裝干魚、豆腐和其他菜)、布袋(裝有少許糯米飯、三個碗及打火石)、飯籮(裝兩斤左右蒸熟的糯米飯)。在苗族人看來,人死了之后就要回到祖先生活過的地方。因此,在亡人歸家的路上生者要為之提供更多便利,其中包括為亡人供飯,給亡人開路,砍馬送亡人等。雖然人已仙逝,但生者仍然要為亡人提供回歸祖先途中所需的干糧,表明了苗族人靈魂不滅的倫理觀念。《砍馬經》詳細交待了杉樹的來歷以及與亞魯王的關系。“多王受優待,享福不知福。吃魯命中樹,啃魯命中竹。”[3]P167這棵杉樹是亞魯王的生命樹,這匹馬是亞魯王的戰馬,亞魯王依憑這匹戰馬打了很多勝仗。但因為戰馬居功自傲,偷吃了生命樹上的糧食種子,破壞了亞魯那多年精心培育起來的物種。亞魯王含淚把戰馬砍死,讓它帶著亡人去追尋亞魯的足跡,回到祖先的故地。“待人死了后,才砍送亡人,亡人騎馬上,噠噠尋祖先。祖先開大門,把他迎進屋,今有某某人,天上尋祖先,今日把你砍,帶他上天庭,你莫怨砍者,應恨你祖先,祖先亞多王,已經許了愿。”[3]P168念完《砍馬經》之后,摩公在馬鬃上噴灑用樹葉泡制后的酒水,然后攜主家眾人,圍著馬逆時針方向轉三圈。(4)砍馬。一般由兩名砍馬師輪流上場,每人砍一刀,并且只能在馬逆時針奔跑時才能動刀砍。被砍的馬在砍的過程中升華成為亞魯王祖先的戰馬,與亡者一同返回亞魯王的時代,回到遠古祖先的身邊。馬蹄、耳朵和生殖器割下放入棺材中陪葬。顯而易見的是,砍馬儀式是對古代戰爭場面的模仿,以這匹英雄而苦難的戰馬所經歷的殘酷血腥的場面讓族人刻骨銘心地見證并銘記亞魯王當年在征戰和遷徙途中所經歷的死亡存亡的考驗。
由此不難看出,傳統的喪葬儀式才是史詩《亞魯王》傳承千年不衰的深厚社會基礎,一旦離開儀式展演,史詩《亞魯王》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間和土壤。事實上,在我國的西南少數民族中還存在著不少口頭流傳的活態史詩,如彝族的英雄史詩《勒俄特伊》也是在喪葬祭祀儀式上由祭司莊嚴地唱誦的,獨龍族的《創世紀》是在祭祀天鬼的儀式上由主祭的祭司唱誦的,云南大姚、姚安一帶的彝族在為亡者舉行的送靈儀式上由祭司畢摩唱誦創世紀史詩《梅葛》,納西族的《創世紀》是在祭天儀式上由祭司東巴唱誦的。西方的史詩書面文本定型較早,已經成為書面的文學經典,但是《荷馬史詩》的背后是一個口傳文化傳統,《荷馬史詩》是無文字時代的歌手們口頭傳唱的,盲人荷馬只是其中的一個歌手,作為歌手的荷馬不單單是一位文藝家,他是帶著古老的沒有文字社會悠遠的歷史記憶唱誦史詩的,史詩背后是深遠的文化記憶。
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到尼采的《悲劇的誕生》,都認為儀式是西方文藝的誕生地。亞里斯多德說,悲劇“是從酒神頌的臨時口占中發展出來的。[1]P14在祭祀酒神的儀式上,由巫師戴著羊的面具,唱著狄俄尼索斯死亡的哀悼之歌。“彌爾頓的《失樂園》是一個哀悼的儀式。”[4]p98歌德的《浮士德》完全是一個社會化“通過儀式”在藝術作品中的范例。[5]p110“詩歌是一種復活和再生的儀式。”[6]p174葉芝的戲劇作品“不是戲劇,而是一種喪失信念的儀式。”[7]p176北美印第安人的口傳神話肇端于儀式,其儀式主要有五種:(1)煙熏祭天地用的貢品(2)潔身禮即洗一次汗浴(3)齋戒和守夜禮儀(4)召喚自然神的巫師儀式(5)公共儀式,大多數是跳舞,包括祈禱,獻祭,紀念祖先和死者。
由此可見,最早的史詩是從儀式中孕育發展出來的,儀式中的程式化、表演化、性格化特征,孕育未來文藝的胚芽。儀式陶冶了人類激越的情感體驗,培養了人類幻想的形象性、藝術的想像力,激發人類用象征的、隱喻的形式來表現人類的情感、渴望和理想。當神話漸漸式微,各種藝術就從儀式中脫胎出來日漸走向成熟。
三 史詩儀式發生說的當代價值
亞里斯多德對酒神祭祀儀式的經典闡釋成了儀式命題的學術原點。苗族史詩《亞魯王》在儀式中產生,又在儀式中口耳相傳為史詩的儀式發生說提供了鮮活的當代案例。史詩的儀式發生說對于文藝起源的探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從儀式中孕育了最早的史詩形式,而最早的史詩卻是一種融混性的藝術,表征了藝術起源時的原生形態。在苗族喪葬儀式上由摩公唱誦的史詩《亞魯王》與宗教祭祀、巫術、音樂、舞蹈等活動緊密結合在一起,集唱、誦、儀式表演于一體,體現了藝術起源的原生態特征。在史詩展演時,“摩公”面對死者,要隨身佩戴一系列的道具,如身穿苗族傳統的長衫,頭戴斗笠,頭帕里裝上稻谷,手提一只雞,腳穿鐵鞋(鏵口),肩上扛著長劍等。此外,在展演過程中,還要配以木鼓、銅鼓、牛角等神器。從儀式展演的聲音類型看,有“器聲”和人聲。其中器聲包括木鼓、銅鼓、牛角、鞭炮、鳴槍等聲音類型,器聲的演奏,其實質是族群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外顯。人聲包括喪禮現場孝女(婦女)們的哭唱聲和摩公唱誦史詩《亞魯王》的吟唱聲。摩公在演誦的時候要根據喪葬儀式的語境氛圍和觀眾的表情來展演,他們那莊重蒼茫的曲調,時而快捷、時而舒緩、時而長嘆、時而手舞足蹈。史詩的表現形式靈活多變,根據史詩《亞魯王》的內容,摩公唱誦的歌調可分為離世調、永別調、開路調、請祖調、砍馬調、發喪調等等。顯然在儀式上展演的史詩不是純文學的,而是融混性的。同時,史詩在漫長的口頭傳承過程中,融進大量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歌謠及諺語等,因此,史詩含納了多種文類要素,既具有強烈的地方特性和民族特性,又具有人類的普適性。
但是,長期以來,“文學的”史詩觀在我國的學術界占據著支配地位,從而導致現代中國學術語境中史詩定位的褊狹化和虛幻化,一般只關注史詩的歷史文化內容、歷史淵源、流傳地域等問題,而對史詩的文類特征、史詩的傳播、儀式語境、史詩歌手等方面重視不夠,導致史詩研究無法延伸到文字記錄以外的廣闊領域。故而,對現代中國幾代學人習慣已久的文學本位史詩觀進行批判性反思,重新構建一種貫通文、史、哲、宗教、道德、人類學的跨學科的史詩觀念十分迫切。
其次,過去的文學研究片面地偏重于漢語書面文獻,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依然活在田野的口頭文學;過去的史詩研究過于偏重文學維度,相當程度上忽視了其他類型史詩的存在。“一種文化從其誕生之初起,就具備一種本性,它就是一種生命形式,雖然歷經變化,但其本性與生命一直貫穿了全部的發展歷程之中。”[8]P2在苗族喪葬上唱誦的史詩《亞魯王》,絕不是純文藝作品,而是與人類的生命活動、文化活動等混沌為一體的原生態文化。儀式是一種符號和意義的復雜體系,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特殊的體驗。因而,史詩的儀式發生說,可以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亞魯王》所蘊含的文化知識資源的總儲量,進而充分地展示和重塑史詩生命的整體過程,對史詩的生命過程、總體精神及整體風貌進行本質還原。對口頭史詩的研究,要突破文人文學的樊籬,重視口頭傳統的特點,注重史詩傳承人、史詩的聽眾和史詩展演語境三者之間的互動,大力倡導具有世界意義的比較口頭詩學研究。
再次,史詩的儀式發生說可以極大地拓展《亞魯王》的研究視野和研究空間。書面史詩的研究一般以史詩文本為依據并參考其他文獻資料,研究相對來說比較單純。以口耳相傳為載體的活態史詩是一種口傳文化系統的信息傳播,僅僅依賴史詩文本是遠遠不夠的。它要求我們必須將目光從史詩文本轉向史詩田野,對其進行動態研究,始終堅持文學與人類學的互動。也就是說,要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以口頭詩學理論、文學人類學理論、間性詩學理論為指導,通過走訪一系列杰出的歌師,并作訪談錄音記錄,把握每一個歌師的成長經歷、個人職業、習藝過程、性格特征、展演實踐、當下的生活狀態等;要深入考察歌師在表演過程中的眼神、表情、手勢、嗓音變化、肢體語言、樂器技巧、音樂旋律等展演風格,對歌師劃分類型,并進行比較研究,分類考察他們的文化傳統、傳承線路、史詩故事的變異和創新,揭開史詩傳承人的本真性、地域文化的多樣性;此外,史詩的接受者——聽眾研究,史詩形成、發展、流傳、變異與創新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對象。
[1]亞里斯多德.詩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2]石泰安.藏族格薩爾王傳與演唱藝人研究[J].民族文學譯叢(第l集),1983.
[3]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亞魯王》文論集:口述史·田野報告·論文[C].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4]Wittrelch,J.A.,Jr.Visionary Poetics: Milton’s Tradition and His Legacy,San Marino[M].Calif: Huntington Library,1979.
[5]Hartman,G.H.The Fate of Reading and Other Essays[C].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
[6]Cope,J.I.The Theater and the Dream: From Metaphor to Form in Renaissance Drama[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7]Gorsky,S,R.A Rital Drama:Yeats’s Plays for dancers,see Modern Drama[M].1974.
[8]朱炳祥.何為“原生態”?為何“原生態”[J].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