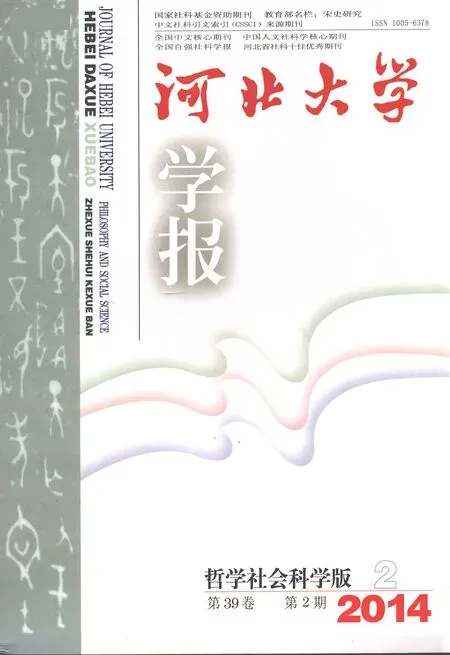華北抗日根據地鄉村婦女形象的重塑
王 微
(南開大學 歷史學院,天津 300071)
目前關于抗日根據地婦女研究的成果豐碩,所涉及的范圍也甚廣,涵蓋了諸如婦女運動、婦女生活、婦女形象等多個方面,其中也不乏創新之作①參見:劉萍:《激進與現實的矛盾——抗戰前期根據地婦女運動發展中的曲折》,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韓曉莉:《太行女性形象的再塑造——太行根據地的婦女解放運動》,《山西大學學報》2005年第5期;張志永:《華北根據地婦女運動與婚外關系》,《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1期;張志永:《政治與倫理的統一:華北抗日根據地和睦家庭的建設》,《河北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林書琦:《延安新女性》,臺灣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但大多研究受傳統革命史觀研究方法的影響,缺乏對歷史復雜性、多面性、曲折性的深描。本文試圖從傳統與革命相互博弈的角度為出發點,以華北抗日根據地為中心,考察中共在民族戰爭、革命的視域下對鄉村婦女不同形象的塑造,探究鄉村婦女形象變遷的復雜性,進而凸顯中共革命進程之不易、婦女形象變遷路程之坎坷以及婦女解放征程之漫漫。
一、傳統華北鄉村婦女形象之素描
中國自古就有“三從四德”之言,“賢妻良母”之說。傳統鄉村社會,父權至上,女性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十分有限。《十里店》曾轉述當地婦女的回憶:“在過去,男人們常常在街上議論村子的事情,我們婦女從來不敢到這種場合去。當有人來到家門口大聲問道:‘屋里有人沒有啊?’的時候,我們婦女就自己回答說:‘屋里沒有人。’婦女在那時根本不被當作人看待。”[1]13這種對女性的偏見,將女性限定于家庭。加之,她們“孤立、無知、缺乏就業機會、在參加工作方面完全受到歧視和強迫結婚的習慣”[2]277。久之,她們形成了一種以家庭為中心,依附男子的生存模式。
再而言之,教育匱乏和生活范圍狹窄,導致婦女的見識亦少。“抗戰初期曾有不少笑話,如唐縣極偏僻的小山溝里,花盆村一個婦女干部,到村里問婦女們是那〔哪〕國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女說‘花盆國的’,一大堆人沒有一個糾正她,連是那〔哪〕國人都不知道。……她們只知道,‘人活一輩子誰不是為吃穿,尋上婆家跟著人家過吧。’嫁到婆家當公婆丈夫和鍋灶的侍奉者,環境造成了她們不會也不可能產生別的想法來”[3]763。面對突如其來的戰爭,她們茫然無措,有的甚至連“日本”都未曾聽說過。起初面對殘暴的戰爭,有些婦女要么“消極的茍安認命和燒香求神保佑禱告‘上蒼’,盼望禍患不要輪到自家”;要么“主張誰來給誰納糧,無論怎樣做,只要安全了就是阿彌陀佛”。當然也有的“積極要求打破現狀,盼著打走日本過太平日子。但不知如何去打,更不相信自己能抗日,只是咬牙切齒的恨日本,盼‘能人’出來抗日救民,打土匪掃除混亂局面”[3]481。此外,一般鄉村婦女對初來的干部和組織不甚了解,以為是來“拔女兵”的,都不敢和婦女干部接近[4]359。
顯然,上述華北鄉村婦女的思想覺悟以及擔當意識不能適應民族戰爭的需要。冀求她們自我覺醒,突破原有的生活空間,自覺投入到抗戰洪流中的可能性甚微。為了動員廣大農婦參戰,中共一方面普遍建立婦救會、自衛隊等婦女組織,另一方面制定了系列法規條例,試圖在組織和法律上保障婦女的切身利益,藉此將其從庭院拉入戰場,人為地幫助她們發生角色上的錯動,塑造出符合戰爭與革命需要的鄉村婦女形象。
二、走出家庭:鄉村婦女之組織與動員
傳統的華北鄉村婦女生活空間限于家庭,并無參加集體生活的習慣。而且傳統農村社會封閉狹窄,鄉土民眾面對一種新組織心存戒備。一些諸如“婦救會干部都是女紅軍,婦女自衛隊就是登女兵,將來要開到火線上去”[4]329“參加婦救會就是給八路軍當媳婦”[5]261等謠言甚囂塵上,更加劇了當地人的疑慮。同時,中共早期的部分婦女干部并不了解農村實際情況,把農村婦女當成城市中的女工、女學生,堅持將她們推進各種婦女組織[4]377。如自衛隊的建立方式是記名造冊,規定凡是年齡在16歲以上45歲以下都是婦女隊員[6]16。組織婦救會也是如此,華北地區很多婦救會“純粹是強迫命令之成績,完全是空空洞洞的一個架子,干部到村,對村的情形莫名其妙,說村民為愚民,光是命令村長,三天完成,為組織而組織”[7]3。這種強制性的組織方式造成很多會員對婦救會認識不夠,甚至有的地區本人還不知道就上了名冊[3]482。面對中共如此強勢之組織動員,華北根據地農婦特別是貧農一般是躲著,原因是怕耽誤了工夫[8]5。有的以為是拔女兵的,不愿讓記名字。尤其是青年婦女害羞,并且不相信自己能成為一個自衛隊員[6]16。
開會、出操是組織婦女集體活動的重要內容,但往往流于形式,強制色彩濃重,不符合實際情況與婦女傳統生活慣習。很多地方“當著要動員時,不顧家庭婦女牽累、生理限制、生活困難等條件,常常要她們出來開會”[9]14。而且“開會之內容,多半是一片抗戰大道理,從國際將到國內,從國內講到華北,與群眾生活,無絲毫聯系,每回開會總是老一套,‘對牛彈琴’自以為美,而群眾對開會厭煩,在召開會時,‘還不是那一套’的呼聲,不斷的從群眾之中發出來了”[7]3。除了開會以外,組織鄉村婦女出操也是當時婦女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當時除了“對婦女自衛隊強迫訓練,經常半天、一天離開家庭集體上操”,還強調“學習整齊劃一的軍隊式的軍事教練。冀中還實行服裝劃一,一律打裹腿扎腰帶”。有的甚至不顧婦女的生命安危在敵據點附近,自衛隊也秘密上操[4]795。上述作法為婦女工作的開展蒙上了一層陰影。與此同時,新型組織的某些作法也不為傳統所接受。如婦救會“晚上開會,打鬧作風”[8]25,自衛隊“男女青年實行露營,或是夜晚隨男自衛隊襲擊敵人時,有個別曾發生男女關系”[4]795。有的縣還號召各村搞“動鋒日”,男女青年過集體生活,每天晚上是集體打游擊,緊急集合,學唱歌。青婦們以參加“動鋒日”為榮,但老年婦女看不慣,不愿叫那樣搞[10]7。此外,婦女參加集體活動勢必要減少在家的時間,耽誤家庭生產。抗戰開始后,各地提出了婦女參加集體農業勞動,許多生產小組、互助組順勢而生。但離開家庭參加農業生產,并沒有改善婦女的生活及地位,反而引起其他家庭成員的不滿。如有的婦女參加集體開荒回家后,已是非常疲倦,但家長卻對其笑罵[4]701。婦女識字班也遇到了同樣的境遇。婦女識字班組織起來了,但“當時學習很散漫,主要內容是唱歌、體操,學員也沒有紀律,到一塊即打打鬧鬧,有的人藉口上識字班,不好好生產,引起家長不滿”[11]1。這些無疑都加重了傳統鄉村社會和家庭對婦女個體及組織的不滿。
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婦女組織在動員婦女、組織婦女活動的過程中,其原則和基礎并未構建于華北鄉村農婦的傳統生活習俗與鄉土民眾的原有習慣之上,只是簡單用粗暴的手段將婦女拉入公共領域。此種方式非但沒有使得革命顛覆傳統,反而憑添了鄉村傳統社會對革命的不滿與錯誤認知。
三、挑戰父權:鄉村婦女之權利獲得
中共除了通過新的組織形式來動員鄉村婦女走出家庭外,還試圖通過賦予她們多種權利,進而幫助這個長期囿于傳統的群體進入抗戰的大環境。在保障婦女權益及切身利益方面,革命對傳統的沖擊更為強烈。試以華北鄉村婚姻、家庭層面為例,來清晰展示革命與傳統碰撞之圖景。
1941年后,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相繼頒布了婚姻條例及實施細則。然而這些彰顯“五四”精神的法律條例并未建立在鄉村實際情況之上。在“五四”婦女解放的話語體系中,包辦婚姻、不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及一些“落后”的婚姻形式和婚俗都是男權對女性的壓迫。中共將自身定位于拯救者,試圖將鄉村婦女從夫權、父權的權力體制中解救出來,從無感情的婚姻束縛中解放出來[12]67。因此,中共極其反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童養媳等不以感情為基礎的婚姻形式,并且試圖在短時間內將這些“陋俗”徹底消除。以至于在執行與貫徹婚姻條例中出現了某些偏差。在反對買賣婚姻方面,對買賣雙方均加以處罰。在結婚年齡方面,對于不合規定年齡的婚姻強迫阻止,即便是轎子已到門口,卻又迫令回去[13]。“在一些地區由于連年災荒及游擊區敵寇奸淫,娘家多把女孩送在婆家,促早日完婚”。中共卻不顧群眾實際生活的困難,把不符合男20歲女18歲的強行拆散[4]791。關于童養媳,有的地方“動員童養媳回娘家,提出如打算將來還要,可供糧食養著,否則就馬上一刀兩斷”[8]16。致使群眾對婚姻法感到恐怖,產生了偷偷結婚,虛報年齡,在暗中變相的進行等現象[13]。
實際上,那些看似落后的婚俗及婚姻方式都是特定經濟環境的產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鄉村社會與家庭結構的穩定。如“童養媳”“買賣婚姻”不但滿足了男性的生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女方家庭獲得一些經濟補償,這也是很多鄉村婦女贊同“買賣婚”的原因所在。她們認為一方面“覺得賣價高是光榮,不愿一錢不花嫁人,感到‘無聲無息的就算嫁了人了,太不值了。’”另一方面“感到叫父母養活一輩子,沒給父母賺一個錢,有點過意不去”[14]406。再者為了解決勞動力不足和男性生理需求方面的問題,“拉幫套”“搭伙計”“半掩門”之類的兩性關系,在華北鄉村也有其生存的空間。事實上,鄉村的的兩性倫理、婚姻形式、婚俗制度等是以經濟或者生活的需要為基礎[15]36。由此看來,這些所謂的“落后”因子,反而成為鄉土社會解決經濟問題及兩性問題的重要因素。
對家庭糾紛問題的解決,在解決方式上,開始只強調斗爭,不知和解[14]436。“有的地方不管是貧苦人家因生活瑣事的口角還是一時的打罵,都機械地反對或斗爭”[4]791。在一些工作較為激進的地方甚至“提出用‘開展斗爭來保證工作的開展’,以‘斗爭’多少作為衡量工作的標準。……臨縣一月開展了40多次‘斗爭’,方式又多為大會斗,戴紙帽子游街、罰鞋、罰錢等辦法”[4]813。這對根據地之社會秩序將是有妨害的,同時這樣的處理,對婦女工作影響也不好,使一般婦女錯誤認知了自身痛苦的根源,“將不良的社會制度所加予她們身上的痛苦完全歸根于兩性斗爭,及青年老年婦女間的斗爭”[16]。使得有些“年輕婦女片面地理解男女平等,夫婦間鬧點小矛盾,就去找婦救會要求離婚。有的兒女不尊重父母,兒媳也不尊重婆婆,兒媳要和婆婆講無原則的平等”[17]200。這些顯然是對鄉村傳統家庭結構及維系家庭穩定的孝道的巨大沖擊。其次,這樣處理,“也會使婦女畏懼斗爭,畏懼將自己真正痛苦提出來解決,如婦救會干部問到婦女是否又被虐待的情形時,她們懶懶的回答:‘沒啦’!或者自己受虐待的情形被婦救會曉得了,那么,她甚至愿意承認這是自己的錯誤……因為對丈夫或婆婆之物質懲罰,實質上是損害了她家庭的利益……婦女的地位并不會因此而有所改善,或反會因此而更糟糕一些”[16]。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反虐待工作后,的確婦女公開受虐待的現象減少了,但暗中的精神上的虐待還很多[4]689。如有的婆婆不允許兒子和媳婦同房,對待兒媳沒有笑臉、指桑罵槐。還有的因不喜歡兒媳便分家,只給年青夫婦極少部分財產使他們生活無法維持。如平山東黃泥一婆婆與兒子、兒媳分家,她的生活很富裕,但兒子和媳婦生活沒法維持[6]12-13。男性農民在這個問題上雖然有所收斂,但認識并未提高。有的“以為不打罵婦女是法令上的規定,所以不敢打罵,甚至以為‘婦女提的太高了’,他們要求在盡義務上的事情多作些,才是男女平等,否則男女是不平等的”[4]689-690。有的在暗中輕微虐待,如在左權有一個較進步的農民,常在夜深人靜時用棍子打老婆,每次只打兩三下[18]。面對革命,習俗并未徹底妥協,反而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回擊著革命所帶來的各種不適。傳統又開辟了新的土壤并快速生根發芽,頑強的抵抗著革命的攻擊。
中共借由改造傳統婚姻與家庭,來改變華北鄉土農婦的家庭地位,將她們拉出家門,塑造出屬于鄉土社會的“新女性”群體,并委以重任。但由于中共在婦女運動中,對于傳統家庭、婦女慣習的忽視及所采用的幾近于顛覆傳統的革命手段及方式,不單嚴重地損害了婦女自身利益,更是對傳統的以父權為主導的家庭及鄉土社會的權益的沖擊與挑戰,影響了原本穩固的鄉村秩序與家庭結構,對抗戰大局極為不利。
四、重新選擇:鄉村“新女性”的重塑
中共無論是對婦女組織上的建設、組織動員還是對婦女權益的保障,都試圖在改造傳統家庭的基礎上,改變華北鄉土農婦的家庭地位,將她們拉出家門,附加給她們以社會重任。在這個婦女新形象塑造的歷程中,革命以十分尖銳的視角及方式直對傳統,試圖以激進的方式將傳統與慣習一夜之間就被消滅地無影無蹤,但結果以革命、中共的失利而告終。如何將不沖擊鄉村傳統與婦女生活慣習、改善婦女家庭與社會地位、保證婦女參與抗日這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呢?它們的契合點又為何呢?中共將婦女參加生產作為突破口,并再三強調鄉村婦女參加根據地的生產事業要與參加家庭經濟生產相一致,其社會與政治的活動也要兼顧家庭生產,以此提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為婦女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創造條件。在此過程中,新的鄉村婦女形象也得以塑造,該形象是以不脫離家庭的生產為基礎,以維系家庭和睦為前提,通過參與生產,以達提高家庭地位,改善家庭關系之目的,大批婦女參與生產也為戰爭提供了大量物資支援。中共不再單純地、蠻力地顛覆傳統,不再將擺脫父權制的家庭置于婦女解放的話語體系,而是在階級矛盾讓位于民族矛盾的思想指導下與傳統相妥協。
為了將這種新的婦女形象加以推廣,已達有效地動員、組織、激勵鄉村婦女參加生產之目的,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地將“生產”灌輸到婦女的認知體系中。“樹立典型模范,并通過反復彰揚模范事跡形成社會效應”[19]74,成為發動鄉村婦女參與生產最主要,也是最富有成效的舉措。婦女勞動英雄、勞動模范便成了活生生的模板,供農婦學習與仿效。其產生途徑主要是在根據地召開的各種會議上,如:“三八”節的紀念大會、勞動英雄大會、總結生產大會等。這些會議都試圖通過各種儀式的展示來激發婦女生產的熱情。正如涂爾干在研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時指出:“儀式是在集合群體之中產生的行為方式,它們必定要激發、維持或重塑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20]11上述各種會場氣氛的營造及在會議期間所舉行的一系列相關的活動勢必會使生活、視野都較為狹窄的鄉村婦女有所觸動。如在黎城“經過一禮拜的宣傳,三八節這一天,全縣婦救村干部和離城十里以內的婦女,在東關召開紀念大會。到會有組織的婦女三千六百二十余人,會場陳列著幾個月來婦女的紡織作品及其他生產品,并有婦女高蹺的表演,盛況空前”[21]。中共通過對彰揚勞動英雄過程中所應用的儀式,開啟了婦女生產的宣傳之門。
鄉村婦女對婦女勞動英雄的崇拜與效仿最初的刺激應源于婦女勞動英雄所獲得的一些獎勵上。從物質方面而言,鉛筆、日記本、紡車等物品或少量貨幣的獎勵,對于普通的鄉村農婦來說都是具有吸引力的。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能夠擁有這些東西是十分不易,也是十分令人羨慕的。倘若能通過勞動像英雄們一樣獲得這些東西也是值得向往的。除了這些有形的,可觸可摸的實際物質獎勵外,那些精神方面的獎勵更是讓這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婦女大開眼界。井陘婦女勞動英雄盧鳳凰的名字在井陘的山溝里回蕩著[22]。“全縣開英雄大會時,郝二蠻的名字刻上了光榮的□□。三專署專員親自給她題了四個大字‘勤樸可風’”[23]。晉中開全區勞動英雄大會,張子春的母親是移民中特色勞動英雄,大家把她請上主席臺,和司令員、專員并肩坐著,受到了親切的招待[24]對于這些平時連名字都很少被稱呼的婦女來說,自己的名字在民眾間廣為流傳應該是一種別樣的感受。再加之紅花、掌聲、題字、熱情的款待都是鄉土婦女未曾經歷與體驗過的,她們對這些都充滿了向往與期待。在這種羨慕情緒的激勵下,學習勞動英雄,努力生產深深印刻于她們心間。
這些物質及精神層面的獎勵不單單攪動了普通農婦的內心,激發了她們生產的熱情,對于獲獎者自身而言,也有同樣的效果。很多婦女勞動英雄在這些未曾親歷和目睹過的場景與儀式下,獲得了更多的動力與能量。“(張子春的)母親興奮極了,感受著有生以來的光榮和愉快。在鼓掌的熱潮中,她向大家講話:‘我是個難民,多虧政府和村里老百姓能夠的救濟幫助,救活了我母子的性命,今天才能翻身。明年我要更好地開荒種地,多打糧食,來回答政府和大家的好心’”[24]。呂香榮在三八節上受過政府的表揚,此后她干得更起勁了[25]。可見,在宣揚模范的過程中,勞動模范的勞動熱忱也得以提高,并且這種積極生產的情緒還會作為一種吸引、帶領普通農婦參與經濟活動的正能量而存在。
典型的塑造、培養及推廣,婦女參與生產的觀念得以灌輸與傳播,新式的鄉村婦女形象也得以建構且具備了量化標準。如唐縣對婦女勞動英雄提出以下的標準:“一、紡織快,質量好,數量多。二、能創造新的生產方式。三,會團結人,督促及幫助別人生產。四,熱心工作,會過日子,能將賺的錢恰當運用。”[26]參與生產是成為勞動模范的前提,但并不是唯一,“勞動模范”的外延遠遠大于其內涵。除了生產、勞動外,家庭和睦、幫助抗屬、識字、支前等也在考核的范圍內。實際上對婦女勞動英雄選拔與推廣即是中共對新式鄉村婦女形象的建構過程。積極參加生產、家庭和睦、團結群眾、積極擁軍支前、努力學習等考量標準因為可以滿足戰爭及根據地經濟的需要也就成為重塑婦女形象的重要因素。通過對這些婦女勞動英雄資料的解讀,“像男人一樣”“和男人一樣”“頂個男人”之類的詞匯也頻繁出現在其中。婦女生產男性化的輿論宣傳,沖擊了“婦女無用”論的傳統觀念,改變了婦女舊的生產習俗,極大的激發了農村婦女的生產熱情。
婦女勞動英雄以一個全能的形象出現,它成了一個近乎完美鄉村女性的代名詞。這種典型的宣傳與彰揚不但使“婦女生產光榮”滲入鄉土社會,也使“婦女還能像男人一樣生產”成為主流的話語體系。農婦可以作為一個有政治人格的個體參與社會事務及婦女應致力于保證家庭的和睦等也被籠括于其中。可見,中共對英模的塑造及推廣可謂益處頗多,這些婦女勞動英雄也逐漸成了“新女性”的化身。
結 語
抗戰伊始,在華北抗日根據地的婦女運動中,革命與傳統便展開了激烈的博弈,革命并非以漸進的方式來緩和與傳統之間的沖突,反而試圖將其意志強加于鄉土習俗之上,并希冀通過較為激烈的方式沖擊傳統,從而結束家庭對婦女的束縛,直接將農婦拉進戰爭的視域。然而隨著中共鄉村“新女性”塑造的進行,婦運卻逐漸偏離中共提出的調動一切力量進行抗戰的軌道,父權制的家庭和鄉村受到革命強烈的沖擊,他們以其自有的方式抗衡著中共及革命,其消極抗戰的態度及舉動不得不讓中共重新思索婦女運動何去何從,最終婦運的重心發生質的改變。
無論是鄉村婦女以何種形象存在都不是她們自主選擇。鄉村婦女形象人為的變革是缺乏對這個群體自身的考量的,在國家、民族、階級的存在下,鄉村婦女是缺少陳述與表達機會的。她們想改變傳統的形象嗎?倘若她們想變,哪種是其目標物呢?囿于原始生活空間、生存環境的限制,她們的大多數沒有走出家庭的渴求與訴求,因此在彼時的歷史情境中,鄉村婦女形象的建構是以戰爭、革命發展為導向,塑造符合革命需要的女性形象,從而最終保證抗戰大業之進行。事實證明,參與生產的鄉村“新女性”更符合中共的需求,在這個鄉村婦女形象的建構中,中共也將生產作為婦女獲得解放的重要媒介,并且該種婦女解放的模式在抗戰后期和解放戰爭中,直至建國后都發揮了極佳的婦女動員作用。
[1]伊莎白·柯魯克,大衛·柯魯克.十里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M].龔厚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達格芬·嘉圖.走向革命——華北的戰爭、社會變革和中國共產黨1937-1945[M].楊建立,朱永紅,趙景峰,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3]晉察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編輯組.晉察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M].中國老年歷史研究會(內部資料),1985.
[4]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37—1945)[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5]河北省婦女聯合會.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第2集)[B].內部資料,1983.
[6]平山婦女工作考察材料(1940年3月20日)[B].平山縣檔案館,檔案號:4-1-76.
[7]中共中央青委.略談青年婦女工作[B].河北省檔案館,檔案號:572-1-175-2.
[8]中共中央婦聯會.獻縣婦女工作簡史(1948年9月)[B].河北省檔案館,檔案號:572-1-180-11.
[9]河北省婦女聯合會.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第4輯)[B].內部資料.1986.
[10]中共中央婦聯會.北岳四分區阜平城南莊抗戰時期婦運簡史(1948年9月)[B].河北省檔案館,檔案號:572-1-180-10.
[11]冀南區黨委婦委會.婦女工作參考材料(第二集)(1948年11月15日)[B].河北省檔案館,檔案號:25-1-319-2.
[12]叢小平.左潤訴王銀鎖:20世紀40年代陜甘寧邊區的婦女、婚姻與國家建構[J].開放時代,2009(10):62-79.
[13]執行婚姻法中的幾個具體問題[N].新華日報:華北版,1942-05-17(2).
[14]山西省檔案館.太行黨史資料匯編(第5卷)[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
[15]張鳴.鄉土心路八十年:中國近代化過程中農民意識的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7.
[16]華北婦女運動的新方向[N].新華日報:華北版,1941-03-07(4).
[17]晉察冀邊區北岳區婦女抗日斗爭史料編輯組.烽火巾幗[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
[18]我所見到的左權婦女[N].新華日報:華北版,1943-03-21(4).
[19]李軍全.政治操控與社會動員:中共對節日的利用和改造(1937-1949)[D].天津:南開大學,2012.
[20]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1]黎城張蘭英當選全縣女狀元 各地熱烈紀念婦女節[N].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03-21(2).
[22]井陘的十一位模范婦女[N].晉察冀日報,1943-04-03(4).
[23]一位出色的女勞動英雄[N].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07-11(4).
[24]移民的女勞動英雄[N].新華日報:太行版,1944-01-21(4).
[25]賽過男子的女兒呂香榮[N].晉察冀日報,1943-06-27(4).
[26]邊區各地婦女熱烈參加生產[N].晉察冀日報,1943-03-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