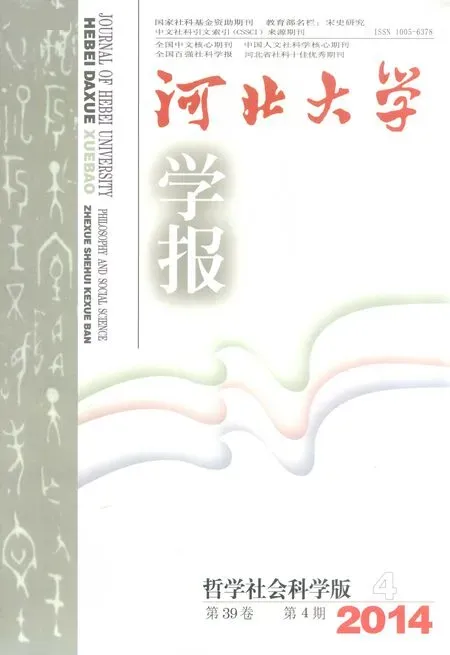日本當代文學批評方法論之辨
張如意,溫榮姹,馬振秋
(1.河北大學 外國語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2;2.唐山學院 外語系,河北 唐山 063000)
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的各種批評方法開始傳入日本。日本在吸收和借鑒這些批評方法的同時,也在不斷探索屬于自己的文學批評之路,逐步形成了諸如“作家論”“作品論”“文本論”和“文化論”等一系列具有日本特色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從時間順序來看,“作家論”大致興起于1950年代至1960年代,“作品論”興盛于1970年代,“文本論”則流行于1980年代,進入1990年代以后,“文化論”又逐步成為主流。在日本學界,關于當代文學批評方法論的發展歷程和演變軌跡,大多數人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關于這些方法論緣何變化及其本質特征等問題,人們關注和論述的卻很少。從哲學上講,方法論是人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和原則,它與認識論和世界觀是緊密相連的,方法論反映著世界觀,反過來世界觀又決定著方法論。在文學批評領域,方法論與世界觀的關系也應該遵循這樣的規律。可以說,日本當代文學批評方法論即體現著日本人對文學的認識和判斷,同時又反映了日本人的世界觀。通過對日本當代文學批評方法論的變化原因和本質特征的探討,不但可以加深對日本當代文學批評方法論的認識和理解,而且還可以藉此管窺當代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世界觀,了解日本文化。從此目的出發,本文在對“作家論”“作品論”“文本論”以及“文化論”的演變歷程進行梳理的基礎上,以“作品論”和“文本論”為重點,闡明并揭示其本質意義及矛盾特征,以期從較深的層面認識日本當代文學批評的特質,并希望能對我國的文學批評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一、從“作家論”到“作品論”再到“文本論”
何為“作家論”?簡而言之,“作家論”是以實證主義為基本理念的一種文學批評方法論。該方法論主張作品是作家精神活動的產物,與作家的實際生活有著直接的聯系,研究活動應該運用實際考證的方法,發掘作家的生活實際和精神世界。正如長谷川泉在談到志賀直哉作品的時候所言:“作為文學作品的《暗夜行路》無論作者的意識如何,都不可能是志賀直哉這一創作主體之外的創作物,從而不能使其與作品‘完全游離’。”[1]基于以上認識,“作家論”偏重于對作家實際生活的考證和傳記的書寫,在20世紀50-60年代,該方法論頗有市場,涌現出一大批以考證為主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因此這一時期也被稱為“作家論”的時代。以夏目簌石研究為例,伊藤整的《現代日本文學大系》中的“解說”(1949)、夏目漱石的次子夏目申六所著《父親夏目漱石》(1956)、鷹見安二郎著《漱石的養父鹽原昌之助》(1963)、江藤淳的《漱石和他的時代》(1970)、荒正人的論文“漱石的陰暗部分”(1971)、越智志雄的《漱石私論》(1971年)、柄谷行人的《畏懼的人》(1972)以及桶谷秀昭的《夏目漱石論》(1972)等基本都是從實存主義的立場出發,以作家為中心,運用實證方法進行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凸顯出該時期方法論——“作家論”的特征。
另一方面,自1950年代起,西方的諸多文學批評方法論已經開始輸入日本。如“新批評”“鑒賞論”“讀者論”等等。受西方方法論影響,一些人開始對實證主義這種“游離于作品之外”的批評方法產生不滿,并試圖探索新的理論。1970年代左右,三好行雄所倡導的“作品論”成為了主流。三好行雄在其代表性論著《作品論的嘗試》的序言中,提出了“鑒賞”的概念,并對“實證主義”進行了嚴厲批判:“鑒賞這種欣賞手段是以具體作品的存在為前提的,不允許鑒賞者游離到作品表達結構的外部。這是鑒賞區別于批評和研究的根本性質。(這)不是美學上的問題,而是文學研究實踐上的問題。針對在批評和研究的名義下所進行的一種頹廢的、忽視乃至輕視作品世界、舍棄作品事實的外在批評的橫行,至少應把作品世界作為一次性的終極對象,這種鑒賞作用的一元化獨立,應該為文學研究中作品論的復權提供最為有力的根據或實踐的成果。”[2]在這里,三好行雄之所以突出和強調“鑒賞”這一概念,其目的并不是打算將它與批評和研究的概念割裂或者對立起來,而是要通過強調鑒賞,提出一種新的方法論即“作品論”,以抵制和批判當時流行的“作家論”。他主張真正的批評或研究應該像“鑒賞”一樣,首先要忠實于作品,不允許超越到作品的外部,即堅持所謂的“內部批評”,而且將這一點看作是文學批評活動唯一的有效途徑;其次對忽視作品,游走于作品之外的實證主義研究“外部批評”進行了痛批,認為它們背離了批評和研究的正道。緣于三好行雄高超的理論水平和對作品精妙的結構分析,開啟了日本文學批評的“作品論”時代,1970年代該方法論盛極一時,對當時的文學批評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種批評方法,雖然很大程度釋放了文學批評的空間,滿足了闡釋的自由,但其將自己封閉在作品內部、斷絕與外部聯系的“自閉性”的矛盾特征逐漸暴露出來,隨著西方新的文學理論的涌入,逐步為“文本論”所取代。
“文本論”是源于歐美的日本本土化的一種文學批評理論,它涵蓋了以巴特、巴赫金、克里斯蒂娃以及德里達等一批西方當代符號論者的思想理論。其中對日本影響最大的當數法國批評家羅蘭·巴特。巴特是介于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之間的文學批評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他的學術觀點就開始被譯介到日本,1979年收錄其8篇論文的單行本《物語的結構分析》翻譯出版后,在日本文學研究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對傳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形成了極大的沖擊。羅蘭·巴特的批評理論最引人注目的有兩點:其一是提出“文本”(text)概念,將“作品”和“文本”完全對立起來,試圖從根本上顛覆“作品”這一傳統概念。巴特在從“作品到文本”一文中這樣寫道:“如同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文學上,馬克思主義、佛洛依德學說和結構主義均要求書寫者、讀者和批評者之間的關系相對化。就如同長期以來按牛頓的思維方式思考一樣,(人們)直至今天仍然在使用作品這一傳統的觀念,針對于此,應該通過拋棄或顛覆從前的范疇而獲得新的對象,這種對象就是‘文本’。”[3]他同時還認為:“作品是物質的碎片,是占據(比如某個圖書館)書籍空間的一部分。而‘文本’則是方法論的場”“文本是不可還原的無數性”等。其二是完全抹殺作家的作用。認為“文本”的意義不在于作家,而在于“讀者”,主張“文本”的意義是無限性的,閱讀是無限自由的,甚至宣判了“作者的死”。巴特的上述觀點,在作家論和作品論占據主流批評地位的時期傳入日本,無疑給日本文學批評界吹入了一股新風。隨著前田愛《都市空間中的文學》對文本論的成功運用,該方法論的理論魅力很快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成為熱門話題,在諸多“文本論“者的文章里甚至不再使用”作品“和”作家“之類的概念,代之以“文本”和“話者”等全新的表述方法。小森陽一在《閱讀的理論》一書的首篇即推出“文本”概念,大加溢美之詞:“當你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會反反復復遇到‘文本’這個詞的。為什么我們把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不叫‘作品’而稱之為‘文本’呢?為什么不使用耳熟能詳的日語表達而用外來語呢?關于這一點我首先想得到你的首肯,即正因為有了作為讀者的你,才使得書籍、這種用文字寫就的本身沒有任何意義的紙和墨的集合體重新獲得了生命和意義。”[4]1很顯然,小森陽一的這番話,不僅表明他無批判地接受了“文本”理論,而且也充分反映了當時日本批評界對巴特理論的欣賞和推崇之情;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品論”批評話語地位的喪失。
“作品論”和“文本論”雖然都強調將批評集中于“作品”或“文本”的內部,但它們二者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作品論”盡管強調通過割裂作品與外部世界的聯系而向作品的內部世界尋求意義和價值,但它并沒有否認作品的客觀實在性,也沒有否認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系。但“文本論”則不同,它不但否定了作品的客觀實在性(“物質的碎片”),而且徹底宣告了作家的“死”。這種對傳統的顛覆,不亞于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場革命,因而這種轉變也被日本文學批評界譽為文學批評的“范式轉換”。誠然,這種方法論改變了傳統的思維模式,使包括作家、作品乃至文學史在內的整個文學批評范疇都開始了新的建構。但是,該理論本身卻存在著一個嚴重的悖論,它觸及到了哲學的根本問題。
二、“作品論“與”“文本論”的本質及其矛盾
1990年代后,雖然“作品論”和“文本論”逐步為新興的“文化論”所取代,失去了主流地位,但它們的影響并沒有從文學批評中完全退去,其代表性概念“作品”和“文本”已然成為文學批評中的重要術語且被廣泛應用。“作品”和“文本”分別是從“作品論”和“方法論”中衍生出來的兩個批評概念,它們在內涵上有著本質的不同。但是,在現實的文學批評和研究中,“作品”和“文本”的概念未必得到了清楚的區分,不僅如此,在一些研究論文中往往被混淆在一起而不加區分地使用。這一現象,不僅日本存在,中國批評界也不鮮見。“作品”是什么?“文本”又為何物?這是在文學批評和研究中首先應該厘清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合理有效地使用這兩個概念。要達此目的,則須從本源上對“作品論”和“文本論”進行深刻剖析。
孟慶樞在“全球化語境下的日本當代文學理論”一文中論及日本的“文本論”時曾這樣寫道:“我國古代文論,包括日本文論都有‘細讀’、‘看取字縫里的意思’之闡釋法,這其實與文本論是相同的。”[5]的確,一般來講,中國傳統的諸如讀取“字里行間”的意思、理解“言外之意”等樸素的文論注重對閱讀對象內部結構的分析,強調闡釋的重要性,其中應該包含著“文本論”的某些意義要素,但是,中國閱讀中所說的“字里行間”或“言外之意”最終還是不能脫離作者的,我們從“字里行間”或“言外”所捕捉的必定是作者的思想意識,所以說在對閱讀或批評對象的認識問題上,中國的古代文論與“文本論”之間是有本質上區別的。與其說中國古代文論與“文本論“相通,還不如說更接近于“作品論”。因為無論是中國古代文論還是日本當代的“作品論”,都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承認作品是一種具有意義的客觀存在,承認作品與作者之間的聯系。在這一點上,日本的“作家論”和“作品論”也存在著某種一致性。正如石原千秋所言:“‘作品論’和‘作家論’是‘近代文學研究’中的兩條大道。有時候二者(關系)是二者擇一的,有時候則是單純相續性的。”[4]288石原千秋所說的“兩條大道”實際是將“作家論”和“作品論”看做兩種大的方法論,它們之間應該是對立統一的關系,既相互獨立又彼此關聯。而在日本的批評現實中“作家論”和“作品論”這種關系卻被扭曲或破壞了。“作家論”只關心“先驗性存在的‘作家’傳記性事實或生活史記述,而忽略了‘作家’唯有通過創造作品才得以成為作家的這個事實”。而“作品論”恰恰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試圖割裂作品外部和內部的關系,而片面地強調從作品內部獲得意義或價值。但話雖如此,二者之間還沒有達到決絕的、相互否定的地步。“作品論”的倡導者三好行雄雖然對“作家論”提出了尖銳批評,反對實證研究,但并沒有否認作家與作品的關系,只不過他把對作者的考察看成是研究和認識作品內部世界的一個手段而已。由此可以看出,“作家論”和“作品論”所存在的齟齬,雖然有悖于辯證法的觀點,但并沒有違背唯物主義,也可以說在哲學最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沒有產生對立。但是,“文本論”則不同,它與“作品論”的分歧是本質上的、不可調和的。因為“作品論”主張先有作品,而后有讀者,讀者雖然可以對作品進行“無限”闡釋,但作者及其創作的歷史仍然是客觀存在的;而“文本論”不但否定作品和作者,認為“文本是從無數的文化中引用而形成的編織物”“讀者”可以對意義進行無限自由的恣意闡釋。從“作品論”到“文本論”這種所謂的“范式轉換”不但被認為是文學批評方法的轉變,而且被譽為一場思維制度的革命。在這種華麗的理論光環下,實際掩藏著的是存在與意識,客體與主體相互關系的哲學本源問題。無疑,“文本論”否認作家和作品的客觀性,抹殺客體的意義,無限夸大了主體即閱讀者的作用,最終陷入了一種“閱讀的虛無主義”[6]。那么,在批評實踐中,是運用新潮的“文本論”還是采用傳統的“作品論”或“作家論”,成為日本當代文學研究者的一個艱難選擇,尤其是成長于后現代主義和文本理論思潮盛行時期的年輕研究者更是茫然不知所措。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方法論問題,而是涉及到如何認識文學,如何欣賞文學等文學批評的根本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在進行文學閱讀或批評之前,必須搞清楚文學的本質和功能是什么。但是,從日本的批評現實來看,很多研究者并沒有對這些問題進行充分的思考,而是一味地套用、模仿所謂新的理論,對文學作品或文本進行恣意的闡釋,而忽視了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賴以存在的基礎,使文學批評成為無本之木。
承認文學的客觀實在性是辯證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很顯然,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看,“文本論”否認作品的存在,也就是否認其客觀實在性,從根本上違背了文學的基本原理。雖然“文本論”也承認“文本”是物質,但它所說的物質是“紙和墨”的“集合體”,是不具備文學意義的物質,因而也就抹殺了文學作品作為文學這一物質的特性和意義,實際上就是從根本上否定了文學作品的客觀實在性。按照“文本論”的觀點,作家生產的不過是沒有任何文學價值的紙墨的集合體,因而也就徹底否定了作家存在的意義。“文本論”否認了文學批評的客觀依據,抹殺了文學鑒賞的標準,從哲學上講是唯心主義的方法論。
三、結 語
正如前文所述,文學批評方法論實際上是認識論和世界觀在文學價值判斷上的一種反映。當代日本文學批評中的“文本論”所倡導的肆意闡釋或無限解讀,看似尊重讀者的無限自由,充分發揮閱讀的“民主”,但實際上是拋棄了批評的根據和標準,從而必然導致人們對文學價值判斷上的混亂。而這種方法論在認識論上的危險并不僅僅在于文學批評本身,因為文學閱讀具有廣泛的社會性,它很容易通過學校的文學教育影響到學生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進一步拓展和延伸到社會中,不僅會改變人們對文學的認識,甚至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意識和思維方法,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因此不可小覷。如何既保證閱讀的自由,又不喪失文學批評的標準,這將是日本文學批評方法論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也值得我國的文學批評注意和思考。進入21世紀后,日本文學批評中的“文化論”更加盛行,它將文學置于文化視域中,似乎使文學批評由“內在”轉向“外在”,對“作品論”和“文本論”的理論缺陷有所糾正,但它能否從根本上化解“作品論”和“文本論”之間的矛盾,解決文學批評中的認識論問題,且其自身所存在的消解文學的藝術性的問題等等,又為我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1]長谷川泉.現代文學研究 情報と資料[M].東京:至文堂,1987:8.
[2]三好行雄.作品論の試み[M].東京:至文堂,1977:9.
[3]ロラン?バルト.物語の構造分析[M].東京:花輪光訳、みすず書房,1979:92.
[4]石原千秋,木股知史,小森陽一,等.読むための理論[M].東京:世織書房,1991
[5]孟慶樞.全球化語境下的日本當代文學理論[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7(3):105.
[6]田中実.読みのアナーキーを超えて[M].東京:右文書院,19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