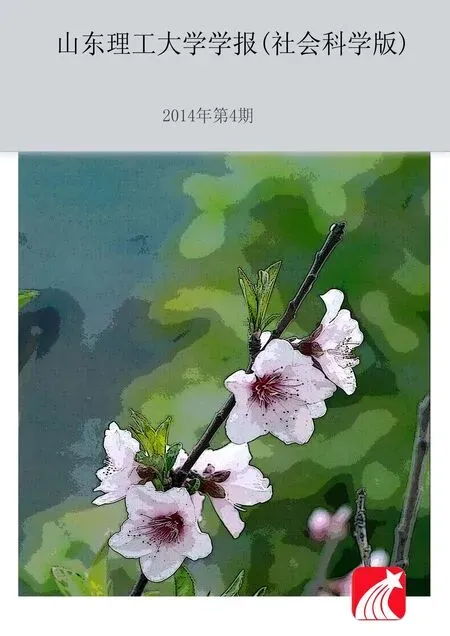清末四大小說雜志與翻譯小說關系研究
闞 文 文
(山東農業大學 文法學院,山東 泰安 271018)
晚清(1840~1911)是中國政治文化激烈動蕩的時代。1840年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西學東漸呈現出強勁態勢,對中國社會產生了猛烈震撼和沖擊。先進印刷技術的引進和新聞報刊事業的盛行,為小說期刊的產生提供了物質條件。小說界革命的發起和小說讀者市場的成熟壯大,種種因素都為報刊小說的崛起和繁榮創造了必備條件。
翻譯小說是報刊小說的重要組成部分。甲午戰爭后,流亡日本的梁啟超閱讀了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使他大受啟發。維新失敗的教訓,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政治小說的強大功用,使他清醒地認識到要開啟民智,小說是最有力的工具。所以,他在《清議報》創刊伊始,就發表了《譯印政治小說序》,號召翻譯外國政治小說,后來又創辦了《新小說》,發動了“小說界革命”。梁啟超從政治宣傳的角度夸大小說的社會功能,讓小說承擔起改造社會和國民的重任,文學領域中的“小說”一門,從叨陪末座的邊緣地位自此一躍而成為中心,成為“文學之最上乘”。在他的號召下,小說創作和翻譯在之后幾年間出現了驚人的發展態勢。
隨著報紙期刊的大量涌現,為刊載小說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傳播載體,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為宗旨的翻譯小說,帶來了翻譯小說的空前繁榮。中國翻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學翻譯活動也由此掀起,外國小說鋪天蓋地涌入中國。《新小說》的誕生,從辦刊內容到形式變化都為后來的小說專刊提供了范本和參照。在它之后,各種以“小說”命名的期刊雜志雨后春筍般涌現,僅1911年前,便有22種,如《小說世界》《小說月報》《小說時報》《中外小說林》《繡像小說》《小說林》等。其中《新小說》《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被阿英先生稱為清末文藝雜志的“四大權威”,“是當時新傾向的代表”。此后,學術界一致認同這種說法,將這四種雜志稱為“晚清四大小說雜志”。
翻譯小說在近代是不容忽視的文學門類,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思想和文學觀念,給中國小說創作帶來了啟發和動力。據日本學者樽本照雄編撰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精確統計,清末民初的翻譯小說數量為1101種,蔚為大觀。[1]352進入20世紀后,其中最著名的《新小說》、《月月小說》等小說雜志都大量刊載外國翻譯小說。
1902~1909年間發行的《新小說》、《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林》這四家最具影響力的小說雜志,非常重視外國小說的譯介,與同時期的其他報刊雜志出版的翻譯小說相比,數量可觀,特點鮮明,清晰地反映了晚清翻譯小說的整體面貌。
《新小說》由梁啟超1902年在日本橫濱創辦,創刊伊始便擬訂“本報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2]《繡像小說》則稱其“遠摭泰西之良規,近挹海東之余韻,或手著,或譯本,隨時甄錄,月出兩期”,[3]都把翻譯小說列為重要門類。據筆者精心閱讀和統計,《新小說》中刊載翻譯小說16種,《小說林》約18種,《繡像小說》20種,《月月小說》約54種,共計108種,約占全部作品的1/2。既有連載多期的長篇小說,亦有中篇和短篇;既有家喻戶曉的名家名著,也有二三流作品。思想意識紛繁復雜,題材內容豐富多彩,翻譯形式也各式各樣,值得研究者給予充分關注。
一、翻譯小說的形式和體例
在四大小說雜志的翻譯作品中,形式上存在著長篇與短篇共用、文言與白話并存的現象,既有很多文言短篇小說,也有大量的長篇白話章回體小說。在長篇小說的翻譯中,作者根據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因襲傳統小說的程式和套路,將外國作品翻譯成章回體。篇中回末仍會出現中國讀者熟悉的“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字句,還有“列位高興聽我的話,且不要忙,容在下慢慢的說”,“看官聽說”等話本小說的老套語言。《新小說》《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和《小說林》刊出的翻譯小說中,43部長篇小說有將近15種采用章回體,回目清晰,對仗工整,語言通俗曉暢。
大量采用章回體的做法,適合期刊雜志的自身特點,更迎合了中國讀者的閱讀習慣。小說雜志常為半月刊或月刊,決定了長篇小說必須進行長期連續刊載。每期刊登一至兩回,回目清晰,結構謹嚴,極大方便了編輯者的編排和讀者的閱讀。《繡像小說》在翻譯小說《小仙源》14回連載完畢后,附有范例一篇,其中寫到“原著并無節目,譯者自加編次,仿章回體而出以文言”,[4]表明了譯者采用的翻譯體例。《小仙源》的章回篇目,如第一回“遇颶風行船觸礁,臨絕地截桶為舟”,乍一看,還以為是中國的舊小說。
古代小說中,文言短篇的形式多用來記述奇人佚事,雜史逸聞,或“志怪”或“志人”。晚清四大小說雜志中有大量的短篇翻譯小說,內容也不外于此。如《新小說》中刊載的雜記小說《知新室新譯叢》,便是周桂笙翻譯的外國筆記小品,介紹國外的風土人情以及新奇之事。還有不少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說集,如《繡像小說》中的《華生包探案》(今譯《福爾摩斯偵探案》)、《天方夜談》等,都采用文言短篇這種形式。而《月月小說》的文言短篇小說最多,高達35種。
翻譯家采用我國古代傳統小說的形式翻譯外國作品,固然與他們受中國傳統小說的影響根深蒂固有關,但深層次考究,也是他們有意為之。在小說這種文學樣式日益注重娛樂功能的同時,小說翻譯家們還自覺使其擔負著教化民眾的重大使命。所以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翻譯作家,雖然倡導“新小說”,希圖借小說宣傳自己的政治思想,達到政治改革的目的,但在形式上不得不采取中國讀者普遍熟悉和喜聞樂見的方式,方能利于作品的傳播和被接受。所以,四大小說雜志里的這些翻譯小說,或者在語言上依舊使用文言,或者沿用章回體,大多以陳舊的風格包含嶄新的內容和新的意境,實為“舊瓶裝新酒”,在翻譯小說發展的初期階段,受到了大批讀者的追捧。
隨著小說翻譯經驗的累積和外國文學作品的影響,翻譯小說在1907年前后達到空前繁榮,翻譯者的創作手法也趨向豐富多樣,并敢于創新求變。如《繡像小說》出現了幾種白話短篇小說,刊登了錢塘人吳梼翻譯的一些作品,有《燈臺卒》(星科伊梯撰,今譯顯克微支)、《山家奇遇》(馬克多槐音著,今譯馬克吐溫)、《理想美人》(葛維士著)、軍事小說《斥候美談》(科楠岱爾著,今譯柯南道爾)等,基本上都是選取外國名家名著,采用暢達平實的白話語體,已經具有現代翻譯小說的雛形,顯示了譯者較高的翻譯水平。
二、翻譯小說的題材類型
1902年出版的《新小說》雜志第一號便將小說的題材分門別類,作了明確細致地劃分,有政治小說、科學小說、偵探小說、愛情小說、歷史小說、冒險小說、哲理小說、法律小說、外交小說、語怪小說等十幾種題材,令人眼花繚亂。其他三大雜志相繼創刊,對這種做法進行學習并大加發揚,類型劃分得更為細致甚至瑣碎。《月月小說》中僅“言情小說”一類便派生出“俠情”、“寫情”、“奇情”、“癡情”等多個類別。題材的分類可以有效吸引讀者,滿足不同讀者的口味,也使我們今天的研究者對當時讀者的審美趣味和編輯者的選編標準有所了解。
政治小說是近代新出現的小說門類,擔負著開啟民智的政治任務。政治小說的最大特征在于宣傳作者的政治思想,具有極強的實用功利性。梁啟超鑒于日本政治小說在推動民眾參與改革中的作用,大力提倡翻譯、創作政治小說。他在1898年創辦的《清議報》中,率先翻譯了《經國美談》和《佳人奇遇》兩部日本政治小說的代表作。他說:“政治小說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懷抱之政治思想也。”[5]37以后的一段時間里政治小說的翻譯大為興旺。《新小說》中的日本加藤政之助著,玉瑟齋主人譯的《回天綺談》《繡像小說》中的《回頭看》《珊瑚美人》等,都是著名的政治小說。而中國讀者對政治小說內涵的理解愈加廣泛,將軍事、戰爭題材也納入進去。如《月月小說》中刊登的“虛無黨小說”系列,《八寶匣》(周桂笙譯)描述的是虛無黨人暗殺活動的經過,冒充俄國大偵探的虛無黨人賴柴洛夫,將稀世的鉆石放到一個精美的裝有機關的八寶匣中,欲通過俄國大使獻給沙皇,借此達到刺殺沙皇的目的,可惜身份暴露導致計劃失敗;《爆裂彈》寫的是虛無黨人彼都和俄國密探克卜,彼此明了對方的身份,卻故意親近,希望探出對方的情報,最終彼都棋高一著,不僅安全轉移了爆裂彈,而且還盜得了黑名單,挽救了若干虛無黨人。這類小說比之純粹的政治小說,可讀性大大增強。
偵探小說令中國讀者耳目一新,它因充滿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和豐富濃厚的趣味性,滿足了市民階層追求驚險的獵奇心理和朦朧的科學邏輯意識;而且偵探小說大多數都揭露社會黑暗、弘揚正義、同情弱者、懲辦罪犯,在內容上與我國傳統的俠義公案小說有很大的相通,因此很受讀者喜愛。晚清四大小說雜志的小說刊載充分反映了這一時代特點,刊登題材類型最多的就是偵探小說,共有長短篇偵探小說20余部,占全部總數的四分之一。較著名的長篇有《一百十三案》(《小說林》)、《黑蛇奇談》(《小說林》)、《華生包探案》(《繡像小說》)、《毒蛇圈》(《新小說》)等。《月月小說》中接連刊登了精彩的偵探故事,如《海底沉珠》敘述離奇的珍珠寶石失蹤案件,還有《三玻璃眼》、《盜偵探》等十一種。這些偵探小說事件集中,情節扣人心弦,結構緊湊,譯筆優美,極大吸引了讀者眼球。
此外還有許多科學小說,也是近代新興的小說類別。《新小說》刊登了法國科學小說作家凡爾納的代表作《海底旅行》,《月月小說》刊印了《新再生緣》《飛訪木星》《倫敦新世界》《空中戰爭未來記》等多部科學小說。其中《空中戰爭未來記》是近代翻譯名家包天笑的譯作,小說幻想20世紀10至30年代,歐洲各國爭霸,憑借飛艇展開空中大戰,帶有豐富的想象色彩。
還有很多作品介紹和鼓吹了西方的冒險進取精神,《繡像小說》中就有《小仙源》《汗漫游》《環瀛誌險》《商界第一偉人》《西譯雜記》等,都屬于此類作品。同時也很重視科學知識的灌輸和解說,例如《幻想翼》傳播天文學知識,《理科游戲》講解物理化學常識。種種不同類型的翻譯小說,向讀者展示了絢麗多姿的社會景象,豐富了國人的視野,擴大了知識面。
三、作者和譯者
四大小說雜志的翻譯小說中,有很多不注明原作者的姓名和國籍。《新小說》除了《毒蛇圈》、《電術奇談》等四部明確署名原作者的作品之外,其余十一部都未標明原作者。其他幾家小說雜志也普遍存在這種情況,而且譯者姓名也常不注明,很多翻譯者的名字絕大多數用字或號來代替,導致一些作品的譯者名姓難辨真實。
表1是繡像小說關于著譯者情況的統計表:完全沒有署名的作品占了雜志刊登譯作總數的三分之一,僅僅標明著者的作品也占三分之一左右。署名美國威士原著的長篇翻譯小說《回頭看》,實際是把小說中以第一人稱出現的主人公的名字誤認為作者;而這部小說本是美國畢拉宓(Edward Bellamy)所作,曾被西方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成《回頭看紀略》(Looking Backward)。[6]131

表1 繡像小說著譯者情況統計表
不注明原著者和譯者,而且譯名混亂,很容易造成一書重譯、多譯和抄襲他人的混亂現象。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翻譯體例的不完備,翻譯者并不著意要說明作品的原著名稱及原作者。因為在他們看來,翻譯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啟迪民智,輸入文明,或者是娛樂休閑,署名與否是無所謂的事情;而且小說翻譯者潛意識里仍有傳統小說觀念作祟,對小說創作甚至小說翻譯都抱有輕蔑態度,因此連他們自己的名字也常常被省略,或者弄上一大堆的筆名和別號,讓研究者頭痛。
但是我們仍可看到一些經常出現在四大小說雜志中的翻譯者,甚至職業翻譯家。他們主要有梁啟超、徐念慈、周桂笙、陳冷血、包天笑、吳梼、陳鴻璧等。他們或是小說雜志的主要創辦人,如梁啟超為《新小說》的創辦者,徐念慈主創《小說林》;或是雜志的編輯,如周桂笙、陳冷血等;或是職業的翻譯家,如吳梼、陳鴻璧,總是活躍在四大小說雜志的翻譯一線。
周桂笙是其中發表翻譯作品最多的一位作家,其作品在1905~1909年頻頻出現在《新小說》和《月月小說》上。譯作上除署本名“周桂笙”外,還常用“知新室主人”、“新庵”、“惺庵”、“穉桂”等筆名。發表的作品有長篇也有短篇,題材范圍廣泛,共計作品17部。重要的有偵探小說《毒蛇圈》《雙公使》,虛無黨小說《八寶匣》,航海小說《失舟得舟》,科學小說《飛訪木星》《倫敦新世界》等。周桂笙本人通曉外語,視野開闊,倡揚虛無黨小說和科幻小說。他還在《月月小說》上倡導成立了“譯書交通公會”,號召翻譯同人規范翻譯行為,進行翻譯文學的交流活動。他的譯筆以白話為主,《毒蛇圈》是近代較早用純白話翻譯的作品,流暢生動。少數短篇小說雖用文言翻譯,但也是淺近通俗。周桂笙為近代開拓翻譯小說新路的急先鋒。
吳梼也是近代著名的翻譯家,曾留學日本,有著豐厚的文學修養和外國語言功底。他在《繡像小說》上發表了多篇小說,均為短篇小說翻譯中的上乘之作。如前面提到的《燈臺卒》《山家奇遇》《理想美人》等小說,都是根據日文重譯的。此外還有一部長篇譯作《賣國奴》(德國蘇德爾曼著,吳譯為蘇德蒙)。當時的短篇小說多采用文言翻譯,吳梼敢于創新,并注重選擇名家名著,對少人問津的外國短篇小說給予充分關注。他的翻譯語言全用白話,而且從過去的意譯轉變為直譯,強調尊重原著。吳梼之后,翻譯家的文學意識逐漸強化,翻譯質量明顯提高。特別是語言逐步走向通俗化,短篇小說也開始增多。
此外,四大小說雜志的翻譯作家群體中還出現了女性翻譯家。《小說林》刊登了女士陳鴻璧的多部翻譯作品,有科學小說《電冠》(英國佳漢著),偵探小說《第一百十三案》(法國加寶耳奧原著),歷史小說《蘇格蘭獨立記》。前兩部小說的翻譯沒有采用傳統的章回體,而用數字分章的形式,破除了舊套。陳鴻璧還以《印雪簃簏屑》為總題編譯了一些有關外國風土民情的逸聞奇事。《小說林》創刊后共刊印十二期,每期都有陳鴻璧的譯作。徐念慈主辦的《小說林》雜志,從審美上更多地接受西方思想,有意識地運用西方純藝術理論,在刊物宗旨和品格上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傾向。在這樣一個重要的雜志上,陳鴻璧受到如此特殊的青睞,由此不難想象她在《小說林》編者心中和當時譯壇上的地位。
四、翻譯方式以意譯和譯述為主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小說翻譯家,為了思想啟蒙和政治宣傳的目的,把作品的主題、結構、人物都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造,任意刪削改譯,被稱之為“豪杰譯”。以《繡像小說》為例,該刊刊登的長篇翻譯小說,為了適應中國人的審美情趣,模仿傳統小說的創作模式,將中國小說中不常出現而卻代表外國小說特色的大段自然景物描寫和人物心理描寫,無一例外地刪掉,而代以“話說”、“卻說”諸如此類的語言。譯者還常根據自己的理解,隨意添增原文中沒有的文字;或者將作品中的人名、地名、稱謂、典故完全中國化,如《華生包探案》、《玉環外史》,篇名便明顯具有中國特色。有的翻譯干脆就是編輯和整理,如《繡像小說》中的《商界第一偉人》,署“憂患余生述”,在全文結束時有一篇“按語”,介紹作品的譯介情況:“按此稿為美洲游學生之譯本,其間事跡多與正史歧異,仆從而潤色之,亦未敢遽行刪改也。聞近有譯其正傳者曰歌普電,讀者曷取以參改之。著者附志。”[7]
美洲游學生究竟為誰不得而知,憂患余生僅僅是根據別人的譯本“從而潤色之”,顯然不能算譯者,而只能稱為整理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按語的最后“憂患余生”的自稱為“著者附志”,充分反映了當時著譯不分的翻譯情況。
這種翻譯方法固然不可取,但卻是中國翻譯文學處于萌芽和發展階段無法避免的現象。譯者在翻譯之初,目的是為了輸入文明或借鑒其思想意義,文學意識薄弱,一般不會考慮文學價值,而盡量追求平易暢順,以有利于層次不高的讀者閱讀和理解。作為文學也許稱不上藝術價值,但是作為國民普及性讀物,卻是功不可沒,影響了一代國人。[8]156
五、結語
晚清四大小說雜志中一百多部翻譯小說里,有一些名家名著,但絕大多數是二流、三流作家的作品。這與譯者欣賞水平和審美眼光有關系,也反映了翻譯初期翻譯者閱讀視野的局限。《新小說》和《繡像小說》突出體現了這一初級階段的特點,無論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所不足。較之《新小說》和《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和《小說林》創刊較晚,分別在1906年11月和1907年2月創刊,而1907~1911年正是近代翻譯文學最繁盛的時期。《月月小說〈發刊詞〉》中云“本志小說之體有二:一曰譯;二曰撰。他山之玉,可以攻錯,則譯之不可緩者也”。[9]把翻譯小說放在第一位,為歷史所未有。《小說林》的宗旨則是輸進歐美文學精神,提高小說在文學上的地位,還在創刊號上刊登了法國浪漫主義代表作家雨果的肖像,以后各期還有大仲馬、狄更斯、司各特等世界著名小說家的畫像和生平介紹,表明它對外國作家的選擇,已開始注意其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文學價值。雖然它的出版時間不長,但文學翻譯的觀念非常鮮明,審美眼光也得到極大提升。
可以說,四大小說雜志上的翻譯小說,清晰地呈現出中國近代翻譯小說的動態發展過程,代表了晚清翻譯小說的最高成就。[10]51
[參 考 文 獻]
[1][日]樽本照雄.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M]. 賀偉譯.濟南:齊魯書社,2004.
[2]梁啟超.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J].新民叢報(十四號),1902.
[3]本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繡像小說(影印本第一號)[M].上海:上海書店,1980.
[4]小仙源凡例.繡像小說(影印本第十六號)[M].上海:上海書店,1980.
[5]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A].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6][美]韓南.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M].徐俠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
[7]商界第一偉人戈布登軼事.繡像小說(影印本第十四號)[M].上海:上海書店,1980.
[8]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9]月月小說發刊詞.月月小說(影印本第一號)[M].上海:上海書店,1980.
[10]闞文文.晚清報刊上的翻譯小說[M].濟南:齊魯書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