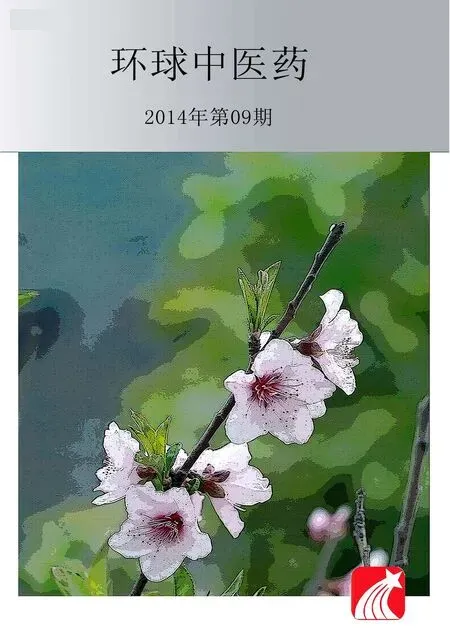淺析“共情”在中醫學中的體現及應用
馬龍 周英武 張慧 劉如秀
共情一詞,譯自英文“empathy”,還可譯為神入、同理心、共感、投情等,最早出現于1909年鐵欽納在“關于思維過程的實驗心理學講稿”之中[1]。1957年,人本主義心理學家Rogers 將“共情”概念定義為“個體體驗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體驗自身精神世界的能力”[2]。近些年來,最新的觀點強調,共情不僅是一種體察別人內心世界,并以關切、溫暖、尊重的方式有效反饋這種理解的能力;更是一種對他人關心、體諒、珍惜、尊重的態度。實質上,共情是能力、態度的集合體[3]。
自20世紀60年代起,“共情”被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廣泛應用于醫療服務領域,在改善醫患關系、提高醫療質量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4]。目前,中國醫務工作者也對“共情”的臨床應用愈加關注,正逐步開展理論研究、教育培訓等工作[5]。“共情”之命名、概念雖為近代西方心理學家所明確提出,然就其應用而言則絕非他們率先之舉。中國傳統中醫學雖無“共情”之說,但在其醫學思想、醫德要求之中對“共情”的核心理念早有體現;在其診療行為之中亦對“共情”的主要技術多有應用。執此觀點,筆者不揣鄙陋,撰文析之,以飧同道。
1 共情在中醫學診療思想中的體現
在醫學領域,“共情”是醫患之間架起的一座心靈溝通的橋梁,醫生關注并主動進入患者的世界,設身處地的體察病患的感受及需求;患者也充分感知醫生的關切、理解及尊重,彼此建立起信任的紐帶,共同努力、相互配合,變被動治療為主動參與,從而達到提高臨床療效的目的。中醫學思想中的“標本相得”觀,正充分體現了共情的這一內涵。
標本相得觀的提出,最早可追溯于《黃帝內經》。在《素問·湯液醪醴論篇》中,黃帝、歧伯答問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于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針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于耳,五色日聞于目,而病不愈者,亦何謂不早乎?歧伯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記。”這一論述明確指出,病人為本,醫生為標,病人與醫生不能很好溝通合作,病邪就不能制服,從反面、否定的角度闡釋了“標本相得”是治愈疾病的基礎。《素問·征四失論》在討論醫家臨癥得失時再次表明了這一觀點,其云:“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治)所以不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說明治療不能收到預期效果(十全者),原因往往不是不熟悉經脈等醫學知識,而是醫患之間缺乏有效溝通,醫生無法了解患者所想,以致不能調其精神、定其意志、使其很好地配合治療,最終內外相失、標本不得。后世醫家對《內經》“標本相得”觀多有傳承。如張景岳在《類經》中提倡治療“必病與醫相得,則情能相浹,才能勝任,庶乎得濟而病無不愈”。
通過上述論述,不難看出“標本相得”觀的核心內容,就是強調診療過程中與病患溝通、協作,并視之為決定治療成敗的關鍵因素;其所謂“相得”則是對醫患間“情通意達、道合志同”理想關系的概括,實質上也是醫患“共情”的一種簡潔表述。
2 共情在中醫學醫德要求上的體現
2.1 以人為貴的思想
共情,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對患者尊重、關愛的態度。中醫醫德中的“貴人思想”則充分體現了共情的這一重要內涵。
“貴人思想”源于儒家“仁愛”的倫理思想,是中醫醫德的中心范疇和靈魂所在。“貴人思想”將人之生命置于最為神圣的位置,《素問》所云“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于人”及孫思邈所謂“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于此”,就集中體現了這一觀點。出于對生命的珍視,以“貴人思想”為重要基礎的中醫醫德就十分強調對病患的尊重及關愛。
中醫歷代典籍對“貴人思想”論述頗多,如孫思邈在《千金藥方》中就要求醫生對待患者應像對待親人一樣關愛,其言:“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媸,冤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靈樞·師傳》也叮囑醫者要“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以傳達對病者的尊重。明·龔廷賢主張“凡為醫者”對待患者,應“志必謙恭,動須禮節,舉乃和柔”,切記“無自妄尊,不可矯飾”,更不得利用技藝以謀財、獵色。明代陳實功要求,醫者對待“娼妓及私伙家”等身份卑賤之人,“亦當正己視如良家子女,不可他意見戲,以取不正”。
“貴人思想”充分闡釋了傳統中醫“生命至重”、“病人至重”的醫療服務理念,以及對病人應尊重關愛、一視同仁的醫德要求。中醫之“貴人思想”與共情的“尊重、關切患者”這一基本理念異曲而同工。
2.2 推己及人的觀念
共情對醫生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進入患者的內心世界,將心比心的去感知、體驗患者的心境;并站在患者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分析問題。中醫學中的“推己及人”觀則充分體現了“共情”的這一重要內涵。
“推己及人”的觀念源自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即孔子所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子所說“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等。中醫學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因而全面繼承了“推己及人”的倫理觀,并將其作為中國傳統醫德中的重要內容,更視為習醫人必備之道德素養。
關于“推己及人”醫德觀的論述,在中醫學文獻中處處可見。如孫思邈對此曾言:“見彼苦惱,若己有之,深心凄愴,勿避險惡,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無作功夫形跡之心。如此可為蒼生大醫。”明代醫家江璀亦道:“人身疾苦,與我無異”。清代名醫費伯雄也說:“我欲有疾,望醫之相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醫之相救者如何?易地觀之,則利心自淡矣。”誠如孫思邈所言,古之能成大醫者,無不是身體力行“推己及人”之仁心的楷模。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體諒“病者度刻如歲”的焦灼,對患者之苦感同身受,雖負盛名卻不“自逸”,“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雖百理之遠弗憚也”。明代醫家張柏更是“人以病起,即夜數十起弗辭”。
由此可見,中醫學早在兩千年前所提出的“推己及人”觀,與共情的“將心比心”、“感同身受”、“換位思考”等核心內容,就其本質而言基本一致,其差別僅在語言表述不同而已。
2.3 待之以誠的原則
共情要求醫生對待患者要真誠,不偽裝、不掩飾、不扮演角色;用真摯誠懇的態度換得患者的信任,使其敞開心扉、暢談感受、有效溝通,最終達到相互理解、相互配合,共同戰勝疾病之目的。中醫學對此稱之為“不欺”。
明代醫家李廷將“為醫之道”,一言概之為“不欺而矣”,曰:“欺則良知日以蔽塞,而醫道終失;不欺則良知日益發揚,而醫道愈昌。欺不欺之間,非人之所能與也。”所謂“不欺”,其首要一點就是“誠待病家”,即不欺病人、坦誠相待。“或立奇方以取異;或用僻藥以惑眾;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魯之輩;或立高談怪論,驚世盜名;或造假經偽說,瞞人駭俗;或明知此病易曉,偽說彼病以示奇”的種種行為,習醫之人皆應唾棄。醫生對待患者一定要坦蕩赤誠,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患者的信賴,相托性命。此正如喻昌所說醫者“敬設誠致問,明告以如此則善,如彼則敗,誰甘死亡,而不降心以從耶”,“此宜委屈開導,如對君父,未可飄然自外也”。
據此,可以看出傳統中醫早已認識到“誠待病家”、“不欺人”,是醫生取得病家信任、配合,實現醫患相得的重要途徑。換而言之,“共情”中的“真誠”原則,早已為傳統中醫所重視、所實踐。
3 共情在中醫學診療行為中的應用
3.1 注重禮儀、贏得信賴
傳統中醫在診療病患時,十分注重醫學禮儀,自覺采用一定的準則來約束、規范自己外在行為。如孫思邈在《大醫精誠》中就要求,醫生在患者家中,一定要保持嚴肅端莊的形象,“夫大醫之體,欲得澄神內視,望之儼然。寬裕汪汪,不皎不昧,不得多語調笑,談謔喧嘩”。之所以如此要求,就是對患者傳遞一種尊重、重視的態度,贏得患者的信賴,從而達到醫患共情的目的。
3.2 善于傾聽、把握病情
現代醫學診斷疾病,往往過分依賴于儀器設備,而忽視患者自身的病感。與之相反,中醫學診療疾病十分注重患者自身的感受。《黃帝內經》有道:“數問其情,以從其意。”該條文就是叮囑醫者一定要注意詢問、傾聽患者的病感、病情;在交流的過程時時顧及患者情緒意志變化,引導病人毫無顧慮的訴說病情、病因,使醫者得之真情,掌握疾病本質。這種關注患者病感的診療理念,在明代醫家張景岳總結的“十問歌”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十問歌”是對十個問診要點的總結,包括“一問寒熱二問汗,三問頭身四問便,五問飲食六問胸,七聾八渴俱當辨,九因脈色察陰陽,十從氣味章神見”。歌中所提到的每一個要點,都是中醫對患者自身感受的詢問。中醫注重傾聽患者自身感受、自覺癥狀的主訴,不僅能使患者充分體會到醫生對自己的關注和尊重,促使其在心理上對醫生產生一種親切感和信任感,更能使醫生從患者全面的主訴中,精準的把握病情本質,進而實現醫患共情、醫患相得。
3.3 尊重隱私、得聞心聲
明代張景岳曾講:“閉戶塞牖,系之病者,欲其靜而無憂也,然后從容又訊問詢其情,委屈順其意,蓋必欲得其歡心,則問者不覺煩,病者不知厭,庶可悉其本末之因而治無誤也。”張景岳所言,就是提醒醫者診療病患,一定要選擇一個安靜的環境,關好門窗,與病人取得密切聯系,耐心細致的詢問病情,務使病人盡吐心聲,從而掌握病情關鍵。陳實功在其“醫家五戒十要”中,也強調“假有不便之患,更宜真誠窺睹,雖對內人不可談,此因閨閫故也”。
從先賢告誡之中,可以切實感受到中醫學對患者人格和權益的尊重,這與其“貴人思想”相統一。注重保護患者隱私的行為,不僅是醫生應具備的醫德修養,也是促進醫患之間達到共情,獲取患者最真實的疾病信息,從而提高臨床療效的手段。
4 體會
“共情”一詞雖為近代西方心理學家所提出,但其核心內涵、技術在中醫學里早有體現和應用。中醫學早在2000年前就能產生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如此先進的醫學理念,筆者認為,這種先進理念的產生,是衍生自中醫學“整體觀”的哲學思想。在中醫“整體觀”中,人是有機的整體;人之軀體、心理統一于這一整體之中,兩者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基于此,中醫看待病人,其著眼點不僅在于“病”,更在于有情有感的“人”,強調醫者設身處地的感受病患苦痛,給予患者理解、尊重、關懷,主動構建和諧的醫患相得關系,“親其師,則信其道”,從而達到彼此信賴、攜手合作、戰勝疾病的目的。
然而,在現代醫學面前,人是肉體的物質,忽略了作為人的心理情感,這就使醫學失去了應有的人文精神,醫患之間缺乏信賴,患者依從性下降,醫生所采取的醫療措施不能得到理解和配合。如此以來,何談良好療效?現代醫學所存在的這一弊端已為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認知。
筆者認為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這一新的醫學模式的提出,共情在醫療領域的作用將會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挖掘,其應用前景將更為廣闊。
[1]趙麗娜,李靜瑤,劉芬.共情研究綜述[J].學理論,2010,(33):80.
[2]王曉燕,彭晶.共情在護患溝通中的應用[J].全科護理,2011,9(22):2032.
[3]Barry A.Farber,Debora C.Brink,Patricia M.Raskin.羅杰斯心理治療[M].鄭鋼,譯.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6:8-15.
[4]姚婷,李勇,郭漢平.臨床共情研究進展[J].醫學與哲學,2012,2B(33):4-6.
[5]于德華,王一方,陳英群,等.醫學生人文醫學教育中的共情培養[J].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10,12: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