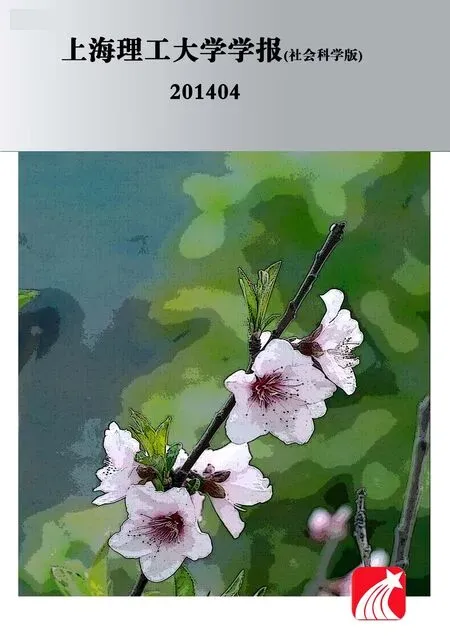文化記憶及想象視角下的《祖先游戲》
吳 慧
(上海海關(guān)學(xué)院 外語(yǔ)系,上海 201204)
文化記憶及想象視角下的《祖先游戲》
吳 慧
(上海海關(guān)學(xué)院 外語(yǔ)系,上海 201204)
到2009年為止,澳大利亞當(dāng)代著名作家亞歷克斯·米勒已發(fā)表了六部極具影響力的小說,寫作技巧的日臻成熟和完美使得他的每部作品都可圈可點(diǎn),令關(guān)注和研究澳大利亞文學(xué)的人們很是滿意。在眾多的作品中,無論從創(chuàng)作技巧,還是從作品傳遞的思想性方面來看,《祖先游戲》堪稱最好的一部。重讀米勒這部獲多項(xiàng)文學(xué)大獎(jiǎng)的作品《祖先游戲》,會(huì)強(qiáng)烈地為作品中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及想象所折服和震撼,而這一切均出自一位澳大利亞作家之筆。針對(duì)文本中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及想象所具有的意義,從德國(guó)學(xué)者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出發(fā),來關(guān)照文化記憶以及想象視角下的《祖先游戲》,以期進(jìn)一步體會(huì)作品的深刻內(nèi)涵以及它在重構(gòu)澳大利亞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化記憶;文化想象;文化身份;中澳關(guān)系
截止2009年已發(fā)表六部極具影響力的小說的澳大利亞當(dāng)代著名作家亞歷克斯·米勒,在寫作技巧方面日臻成熟和完美,每部小說都可圈可點(diǎn),好評(píng)如潮,令關(guān)注和研究澳大利亞文學(xué)的人們很是滿意。從20世紀(jì)90年代始已發(fā)表的小說《祖先游戲》、《被畫者》、《忠誠(chéng)的條件》到參加澳大利亞總理文學(xué)獎(jiǎng)角逐的《愛之歌》(LoveSong),讓讀者目睹了一位作家的成長(zhǎng)軌跡。然而,在眾多的作品中,無論從創(chuàng)作技巧,還是從作品傳遞的思想性方面來看,筆者始終覺得《祖先游戲》都是最好的一部。其實(shí),這也印證了作者本人的看法。2002年冬季,亞歷克斯·米勒在上海訪問期間,曾接受我國(guó)著名澳大利亞文學(xué)研究專家黃源深教授的采訪,當(dāng)黃源深教授問:“假如要在你過去已發(fā)表的六部小說中選出一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只選一部作品,而不是兩部,我會(huì)毫不猶豫地選擇《祖先游戲》,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這種觀點(diǎn)呢?” 米勒回答說: “我想你是對(duì)的。”[1]當(dāng)人們今天再次重讀米勒的這部獲多項(xiàng)文學(xué)大獎(jiǎng)的作品時(shí),會(huì)強(qiáng)烈地為作品中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及想象所折服和震撼,而這一切均出自一位澳大利亞作家之筆。那么在今天看來,文本中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及想象又究竟有何意義呢?筆者擬從德國(guó)學(xué)者阿斯曼的文化記憶理論出發(fā),來關(guān)照文化記憶以及想象視角下的《祖先游戲》,以期進(jìn)一步挖掘該作品在重構(gòu)澳大利亞文化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文化記憶” 在《祖先游戲》中的顯現(xiàn)
在德國(guó)學(xué)者阿斯曼(Jan Assmann)看來,所謂文化記憶就是一個(gè)民族和國(guó)家的集體記憶力,所要回答的是 “我們是誰(shuí)” 和 “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 的文化認(rèn)同性問題。文化記憶的內(nèi)容通常是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共同擁有的過去,其中既包括傳說中的神話時(shí)代也包括有據(jù)可查的信史[2]。“文化記憶有其固定點(diǎn),它的范圍不隨著時(shí)間的變化而變化。這些固定點(diǎn)是過去的一些至關(guān)重要的事件,其記憶是通過文化形式(文本、意識(shí)、紀(jì)念碑等)以及機(jī)構(gòu)化的交流維持的,人們稱之為‘記憶形象’”[3],具體到文學(xué)文本中的文化記憶與想象應(yīng)該指的是 “藝術(shù)家以屬于歷史的事實(shí)、現(xiàn)象、故事、人物作為創(chuàng)作的素材,但是在運(yùn)用它們的時(shí)候,將這些素材轉(zhuǎn)換為具有文化懷想特征與文化記憶色澤的內(nèi)容,在作品中注入了一種豐富的有指向的文化意味”[4]。想必《祖先游戲》真正撼動(dòng)人心的原因應(yīng)該是一位未曾在中國(guó)生活過的澳大利亞人,與一些中國(guó)人共事,通過訪談、閱讀,獲得大量素材后,大膽將其轉(zhuǎn)換成了具有 “文化懷想特征與文化記憶色澤的內(nèi)容”,在形、色、味等方面均達(dá)到了符合現(xiàn)實(shí)的境地。讀者閱讀體驗(yàn)后得到滿足當(dāng)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德國(guó)作家格拉斯曾經(jīng)說過: “一切都沒有過去,什么都會(huì)重新來過的。” 在他看來,小說家的任務(wù)原本就是要將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聯(lián)系起來,構(gòu)成一個(gè)虛構(gòu)的全景圖[5]。倘若我們將米勒的文學(xué)回憶放在這一框架中,就會(huì)發(fā)現(xiàn)米勒演示的雖是個(gè)體的記憶,但指向卻是民族的集體記憶。《祖先游戲》所截取的時(shí)代背景分別是19世紀(jì)中葉發(fā)生在澳大利亞歷史上的 “淘金熱” 時(shí)期,20世紀(jì)30年代日本侵華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以及20世紀(jì)70年代澳大利亞多元文化時(shí)期,描寫了中國(guó)福建移民鳳氏家族四代人在澳大利亞生活的故事。這與人們對(duì)中國(guó)文化乃至對(duì)澳大利亞文化記憶完全吻合。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澳大利亞文化的發(fā)展主要經(jīng)歷了三個(gè)階段:土著文化階段、民族文化階段和多元文化階段。由于種族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澳大利亞文化的第一和第三階段往往被忽視了……就澳大利亞而言,土著文化、亞太文化、除英國(guó)以外的歐洲文化以及美國(guó)文化的影響都在其文化的表層和深層留下了極為深刻的痕跡。澳大利亞文化是諸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融合的產(chǎn)物[6]3-4。也就是說。處于亞文化地位的中國(guó)文化在澳大利亞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作家們有義務(wù)和責(zé)任如實(shí)反映這一層面的文化內(nèi)容,對(duì)這一事實(shí)的文化記憶也是一個(gè)國(guó)家發(fā)展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米勒這位有著強(qiáng)烈使命感的作家責(zé)無旁貸地承擔(dān)起了這一使命,以文學(xué)文本的形式如實(shí)地記錄和呈現(xiàn)了這一歷史事實(shí)。
給讀者最深刻印象的是該小說的宏大如史詩(shī)般的氣勢(shì)。以現(xiàn)在敘述為切入點(diǎn),米勒巧妙地將故事的情節(jié)回溯到19世紀(jì)50年代,通過時(shí)空交錯(cuò),形成了澳大利亞發(fā)展的寓意。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部小說是一部有著大量事實(shí)細(xì)節(jié)的歷史書。在空間上,該小說超越了澳大利亞小說多局限于歐洲或澳洲的限制,將神秘的東方文化要素植入小說中,使澳大利亞讀者有機(jī)會(huì)體驗(yàn)和了解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guó)文化,也使中國(guó)讀者重溫自己的文化記憶,加強(qiáng)對(duì)自己身份的認(rèn)同感。而在重溫文化記憶的過程中,米勒以他超凡的能力將一些無形的印象和感覺轉(zhuǎn)化成了具體的描述。女主角之一的蓮在結(jié)婚后重游黃玉華位于杭州的住所時(shí)的描述就是極佳的一個(gè)佐證: “在她面前是又臟又窄的空地,四周是黑乎乎的污漬斑斑的磚墻,院子很像上海的廉價(jià)中式小吃店后的小巷,腐爛的白菜幫、草和鴨糞散落在院中。她快走四步來到了倉(cāng)房的入口處,倉(cāng)房里彌漫著家禽的糞便散發(fā)出的酸臭味。”[7]“記憶形象” 的運(yùn)用在這里達(dá)到了完美的境地,有曾經(jīng)生活在浙江的讀者對(duì)這一段的描述感到驚訝不已。這位在1937年并不曾生活在杭州的澳大利亞作家何以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杭州有如此精準(zhǔn)的描述呢?有關(guān)這一時(shí)期的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作者是如何捕捉的呢?在《中國(guó)印象》一文[8]中,米勒本人如是說: “并非歷史,而是印象保持了歷史的原貌。”這恐怕也是創(chuàng)作素材轉(zhuǎn)換為文化記憶色澤和文化想象在發(fā)揮作用的最好證明吧。讀者禁不住要為作者捕捉生活、再現(xiàn)生活的能力贊嘆不已。
二、“文化記憶” 賦予《祖先游戲》的時(shí)代意義
另一方面,從移民個(gè)人的外部經(jīng)歷向內(nèi)在情感描述邁進(jìn)的這一過程也表明了澳大利亞小說朝國(guó)際化寫作技巧邁進(jìn)的進(jìn)步。毋庸置疑,米勒在小說文化記憶情節(jié)的構(gòu)成上是勝人一籌的,他已經(jīng)以超出英國(guó)以外的亞洲國(guó)家,特別是以對(duì)中國(guó)文化記憶和想象的形式賦予了這部小說以現(xiàn)代的意義,即轉(zhuǎn)向亞洲而非歐洲和美國(guó)來探尋澳大利亞和其他國(guó)家之間在文化和經(jīng)濟(jì)上的聯(lián)系,這一手法也印證了在該部小說開始時(shí)Soren Kierkegaard所說的話: “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已喪失了有關(guān)家庭與種族的基本分類,使得每一個(gè)人都完全屬于自己,從某種嚴(yán)格意義上來講,個(gè)人成為自己的救世主。” 有關(guān)中國(guó)文化的記憶和想象不僅體現(xiàn)了作者有意要強(qiáng)調(diào)澳大利亞文化多元性的特點(diǎn),也道出了作為亞文化的中國(guó)文化在澳大利亞發(fā)展過程中所起的不可小視的作用,同時(shí)也刻意拉近了澳大利亞與亞洲國(guó)家間不可隔斷的關(guān)系。因此,在這一層面上,《祖先游戲》絕不僅僅是一本小說而已。正如一位澳大利亞作家Sophie Masson在她的評(píng)論中所寫的那樣: “這不是一本拿起來只要花幾個(gè)小時(shí)就可讀完的書;它也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它的內(nèi)容豐富,富于啟發(fā)力。有關(guān)中國(guó)和中國(guó)社會(huì)的一級(jí)片段使得這本小說很獨(dú)特和特別。小說充分運(yùn)用了幻象和奇特的感覺,讀者必須要進(jìn)行二次思考,要看兩遍,讀兩遍。”[9]
透過這部小說,讀者還可以目睹發(fā)生在澳大利亞的文化變化,這一變化絲毫不亞于他們的祖先在19世紀(jì)最后的10年里戰(zhàn)勝經(jīng)濟(jì)蕭條,設(shè)計(jì)并最后在1901年建立了聯(lián)邦國(guó)家給澳大利亞帶來的巨變。這一變化顯示出澳大利亞已充分認(rèn)識(shí)到了其遠(yuǎn)離母國(guó),距離亞洲國(guó)家較近的事實(shí)和重要意義。這本小說可以說掀起了有關(guān)亞洲敘述小說的第二次浪潮,先于米勒進(jìn)行創(chuàng)作的澳大利亞作家們,如:Koch,Grant,Drewe,Moffit等通常都是間接地通過人物尋找亞洲導(dǎo)師,來為讀者提供一種漸漸消退的因在越南戰(zhàn)爭(zhēng)中澳大利亞所扮演的角色而帶來的負(fù)罪感。米勒卻將視角聚焦在澳大利亞歷史上長(zhǎng)久存在的中國(guó)人身上,所以,很少有作品像米勒的這部小說一樣在思考澳大利亞一個(gè)半世紀(jì)以來如何與中國(guó)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米勒是在為存在于文化表層下面的亞文化在歡呼,這絕非易事。這也就是為什么有讀者說這是一部充滿希望的小說,它攪動(dòng)了深植于許多澳大利亞人內(nèi)心深處的東西。作為生活在當(dāng)代的澳大利亞作家,在思考有關(guān)自己國(guó)家的文化記憶時(shí),肯定會(huì)提出這一類問題,諸如:作為一個(gè)國(guó)家,它已走過了哪些路,或者它會(huì)有可能走向何方?有關(guān)鳳氏家族第一代的回憶始于19世紀(jì)中葉,這讓讀者自然就想起了當(dāng)時(shí)發(fā)生在澳大利亞的 “淘金熱” 以及在此過程中華人所遭遇的一切。
眾所周知,澳大利亞最初是英國(guó)政府在南半球建立的罪犯安置地,所以,英國(guó)文化的傳統(tǒng)和價(jià)值觀烙印被永久地刻在了這片土地上。然而,1851年隨著 “淘金熱” 浪潮而涌入的其他歐洲、亞洲、美洲的淘金者們打破了澳大利亞白人文化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從此,亞文化與帶有英國(guó)文化烙印的白人主流文化之間的沖突也就成為必然。小說中第一代鳳在廈門嗅到了有可能 “變成一個(gè)富人” 的希望的氣息后,義無反顧地背井離鄉(xiāng),踏上澳洲大陸。可是,他并沒有如愿以償成為一個(gè)富人,而只是成了一個(gè)牧羊人,白人文化的排他性使他根本無法融入到主流文化中。是金礦的發(fā)現(xiàn)為他帶來了轉(zhuǎn)機(jī),在他和好友帕特里克掩埋另一位被白人殺害的好友時(shí)無意間發(fā)現(xiàn)了金礦。雖然不久后他門發(fā)現(xiàn)的金礦被官方占有,但無意間發(fā)現(xiàn)的金子徹底改變了他的境況,他因此而建立起了 “維多利亞鳳凰合作社”。這段有關(guān)鳳的個(gè)人經(jīng)歷演示無疑很好地重現(xiàn)了澳大利亞歷史上的 “淘金熱” 以及白澳政策盛行時(shí)期的華人的苦難經(jīng)歷。也正是通過對(duì)個(gè)人經(jīng)歷進(jìn)行演示的交際記憶的方式,米勒達(dá)到了構(gòu)建澳大利亞民族文化記憶的目的。這與中國(guó)的澳大利亞文學(xué)研究專家的觀點(diǎn)不謀而合,黃源深教授在《從孤立中走向世界》一書中對(duì) “淘金熱” 在澳大利亞文化方面產(chǎn)生的作用做過如下描述: “當(dāng)時(shí)的土著文化已根本不可能構(gòu)成與歐洲(英國(guó))文化傳統(tǒng)相抗?fàn)幍木置妗H欢?隨淘金熱潮而到來的亞洲(中國(guó))文化卻變得日益強(qiáng)大起來……在一些淘金人集中的城鎮(zhèn),中國(guó)文化已成為一股強(qiáng)大的文化力量與英澳文化并存。”[6]34或許正是由于中國(guó)文化在澳大利亞歷史上的地位,決定了米勒在選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背景和身份時(shí)將視角的重點(diǎn)聚焦在了中國(guó)移民及其后代的身上。其實(shí),這也是還民族文化記憶以本來面目的一種做法。
但是,身為移民作家的米勒深知移民在澳大利亞經(jīng)歷的 “無根” 與 “異化” 的痛楚,作家將對(duì)這一心路歷程的敘述用小說文本的形式定格在鳳二維多利亞的身上,她形容自己在母親和姐姐中間始終是一個(gè)陌生人,憑借她本人的作家身份,她預(yù)見死亡是她唯一的歸宿。而有關(guān)大多數(shù)移民在澳大利亞經(jīng)歷的身份迷失則在鳳家第三代人身上凸顯出來。這是通過作者截取的第二個(gè)歷史階段來反應(yīng)的,抗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中國(guó)不僅在外部淪為眾多的帝國(guó)主義列強(qiáng)瓜分的對(duì)象,在思想意識(shí)上也受到重創(chuàng),一部分生活在國(guó)外的中國(guó)人放棄了對(duì)自我身份的認(rèn)同,轉(zhuǎn)而開始憎恨中國(guó)文化,更有甚者開始鄙視那些想保存它們的人,并將一切具有中國(guó)文化特征的東西拒之門外,以此來顯示他們對(duì)純正的國(guó)際主義的承諾。據(jù)此,在澳大利亞形成了一種 “錯(cuò)位的文化”。以鳳氏家族三代人對(duì)自身中國(guó)文化記憶的背叛來折射澳大利亞歷史上眾多移民的經(jīng)歷,也顯示出了米勒在充分利用史實(shí),高度概括地進(jìn)行藝術(shù)加工方面的非凡能力,她在積聚能量為小說的高潮部分做鋪墊。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形成了澳大利亞文化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因?yàn)樵谶@之后美國(gu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開始改變著澳大利亞人的思維,使得澳大利亞逐步走出先前的 “唯英獨(dú)尊” 和 “唯我獨(dú)尊” 的誤區(qū),迅速地成長(zhǎng)、堅(jiān)強(qiáng)、走向成熟[6]43-44。這個(gè)時(shí)期的澳大利亞文化處于相對(duì)較寬容的 “多元文化主義” 階段,隨著非英裔移民人數(shù)的大量增加,澳大利亞對(duì)亞洲人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改變。20世紀(jì)50年代,白澳政策已開始松動(dòng),到了70年代,澳政府正式提出了多元文化的概念:國(guó)內(nèi)各民族應(yīng)當(dāng)在平等的原則上保存自身的傳統(tǒng),并達(dá)到共榮共存,共同為澳大利亞的發(fā)展而努力[6]48。然而,外部政策的改變并不能迅速地改變各國(guó)移民的生存狀態(tài),米勒的小說文本對(duì)這段歷史的再現(xiàn)則是通過鳳氏第四代人——浪子來完成的。這個(gè)生存在中西方文化夾縫中的人物感到無所適從,他從小接受的是父親為他指定的西方教育,而母親又試圖將他拉回到中國(guó)文化一側(cè),結(jié)果致使錯(cuò)位感和異化感在他身上達(dá)到了極致,他先是燒毀了象征祖宗的家譜,后又把世代相傳的寶鏡在一個(gè)月黑風(fēng)高之夜扔進(jìn)了錢塘江,可這樣的舉動(dòng)都無法消除他的錯(cuò)位和異化感,于是,“放逐” 成了他 “不可逃避的任務(wù)” 和生存狀態(tài)。可逃離祖先文化疆域的短暫的解脫并沒有讓他真正釋然,隨之而來的 “無根” 的折磨更令他痛苦不堪,關(guān)于本民族的文化記憶不時(shí)地在他的身上顯現(xiàn),表面上無論他怎么排斥祖先的文化,可心靈上的歸屬感還會(huì)使她很難完全融入到新的國(guó)度,內(nèi)心深處的家園早已使他具有了拒絕被新的國(guó)度的信仰感染的免疫力,那些早已失去的祖先們無時(shí)無刻不在對(duì)活著的人 “施加著影響力”[10]127。米勒這里顯然是想借浪子對(duì)鳳氏家族祖先的文化記憶來昭示亞文化也應(yīng)被視為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主流文化享有同等的作用,所有進(jìn)入澳大利亞的文化都不應(yīng)被視作 “異類”,文化一經(jīng)移植,就該成為當(dāng)?shù)氐奈幕0拇罄麃單幕嘣缘谋举|(zhì)就是: “不管是蘇格蘭人,還是中國(guó)人,有某種東西是相同的。這種東西同樣存在于我們中國(guó)人和蘇格蘭人的心靈深處……不管我們?cè)趺磁?都無法把它抹去,而別人不管如何努力,都無法模仿。”[10]20-21因?yàn)?“‘歷史記憶’是一個(gè)民族經(jīng)過歲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個(gè)時(shí)代風(fēng)吹雨打后所保留的‘前理解’,是一個(gè)社會(huì)走向未來的反思的基點(diǎn)”[11]。
三、“文化記憶 ” 對(duì)小說主題的升華
米勒設(shè)想憑借文化記憶素材的積累,以小說文本中的文化記憶和想象來影射澳大利亞未來的效果至此達(dá)到了,而且是以酣暢淋漓的方式讓讀者體會(huì)到的。文本層面上主人公的個(gè)體記憶明顯有指向文本以外文化記憶的作用,作者在此要達(dá)到的目的,是通過講述個(gè)體的經(jīng)歷來啟發(fā)讀者思考與反思。人們不得不贊嘆米勒在運(yùn)用文化記憶方面的獨(dú)到之處,那就是他借助某種方法把作為文學(xué)現(xiàn)象的歷史變成了敘事,即歷史事件被作為敘述者的親身經(jīng)歷或體驗(yàn)過的故事講述了出來。結(jié)果就是無論來自哪個(gè)國(guó)家的移民讀者都會(huì)積極地介入作品中,在接受文本敘事的同時(shí)還完成了反觀自我的任務(wù),而作品也自然地實(shí)現(xiàn)了由個(gè)體記憶向文化記憶的轉(zhuǎn)化。文化以及想象在米勒的小說文本中不僅是他作品的主題,同時(shí)也是他展開敘事的緣由,通過最大限度地調(diào)動(dòng)文化記憶和想象的方式,米勒讓澳大利亞文化的特征得以具體化和形象化,也使文學(xué)在文化記憶和想象中的特殊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因?yàn)槊桌諏?duì)歷史事件的敘述和再現(xiàn)是有所選擇的,而不僅僅是歷史事件的簡(jiǎn)單翻版。米勒的小說文本清楚地告訴讀者,在多元文化雜交的時(shí)代,文化身份問題是不可回避的。無論一個(gè)居住在澳大利亞的人多么灑脫,就算他可以灑脫到像利奧塔所說的那樣,進(jìn)入當(dāng)代通俗文化的零度態(tài),他也還是無法擺脫自己的文化身份,因?yàn)樗南嗝病⒛w色等特征都是無法改變的。所以,在這個(gè)多元文化雜交的時(shí)代,選擇做文化上的 “無根” 的世界公民或選擇與本民族文化記憶認(rèn)同,只做它的代言人都是不足取的。全球化時(shí)代需要的是 “既具有本民族文化記憶的深刻底蘊(yùn),又具有健全開放心態(tài)和全球文化視野的世界公民”[12]。該部小說在這個(gè)層面上的深刻意蘊(yùn)是任何其它澳大利亞作品都無法媲美的。
米勒《祖先游戲》的重要作用不僅在于它幫助讀者厘清了澳大利亞歷史上中國(guó)與澳大利亞彼此間的關(guān)系,而且讓讀者透過文學(xué)敘事承載的文化記憶及想象變成了馳騁在澳大利亞文化疆域中的騎手,一路走來既領(lǐng)略了澳大利亞的自然風(fēng)貌,也在米勒的引領(lǐng)下穿梭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們的母國(guó)文化的疆域中,仔細(xì)品味各種不同文化的滋味,從而體味到了一個(gè)以多元文化為特征的國(guó)家和民族在一步步形成自己文化特色的過程中所走過的艱難歷程。筆者之所以認(rèn)為該部作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充滿希望的作品就是因?yàn)樽x者在解讀這部作品時(shí)會(huì)漸漸悟出:米勒竭力塑造一個(gè)亞洲家庭幾代人與澳大利亞有聯(lián)系的良苦用心在于他想告訴人們澳大利亞政府正在尋求與亞洲源遠(yuǎn)流長(zhǎng)的聯(lián)系,將鳳氏四代人這樣一個(gè)亞洲家庭生活在澳大利亞作為作品的敘述主線旨在頌揚(yáng)主流文化中的亞文化,作者以歷史的眼光和敘事方式冷靜地考察了中國(guó)與澳大利亞在歷史和人類史上長(zhǎng)期而復(fù)雜的交往,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清楚地告訴讀者澳大利亞正在日益變得成熟,她已勇于承認(rèn)自己在歷史上的過失。雖然澳大利亞人未必真的能改變對(duì)亞文化的態(tài)度,但這部作品在促進(jìn)文化認(rèn)同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因?yàn)?“它將永遠(yuǎn)改變我們對(duì)澳大利亞的看法”[13]。
[1]亞歷克斯·米勒,黃源深. 追尋記憶和想象的創(chuàng)作[J].譯文,2003(2):57-61.
[2]王霄冰. 文化記憶、傳統(tǒng)創(chuàng)新與節(jié)日遺產(chǎn)保護(hù)[J].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1):41-48.
[3]簡(jiǎn)·奧斯曼. 集體記憶與文化身份[J]. 陶東風(fēng),譯. 新德國(guó)批評(píng),1995(6):125-133.
[4]王霄冰. 文化記憶與文化傳承[J]. 勵(lì)耘學(xué)刊,2008(1):227-236.
[5]馮亞琳. 記憶的構(gòu)建與選擇——交際記憶與文化記憶張力場(chǎng)中的格拉斯小說[J]. 外國(guó)文學(xué),2008(1):84-90.
[6]黃源深,陳弘. 從孤立中走向世界[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7]吳慧. “無”與“靜”——以《被畫者》為中心透視亞歷克斯·米勒的小說藝術(shù)[J]. 名作欣賞,2009(8):72-75.
[8]Miller A. Chinese Impression[N].24 Hours Supplement,1995-06-25(第6版).
[9]Masson S. Comment on The Ancestor Game[J].Australian Book Review,1993(4):42-44.
[10]Miller A. The Ancestor Game[M].Sydney:George 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92.
[11]馮海燕. 文化戰(zhàn)火中的鳳凰涅槃——解讀澳大利亞作家米勒的小說《祖先游戲》[J].湛江海洋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4,24(2):91-96.
[12]張明德. 多元文化雜交時(shí)代的民族文化記憶問題[J].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2001(3):11-15.
[13]Rimer A. Exiles from the past[N].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992-08-15(第4版).
(編輯: 朱渭波)
TheAncestorGame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MemoryandImagination
Wu Hui
(DepartmentofForeignLanguages,ShanghaiCustomsCollege,Shanghai201204,China)
Today we will again b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about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ovelTheAncestorGameof Alex Miller for which he has won several awards. All are so vividly described and expressed by an Australian writer who has never been living so long in China. We cannot help asking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memories and imaginations in the text concerning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will try to decode the prize-winning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emory and imagination based on the German scholar Jan Assmann’s cultural memory theory so as to find out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embedded in it and the role played by it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Australian culture.
culturalmemory;culturalimagination;culturalidentity;sino-australianrelationship
2013-12-27
吳 慧(1964-),女,教授。研究方向澳大利亞文學(xué)、英美文學(xué)。E-mail: lisa_happy_hi@163.com
I 106.4
A
1009-895X(2014)04-0353-05
10.13256/j.cnki.jusst.sse.2014.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