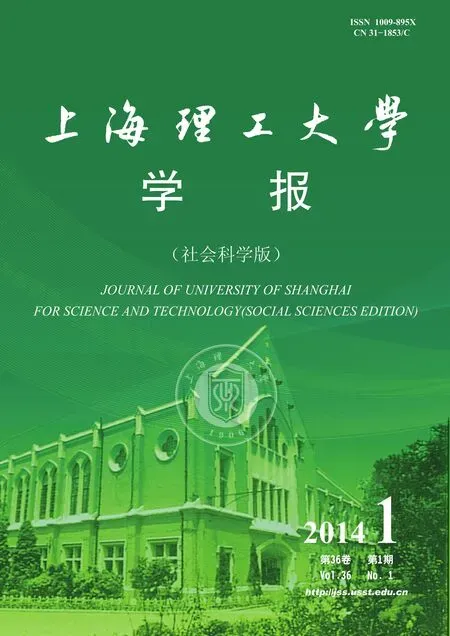蒂姆·溫頓《淺灘》中的生態思想
徐顯靜
(1.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上海200093;2.上海外國語大學研究生院,上海200083)
《淺灘》是一部旗幟鮮明的生態小說,發表后即獲澳大利亞最重要的文學獎“邁爾斯·弗蘭克林獎”。小說圍繞澳大利亞傳統產業捕鯨業的興衰展開,再現了白人在澳洲這塊古老又嶄新的大陸150多年的定居史。充滿了悲劇色彩的庫珀家族是這一歷史進程的見證者,世世代代都與鯨結下了不解之緣。來自美國的先祖納撒尼爾·庫珀是安吉勒斯捕鯨業的締造者之一,他用日志記錄下了這個過程。但是早年血腥的捕鯨活動給納撒尼爾造成了嚴重的精神創傷,這種創傷甚至波及了后代。與其祖先相反,庫珀家族的第五代繼承者昆尼·庫珀卻是鯨魚的守護天使,她身上寄托著作者的生態理想。通過《淺灘》蒂姆·溫頓想要傳遞的生態觀就是:無論是日志中所記錄的早在150年前納撒尼爾·庫珀對于殘忍的捕鯨活動表現出的質疑和彷徨,還是現實生活中安吉勒斯小鎮岌岌可危的捕鯨工業都明白無誤地表明:人類無權這樣踐踏自然,毫無節制地獵殺同樣具有生存權的海洋生物。遺憾的是,小說雖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但除了一些介紹性的書評略有提及外,在文學批評界卻鮮有人對文本中體現的作者的生態意識做深入分析。本文將利用西方生態文學批評理論,從分析庫珀家族四代人與捕鯨業的糾葛入手,通過對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對現代捕鯨工業的批判、對工業社會開發的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對澳洲土著生態智慧的借鑒四方面解讀《淺灘》中體現的溫頓的生態文學思想。
一、對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以人為宇宙中心的觀點,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是一切價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內在價值而只有工具價值[1]51。20世紀最著名的生態文學作家雷切爾·卡森認為,人類征服和統治自然的根源就是人類中心主義。她指出“猶太—基督教教義把人當做自然之中心的觀念統治了我們的思想”,于是“人類將自己視為地球上所有物質的主宰,認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專門為人類創造的”[2]171。
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控訴在文本中比比皆是。比如,丹尼爾·庫珀哀嘆: “因為那些居住者的罪過,野獸和飛禽都一掃而光。”[3]75人類為了自己的生存,使得地球上的無數飛禽走獸滅絕。生態學家的確認為消失的物種是對人類的一種警告,告誡人們在恐怖的情況出現之前,最好停止掠奪自然資源[4]81。又如,遵循自然法則也那么難[3]282。人類破壞自然法則,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災難。于是大自然就用自己的方式懲罰人類,澳大利亞在70年代末經歷了連年干旱。所以“由于人的可憐的自尊的緣故,光之父不讓雨落下來。自尊可以休矣。但是,自尊等待著,直到其他一切都凋謝了”[3]282,這才是人類的悲哀。此外,人類必須認識到“不采取行動也是一種罪孽”[3]96。面臨著諸多環境問題,每個人都“具有天賦的義務去醫治自然受到的創傷,并保護自然不再受到蹂躪,不再呈現死亡的跡象”。正如利奧波德指出的:保護生態整體,是每一個人的責任[2]199。
溫頓態度堅決地批判了把《圣經》作為人類荼毒生靈的理論依據行為。溫頓小說中常常刻意使用圣經訓示或直接引用圣經經文,使之在小說文本內產生一種預言式的共鳴,使人物達到一種崇高莊嚴的境界[5]476。但是在環境保護問題上,他對以基督教為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進行了批判。例如,前文所引丹尼爾的哀嘆實則語出《圣經·耶利米書》。又如,他引用了以賽亞的一段話:“到那日,耶和華必用他剛硬有力的大刀,刑罰鱷魚,就是那快行的蛇;……并殺海中的大魚。”接著作者痛斥:這些無知的家伙相信抹香鯨就是毒蛇,惡魔的代理[3]121。納撒尼爾·庫珀的日志中細致入微地記錄了人物內心的彷徨和掙扎,捕鯨經歷給納撒尼爾造成了心靈嚴重的創傷,使他對上帝產生了質疑,喪失了信念的他,不能給予和接受愛,眾叛親離,最終自殺。懷疑上帝,是因為《圣經·創世紀》里上帝賦予人至高無上的權利:人類是萬物之主,人類早就獲得了上帝的授權,人類可以對自然萬物隨意處置[2]172。通過納撒尼爾這一人物形象說明:在目睹人類為了自身的貪欲而荼毒生靈時,人們也會經歷信念消失,精神萎縮,甚至異化。此外文中多次提及《圣經》中約拿與鯨魚的典故,但《淺灘》提出的問題不是約拿被鯨魚吞下,而是人類吞噬鯨魚將會發生什么[6]221,其寓意耐人尋味。
《淺灘》還表達了溫頓樸素的生態倫理思想。生態倫理學是由法國哲學家史懷澤和英國環境學家利奧波德創立的,史懷澤從對生命的崇拜出發,進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的倫理學。利奧波德則提出了“大地倫理”概念[7]1185。他認為現在的倫理學研究要把道德權利擴展到動物、植物、土地、水域和其他自然界的實體,確認它們在一種自然狀態中持續存在的權利。即從人類中心主義的倫理過渡到生態中心主義的倫理[1]37。生態倫理學理念能有效打破人類中心的思維方式,把人類與生態系統中的其他部分看成大地共同體平等的成員。《淺灘》明確指出“要是我們能證明它們富有智慧,我們就可以保護它們了”是地地道道的“智慧怪論”、“倫理垃圾”,因為“一件東西不需要有智慧才能找到存在的理由”[3]152。正如小說中環保主義者馬克斯所言“鯨魚是地球上的居住者——它們需要保護,就這么回事,因為它們指定要在這兒,不需要論證合理性”[3]152。人類生存并且使其他生物也能夠生存在溫頓筆下是不言自明的事實,無須任何證明。
二、對血腥捕鯨工業的批判
捕鯨業是19世紀30年代羊毛成為主要產品前,澳大利亞的支柱產業。但是由于人類長期的恣意捕撈,更由于捕鯨手段的日益更新,二戰末,海洋的鯨魚資源就顯示出了枯竭的跡象,捕鯨站也陸續關閉,澳洲最后一個以陸地為基礎的捕鯨站就位于西澳阿爾巴尼 (Albany),也被迫于70年代關閉[4]79。所以,說“正是這些捕鯨工創造了這個國家”[3]40一點兒也不為過。
先祖納撒尼爾·庫珀早年在捕鯨船上工作,親歷了這項血腥產業的發跡:當時捕鯨設備落后,生活環境惡劣,人類在大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早期的捕鯨過程伴隨著病、死、瘋的痛苦,同時還有遺棄、冷漠、人性的喪失。他在日志中記錄下了在當時艱苦環境下人類異化的生活:捕鯨工酗酒、斗毆;把被打掉的左耳垂藏在水手柜里;發泄生存壓力,玩土著女人甚至奸后將其分尸;厭惡甚至雞奸同伴;在同伴死后就隨意丟棄或者吃了他們的肉……于是從事著血腥產業的人也變得面目猙獰起來。人們做著殘忍的工作,精神也處于崩潰邊緣。正如阿爾·戈爾所斷言:環境危機就是精神危機。捕鯨工的殘忍使人退化成野蠻人,禽獸不如。
捕鯨的罪惡甚至波及后代。在缺少父愛家庭里長大的馬丁·庫珀是個神經質,他無能卻又自尊,開槍自殺后給妻子和兒子留下一屁股債務,還使他們丟了土地[3]87。馬丁的兒子丹尼爾也受家族的影響喪失了愛與被愛的能力,致使妻子一生孤獨,在剛剛品嘗到丈夫的愛時卻意外身亡。妻子的身亡,使丹尼爾猛然覺醒,追悔莫及,于是,晚年的他一直在孤獨地探求罪過與救贖之道。
現代的安吉勒斯 (以阿爾巴尼為原型)正是1978年澳大利亞社會的縮影:經歷著氣象的 (暗示精神上的)干旱,面臨著資源枯竭及外界要求停止捕鯨的內外壓力,最后一批捕鯨從業者在做著最后的抗爭,拼命想要留住這種行將消失的生活方式[4]79。因為對于當時的小鎮人來說,沒有了捕鯨業,人們將面臨著失業,生活方式將面臨重大轉變。環保主義者所面臨的壓力和抵制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溫頓并沒有放棄努力。為了喚醒人們的同情心和環保意識,他不動聲色地把捕鯨工業血淋淋的場面描述給讀者看:雌鯨為了保護幼鯨,暴露自己,慘遭殺戮[3]160;小鯨從母體破腹而出;群鯨大批涌向海灘集體自殺……場面悲壯至極、令人為之動容。由此,溫頓對捕鯨業的批判是血淋淋的。
昆尼·庫珀是批判現代捕鯨工業及作者環保理念的踐行者。她清楚地意識到“已經等不及自上而下來改變一切了。鯨們已經奄奄一息,正被滅絕”[3]63。商業捕鯨破壞了自然美和詩意生存,捕鯨業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海洋里最大動物鯨的滅絕,繼而導致一場生態災難。為了參加國際環保組織的護鯨行動,昆尼甚至不惜與著迷于這一傳統產業的丈夫克里夫鬧翻。克里夫喜歡閱讀《白鯨》,“驚嘆鯨魚龐大的身軀,羨慕那些捕獲并肢解鯨魚的人”[3]36,這些顯然是主張護鯨的昆尼無法茍同的。但是在與妻子分居期間克里夫仔細閱讀了納撒尼爾記下的日志,這深深教育和感化了他。讀懂了庫珀家人,也逐漸理解了妻子的護鯨舉動,最后他把“魚槍丟到街上的垃圾桶里”[3]267,加入了保護鯨的行列。除了丈夫的不理解,小鎮的人也敵視昆尼。在她第一次參加環保者抗議活動時,那個“曾經開過她們校車的可愛家伙在罵她”[3]38,甚至到后來,昆尼聽見了槍聲。昆尼雖然在小鎮人眼中是異端,但她畢竟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面臨著“做地球的朋友,你就不得不做人類的敵人”[2]124的痛苦抉擇,她選擇了向前而不是退縮。面對早已深刻異化的人與自然的關系,一個人的抗爭力量雖然有限,但環保運動需要這種不懈努力,更需要《淺灘》這樣的生態文學作品來喚醒早已麻木的人類。
三、對社會開發的工具理性批判
小說中的人物德斯·普斯特林是個房地產商,在他身上充分體現著西方現代社會的一些理念,如開發、競爭等。他野心勃勃,想趁佩爾牧師退休后,把教會用作某種經濟上的掩飾和騙稅的手段,然后去買地、開發;他還打算以小鎮150周年慶祝活動為契機,發展旅游、餐飲等所謂讓小鎮活起來的產業等。他的目的就是賺錢,他的行為試圖抹掉小鎮與大海的古老的、確定的聯系。意味深長的是,他是不能生育的[4]79。溫頓批判了這種以犧牲其他物種利益為代價的社會經濟開發,而普斯特林的不育則暗示著無論產生多少經濟利益,這種發展模式終將是無果的,因而也是不能持續的。
拖拉機、推土機以及卡車等意象出現在溫頓的多部作品中,具有深刻含義。它們代表著工具理性,彰顯著技術改造世界的霸權。隨著工具理性的極大膨脹,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以至于出現了工具理性霸權,從而使得工具理性變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8]88。推土機等是現代技術的產物,它們是經濟開發的先鋒部隊,把自然的原生態,人與自然和諧的生存狀態一手毀掉。出現在海灘上的推土機意象更加耐人尋味:當人類開發的觸角已經伸到了陸地邊緣——海灘,這就意味著這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最后生態烏托邦家園也行將被吞噬,社會經濟開發對傳統生活方式的侵蝕和擠占也就發展到了極限。
此外,小說第一章有個細節值得關注:她 (昆尼)不允許在水下使用武器[3]4。隨著技術進步,正是使用武器 (大炮)捕鯨,進行商業捕鯨,才造成了鯨的瀕臨滅絕。工具理性借助科技的力量,人們改造或是更確切地說是破壞自然的速度顯著加快了,全世界范圍內,工業和科技文明對自然的征服和破壞,在20世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生態文學作品有責任和義務“向工業化和科學技術發出強烈的質疑和激烈的批判”[2]177。《淺灘》向讀者揭示了工具理性霸權向人類詩意棲居的烏托邦家園蠶食鯨吞、步步滲透的過程,期間人類逐漸變成面目猙獰的征服者,自然則變成了所謂的資源,因此這一過程同時伴隨著人的異化和自然的物化。但是,作者并未放棄希望,因為有昆尼這樣寄托著作者生態烏托邦理想的人物在:兒時的昆尼天真爛漫,會同海豚說話,能在海貝里聽到上帝的聲音;成年的她雖然被安吉勒斯小鎮的人們視為怪人、異端,但是由于童年起便與鯨魚相伴嬉戲的個人經歷,昆尼終于成長為一位勇敢的環保衛士。正如《淺灘》中環境保護者弗勒爾所說:“我們的未來在于物種之間的交流,在于與環境共存。”溫頓希望人與自然可以進行交流,和諧共生。
值得一提的是,《淺灘》的續篇短篇小說《游泳》繼續著這種對社會開發的工具理性批判。當昆尼一行回到外祖父的農場時 (現在歸普斯特林所有),看到的是普斯特林開發理念造成的惡果:土地被過度放牧,變得溝壑縱橫;農場大門口赫然掛著一個告示牌—— “禁止穿越,射殺袋鼠中,請勿靠近”。昆尼兒時的天堂現在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雖然捕鯨業終于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社會開發的腳步并未停歇,在“城市海灘”上,有錢人正在為美國游客修建濱海旅館。克里夫說:“他們在撕碎我青春的源泉。”他們六歲的女兒點點說:“他們把一切弄得亂七八糟。”[9]76旅游開發正以不可逆轉之勢繼續著,生態保護的任務任重而道遠。
工具理性也助長了人類的征服欲望。在圍繞著捕鯨—護鯨這一主線,作者還別出心裁地穿插了特德·貝爾捕鯊的輔線。特德·貝爾試圖要在安吉勒斯捕到世界上最大的鯊魚,要破1 900磅的紀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最終捕到了一條2 700磅的大白鯊。然而,貝爾的成功并非偶然。表面上,人類又一次征服了海洋里最兇猛的生物鯊魚,滿足了人類無限膨脹的征服欲望。但是,之所以引來巨鯊,是因為安吉勒斯擁有捕鯨產業,是捕鯨活動的血腥引來了大批的鯊魚前來光顧。設計特德·貝爾捕鯊的次要情節,不僅彰顯了溫頓對人類征服欲望的批判,而且強化了生態保護主題。特德·貝爾破世界紀錄的捕鯊活動正值小鎮成立150周年的紀念活動,人們復制早年的捕鯨船“奧農”號,進行旅游促銷,歡迎女皇來訪,在沸騰的慶祝活動中,讀者分明聽到了喪鐘在鳴,為鯨,為鯊魚,更為執迷不悟的人類自身。因為在一派歌舞升平的鬧劇的背后,是人們深陷危機而不自知的愚蠢。人類的征服欲望永無滿足之時,這樣的欲望在現代危機四伏的生態環境中顯得荒謬。在現代化武器協助下,人類似乎愈加強大,但作為自然界的一種生物其面目卻愈發猙獰,人類欲望膨脹導致瘋狂地掠奪自然,導致扼殺人的靈魂和美好天性,人類再也沒有閑情逸致享受詩意的棲居。
四、對土著生態智慧的借鑒
溫頓充分意識到土著文化的價值和重要性,并在多部小說中融入了土著元素。如在《云街》中,有位神秘的土著人物時常出現,給彷徨中的費希指點迷津。又如,在《土樂》中他更是讓主人公魯按照土著人的方式,在“地圖外”而不是在“地圖上”行走,即摒棄對現代文明的產物——地圖的依賴,僅靠一支低音風笛、一根釣魚線過簡樸的荒野生活。歷經生存考驗及自然的錘煉,魯受傷的心靈逐漸康復了[10]313-314。
當被問及比起西方文化來他是否與土著文化更接近時,溫頓回答:“我應該說比起我的蘇格蘭祖先來,我離土著文化更近,我已經學會離這塊土地更近,但這幾乎不能與真正的土著意義上的歸屬相比。我羨慕土著人與大地及部落神靈的同一性。”[11]107景觀在溫頓的小說中的重要性不亞于其中的人物,因此溫頓也被稱為“景觀作家”。在他的小說中反復表達了文學與景觀間的緊密關系,景觀被賦予了他個人的特質。他對空間景觀的探討方式常常使人想起澳洲土著文化,特別是土著人有關人屬于地球的理念[11]101。
對土著人來說,不是土地屬于你,而是你屬于土地。土地不是你的家園,它是你的偶像,你的圣地,你的臍帶之地。與土地分離就意味著被置于地獄的邊緣,卡在生死之間[12]21。溫頓吸收了這種價值觀,《淺灘》中昆尼能在海洋中自由地游泳,連他的丈夫克里夫都不禁覺得她“不該生為陸地哺乳動物”[3]4,她六歲的女兒也是在學會說話之前就會游泳了[9]76,因此你不得不產生她們是屬于海洋的想法,而不是相反。而昆尼對安吉勒斯故土的眷戀更是刻骨銘心。環保活動失敗后,昆尼作為一個失敗者、甚至棄兒,帶著深深的遺憾被迫離開自己深愛的家鄉。在《游泳》中:闊別七年后,昆尼和丈夫回到了安吉勒斯小鎮,并且帶了女兒點點來朝拜自己的圣地,來延續這種與故土的難以割舍的臍帶關系。因為只有這樣,昆尼才能繼續正常地生活。
澳洲土著文化的基礎信仰是泛靈論。泛靈論的文化信仰有兩個明顯特征,一是相信現象世界是活生生的世界;二是相信非人類世界不僅是活生生的,而且到處是能夠與人交流的言說主體。在泛靈論的社會中,道德關懷涵蓋的不只是上帝、天使、圣人以及其他人,也涵蓋其他存在物,一切存在物都有神性。這與利奧波德提出的“大地倫理”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借鑒土著生態智慧是因為泛靈論社會幾乎毫無例外地避免了環境災難[1]61-62。溫頓對白人恣意開發澳洲西海岸的行為深感不安,如《游泳》中所述,他無法容忍看到沙岸上的起重機、鋼鐵架子、建筑工人和地上可怕的傷口[9]76。溫頓把這種對工具理性開發的質疑與自然的敬畏融入字里行間,在溫頓看來,海灘的破壞仿佛是在自己的軀體上開挖出大洞,令人感到切膚之痛。而這正契合了土著文化的生態思想:土著人認為總是對土地做著什么將會導致恐怖的后果,而這正是白人來到后一直在做的事情[12]21。
西方生態批評學者認為,從根本上說,當今世界面臨的生態危機反映的正是西方文化的危機,西方文化要實現自救,就必須放棄殖民心態,虛心向其他邊緣化、受壓制的文化學習生態智慧,反省自己的進攻性、侵略性行為[1]297。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澳洲興起了一股土著文化熱,白人主流文化對土著文化的態度開始改變,許多有識之士開始認真研究土著文化,解讀其古老而深刻的智慧,而作者生活的西澳又恰巧是土著文化研究與保護做得較好的地方,土著文化對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土著文化里萬物有靈,人類要負責照看好本部落的土地及萬物。在土著部落的交際網絡里,人類與自然親密無間,充分了解與其共生的萬物,能與之進行交流[13]300。于是《淺灘》中兒時的昆尼可以與海豚說話,《云街》中豬開口說話了。溫頓小說中的人物大多不善言辭,但卻能與大自然進行無障礙溝通。可見,交流未必要通過人類語言這個單一渠道進行,人類不應因為擁有語言能力就在“偉大的生命之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凌駕于其他生物之上。因此,工業社會的人類的確能從土著文化那里獲得靈感,從而做到對自然界的互聯、互惠交往模式做出反應,滋養自己的生命,也滋養萬物的生命[13]300。溫頓借鑒土著文化中充滿生態關懷的價值觀念,希望勸說人類放棄把自然及其他存在物當成沉默的他者的做法,自然的主體性是土著人和西方人可共同參與的建設性對話領域[14]57。面對眾聲喧嘩的自然界,人們應該心生敬畏與尊重,從而找到拯救之路。
五、結束語
雷切爾·卡森在《寂靜的春天》中控訴了DDT等化學農藥在大地上甚至天空中的荼毒生靈,進而指出是人類一手毀掉了有聲有色的春天,使一切歸于死寂。溫頓在《淺灘》中則控訴了人類將海中的鯨魚獵殺殆盡的罪行,暗示出如果不采取措施人類又將一手制造出另一個生態悲劇——寂靜的海洋。為了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作者在文本中不惜筆墨再現了工業捕鯨、解剖巨鯨的血腥場面以及群鯨集體自殺的悲壯場面,令人不得不去思考該怎樣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這一重大命題。在《淺灘》中溫頓通過對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對現代捕鯨工業的批判、對社會開發的工具理性批判表達了他反對人類以任何理由為借口大肆捕鯨,致使淺灘真正的主人座頭鯨、露脊鯨、鯊魚等大型海洋生物瀕臨滅絕的環保理念。最后,通過借鑒澳洲土著文化中充滿生態關懷的價值理念,溫頓表達了自己的生態倫理思想,希望啟迪深陷生態危機的人類找到拯救之路。總之,這部發表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以環保為主題的小說為安吉勒斯小鎮完成從捕鯨業向觀鯨旅游業的華麗轉身吹響了號角。各物種間平等交流,和諧共生,是溫頓本人,也是全世界具有生態意識人士共同的生態理想。
[1]胡志紅.西方生態批評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2]王諾.歐美生態文學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蒂姆·溫頓.淺灘 [M].黃源深,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4]Turner J P.Tim winton’s shallows and the end of whaling in australia [J].Westerly,1993(1):79-85.
[5]黃源深.澳大利亞文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476.
[6]Willbanks R.Shallows[J].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5,69(1):221.
[7]任重.全球化視閾下的生態倫理學研究述論 [J].生態環境學報,2012,21(6):1184-1188.
[8]汪民安.文化研究關鍵詞[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88.
[9]Winton T.Mininum ofTwo[M]. Camberwell:Penguin Books Australia Ltd,1998:76.
[10]Jacobs L.Tim Winton and West Australian Writing [M]∥Nicholas B,Rebecca M.A Companion to Aus lit since 1900.New York:Camden House,2007:307 -320.
[11]Ben-Messahe S.Mind the Country—Winton’s Fiction[M].Crawley:University ofWestern Australia Press,2006.
[12]Butstone D.Spinning stories and visions [J].Sojourners,1992,21(8):21.
[13]Rose D.An indigenous philosophical ecology:situating the human [J].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2005,16(3):294 -305.
[14]Prigogine I.The End of Certainty:Time,Chaos,and the New Laws of Nature[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