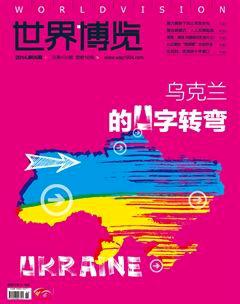維也納模式:人人買得起房
龔志偉

導語:維也納模式最重要的一個要素,既不是它的建筑理念和工程質量,甚至和郊區規劃也沒多大關系,而是其對社會結構、人民、社會趨勢、增強社區凝聚力的注重。
20世紀的維也納一度陷入住房匱乏的窘境,各種民生困厄應運而生,針對這一社會難題,奧地利政府所標榜的社會主義開出了藥方,他們推出了稍后聞名于世的“維也納社會所有制住房模式”。
維也納民居工程尊奉現代柯布西耶建筑學派的理念,在“敞亮、透氣、溫暖”的地區建造住房,從而把一直以來蜷縮在工業化角落里的那些“促狹、陰冷、昏暗”的貧民窟掃入歷史。當時所建的大多數新型居民區都坐落于老城區之外。維也納模式基本延續至今,影響深遠:今日約60%的維也納市居民都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屋里,至于房地產市場則由市政府操控。感謝過硬的建筑設計,數十年來樓房越造越多,“社會所有制住房”的聲譽卻歷久彌新。
美國的失敗
美國都市的情況與維也納迥異。在諸如圣路易斯、芝加哥、巴爾的摩等城市里,同樣坐落于“敞亮、透氣、溫暖”區域的大型公屋街區比維也納遲來了三十多年,彼時正逢二戰結束后退伍軍人的歸國潮,為滿足大量回流的人口,這一新事物應運而生。當年的巴爾的摩為了建造公屋社區,曾成片成片地拆除居民區——所謂的“貧民窟”、“刁民窩”,隨之而來的還有高速公路,野心勃勃的筑路計劃把更多的附近民居夷為平地。
這些厚樓板、高樓身的現代獨棟樓房在推出伊始一度飲譽建筑界,但不久之后人們便發現問題多多。緊挨著巴爾的摩市中心東西兩端的公屋綜合社區在交付使用后不久,環境便漸漸惡化,人們覺得它們的存在阻礙了周邊商業區的發展。于是,一些房齡不滿50年的樓房在一片爭議聲中被爆破拆除,不僅巴爾的摩城,全美各地都可見到這幅畫面。
有鑒于此,商業區的店家物業、房產律師、低收入的房客、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這些在尋常生活中幾乎沒有交集的人群凝聚在一塊兒,強烈支持拆除戰后建造的公屋,這批人成為推倒公屋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甚至謀得了巴爾的摩市住房署開具的允許決議,拆除該市的“貧民集中營”。一時間各種主張聚合在一起,醞釀出新的居住概念。于是聯邦政府引入金額龐大的扶持基金,舊樓房被夷平,一座座包容各收入階層的社區在原地拔地而起。
那么,為什么公屋在奧地利和美國兩國會有如此天差地別的遭際呢?
在美國,種族之間的矛盾、歧視、隔離,黑人為爭取公民權利掀起的斗爭,以及徹底的郊區化,諸相此起彼伏,而類似因素在絕大部分的歐洲地區幾乎難覓蹤跡。美國曾發生過非常嚴重的“白人逃離市區”現象,其后不久,各族群、各文化背景的中產階級也紛紛逃離市區,但維也納和大多數奧地利城市并不曾出現過這種情況,所以窮人扎堆市區的狀況并不顯著,反倒是郊區住著大批窮人。大規模的住房計劃打造出了歐洲的窮人聚居模式,比如柏林的馬克森徹-威爾特小區。可見,美、歐的保障性住房分別集中在市區和郊區。
在法國的“班魯危機”中,全世界坐在電視機前的看客們目睹了法國周邊幾個小鎮上示威游行者燃放的焰火,警民之間的激烈沖突,也由此見識了歐洲的郊區。對照1968年發生在美國各地的騷亂,各幅畫面都頗為相似,但不同之處在于,美國城市的騷亂(巴爾的摩就是其中一例)大多發生在市中心的居民區。
維也納的完整措施讓一切變為可能
有人把住房政策在奧、美兩國的差異歸因于歐洲實行“社會主義”,而美國奉行“資本主義”,但若細觀兩者,很快就會察覺如此解釋未免失之簡單。淺薄的思維定勢是惑于名實的結果,實則歐美的真實情況恰恰相反:美國的居民區由地方政府、即市政府住房機構主導建造;歐洲絕大部分“社會所有制住房”則被政府移交給具有非盈利性質的房企和施工單位,最近幾十年,幾乎所有歐洲的“社會所有制”住房都由這些企業設計、建造并維護。
不僅如此,當前歐洲大多數城市都拋售了政府所持有的公屋產權,像維也納依然保有20萬套市屬產權公寓的做法在歐洲城市中已十分鮮見。私有化戰略的浪潮席卷了歐洲的各個角落,包括住房。同樣狂飆突進的,還有政府權力下放的潮流。現在,德國政府就把維護國內全部住房保障的職責下交給各個州去管,轉而給予個人住房補貼。在大西洋的彼岸,美國政府所采取政策始終是狠抓房屋產權,目前全美擁有房產的比例相較奧地利高出10個百分點。不過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裂,或許居高的個人住房擁有率已經觸到了天花板。
歐洲的住房政策不僅國與國之間各不相同,即州與州、省與省之間也存在區別。與美國政府推出“住房保障與郊區新城”(縮寫為HUD)政策相似,歐洲的住房改革從課稅減免到收入擔保,一攬子方案極其復雜,非細致研究不能預測其發展趨勢,本文自然無法深入展開。不過有一點顯而易見:美國與歐洲兩大模式正逐漸呈現出合流的趨勢,即減少政府的直接干預,縮減貨幣補貼的投放量,轉而刺激私營企業的介入。
維也納模式最重要的一個要素,同時也是世人討論最多的一點,既不是它的建筑理念和工程質量,甚至和郊區規劃也沒多大關系,而是其對社會結構、人民、社會趨勢、增強社區凝聚力的注重。維也納模式在住房和藝術、繼承與創新、市中心和郊區新城、公共空間和環境氣候、公民參與和社會融合等方面給予我們思考和啟發。
一座可持續發展、運作自如的城市提供了住房以及全部配套服務,維也納市政府的一整套政策措施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它依然是全世界的樣板。維也納市住房署推出了價格親民、用料環保、設計精致的住房,目標居民不分收入階層,也不分年齡段。事實上,維也納每年用以修繕和建造“社會所有制住房”的財政預算高達幾億美元,相比之下,許多規模遠比維市龐大的美國城市在該領域的投入卻望塵莫及,不知相關部門負責人是否感到愧赧?資金投入尚遠不是全部。維也納市住房署設有一個下屬單位——住房研究所,該所專門收集各種案例和數據,研究如何指導城市跟上時代的腳步,行走在國際變革的前沿。
住房作為保障人類尊嚴和生活質量最根本的先決條件,從來就是對各國政府的公共管理政策的一個考驗。無論政治立場的左右,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單靠一個“自由”的市場永遠不可能滿足全社會的住房需求,合適的公共政策不可或缺。所以,不管客觀上存在多大差異,維也納模式依然不失為值得學習的榜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