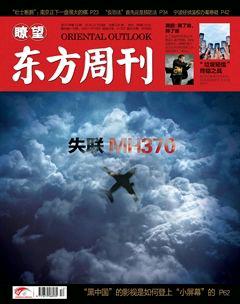推動我改變命運的人
時而,時光會把我帶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當時我在讀高中,坐在教室里,那是一堂化學課。
我讀高中,是1977年到1979年,“文革”剛剛結束,那是一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時代。當時學校一共八個班,只有一個文科班,叫文科二班。我的數理化底子很差,卻被分到一個理科班。因為自知考學無望,我就在學校挨日子,想把高中兩年混過去算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半不知不覺過去了。其間,除了跟同學一起玩耍,大多會找來一些課外書讀,古詩、小說,及各種雜書,也抄抄字典,還寫寫詩和小說,心里暗藏著一個文學的夢。這些,算是給我的高中生活些許安慰。
被捉
在這天的化學課上,像往常一樣,老師在臺上講,我在下面讀一本與化學無關的書。書叫什么名字,早已不記得了,仿佛是從村子里老學究那里借來的一本古書,也只記得那書厚厚的,老家的話叫“大本頭”。
我正讀著的時候,書被人一把奪去了。我腦子里閃了一句“完了”,立刻抬頭,是化學老師,正威嚴矗立在我面前。教室內一片寂然,所有的同學都轉過頭來,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化學老師姓齊,叫齊平遠,是學校的教導主任。齊老師長相很兇,眼睛本來就大,瞪起來更大,牙齒有些外凸,說話大嗓門,不留情面。平常,像我這樣不起眼的學生,哪怕沒犯什么錯,見到他都懼三分,盡量躲開。而現在,我在他的化學課上竟然在讀一本“閑書”,那證據正抓在他手里呢。
同學們在等著看一場好戲,我不知所措。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齊老師并沒有把書砸在我頭上,或者當場撕掉,或者沒收而去,而是,拿著那本書,隨意翻著,說了一聲:“你……倒讀起大本頭嘛,啊?”
班上有幾聲稀落的笑,應和著齊老師的話。誰都聽得出來,齊老師是在嘲笑我。但不知怎的,我竟從齊老師的話里聽出幾分驚異和欣賞的意味,并且,仿佛受到他的鼓勵,我內心蹦出一句話來:“齊老師,本來……我是可以學好文科的……”
本來,齊老師已經把書“甩”回到我的課桌上,算是對我例外客氣了。聽到我說這話,正轉身走回講臺的齊老師停了一下,回頭看了我一眼,用很高的嗓門:“是嗎?”
每個同學都聽到了齊老師的那聲“是嗎?”附和的笑聲也多了一些,仿佛是火上澆油。按說,在這個時候,我該羞愧難當,噤聲不語便罷了。但問題在于,我以為齊老師是認真的,雖然語氣聽似嘲諷,他的那聲“是嗎”可能真的是詢問,看我說的話是不是當真。
于是,又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大聲說出下面的話:“是的,齊老師,如果我能讀文科班的話,我一定會考上大學……”
說出這話的時候,我內心有惶惑,也有堅定,只是我也不知道是從哪里來的勇氣讓我這樣說,反正是“豁出去了”。
還沒等齊老師有所反應,同學們全都笑起來了。在我們這個班,沒有人敢想考大學的事。在笑聲中,齊老師也不再理我,只是返回講臺,繼續講課。這堂化學課剩下的時光,我不知道是怎樣度過的,聽不進課,也沒敢再看那“大本頭”,更不敢抬頭看齊老師一眼。
轉折
這堂課后,我的生活又恢復到從前的樣子。記不清是在多長時間之后,學校教務處來了一個通知:王學富從理科四班調到文科二班。
半年之后,我參加了高考,文科總分全校最高。
后來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齊老師,他正騎著自行車。我畢恭畢敬向他打招呼,期待他停下來,我好跟他說幾句感謝的話,但他像一個普通的老師遇到一個普通的學生一樣,嘴里應答了一聲,繼續騎車向前去了。我站在那里,目送他遠去,心里想說的話,也沒有說出來。
事情從發生到現在,30多年過去了。這是一堂普通的化學課,與化學無關,卻與我的人生關系重大。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只顧沿著鋪好的一條路向前跑,都沒來得及去品嘗其中的意味,但現在想起這件事,我對人生就有了許多的感慨和感恩。
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遭遇一些關鍵的時刻和一些關鍵的人物,仿佛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有些關鍵的事情發生了,影響甚至決定我們后來生活的走向。高中那堂化學課,便是我早年生活的關鍵時刻,在這堂課上,我遇到一位對我人生抉擇產生重大作用的關鍵人物—齊平遠老師。雖然,打那以后,我沒有再見到他,但他對我的影響卻持續存在。我跟人講這個故事,甚至不知不覺在讓自己活出這個故事。有許多人問我:為什么選擇從事心理咨詢?對這個問題,我一直無法提供完全的答案,因為這背后的動因很多,很復雜。包括,當我講到齊老師的故事,我會想到,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經歷惶惑,雖然他內心有成長的渴望,現實中卻有許多的阻礙,這阻礙包括環境的,心理的,知識的,經驗的……他并不明白,也不確定,因而不能作出選擇,甚至,他內心里本來有夢想,卻不敢講出自己的夢想。這時,他需要有人幫助他跨過這個關口。在我人生處于惶惑的關口,有像齊老師這樣的人推了我一把,我便跨過來了。現在,我選擇心理咨詢,是在做跟齊老師同樣的事情:在人需要幫助的關口,我前去“推”他一把,讓他跨過去。
意味
齊老師的故事,我給許多人講過。許多人都問:齊老師后來怎樣?我卻不知道。三十多年過去了,甚至齊老師是否還活在這個世界上,我都不知道。
去見一見齊老師,是多年來我內心里的一個念頭,每講一次齊老師的故事,內心里的這個念頭就變得越強烈。于是,通過高中時期的同學,我打聽到了齊老師的消息。
在棗陽城西的一個有點狹促的民宅里,我終于見到了齊老師。我驚訝地發現:原來齊老師個頭并不高大,是一個有些瘦小的老先生。開口說話,嘴里只有稀落的幾顆牙,但言語與神態,都透露出一種溫厚與體諒,顯得如此和藹可親。
想起高中時的齊老師,我想到一句詩:
小時候,家具又高大,又莊嚴;
見到后來的齊老師,我想到下一句詩:
長大了,家具又矮小,又破舊。
在這兩句詩里,我讀出豐富的情感的意味。過去,我常用這詩來比喻父母與孩子的關系。在我們幼小的時候,父母顯得高大而莊嚴;當父母年老的時候,我們再來看,卻是矮小而破舊的父母。這是人生的兩個境界。但是,當我們心靈真正長大了,我們就進入到第三個境界。這時,我用心靈的眼睛去看齊老師,內心里涌出第三句詩:
真正長大了,家具依然高大,依然莊嚴。
那天,齊老師講起自己的人生經歷。
在他讀高中的時候,整個棗陽只有幾十個高中生。后來“文革”發生了,他失掉讀大學的機會。后來,雖然成績卓然,又因為家窮而選擇讀師范,成了一位教師。他不止是一個好的化學老師,也是一個給人帶來生命影響的好老師。
我為什么要從中文系講師轉行到心理學領域呢?也許從這個故事中能找到答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