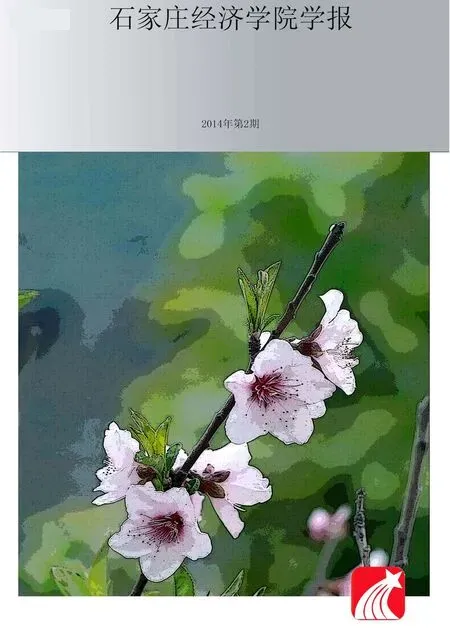新形勢下中國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重構探討
彭清華,羅瑩燕
(福建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新形勢下中國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重構探討
彭清華,羅瑩燕
(福建師范大學 經濟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在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沖擊下,由于土地要素的產權界定不清、產權交易受限,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重構必要性日益強化。文章提出當前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根本點、立足點及長遠點,以更好地明晰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定向。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產權重構;新形勢
一、引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這詮釋了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業、農民及農村的發展重要性。而土地是農業生產、農民致富及農村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層次將制約“三農”問題的有效破解。全會提出了“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等內容,這些闡述突顯了當前農村土地要素產權重構改革與完善的迫切性。
自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演變經歷了三次重大的變革:一是1950年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二是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農村土地制度由農民個體所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三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確立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1]。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但隨著改革的不斷全面、深入,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存在的問題日益顯現,制約著“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目前圍繞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走向,理論界進行了廣泛探討,大致可以歸納為三種觀點:一是倡導農村土地私有化,實現農民對土地的“完全產權”,代表學者有陳志武、許成鋼、茅于軾等人;二是黨國英、張德元等學者主張農村土地國有化,消除土地制度的城鄉二元性,強化國家對土地宏觀調控力度;三是部分學者認為在現行農村土地制度加以完善,不倡導私有化或國有化改革,如秦暉。
鑒于此,農村土地制度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改革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但對其改革走向仍存在較大的分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求其生活方式、職業選擇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從農到非農的轉變。面對新的研究背景,文章分析當前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必要性,探討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重構問題,以此明晰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走向。
二、新形勢下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必要性分析
隨著改革的不斷全面、深入,我國的改革事業步入“深水區”,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與艱難性愈加突出。周其仁認為“包產到戶提高的生產效率,因缺乏全面的深層構造改革,正在遭到交易費用急劇上升的抵消”。[2]對于當前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理論界的論據可歸結為:一是農地規模化經營的發展需要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約束下農地分配“福利化”形成矛盾,不利于農業生產的效率提高(周文,2006);二是土地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致使農民對土地生產進行“有限投入”(楊小凱,2002;林毅夫,2005;文貫中,2000)[3]。姚洋(1998)認為地權的不穩定性和對土地交易權的限制將限制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減少農戶對土地的長期投入[4];三是對政府的土地管理的規范需要。楊小凱(2002)認為土地私有化將使對土地管理納入到法制化軌道[5]。當前的土地制度產權構造為基層政府、村級組織向農民征收費用提供了合法性(劉守英,1999)[6];四是維護農民權益與促進農民致富的發展目的。黨國英(2003)認為農民在土地使用權流轉當中的主體地位和土地流轉的范圍在很大程度上仍受限制,土地發包方仍能夠調整和收回土地。[7]秦暉(2004)研究認為“在當前條件下侵犯農民的公民權益往往是通過侵犯農民的合法土地權益表現出來的”。[8]因此,推動農村土地制度開啟新一輪的改革已成為理論界的共識。
(一)土地要素的產權界定問題
自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國農村土地制度在產權界定上存在模糊性,且隨著城鎮化的推進,這種模糊性日益強化。這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方面土地所有權的管控問題。土地集體所有制介于私有制和國有制之間,是土地公有制的一種具體制度設計。周其仁認為“集體公有制既不是一種共有的、合作的私有產權,也不是一種純粹的國家所有權;它是由國家控制但由集體來承受其控制結果的一種農村社會主義制度安排”。[2]由此,我們明晰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控制交由國家,以此確保土地制度的公有性質,而土地所有權的管理由集體進行,這個“集體”如何界定,是鄉鎮政府?還是村級組織?甚至是土地發包時的生產小組?隨著城鎮化的外延式擴張,農村土地的征用是由鄉鎮政府規劃決定,還是由村民自治組織進行民主決策?由于城鄉間土地價值存在落差,在城鎮化的沖擊下,這種價值落差吸引鄉鎮政府、村委會及生產小組爭相介入土地的征用問題。這表明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管控問題仍存在模糊性,且在城鎮化的沖擊下日益強化,這將極大制約了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有效管控。
另一方面,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是否包含土地價值增值帶來的財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農民排他性土地使用權,即允許農民依托土地要素進行生產,承認其對生產所得到的財富所有權。在城鎮化的沖擊下,農村(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土地價值存在增值預期。土地帶來的財富不僅僅包含依托土地要素生產得到的財富,還包含土地自我價值增值帶來的財富。當前農村土地制度對土地價值增值那部分財富的歸屬界定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是否承認農民擁有土地價值增值的財富所有權?這種模糊性引起了不少農民因土地征用產生利益糾紛事件。
(二)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問題
自改革開放,農村勞動力大量地由鄉到城、從農到非農轉移,形成了日益壯大的“農民工”群體。在職業轉變過程中,農民工脫離土地,農業生產由主業轉變為副業,甚至被完全放棄,出現了“土地拋荒”現象。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市民化是農民工未來的發展定向。實現農民工市民化要求其職業轉變具有完全性,即剝離依附于農民身份的生產要素。當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給予了農民排他性土地使用權,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約束下,農民對土地要素的排他性使用權是否可以讓渡、流轉。在缺乏土地所有權,農民工面對較高的交易費用,只能“無償”地放棄土地要素的排他性使用權,出現“拋荒”行為。土地作為農村重要的生產要素,在職業轉變過程中,農民工消極地放棄土地要素的排他性使用權,這是對土地使用權的閑置與浪費。由于戶籍制度的約束及城鄉經濟差距日益擴大,農民工的市民化資本要求不斷提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對依附于農民身份的生產要素的剝離,脫離土地要素。因此需要重視這一生產要素的剝離過程,以此為農民工市民化資本進行有效積累。而這一土地要素的剝離程度受到當前農村土地制度的約束,涉及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問題,能否允許農民工利用對土地要素的排他性使用權的有償流轉為自身的市民化資本進行有效積累。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農民工走向市民化,原有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問題亟需有效地解決。
三、新形勢下我國農村土地要素產權重構分析
在土地要素的產權界定方面上,關于土地所有權的管控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對于是否承認農民擁有土地價值增值的財富所有權,全會提出了“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而在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方面上,全會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土地租賃、轉讓、抵押二級市場”及“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功能”等內容。[9-12]
(一)把握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根本點:保證土地的性質與發揮國家對土地的規范作用
由于傳統文化觀念、意識形態等因素的作用下,土地對農民而言,其意義是多元的且深刻的。保證農村土地制度的社會性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必然條件,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保證之一。而這將約束農村土地要素的所有權不能私人化。在保證農村土地所有權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同時,需要在宏觀層面上發揮國家對土地用途、土地交易等內容的規范作用。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發揮國家對農村土地用途、交易等環節的規范角色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比如日本十分重視對土地用途的農用管理。針對當前的農村土地管理,國家應弱化微觀層面上過多干預與約束,更多的是強化宏觀層面上規范與指導。這種規范與指導不僅要明確界定出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特別是土地價值自我增值那部分財產權,也應為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創造制度性條件,讓農民充分利用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交易,進而加快市民化資本積累。
(二)突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立足點:深化土地改革與“三農”問題關系機理
自改革開放,我國“三農”問題日益突出,在新型城鎮化的催化下,“三農”問題亟需有效的破解。作為農村經濟制度的核心與基礎,農村土地制度的新一輪改革應突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立足點,即深化土地改革與“三農”問題關系機理。這種關系機理的深化表現在:
首先,土地改革促進農民致富。在務農期間,土地作為農民最重要、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是生活致富的主要來源。但隨著職業的非農化,不少農民蛻變為農民工,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卻難以成為其有效的致富來源。當前推動農村土地要素產權重構,文章認為應從產權界定與產權交易兩方面,充分地促進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成為農民(特別是農民工)重要的致富來源。一方面在土地要素的產權界定,明確農民有權參與農村土地價值增值所帶來的財富分配。在城鎮化的沖擊下,土地價值的城鄉落差創造了農村土地價值增值空間與增值潛力。為此,參與農村土地價值增值所帶來的財富分配將促進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較大增加。另一方面在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允許農民有權通過市場交易進行土地要素排他性使用權的讓渡與流轉。通過流轉,農民可以利用產權交易發現土地使用權的“市場價格”,充分整合地域范圍內的土地資源,進而實現土地生產規模化。與之同時,在市場價格激勵下,農民工可以積極讓渡、流轉土地使用權,為自身的市民化進行資本激勵,而不是消極地放棄、閑置土地使用權,致使“土地拋荒”。
其次,土地改革促進農業生產。土地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載體,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廣度與深度制約著農業生產的效率釋放。在土地要素產權重構中,一方面突顯農村土地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切實發揮國家對土地用途的規范作用,充分保障農村土地要素的生產用途,約束農地的非農化開發,進而強化經濟發展的“糧食安全”。與此同時,對于農村土地價值增值帶來的財富分配,有必要從中劃分一定比例形成農業生產支持基金,為農業生產的設施完善、技術創新與推廣等提供必要的資本支持,從而促進農業生產;另一方面在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上,構建城鄉統一的用地市場,讓農民在市場價格的引導下對土地使用權進行充分的流轉、讓渡。在農地用途的生產性約束下,土地使用權的充分流轉有利于地域內農民整合土地資源,推動農業生產規模化,進而提升農業生產的效率水平。
最后,土地改革促進農村發展。土地制度是農村經濟發展制度的核心與基礎,其改革成敗關系到農村經濟的長遠發展。在土地要素產權重構中,一方面保證農村土地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在制度層面上有利于維護農村發展的社會穩定。面對農村土地價值增值所帶來的財富分配,有必要劃分一定比例的財富為農村發展的公共產品普及與改善提供必要的資本支持,從而改善農村經濟的發展環境;另一方面以市場交易為手段推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與讓渡,充分激活資本要素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以此強化農村經濟的發展活力。
(三)明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長遠點:弱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
自封建社會,我國經歷了數十次土地制度的變革,從租庸調制、攤丁入畝到農民土地所有制,再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形態各異、性質不一,但在農耕文明的深遠影響及工業化落后的制約下,這些土地變革的長遠點都在于固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比如,現有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賦予農民排他性土地使用權,但這種使用權只有在從事農業生產條件下才能成為農民的致富來源。隨著職業的非農化,不少農民蛻變為農民工,原有的土地使用權卻無法通過流轉或讓渡為農民工帶來財富。在缺乏土地要素的產權交易條件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所賦予的排他性土地使用權一定程度上固化了農民與土地的束縛關系。當前,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讓更多的農民在生活方式、職業選擇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從農到非農的轉變。而農民市民化要求農民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進行關系剝離。面對這樣的改革背景,當前我國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長遠點與之前的歷次土地改革不同,在于弱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促使入城農民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進行關系剝離,從而增強農民市民化的全面性。在弱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時,要十分重視農民市民化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剝離這兩者的協調性。一方面把握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根本點,發揮國家在宏觀層面上的規范作用,讓農民市民化與土地要素剝離兩者有序、協調進行,以此深化土地改革與“三農”問題的關系機理;另一方面以市場交易促進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讓渡,充分利用土地要素的剝離過程為農民市民化進行資本積累。當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被過早剝離,農民因市民化資本不足,其職業選擇、生活方式將受到突變性沖擊,致使失業、蝸居等現象出現;當農民市民化快于土地要素剝離,表明農民的職業選擇、生活方式仍與土地存在關聯,弱化市民化的完全性。因此在新型城鎮化的沖擊下,推進農村土地改革應明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長遠點,弱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強化農民市民化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剝離這兩者關系的協同性。
四、結語
文章研究認為當前我國應積極推動農村土地要素的產權重構:一是把握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根本點,保證農村土地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發揮國家對土地用途、土地交易等方面在宏觀層面上的規范作用;二是突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立足點,深化土地改革與“三農”問題關系機理;三是明確土地要素產權重構的長遠點,弱化人與地的束縛關系,強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與依附于農民身份的土地要素剝離這兩者關系的協同性。在研究中,文章認為對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僅在分配主體上兼顧國家、集體、個人,更要將其與“三農”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促進“三農”問題的有效破解。
〔1〕 王永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演變的歷史考察[J].鞍山鋼鐵學院學報,2002(10):388-393.
〔2〕 周其仁.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3〕 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姚洋.農地制度與農業績效的實證研究[EB/OL].(2005- 11- 25)http : / /www.ccer.edu.cn.
〔5〕 楊小凱.中國改革面臨的深層問題——關于土地制度改革[J].戰略與管理,2002(5):1-5.
〔6〕 劉守英,蔣省三.南海土地股份制調查報告[Z].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3.
〔7〕 黨國英.關于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J].國土資源,2003(6):13-15.
〔8〕 秦暉.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思考[N].經濟觀察報,2004-11-13.
〔9〕 周文,倪瑛.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問題探討[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6):100-104.
〔10〕 盛洪,沈開舉.土地制度研究(第一輯)[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11〕 科斯,阿爾欽,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N].人民日報,2013-11-16.
(責任編輯 周吉光)
Study on the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 Factor in New Situation
PENG Qing-hua, LUO Ying-ya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he view of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new agricultural-operation system,giving more property rights to farmers,making a good balanced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building a healthy urbanization that puts people at the center.Owing to the unclear defini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limit of property transactions,it is necessary to make the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s factor in the impact of new urbanization.The paper studies the basic point,footing point and long-term point of the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rural land’s reform.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property reconstruction; new situation
2013-11-22
彭清華(1988—),男,福建泉州人,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西方經濟學。
F321.1
A
1007-6875(2014)02-00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