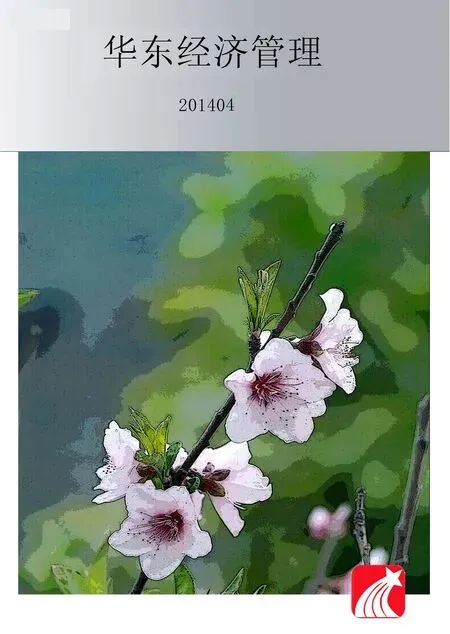農村勞動力遷移、老人照顧需求與社會支持介入方式分析
寧滿秀,荊彩龍
(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 言
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口預期壽命得到普遍延長,出生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家庭中老年人口數目不斷增長,加劇了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1]。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截止到2011年,我國65歲以上的老人已達1.23億人,占總人口的9.1%。另外,根據全國老齡委的預測,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的總量將超過4億人,占總人口的30%。在今后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都會保持著很高的遞增速度,屬于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2]。顯然,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必然引發老年人照料服務需求量的急劇增加。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促使地區與行業之間的要素流動壁壘逐漸消除,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已成為一種長期趨勢。據統計,2010年全國外出就業的農村勞動力達1.5萬億,其中大多數是15~35歲的青壯年勞動力,致使大量老人留守農村。由于成年子女的外流,潛在照料提供者的數量減少,農村留守老人既要承擔繁重的家務勞動,又要承擔照看孫子女的責任,更為嚴峻的是,原先由外出子女耕種的土地自然而然地轉嫁到農村留守老人身上,加重老年人的耕作負擔,弱化了子女照料老年人的家庭養老功能。此外,在社會生育率降低的同時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攀升使潛在的家庭照顧資源愈發減少。因此,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引發了由家庭提供照顧服務的現實困境,傳統上單純依靠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親情關系來解決農村老年人照料問題已越來越不具備現實可行性[3]。
在社會經濟結構、人口結構轉型與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的多重背景下,本文基于農村老年人照顧需求的變化,試圖探討傳統家庭養老體系是否能給老年人提供適時且足夠的照顧支持?現有的家庭照料體系是否需要政府支持政策的協助?而未婚或喪偶的獨居老人又是通過何種途徑滿足其照顧需求?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支持網絡的構建將如何滿足農村老年人的照顧需求,各類型長期照顧服務如社區式、機構式等正式服務體系如何補充非正式照料體系的不足?
二、基于社會支持理論的分析農村老年人照顧需求
Gallo[4]將社會支持體系分為社會關系的量與社會關系的質,就是由社會網絡和社會支持所組成。然而,高迪理[5]認為“社會支持”與“社會網絡”是兩種不同又相關的概念,并指出有社會網絡存在不見得有社會支持,但社會支持的提供與感知必須在社會網絡存在時才能順利進行。“社會支持”是屬于主觀感知的概念,當事人能夠感受到某些支持性行為滿足其需求、解決其問題的功能。而“社會網絡”則屬于客觀結構的概念,即與當事人相關的各成員在網絡中是如何組成與分工。因此,本文根據不同的社會網絡帶來社會支持功能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老人需要什么樣的社會支持網絡滿足其照顧需求。農村老年人照顧需求分析視角的實質即是將老年人照顧需求與社會支持網絡相結合,在社會支持網絡的基礎上關注老年人照顧需求與需求滿足的互動關系,即:農村老年人照顧需求分析視角依托于社會支持網絡的相關理論。
(一)層級補償模式
層級補償模式主張近親(特別是配偶和子女)是社會支持的核心,老人需要幫助時首先會尋求近親協助。正如Shanas[6]所解釋:當老人沒有子女時,一項家庭替代原則將會啟動,其兄弟姐妹、侄兒外甥、及侄女外甥女通常會履行子女的角色及責任。即老人在使用社會資源時會有選擇的偏好,他們會首選與自己最親近的人,即非正式的社會支持。當非正式的社會支持并不能滿足老年人照顧需求時,老人才會轉向正式的社會支持體系求助。同時,層級補償模式說明,老人照顧工作所需要的社會資源并不是基于職務、金錢等因素,而是在于心理程度上的親近疏遠,如果老人能夠獲得家庭子女與親屬的照料支持,那么,他就不會轉向正式照料體系尋求支持。通常而言,老年人在非正式支持體系中所獲得的幫助越多,尤其是從接觸最親密的家人包括配偶和子女獲得的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滿足度越高,生活質量越高。
(二)任務分工模式
任務分工模式認為,在滿足老人照顧需求層面,親戚朋友以及鄰居對配偶和子女的替代效果是有限的。一般而言,朋友或鄰居提供的協助通常是小規模且短期性的項目,如購物或提供交通協助;需要長時期且個人層面的協助則由親屬履行;特定職務則由配偶或子女提供協助。根據任務分工模式,當某一特定支持來源無法獲得時,除非有類似特征的支持體系予以替代,否則會導致某些照顧需求無法獲得滿足。以無子女者為例,子女具備的特定功能雖然可通過某些類似父母-子女關系者予以執行,但親戚朋友以及鄰居卻無法完全替代配偶及子女的照顧功能。實質上,任務分工模式涵蓋了層級補償模式的觀點,當缺乏某一可執行特定任務的理想照顧者時,個人將會選擇結構相似的照顧者予以替代;與其不同的是任務分工模式認為當個人缺乏執行特定職務的理想照顧者時,選擇另一功能近似的照顧者予以替代可能導致照顧質量的降低[7-8]。
(三)壓力緩沖模式
Sharkey是壓力緩沖模式的開創者,他認為,當老年人受到壓力沖擊時,如果社會支持網絡給予老年人適當的幫助使壓力沖擊得以緩沖,老年人就能夠盡快恢復正常的生活狀態;反之,壓力長時期得不到緩解和消除則會造成老年人抑郁等身心疾病。可以說,包含傳統家庭養老體系在內的社會支持的介入在老年人遭遇嚴重生活事件沖擊時具有壓力緩沖作用,能夠緩解老年人的不滿情緒,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質量。
社會支持對老年人壓力的作用效果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直接模式,即不管壓力是否發生,老年人都可以直接從社會支持中得到益處。如果農村老年人接受社會支持能夠增強老年人幸福感并且促進老年人對團體的歸屬感與自尊,那么,社會支持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有直接的積極效果,但沒有緩沖效果[9];另一種模式是壓力緩沖模式,即社會支持對老年人經歷壓力事件后產生的負面影響有緩沖效果[10-11]。緩沖模式主張當壓力不存在時,社會支持對老人憂郁并無特別影響,但是當老年人遭受嚴重的生活打擊,老年人心理和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時,社會支持的介入可以降低老年人所承受的壓力,間接降低老年人身心受到的負面影響,并且壓力愈大,緩沖效果愈顯著。
三、勞動力遷移背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照顧需求與社會支持介入方式
(一)勞動力遷移背景下農村老年人的照顧需求
國內外諸多研究表明,未滿足需求是導致老年人增加醫療服務利用及疾病惡化的關鍵,也是決定老人是否需要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的重要因素[12]。因此,本文從生活照顧需求、經濟支持以及情感需求三個層面分析農村老年人的照顧需求及其差異性,以期通過對農村老年人未滿足需求的了解探討農村老年人的長期照顧服務問題。
1.生活照顧需求
按照生命周期規律,老人達到一定年齡時身體機能退化的趨勢明顯加劇,遭受疾病困擾、日常功能缺損的可能性增大,自理能力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代際之間空間上的分離使得外出務工的子女難以為父母提供經常性的照料支持,影響了老人照料資源的可獲得性。一旦老人身體健康惡化,子女對老人的照料感到力不從心。與配偶同住的農村老人,配偶可能會提供生活上的照顧,緩解子女照料上的壓力;膝下無子女和喪偶的空巢老人一旦遭遇重大疾病的沖擊更將無人照顧,嚴重降低老年人獨立生活的能力進而加速老年人的死亡。由此可見,當老人因身體機能障礙需要料理家務(洗衣服、準備餐食及打掃房間等),或個人照顧(協助梳洗、洗澡、如廁)等勞動密集型的照顧需求時,子女在身邊更便于提供生活照顧[13]。毋庸置疑,研究農村老人生活照顧需求滿足問題是對家庭養老思考的應有之義。
2.經濟支持
隨著老人年齡增大及其健康狀況惡化,勞動時間的供給大幅減少,收入不斷降低。身體機能衰退和勞動能力的喪失使得農村老年人無法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支撐生活,需要依賴子女的經濟支持。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遷移使得成年子女收入增加,子女可能會通過收入轉移使父母退出農業勞動,改善老人的經濟福利水平并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但是,通常情況下,農村老年人并沒有因子女外出打工而增加收入。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在建房、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經濟壓力以及他們收入的有限和不穩定,外出成本較高等都限制了外出家庭成員為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的能力[14]。因此,可交換資產或可流通財富的缺乏限制了農村老人的退休,他們不得不延長勞動年齡以增加儲蓄養老。從某種意義上講,農村空巢老人經濟上的依賴性加強,雖然家庭可能具備響應這些危機的能力,但其提供經濟支持的能力卻可能在長期缺乏社會機構支持的情況下隨時間延長而遞減。
3.情感慰藉需求
人到垂暮之年,一方面,需要面對喪失親友、愛人以及喪失勞動能力等生活事件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老年人缺乏對死亡的了解也加重了其對死亡的焦慮。此外,勞動力遷移加劇家庭分化并改變了“養兒防老”的傳統理念,代際居住安排的分離使得老年人不能夠享受子女膝下承歡。“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成為農村空巢老人的真實寫照。空巢老人處于孤獨、寂寞需要向別人傾訴、“排遣”時,情感支持需求無人滿足,長此以往空巢老人容易患上抑郁癥,更有甚者患上“空巢綜合征”。顯然,勞動力外流致使農村空巢老人增多凸現了農村老年人情感和心理健康問題的嚴重性。如果能在農村建設老年人活動中心,提供老人繼續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來維持老人與他人的互動交流,老人可能不會面臨自我價值感喪失的危機。國外研究也指出,老年人與朋友、鄰居交往似乎比家人更能增加信心,更有利于老年人排遣孤獨寂寞。這是因為同代同齡老人似乎有更多的共同點,且交往不是強迫的,而是友誼維持的[15-16]。
(二)社會支持網絡在老人照顧中的介入方式
社會支持網絡由政府、社區以及家庭三方組成,能夠提供的社會支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①工具性社會支持。工具性社會支持是指得到具體的幫助與支持,如提供服務、金錢支持或生活物品等[17]。支持接受者對于所得到支持內容類型,根據接受者需要情況有不同重視程度,如對于經濟匱乏者,物質與金錢支持重要性較高;行動不便的人,外出交通的協助重要性較高;失能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日常生活協助的重要性較高。②情緒性社會支持。情緒性社會支持是指個人感受到他人對自己的關懷、尊重并強化自我價值[18]。③信息性社會支持。信息性社會支持是指他人幫助個體了解壓力事件,使個體相信本身擁有的資源與應對的策略能夠處理此壓力[19]。
社會支持對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經濟、心理以及身體等不同功能的維護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良好的社會支持是老人健康的保護性因素。有研究指出,老人的社會支持在老年生活中具有緩和生活壓力的功能[5],讓老人得以面對生理的病痛及生活環境或角色的改變所帶來的沖擊。具體而言,在身體健康方面,充足的社會支持可以減緩身體功能的退化,使老人維持良好的健康狀況;在心理健康方面,社會支持與老人的心理適應能力、憂郁程度等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缺乏社會支持的老人明顯有較高的憂郁程度[20],尤其是遭受嚴重生活打擊。
社會支持網絡的理論基礎在老人照顧類型的研究中是沿著婚姻居住狀態發展的照顧網絡而側重不同層面,“層級補償模式”強調各種支持來源的可獲得性,“任務分工模式”和“壓力緩沖模式”則分別關注不同婚姻狀態、居住狀態下老年人的照顧需求。本文期待藉由三種理論模式理順婚姻居住狀態對老人照顧需求的影響,并通過社會支持網絡所能提供的社會支持來探討不同婚姻居住狀態下社會支持與農村老人照顧需求的內在作用機制。
擁有婚姻關系且與子女居住的老人,家庭養老體系可以供給老年人物質上的資助、生活信息的提供以及情感支持,使得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不虞匱乏,并在人際互動中感受到愛與尊重,有助于老年人應對嚴重生活事件以及維持健康生活,最終將提高老年人生活滿意度,避免過早進入長期照料機構并減少對公共及醫療資源的依賴。所以,這種類型的農村老年人較少使用社區式服務和機構式服務。應當指出,對有配偶者而言,婚姻狀況的解體(如配偶死亡或離婚)或配偶無法繼續提供照顧功能時,老年人照顧需求提供者發生了結構性的改變,也導致傳統家庭養老體系的改變。Tennstedt等人[21]指出,傳統家庭養老體系失效通常發生在配偶死亡或子女外出無法繼續提供照顧。在這種情況下,獨居者即為機構式服務和社區式服務使用的高危險群,也是長期照顧政策應重點關注的目標人群。農村勞動力外流致使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發生改變,親子居住安排空間上的遠離使傳統家庭養老體系失效,農村空巢老人并不能完全依靠外出務工子女回家照顧。對于未與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來說,社區可以針對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提供各種福利服務,例如,居家服務,營養膳食服務,白天照顧或者是短期照顧或臨時照顧以及咨詢提供等等,這樣能夠使空巢老人在所熟悉的環境中就近取得資源獲得協助來滿足需求。對于子女外出務工,喪失配偶,自己無生活能力的老人,養老機構可以提供老年人住宿服務、緊急送醫服務、社交活動服務、教育服務、保健服務、醫療服務等,提高了空巢老人對公共資源的依賴,也有助于老年人應對嚴重生活事件以及維持健康生活。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彌補了家庭養老的不足,針對不同居住安排下的老年人提供不同的社會支持,滿足了老年人的照顧需求,推動多種養老方式共同協調發展的養老服務體系的構建[22]。
已有文獻在討論老人照顧需求與社會支持關系時,似乎都直接或間接立基于一個基本假設:老人擁有社會網絡資源就一定會得到相應的社會支持,其照顧需求將得到滿足。事實上,老人擁有的社會網絡并不代表他們的照顧需求就能獲得滿足[23]。特別是,生育率下降和家庭規模縮小削弱了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尤其是農村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攀升以及正式照料制度的缺失導致老年人面臨日益嚴重的“看護”危機。雖然這并不必然導致家庭成員間關系的急劇減弱,但代際之間的生活互助肯定會受到制約并趨于弱化[24]。尤其是當農村老年人年老病衰的時候,所謂的“親奉湯藥”已無可能,只能請人代理。家庭失靈導致成年子女無法繼續發揮照顧功能,其他資源(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的適時介入與配合具有合理性與必要性。為了彌補家庭照顧的落差,以便老人能在熟悉的社區中得到安養照顧,政府應該有計劃、有組織辦理相關的社區照顧服務或者鼓勵提供機構服務,尤其是對獨居老人或因行動不便而其子女均在外務工無法提供家庭照顧的老人來講顯得尤為迫切。當子女外出打工無暇顧及老年人時,社區可以根據老年人的具體需求提供居家服務;同時在家庭經濟允許的條件下也可以將老年人送往正式的養老機構照顧。同時,由于農村基礎設施不健全,缺乏必要的休閑娛樂設施,加上子女外出務工老人無人陪伴情感需求得不到滿足,機構和社區應該提供必要的情緒性支持和信息性支持,豐富農村老年人生活,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四、結論與啟示
“以家庭為中心”的照顧模式將是今后相當長時期內農村老年人養老的基本模式。我國政府部門及社會輿論也不斷宣揚我國是以家庭和孝道為中心的儒家倫理模式,期待通過儒家倫理的強調將照顧問題家庭化及道德化;但我們卻不能忽略儒家倫理對家庭孝道觀念的理想化,尤其是目前社會變遷已經重塑了家庭關系與家庭功能、夫妻之間的權利格局,儒家傳統價值觀在代際間傳遞日益減弱,理想家庭在現實社會中具體實踐的可行性微乎其微。
基于傳統家庭養老體系與農村勞動力外流所引致的代間交換力量不足以滿足農村老人照顧需求的現實,本文從農村老人需求差異性角度出發,在審視老人在家庭主義及國家意識的夾縫間獲得照顧現狀的基礎上,探討了滿足老年人照顧需求的政策途徑,即通過農村老年人照顧需求以及我國社會支持網絡體系構建分析我國長期照顧政策發展的定位與方向:
(1)主張我國長期照顧政策應以家庭為照顧服務提供單位,對此,通過城鎮化、現代化建設帶動本地經濟和產業的發展,以提高本地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少農村勞動力外流,從而保證成年子女在家庭照料與勞動就業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關系,在不影響成年子女就業的同時也滿足老人的照料需求;與此同時,創新“喘息服務”等居家養老模式,盡可能通過社區以及機構將服務輸送到農村老人所在家庭,避免讓老人遷就照顧現實而不得不進行晚年居住安排的變遷,讓老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圈內就近獲得照料與關懷,實現老人“就地老化”的目的。
(2)在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就業的宏觀背景下,相關決策部門一方面可以通過破解農村老人與成年子女隨遷的制度障礙,鼓勵老人與成年子女隨遷,在不降低成年子女就業流動性和增加其照料機會成本的情況下保障老人能夠得到應有的照料;另一方面,應當完善社會醫療與養老保障制度,構建城鄉統籌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之間的銜接與接轉,從而保障農村老人在隨遷以后能夠在社會保障體系內享受相應的福利保障。
總而言之,與其在傳統家庭養老體系和正式照料體系之間劃下一道鴻溝,更務實地作法應是構建“政府-社會組織-機構-社區-家庭”多中心的社會支持網絡體系,真正實現在地老化、健康老化、積極老化的養老目標,促進和諧社會的發展。
[1]董力堃.強化政府養老保障責任的理論模式與路徑分析[J].華東經濟管理,2010(9):133-137.
[2]胡宏偉,時媛媛,肖伊雪.公共服務均等化視角下中國養老保障方式與路徑選擇——居家養老服務保障的優勢與發展路徑[J].華東經濟管理,2012(1):119-123.
[3]劉曉梅.我國社會養老服務面臨的形勢及路徑選擇[J].人口研究,2012(5):104-112.
[4]Gallo Joseph J.The effect of support on depression in caregivers of the elderly[J].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1990,30(4):430-436.
[5]高迪理.社會支持體系概念之架構之探討[J].社會發展季刊,1991,54:24-32.
[6]Shanas E.The family as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in old age[J].The Gerontologist,1979,19(2):169-174.
[7]Barrtee A E,Lynch S M.Caregiving Networks of Elderly Persons:Variation by Martital Status[J].The Gerontologist,1999,39(6):695-704.
[8]Wu Z,Pollard M S.Social support among unmarried childless elderly persons[J].The Journal of Gerontology,1998,53(6):324-335.
[9]Thoits P.Conceptual,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studying social support as a buffer against life stress[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82,23(1):145-149.
[10]Caplan G.Social support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Lectures on Concept[M].New York:Behavioral Publications,1974:143-147.
[11]Cohen S,Wills T.Stress,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8(2):310-357.
[12]Pendry E,Barrett G,Victor C.Changes in household composition amongthe over sixtie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health and lifestyles surveys[J].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1999,7(2):109-119.
[13]Tennstedt S L,Crawford S L,McKinlay J B.Is family care on the decline?A longuitudial investigation of the substitution of formal long-term care services for informal care[J].The Milbank Quarterly,1993,71(4):601-624.
[14]賀聰志.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老人生活照料的影響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0(3):46-53.
[15]Gottlieb Benjamin H.Social Support Strategies[M].Sage Publication Inc,1983:239-241.
[16]霍曼N R,基亞克H A.社會老年學——多學科展望[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116.
[17]Christopher T Whelan.Relationship of age,education,and occupation with dementia among community based sample of African[J].Arch Neurol,1993,53(2):134-140.
[18]Taylor D H,Schenkman M,Zhou J,et al.The relative effect of Alzheimer′s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s,disability,and comorbidities on cost of care for elderly persons[J].Journal of Gerontology:Social Sciences,2001,56(5):285-293.
[19]Wills T.Supportive func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5:61-82.
[20]Cheng S,Chan A C M.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Journal of Gerontology:Psychological Sciences,2006,61:262-269.
[21]Tennstedt S L,McKinlay J B,Kasten L.Unmet need among disabledelders:A problem in access to community long term care?[J].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1994,38(7):915-924.
[22]汪大海,張建偉.福利多元主義視角下社會組織參與養老服務問題——“鶴童模式”的經驗與瓶頸[J].華東經濟管理,2013(2):118-122.
[23]王躍生.當代中國家庭結構變動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6(1):96-108.
[24]葉菲菲,寧滿秀.居住安排對農村老人照顧需求滿足的影響——兼論我國老人照顧政策選擇[J].福建行政學院學報,2012(6):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