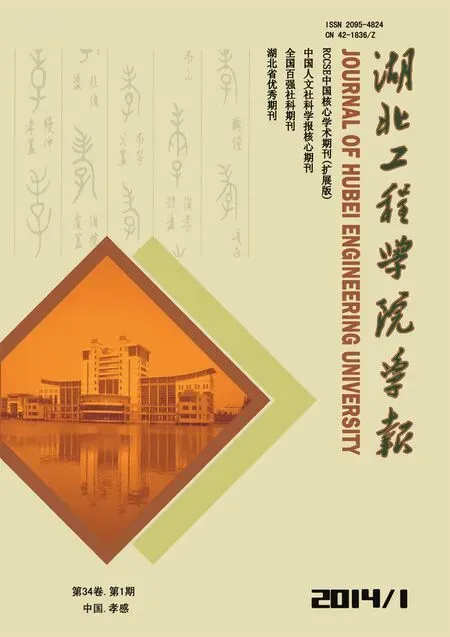從《蛙》中的農民形象看莫言對現代文明的反思
張 麗
(1.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江西 南昌 330077;2.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2)
歌德曾說:“現實主義作家認為小說是一種以塑造人物形象為主的記敘性文學體裁,應把人物看作是小說的靈魂。”[1]中國當代小說成功塑造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物,但在各類人物中,農民形象塑造得最為出色。從古至今,農民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面臨的沖擊和困惑最具代表性和隱喻性。作為一個被現代化改造的群體,他們既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刻骨銘心的體驗者,又是中國農村巨大深刻歷史性變革的見證者,是現代化的主體。他們構成了獨特的形象體系,這一體系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因此,文學作品中所塑造的農民形象與生活中真實的農民形象相比,有了更加豐富的擴展空間,在現實語境與精神構建兩個層面上蘊含著耐人尋味的審美價值。
在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學中,農民成了落后、愚昧、守舊、迷信等傳統社會性質的標志。農村留給讀者的大多是破落和衰敗的景象,破落和衰敗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象征和國家民族遭受侵略時的隱喻,對這種頹廢景象和農民生活狀況的描述,一方面是一種現代意識的覺醒和國家民族身份的自我確認;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中國農村進行革命和現代化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發展到現代,農民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體現在物質條件的改善,更體現在當代農民于傳統與現代相互交融中價值觀念的轉變。因此,一批性格多元、美學品質豐富、文化內涵復雜的新農民形象便進入到作家的視野中。莫言就是其中一位。莫言對農民的認識是獨特而深刻的,他在農村度過自己的童年,對農村生活有深刻的記憶。因此,在其農村題材的小說中,他沒有回避或遮蓋農村的一些現實和苦難,而是在真實描繪這些生活的基礎上,展現不同時代農民的生存狀態。他同情農民的遭遇,關心農民的命運,也從中洞察了中國農民的病態與弱點,針對這些病態和弱點,他提出: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新時代的農民必須要改變自身的不足,融入到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中。
提到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時,莫言曾說:“如果說我的作品在國外有一點點影響,那是因為我的小說有個性,思想的個性,人物的個性,語言的個性,這些個性使我的小說中國特色濃厚。我小說中人物確實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起來的。我不了解很多種人,但我了解農民。土是我走向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2]前言2可以看出,作家濃厚的鄉土情結和對農民形象的熱愛程度。莫言在描寫鄉土風情特色的基礎上,把目光投射到農民面對社會快速發展時的心理變化過程。對這種心理變化過程的探索,一方面表現了作家對農村現代化建設所持的肯定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家對傳統的“城市/農村”二元論思維的反思。《蛙》中塑造的農民形象便表現了莫言對“城市/農村”二元論思維的超越現代文明沖擊下農民精神世界的擔憂。
《蛙》以在農村做鄉村醫生的姑姑的人生經歷為線索,展現了新中國六十年波瀾起伏的生育史,真實記錄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廣大農民平凡而真實的生活。小說以農民的生活為題材,以姑姑的生活為主線,并穿插了農村具有代表性的各類人物的故事,主要有陳鼻的故事、小跑的故事、袁腮的故事。眾多的人物形象展現了當下農村的生活百態和以蝌蚪為敘述者的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蛙》中除了敘述形式比較特殊之外,小說中農民形象塑造擺脫了之前比較單一的趨勢,出現了理想的追求者、為改變命運的奮斗者、游蕩的破壞者等多種農民形象。
一、裂變與重構——農民形象的多元化
莫言的小說深受齊魯文化的影響,長期的農村生活和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使他有了“農”的思想、“農”的精神、“農”的審美趣味,因此,莫言始終堅持著“農”的身份,以“農”的視角來關照鄉村生活,謳歌傳統的鄉村文明的同時也在反思和排斥著現代城市文明。他以山東高密東北鄉的民間文化為基礎,采用民間寫作立場,貼近底層民眾的生活狀態,從而能準確地發覺農民的靈魂深處,剖析他們深層的精神世界。《蛙》是圍繞鄉村生活中的結婚、生子主題展開,比較突出的也是具有“農”意識的勞動者。他們既是鄉村中對理想的執著追求者,也是努力改變命運的奮斗者。他們的變化從不同層面展示了新時期當代農民復雜和真實的一面,并揭示了農民在現代化、工業化過程中的種種變化。
1.理想的追求者。莫言把傳統意義上很順從的“良民”,放到商品經濟的改革大潮中。他們欣然接受了改革所帶來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教育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不斷改變自己以適應社會的發展。在這種改變過程中,他們堅持對事業、愛情的執著追求,不管成功與失敗,為自己的信念而活,從而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蛙》中的姑姑便是對事業執著追求的典型。在故事沒有開始敘述之前,敘述者先向讀者交代了年輕時剛做鄉村醫生的姑姑:“一個騎著自行車在結了冰的大河上疾馳的女醫生形象,一個背著藥箱、撐著雨傘、挽著褲腳、與成群結對的青蛙搏斗著前進的女醫生形象,一個手托嬰兒、滿袖血污、朗聲大笑的女醫生形象,一個口叼香煙、愁容滿面、衣衫不整的女醫生形象……您說這些形象時而合為一體,時而又各自分開,仿佛是一個人的一組雕像”[2]3接著敘述正式開始,首先出現在讀者面前剛參加工作的姑姑熱情、干練、有正義感,當她第一次為艾蓮接生時,看到村里的“老娘婆正騎在艾蓮身上,賣力地擠壓著艾蓮高高隆起的腹部”[2]16時,姑姑“扔下藥箱,一個箭步沖上去,左手抓住那老婆子的左臂,右手抓住老婆子的右肩,用力往右后方一別,就把老婆子甩在了炕下。”[2]17其次展現了姑姑對事業執著追求的信念。姑姑年輕時,不僅是村里的美女,也有去正規醫科大學學習的經驗,對當時醫療技術比較落后的農村來說,這類醫生很少,姑姑有機會去條件更好的醫院工作,但她堅守在養育她的農村,為農村計劃生育政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作為一名為計劃生育奉獻的醫療工作者,姑姑的信仰是非常堅定的,她為了完成計劃生育的使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她的額頭被張拳打破,也曾被人用剪刀戳,但她始終認為:“計劃生育是國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糧食不夠吃,衣服不夠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質量難提高,國家難富強。我萬心為國家的計劃生育事業,獻出這條命,也是值得的。”[2]107在小說中,敘述者對姑姑的敘述始終是崇拜和敬仰的,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姑姑作為改革開放初期的勞動者的代表,他們對社會所做的貢獻不可磨滅。
如果說姑姑是對理想堅定執著的追求者,王肝則是一個勇于拋棄世俗偏見大膽而浪漫的愛情追求者。他從小便單戀小獅子,并不斷默默給她寫情書:“如果你不答應我,最親愛的,我不會退卻,不會放棄,我會默默地追隨著你,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我會跪在地上親吻你的腳印。我會站在你窗前,注視著室內的燈光,從它亮起,到它熄滅。我要把自己變成一根蠟燭,為你燃燒,直至燃盡。”[2]101這份情書簡單而質樸,然而就是這簡短的幾句話,表現了王肝對愛情的執著與專一,也代表了新時代農民相親相愛、相互扶持的愛情觀。如果說王肝對愛情的追求比較直白的話,秦河對愛情的追求就顯得默默無聞,秦河一直單戀著姑姑,從未表白,直到姑姑與郝大手結婚后,他將失戀的痛苦轉化為藝術,成了高密東北鄉的工藝大師,他捏的泥娃栩栩如生,吹彈可破。
總之,這類形象比較突出的特點是對理想和事業堅定、執著,對生活樂觀、熱情,他們是莫言小說中新時期農民的代表,在對理想的追求中,他們也會遇到挫折,也會面臨種種誘惑,但樂觀的精神和堅定的信念支撐著他們繼續努力下去。
2.為改變命運的奮斗者。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化改革大潮涌向農村,農民從各種渠道看到了城鄉、貧富之間的差別,他們開始感到不公、羨慕、驚奇,夢想著改變自己的命運。這類型的農民超越了老實厚道、安分守己的小農思想,成為積極進取,有商業頭腦和創新精神的奮斗者。他們反映了現代化的發展和農民對自身精神和物質要求的提高,貧困不再是一種物質上的刺激,而是一種社會心理過程。《蛙》中所塑造的這類農民形象,有的直接響應改革的號召,通過經商,成為“有錢人”,如陳鼻在他年輕的時候,就成了村里比較出名的萬元戶,他通過去深圳倒賣電子表,去濟南批發香煙,讓老婆王膽在集市上出售而致富。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的文學作品中比較常見。有的堅信“知識改變命運”,通過考上大學的方式,離開農村,走向城市,在城市中安家落戶,他們中一部分人通過奮斗獲得了豐厚的物質財富,掌握了一定的權力后,認為自己已經脫離了農村,成為真正的“城里人”,但從出生以來獨具特色的一個習慣或一個眼神卻始終無法改變他的農民身份。如肖下唇考上大學后走出農村,若干年后,敘述者小跑從他身上的名牌服裝、步履輕快的走路姿勢和充滿自信的臉部表情中,判斷出他成為“一個有身份的人”。對這類通過自己努力改變命運的新型農民,作者肯定了他們奮斗中的韌勁,說明了農民也可以掌握、改變自己的命運。但令作者擔憂的是, 在新型農民中,一部分人會因價值觀念的轉變而放松對自身的約束,從而走向墮落。肖下唇的成功和墮落便是很好的例子。
3.游蕩的破壞者。他們在現代農村小說中既是迷失自我,面對挫折以消極的態度聽之任之的悲觀者,又是缺乏競爭能力和道德觀念的旁觀者。他們生活在社會夾縫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只能以“混”的方式來茍且偷生。他們的存在有深刻的社會原因,這加深了讀者對社會的思考。比較典型的是袁腮。年輕時的袁腮,在別人看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個能預知未來的大能人,從別人對他的評價中可以得知,袁腮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但他沒有正確運用自己聰明的頭腦,而是做一些違背倫理和社會道德的事,在他的腦海中,人的價值、人的追求都以錢為目標,他迷失了作為農民真正樸實的一面。還有受到打擊后一蹶不振的陳鼻,在老婆死后,以前被別人羨慕的萬元戶,整日喝酒,喝醉了又哭又唱,滿街亂竄,把之前的存款全部揮霍完后,在李手的飯店里當偽桑丘。當小跑敘述在堂吉訶德飯館見到年輕時的好友時,語氣非常冷靜:“那天晚上,我一眼就認出了陳鼻。雖然將近二十年我沒見過他,但即便是一百年沒見過,即便在異國他鄉,我也能認出他來。當然,我想,在我們認出了他的同時,他也認出了我們。童年時的朋友,其實根本不需要眼睛,僅憑著耳朵,從一聲嘆息、一聲噴嚏,都可以判斷無疑。”[2]238多年的好友,在這種情景下見面,更多的是無奈。
現代化進程中,鄉村沒有了安靜、質樸的氛圍,取而代之的是喧囂的商業化色彩,城市與農村完全成了先進和落后的象征,城市作為現代文明的象征侵蝕著農村,城市給當下農村的生活、文化和秩序帶來了沖擊。然而在這樣的沖擊中,作家面臨的一方面是養育自己的故鄉,另一方面是現代文明,在創作中出現了進退兩難的情感困惑。
二、莫言的情感困惑對農民形象塑造的影響
中國傳統的小說模式比較講究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在這個過程中,注重故事的講述和懸念的設置。近代中國的小說模式在原來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變,作家在注重故事情節塑造的同時,也融入了抒情環節和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從而豐富了文學的表現力。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都有他自己的價值尺度,在文化多元的21世紀,莫言既借鑒了西方小說的敘事方式和表現手法,又融合了中國本土文化的多種文學現象所具備的敘事方式,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創作方法。在他的創作中,他將自己的想象力融入到尋常百姓生活中,展現當代中國鄉村生活的真實風貌。他熱愛自己的故鄉,對高密東北鄉傾注了所有的激情和夢想,將自己的靈魂安放在這一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上。但與此同時,莫言也對現代文明沖擊下的價值缺失、方向迷失的現象表示了擔憂。《蛙》中的各類農民形象,既體現了他們渴望現代化的情緒,又體現了作者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徘徊與困惑。
在中國,鄉村是一個獨特而有豐富內涵的文化發源地,也是眾多知識分子心中一塊潔凈的精神領域,它一方面具有古代文學傳統中的田園詩意,另一方面也是現代化的產物。莫言的鄉土情結,源于他對鄉村深深的依戀和對故鄉的審美幻想。20世紀初,中國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代表了中國社會轉型帶給人們內心的矛盾和情感沖突。城市和農村之間的關系不僅表現在文化的沖突上,也表現在人們的精神追求、物質享受、價值判斷等方面的不同,而能表現這些關系的最好載體就是文學作品。在高密生活了近二十年的莫言,從小就對高密的鄉村生活有著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童年是在饑餓、貧窮中度過,他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十年“文革”,因此,他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直到今天,他骨子里還是與農民和鄉村有著剪不斷的聯系。同時,他文學創作的文化背景來自于山東高密東北鄉的高密文化,而高密文化結合了齊魯文化中魯文化的理性與厚重,齊文化的感性與飛揚,這些使莫言文學作品中的高密文化具有開放性、兼容性、禮儀性和智慧性的特色。他因此在小說中縱情謳歌齊魯大地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跡,并有意無意突出故鄉農民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所遇到的各種困惑,從而觀察這些苦難對人性變化的影響。
莫言小說中所表現的農民與鄉村的關系不是看與被看的關系,而是相互融合的關系。他由于從小便躬耕于山東高密東北鄉這塊多情的土地上,對那里的一切,都有一股割舍不斷的鄉情,他只能通過自己的小說講述這塊土地的悲苦、傳奇和夢想。童年的經歷,對莫言來說既是一種磨練,也是一筆用不完的精神財富。雖然后來他從軍,但小說中很少涉及軍旅題材。作為一個農民作家,他有著農村生活的根,有著農民的血液和氣質。他在書寫這一群體的生活時,也表達了他們長期以來受壓抑的心聲,但他對個人和鄉土苦難的關照同樣也帶著知識分子的理性,莫言是以痛苦為起點來揭開他的人生序幕的,他的人生體驗決定了他對中國農村歷史和現實有獨特的認知方式。他堅定地認為,在新中國,農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因此,他在謳歌高密文化獨具特色的鄉土風情時,不自覺地要構建一個詩意的精神家園。但這個理想的精神家園,在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阻撓和變異,一方面是對故鄉的眷戀,不希望故鄉傳統文明中的美好被現代文明破壞,另一方面,又希望農民通過努力過上富裕的生活。這樣就使作家對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現代文明產生了焦慮情緒,同時開始擔憂現代社會進程中農民身上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
三、結 語
莫言是中國當代文壇比較有爭議的鄉土敘事作家,雖然他既屬于尋根派小說家,又帶有先鋒派小說家的某些特點,但他對鄉土小說中所體現的現代文明具有獨到的見解,即在繼承和發揚的基礎上不斷反思并超越。他的民間創作立場表達了他對傳統文明的繼承和發揚。陳思和曾經對作家創作的“民間立場”有過精當的論述,他認為:“民間立場是指中國文學創作的一種文學形態和價值取向,在實際的文學創作中,‘民間’不是專指傳統農村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其意義也不在于具體的創作題材和創作方法。它是指一種非權力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和空間,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隱藏在民間,用講述老百姓的故事,作為認知世界的出發點,表達原先難以表述的對時代的認識。”[3]中國的鄉土文學從魯迅開始,發展到現在經歷了近一個世紀,莫言的高密東北鄉系列打破了以往以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文學中對和諧美的追求,他不再將故鄉和故土作為夢中所追求的理想世界,他放棄以往對鄉土文明中美好一面的謳歌和頌揚,而是將農村的原生態生活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也運用審丑、變形等手法描繪鄉村生活。莫言更加關注的是人類生命的物質狀態,他把生活還原為最基本的兩個字:吃和性,他像人類學家一樣,以“他者”的目光對故鄉進行了“田野研究”進而站在被研究對象的文化觀點上來了解特定文化內部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現象,他因此也發現了農民文化的本真意義以及與中華民族的災難深重和強悍的生命力之間的內在關系,這些使他筆下的鄉村具有渾然狀態下的豐富內涵。
“當時代進入比較穩定、開放、多元的社會時期,人們的精神生活日益豐富,那種重大而統一的時代主題往往攏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價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狀態就會出現。文化工作和文學創作都反應了時代的一部分主題,卻不能達到一種共名狀態,我們把這樣的狀態稱作‘無名’。無名不是沒有主題,而是多種主題并存。在共名狀態下,知識分子對社會履行的責任顯得比較重大,而無名狀態下相對要輕些。”[4]社會改革使農村的生活條件改善,農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隨之而來的是城鄉之間距離的縮小。《蛙》中,無論是理想的追求者,還是為改變命運的奮斗者、游蕩的破壞者,他們的性格中既有堅韌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當韌性戰勝了奴性時,他們會保持真正的自我,為了理想而不懈努力;當奴性戰勝了韌性時,他們會迷失自我,逐步墮落而成為現代社會的破壞者。莫言站在理性的高度,努力表現現代文明沖擊中的農村變革和新一代農民的成長歷程,他關注農民的內心世界,把農民的生活納入作者所追求的精神世界中,并把自我意識的覺醒程度作為現代文明下新型農民的評判標準。這些農民形象蘊含了現代人對社會、對人性的反思和擔憂,這也說明了莫言在建構農村小說的敘事模式時,沒有擺脫城市/農村的二元論思維模式。
總之,莫言的鄉土小說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摒棄了傳統文學的創作原則,試圖建立自己的規則和范例,他的小說是一種無視任何既定規范的、極度自由的“破壞性”文學。毛姆曾說:“要想誠懇地批判文學作品的優劣實在太難了。批判一部作品,幾乎不可能不受評論家或大眾的影響。對于公認的偉大作品來說,它之所以偉大,一部分是輿論意見賦予的,這使其評價工作更加困難。”[5]在莫言的自我認知和感受中,他敘述普通人的真實故事,對自己所生活的高密東北鄉的地域文化有著強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因此,從高密東北鄉文化這一視角切入,通過對其中農民形象的解析,探究他們在作品中所蘊涵的文化因子,并分析這種“文化因子”對作家文化心理的深層影響,進而了解他在鄉村與城市、傳統與現代之間徘徊、迷惘的矛盾心態后,不得不說:“莫言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具有憂患意識的農民作家。”
[1] 愛克曼.歌德談話錄[M].朱光潛,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59.
[2]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
[3] 陳思和,何清.理想主義與民間立場[J].中山大學學報,1999(5):25.
[4] 陳思和.陳思和選集[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165.
[5] 薩默塞特·毛姆.作家筆記[M].陳德志,陳星,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