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論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
——以《新事論》為中心
代 云
(河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 哲學(xué)與宗教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馮友蘭論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
——以《新事論》為中心
代 云
(河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 哲學(xué)與宗教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0002)
馮友蘭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以家為本位的生產(chǎn)方法,孝在傳統(tǒng)中國(guó)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忠是通過(guò)孝成為一種道德而被接受和實(shí)踐的。他還認(rèn)為近代以來(lái)孝的地位發(fā)生根本變化,不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通過(guò)進(jìn)一步的分析,我們認(rèn)為在傳統(tǒng)中國(guó),孝的地位不僅來(lái)自生產(chǎn)家庭化這一“共相”,還根源于中國(guó)無(wú)宗教傳統(tǒng)這一“殊相”。
馮友蘭;孝道;《新事論》
馮友蘭(1895-1990),現(xiàn)代中國(guó)著名哲學(xué)(史)家,新理學(xué)哲學(xué)體系的創(chuàng)始人。他主張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要“接著講”,他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特別是宋明理學(xué)的批判式繼承是中國(guó)哲學(xué)返本開(kāi)新的典范。
《新事論》寫(xiě)于1937年6月,是馮友蘭先生“貞元六書(shū)”之一。該書(shū)共十二篇:別共殊、明層次、辨城鄉(xiāng)、說(shuō)家國(guó)、原忠孝、談兒女、闡教化、評(píng)藝文、判性情、釋繼開(kāi)、論抗建、贊中華。《新事論》中的前兩篇相對(duì)于后十篇而言,前者重在“講理”,后者重在“說(shuō)事”。“別共殊”、“辨城鄉(xiāng)”、“說(shuō)家國(guó)”、“原忠孝”與本文關(guān)系密切。本文以此為文獻(xiàn)根據(jù),探討馮先生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批判與反思。
一、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物質(zhì)基礎(chǔ)
馮友蘭先生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以家為本位的生產(chǎn)方法。他是從哲學(xué)角度一步步地得出這個(gè)結(jié)論的。
1.用類(lèi)的觀點(diǎn)看文化,從經(jīng)濟(jì)制度的不同說(shuō)明中西的不同。在“別共殊”中,馮先生解釋了共相與殊相,認(rèn)為殊相是個(gè)體所有之性,共相是某一類(lèi)事物之理。他說(shuō):“每一個(gè)體所有之許多性,各不相同。所以個(gè)體是特殊底,亦稱殊相。而每一類(lèi)之理,則是此一類(lèi)的事物所共同依照者,所以理是公共底,亦稱共相。”[1]198
然后他從類(lèi)的角度分析個(gè)體之性,區(qū)分個(gè)體的主要性質(zhì)與偶然性質(zhì):“從某類(lèi)之觀點(diǎn),以觀某個(gè)體,則某個(gè)體于此方面所有之某性,即是其主要底性質(zhì),其所有之別底性,即是其偶然底性質(zhì)。”他用這種區(qū)分方法來(lái)研究文化類(lèi)型,認(rèn)為從個(gè)體的觀點(diǎn)所說(shuō)的文化是文化的殊相,從類(lèi)的觀點(diǎn)所說(shuō)的文化是文化的共相。 他說(shuō):“我們可從特殊的觀點(diǎn),以說(shuō)文化,亦可從類(lèi)的觀點(diǎn),以說(shuō)文化。如我們說(shuō)西洋文化、中國(guó)文化等,此是從個(gè)體的觀點(diǎn),以說(shuō)文化,此所說(shuō)是特殊底文化。我們說(shuō)資本主義底文化,社會(huì)主義底文化等,此是從類(lèi)的觀點(diǎn),以說(shuō)文化,此所說(shuō)是文化之類(lèi)。”[1]199
他認(rèn)為西洋文化就文化的類(lèi)型而言,是近代文化或現(xiàn)代文化,所謂中西之不同實(shí)是古今之異。
在“辨城鄉(xiāng)”中,他按“別共殊”中留下的問(wèn)題,從文化的類(lèi)型來(lái)說(shuō)中西之異。他認(rèn)為:“英美及西歐等國(guó)所以取得現(xiàn)在世界中城里人的地位,是因?yàn)樵诮?jīng)濟(jì)上它們先有了一個(gè)大改革。這個(gè)大改革即所謂產(chǎn)業(yè)革命。這個(gè)革命使它們舍棄了以家為本位底經(jīng)濟(jì)制度,經(jīng)過(guò)了這個(gè)革命以后,它們脫離了以社會(huì)為本位底生產(chǎn)方法,行了以社會(huì)為本位底經(jīng)濟(jì)制度,這個(gè)革命引起了政治革命及社會(huì)革命。”[2]222
這樣就可以從經(jīng)濟(jì)制度的不同界定文化類(lèi)型的不同。經(jīng)濟(jì)制度就成為使某文化之所以為某文化的理,也即共相。
2.從家本位的經(jīng)濟(jì)制度論說(shuō)傳統(tǒng)中國(guó)以孝為中心的道德規(guī)范。馮先生在“說(shuō)家國(guó)”篇中從中國(guó)近百年來(lái)經(jīng)過(guò)的變化探討了兩種文化類(lèi)型,即生產(chǎn)家庭化的文化和生產(chǎn)社會(huì)化的文化。
他認(rèn)為文化類(lèi)型與生產(chǎn)制度相表里。“有了以家為本位底生產(chǎn)制度,即有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為生產(chǎn)家庭化底文化。有了以社會(huì)為本位底生產(chǎn)制度,即有以社會(huì)為本位底社會(huì)制度。以此等制度為中心之文化,我們名之為生產(chǎn)社會(huì)化底文化。”[3]230這是從生產(chǎn)制度的不同來(lái)解釋文化類(lèi)型的不同,而生產(chǎn)制度的不同又來(lái)自生產(chǎn)方法的不同。“用家為本位底生產(chǎn)方法生產(chǎn),即是所謂生產(chǎn)家庭化。”[3]231
他認(rèn)為傳統(tǒng)中國(guó)即是生產(chǎn)家庭化的社會(huì),在這種社會(huì)中,“一個(gè)人的家是一個(gè)人的一切”,因此“在生產(chǎn)家庭化底社會(huì)里,一切道德,皆以家為出發(fā)點(diǎn)、為集中點(diǎn)”。[3]235這一歷史事實(shí)有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特征,“在某種底生產(chǎn)方法之下,社會(huì)必須有某種組織,人必須有某種行為。對(duì)于人此種行為之規(guī)定,即是道德”。“生產(chǎn)方法不是人所能隨意采用者,所以社會(huì)組織及道德亦不是人所能隨意采用者。”[3]236
因此在“原忠孝”一篇中,他說(shuō):“在此種社會(huì)中,‘孝為百行先’,是‘天之經(jīng),地之義’。這并不是某某幾個(gè)人專憑他們的空想,所隨意定下底規(guī)律。照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的組織,其中之人當(dāng)然是如此底。”[4]247
從馮先生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物質(zhì)基礎(chǔ)是以家為本位的生產(chǎn)方法。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孝的地位對(duì)于傳統(tǒng)中國(guó)而言具有客觀必然性和不可選擇性,在中國(guó)歷史上,它是某種生產(chǎn)方法和社會(huì)制度的產(chǎn)物,與這種生產(chǎn)方法和社會(huì)制度在社會(huì)中的主導(dǎo)地位相表里。如果用馮先生常用的術(shù)語(yǔ)來(lái)表述的話,則可以說(shuō),孝對(duì)于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是“習(xí)”而不是“性”。
二、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的功能
1.鞏固以家為本位的社會(huì)組織。馮先生認(rèn)為:“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中,家是經(jīng)濟(jì)單位,是社會(huì)組織的基本。家既是社會(huì)組織的基本,所以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中之人,必以鞏固家的組織為其第一義務(wù)。”[4]247而“舊日所以以孝為道德的中心者,即因孝是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也。在舊日凡可以鞏固家的組織底行為,或可以延續(xù)家的存在底行為,皆是孝的行為。例如舊日兄弟不和,或妯娌不睦,均可稱為不孝底行為。因此等行為,足以招致家之分裂也。在舊日,兄弟分居,雖不是不道德底行為,而亦不是光榮底行為。‘五世同居’雖不是人所必行底道德底行為而卻是很光榮底行為。娶妻生子,亦是孝的行為,因此等行為,乃所以延續(xù)家之存在也。‘不孝有三,無(wú)后為大’,照舊日的看法,人人都有為其祖先傳嗣的責(zé)任”[5]329。
總而論之,孝在傳統(tǒng)中國(guó)是以家為本位的生產(chǎn)方法和社會(huì)制度的產(chǎn)物,反過(guò)來(lái),孝作為一切道德的中心,它又鞏固和強(qiáng)化著家這一基本組織的地位。馮先生認(rèn)為舊中國(guó)社會(huì)組織堅(jiān)固而非一些人所說(shuō)的一盤(pán)散沙,主要就是從這里著眼的。
2.以孝為出發(fā)點(diǎn)盡忠。馮先生說(shuō):“在舊日對(duì)于男子說(shuō),忠孝是為人的大節(jié)……對(duì)于男子來(lái)說(shuō),最大底道德是忠孝。”[4]241一個(gè)男子對(duì)父盡孝、對(duì)君盡忠,是為忠臣孝子。忠與孝之間,“在普通底情形中,須要‘移孝作忠’。因?yàn)椤菩⒆髦摇嗍堑赖碌资隆7彩堑赖碌资拢粋€(gè)孝子都須做,因?yàn)檫@些事都是可以使父母得美名者,可以使‘國(guó)人稱愿然曰:幸哉!有子若此。’凡不道德底事,一個(gè)孝子都不可做,因?yàn)檫@些都是可以使父母得惡名者”[4]246。
這即是說(shuō),傳統(tǒng)社會(huì)中男子盡忠的出發(fā)點(diǎn)和歸宿是盡孝,盡忠是為了盡孝,忠是通過(guò)孝成為一種道德而被接受和實(shí)踐的。
關(guān)于其中的原因,馮先生進(jìn)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先從國(guó)的古今含義之不同論起。如:“舊日所謂國(guó),與我們現(xiàn)在所謂國(guó),其意義大不相同”[3]237,因此不可一概而論之。又如:“舊日所謂國(guó)者,實(shí)則還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國(guó),國(guó)即是皇帝之皇家,所謂家天下是也。所以漢朝亦稱為漢家。”[3]237這實(shí)際上指出了傳統(tǒng)社會(huì)家國(guó)同構(gòu)的特征,雖然馮先生沒(méi)有這樣明確地表述。與此同時(shí),他強(qiáng)調(diào)家相對(duì)于國(guó)、孝相對(duì)于忠在理論上處于優(yōu)先地位。他在評(píng)論程頤關(guān)于東漢趙苞在忠孝之間選擇的觀點(diǎn)時(shí)說(shuō):“從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的觀點(diǎn)看,至少在理論上,孝是在忠先底。”[4]246原因在于:一個(gè)人(在傳統(tǒng)社會(huì)指男人)可以不是君的臣,卻不可能不是父的子。“事君是替人家做事,所以人可以事君,可以不事君。臣如與君不合,可以‘乞骸骨’,可以‘告老還鄉(xiāng)’。但事親則不能如此。子對(duì)于親,不能‘乞骸骨’,亦不能‘告老還鄉(xiāng)’。為什么呢?因?yàn)槭掠H是自己的事,并不是別人的事也。別人的事,我可以管,可以不管;我愿意管則管,不愿管則不管。但我自己的事,則不能不管也。”[4]248此即是人可逃于君,不可以逃于父。父之所以是不可逃的,是因?yàn)檫@種關(guān)系是不可選擇的:一個(gè)人無(wú)法選擇自己的出生,無(wú)法選擇自己的父母。相對(duì)而言,一個(gè)人可以選擇是否出仕、是否事君。這就是孝相對(duì)于忠在理論上處于優(yōu)先地位的原因。
三、孝與忠在實(shí)踐中的沖突與解決
在“原忠孝”一篇中,馮先生用了大量篇幅討論忠與孝的沖突及解決。他把忠與孝的沖突與解決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一般沖突,一種是極端沖突。他論說(shuō)的重點(diǎn)在后者。
一般沖突又有兩種具體情況:一是“一個(gè)人為‘王事’奔走,不能在家侍奉父母……于此時(shí)應(yīng)‘移孝作忠’,這是沒(méi)有什么問(wèn)題底”[4]244。二是“因‘王事’而要犧牲自己,自己如果犧牲,父母即沒(méi)有了或少了一個(gè)兒子”。他認(rèn)為“于此時(shí)應(yīng)‘移孝作忠’,亦是沒(méi)有問(wèn)題底”[4]244。
極端沖突的情形是“一個(gè)人若盡了忠,不但在消極方面不能盡孝,而且在積極方面為他的父母招了‘殺身之禍’,在這種忠孝不能兩全的事例中,忠孝的沖突達(dá)于極點(diǎn)”[4]244。
極端沖突的解決,馮先生以后漢趙苞的事不入“孝義傳”而入“獨(dú)行傳”來(lái)說(shuō)明儒家的解決之道,即合乎中道。趙苞在面對(duì)沖突時(shí)“破賊以為忠臣,后殉母以為孝子”。這被認(rèn)為是“偏至”而非“周全之道”[4]245。馮先生認(rèn)為這種評(píng)價(jià)與家本位的道德要求有關(guān)。他說(shuō):“趙苞的行為雖是很壯烈底,但以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說(shuō),他的如此行為尚不是最得當(dāng)?shù)祝床缓虾踔械馈!盵4]245
如何才是“合乎中道”的解決辦法,馮先生舉程頤的觀點(diǎn)來(lái)說(shuō)明:“趙苞馬上辭遼西太守之職,把軍隊(duì)及城池交與別底漢將,然后他自己以個(gè)人資格,往贖其母。”[4]245他認(rèn)為這種辦法雖然缺乏可操作性,但道理是說(shuō)得通的。“因?yàn)檎找约覟楸疚坏咨鐣?huì)制度,一個(gè)人是他的家的人,他在他的家外擔(dān)任職務(wù),是替別家辦事,在朝做官,是替皇家辦事,皇家亦是別家也。所以若在平常情形下,人固然須先國(guó)后家,移孝作忠,但如因替別人做事,而致其父母于死地,則仍以急流勇退,謝絕別人之約,還其自由之身,而顧全其父母。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中,這是說(shuō)得通底。在這類(lèi)底社會(huì)中,人本是以家為本位底。”[4]246
這即是說(shuō)在傳統(tǒng)社會(huì),忠孝絕對(duì)沖突時(shí),解決方法是孝先于忠。馮先生仍以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制度及相應(yīng)的道德要求來(lái)作解釋,有充分根據(jù)。
四、傳統(tǒng)孝道的現(xiàn)代境遇
1.孝不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由于馮先生是從家本位的社會(huì)制度對(duì)人的行為的要求來(lái)解釋孝在傳統(tǒng)社會(huì)的地位的,因此,他對(duì)近代以來(lái)傳統(tǒng)孝道的現(xiàn)代境遇也是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詮釋的。他說(shuō):“在新底生產(chǎn)方法,新底經(jīng)濟(jì)制度正在沖破家的壁壘的時(shí)候,家的壁壘不復(fù)是人的保障,而變成了人的障礙。……孝是所以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家的壁壘既成了人的障礙,所以孝在許多方面,亦成了人的障礙。”[4]250這仍是從孝的物質(zhì)基礎(chǔ)來(lái)進(jìn)行分析。
當(dāng)中國(guó)社會(huì)近代以來(lái)從以家為本位向以社會(huì)為本位的生產(chǎn)方法、社會(huì)制度轉(zhuǎn)變時(shí),孝的地位發(fā)生根本變化。“在以社會(huì)為本位底社會(huì)中,人在經(jīng)濟(jì)上,與社會(huì)融為一體,其全部底生活,亦是與社會(huì)融為一體,在此等社會(huì)中,家已不是社會(huì)組織的基本,所以在此等社會(huì)中,人亦不以鞏固家的組織為第一義務(wù),或亦可說(shuō),在此等社會(huì)中,作為經(jīng)濟(jì)組織底家的組織,已不存在,所以亦無(wú)可鞏固了。在此等社會(huì)中,人自然不以孝為百行先。……在此等社會(huì)中,孝雖亦是一種道德,而只是一種道德,并不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4]247基于這個(gè)理由,他認(rèn)為仁義禮智信是“常”,而忠孝不是“常”。他說(shuō):“此五常是無(wú)論什么種底社會(huì)都需要底,這是不變底道德。”[5]327“忠孝是因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而有底道德,這一點(diǎn)昔人雖未看清楚,但昔人雖以忠孝為人之大節(jié),但不名之曰常,這是很有意義底。”[5]328
2.對(duì)五四批判的反批判。基于對(duì)傳統(tǒng)孝道與家本位社會(huì)制度的關(guān)系,馮先生在“原忠孝”一篇里對(duì)清末民初文化批判者對(duì)孝道的批判進(jìn)行了理論反思與回應(yīng)。
他批評(píng)民初人的見(jiàn)解:“民初人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底禮教’,對(duì)于孝特別攻擊。有人將‘萬(wàn)惡淫為首’改為‘萬(wàn)惡孝為首’。他們以為,孔家店的人,大概都是特別愚昧底。他們不知道,人是社會(huì)的分子,而只將人作為家的分子。孔家店的人又大概都是特別殘酷,不講人道底。他們隨意定出了許多規(guī)矩,叫人照行,以致許多人為這些規(guī)矩犧牲。此即所謂‘吃人底禮教’。”[4]249他著重指出這種見(jiàn)解作為一種思想是極其錯(cuò)誤的,他分析說(shuō),民初人以為孔子、朱子以一己之見(jiàn)加之于整個(gè)社會(huì),人們愚昧地接受不知反抗,直到民初,人們才覺(jué)悟、反抗,他評(píng)價(jià)說(shuō):“民初人自以為是了不得底聰明,但他們的自以為了不得底聰明,實(shí)在是他們的了不得底愚昧。他們不知,人若只有某種生產(chǎn)工具,人只能用某種生產(chǎn)方法;用某種生產(chǎn)方法,只能有某種社會(huì)制度;有某種社會(huì)制度,只能有某種道德。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huì)中,孝當(dāng)然是一切道德的中心及根本。這都是不得不然,而并不是某某幾個(gè)人所能隨意規(guī)定者。若譏笑孔子,朱子,問(wèn)他們?yōu)槭裁粗v他們的一套禮教,而不講民初人所講者,正如譏笑孔子,朱子,問(wèn)他們?yōu)槭裁醋呗纷R車(chē)轎子,而不知坐飛機(jī)。孔子,朱子為什么不知坐飛機(jī)?最簡(jiǎn)單底答案是:因?yàn)槟菚r(shí)候沒(méi)有飛機(jī)。晉惠帝聽(tīng)說(shuō)鄉(xiāng)下人沒(méi)有飯吃,他問(wèn):‘何不食肉糜?’民初人對(duì)于歷史的看法,正是此類(lèi)。”[4]250
馮先生一方面肯定對(duì)孝的這種批判是中國(guó)社會(huì)的轉(zhuǎn)變(從家庭本位向社會(huì)本位)在某一階段內(nèi)應(yīng)有的現(xiàn)象,另一方面分析了歷史上孝道觀念與實(shí)踐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由此而肯定其歷史的合理性。這一判斷不論方法還是結(jié)論都是科學(xué)的,合乎歷史事實(shí)并經(jīng)得起時(shí)間考驗(yàn)。在第一代現(xiàn)代新儒家中,他的回應(yīng)最直接也最有力度和深度。
五、結(jié) 語(yǔ)
如上所論,馮友蘭先生從物質(zhì)基礎(chǔ)、功能、實(shí)踐困境、現(xiàn)代境遇等方面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孝道所作的分析與闡釋是科學(xué)的,結(jié)論令人信服,是經(jīng)得起檢驗(yàn)的。
秉承馮先生對(duì)中國(guó)哲學(xué)“接著講”的態(tài)度,如果有所增益和補(bǔ)充的話,也許在于對(duì)孝的獨(dú)特性來(lái)源的解釋。馮先生說(shuō):“在未產(chǎn)業(yè)革命底地方,無(wú)論這地方是東是西,生產(chǎn)方法在某一個(gè)階段內(nèi),都是如此以家為本位。”[3]231
這里有一個(gè)問(wèn)題:如果在生產(chǎn)社會(huì)化之前,世界各地區(qū)都曾實(shí)行以家為本位的生產(chǎn)制度,那么為什么獨(dú)有中國(guó)會(huì)形成如此深厚的孝文化傳統(tǒng),變成一種世界獨(dú)有的文化現(xiàn)象?這里的獨(dú)特性根源何在?馮先生的主張可以解釋“有”,沒(méi)有解釋“獨(dú)有”。
關(guān)于這一點(diǎn),也許可以從傳統(tǒng)中國(guó)缺少宗教傳統(tǒng)這一獨(dú)特的文化性格來(lái)說(shuō)明。崔大華先生在解釋儒學(xué)的倫理道德特質(zhì)的形成時(shí),以古印度宗教形態(tài)演進(jìn)過(guò)程為參照,認(rèn)為在古代印度經(jīng)歷了從祭祀宗教向皈依宗教的過(guò)程。而在中國(guó),連一般過(guò)程也沒(méi)有發(fā)生:“一個(gè)巨大的政治變遷——殷被周滅亡,阻止了、破壞了這一古代宗教思想和實(shí)踐發(fā)展的一般進(jìn)程。一種十分獨(dú)特的社會(huì)政治原因,使中國(guó)古代思想發(fā)展主潮由宗教性質(zhì)的轉(zhuǎn)折向道德性質(zhì)的。”[6]
實(shí)際上,這一轉(zhuǎn)向不僅可以解釋儒學(xué)的倫理道德特質(zhì)的形成原因,由于儒學(xué)作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主流的地位,還可以解釋傳統(tǒng)中國(guó)缺少宗教傳統(tǒng)這一現(xiàn)象。由于沒(méi)有成熟的宗教,中國(guó)人無(wú)彼岸觀念,價(jià)值是在此世尋找和實(shí)現(xiàn),而此世的生活對(duì)于傳統(tǒng)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就是家中的生活。因此,在傳統(tǒng)中國(guó),孝的地位不僅來(lái)自生產(chǎn)家庭化這一“共相”,還根源于中國(guó)無(wú)宗教傳統(tǒng)這一“殊相”。
[1] 馮友蘭.新事論·別共殊[M]//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馮友蘭.新事論·辨城鄉(xiāng)[M]//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3] 馮友蘭.新事論·說(shuō)家國(guó)[M]//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4] 馮友蘭.新事論·原忠孝[M]//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 馮友蘭.新事論·贊中華[M]//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6] 崔大華.儒學(xué)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責(zé)任編輯:祝春娥)
2014-04-05
河南省社科院資助項(xiàng)目(2013D17)
代 云(1973- ),女,河南舞陽(yáng)人,河南省社會(huì)科學(xué)院哲學(xué)與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法學(xué)碩士。
B82-09
A
2095-4824(2014)04-001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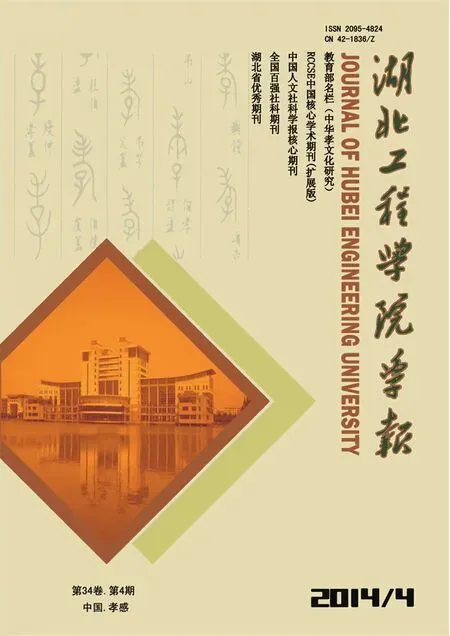 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年4期
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年4期
- 湖北工程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侵權(quán)責(zé)任中損益相抵原則的適用范圍及計(jì)算方法
- 企業(yè)慈善責(zé)任的效益分析與對(duì)策研究
- 西人眼中的中國(guó)文化與中國(guó)人
——《十八世紀(jì)西方中國(guó)國(guó)民性思想研究》 - 地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學(xué)邏輯
——以建國(guó)以來(lái)農(nóng)村土地產(chǎn)權(quán)制度的嬗變?yōu)榫€索 - 論輿論監(jiān)督對(duì)法院審判活動(dòng)之影響及規(guī)制
——兼論監(jiān)督與審判的關(guān)系 - 法治視野下的警察形象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