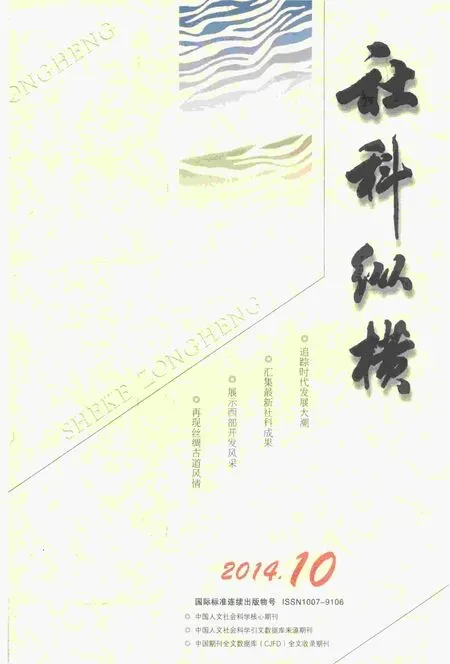中國當前法律文化沖突成因及整合功能
劉 葦
(西南政法大學 重慶 401120)
法律文化沖突就是法律文化與其所處社會生活之間的非耦合狀態在法律文化自身中的具體表現。法律文化沖突通常表現為法律文化觀念形態和制度形態兩個維度上與社會現實之間的不適應。就法律制度、法律規范、法律設施等法律文化的制度形態而言,往往能夠經由國家的推動通過立法、法律移植、制度變革等手段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更新與建立。但變化相對緩慢的法律文化觀念形態常常成為阻礙法律文化制度形態更新的力量來源,并且在社會生活中排斥新生的制度形態,從而造成法律文化內在的激烈沖突。在法律文化兩個不同層面的沖突當中,法律文化觀念形態沖突是其根本性沖突所在。這或許是因為,法律文化觀念形態沖突不僅僅表征著法律中所蘊含的態度和價值與現實之間的沖突,它更表現為一種深層次的上位文化范疇與現實之間的沖突。當我們試著去探求我國當前社會嚴重法律文化沖突成因的時候,我們無法逾越文化變遷的軌跡。我國傳統法律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觀念形態是引發我國當下法律文化沖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傳統法律文化觀念形態引發的沖突
(一)傳統法律文化的獨特性引發沖突
法律文化沖突往往發生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尤其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革或者革命時,法律文化沖突往往表現的尤為激烈。縱觀我國近代歷史,至從清末以降,我國社會就一直處于劇烈的變遷當中。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再到新文化運動,直至新中國成立,救亡圖存就一直是我國社會的主旋律。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如今,發展社會經濟、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則成為了新的社會主題。但無論是救亡圖存也好,還是改革開放也好,都使得我國社會始終處于一種劇烈的變遷當中,法律作為政府應對社會變遷所產生的紛繁復雜社會問題的有效工具,同樣也必然處于劇烈的變遷中。而移植和借鑒外域的先進法律文化作為一種立竿見影的途徑,成為了我國法律被動適應社會快速變動最為重要的方法與手段。這導致我國自身的法律文化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外來法律文化的不斷沖擊,源于傳統文化的制度形態早已土崩瓦解成為歷史的塵埃。但其繼承于傳統文化的觀念形態卻依然存在,并且傳統法律文化觀念形態“在我國法律生活中的統治地位并沒有太大改變,只不過由前臺轉為幕后、由制度統治變為思想統治而已。”[1]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雖然在一個多世紀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為了應對社會關系變化我國引入了大量外來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理念。但是,在中國人與法律相關的態度與價值觀念中,中國自身的文化依然牢牢的占據著統治地位。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孕育出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它與各種外來文化有著巨大的差異,無論是關于人的本質、社會結構、事實建構方式還是宇宙等概念在文化上的內涵都各不相同。但是,正是這些由文化所設定的概念賦予了生活以意義。法律無論是其自身的樹立又或是適用,都離不開這種賦予生活以意義的文化環境。法律不僅僅是對爭議的解決,更為重要的是對人的行為做出界定,并且法律對人行為地界定必然是在文化為其設定的意義框架內完成的。在文化上而言,法律所定義的乃是一種關涉人類行為及意義的狹義領域,即塑造人類社會規范行為并賦予其含義、價值、目的和方向。法律文化作為文化的一個下位概念,由于文化自身獨特性的存在使得法律文化獲得解釋的框架具有了獨特性,因此文化所具有的獨特性必然映射于法律文化之中。文化所具有的獨特性導致中國法律文化與外來法律文化之間在法律文化觀念形態上存在巨大的差異,這一差異正是我國文化獨特性的具現化表現。
一個民族的文化決定了對他們對待法律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又決定了這個民族應當具有怎樣的法律。法律心理、法律意識、法律思想體系等法律文化觀念形態,都與人的精神領域相關,并且都表現為人對待法律的一種心理狀態。雖然,從法律心理到法律意識再到法律思想體系,人們對待法律的態度經歷了一個由特殊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過程,但卻并未溢出“態度”這一范疇。一個民族對待法律的態度可以被看做一種歷史經驗,一種群體在面對法律時源于共同文化而產生的共同歷史經驗,這種共同體的歷史經驗被以法律文化觀念形態這一形式保留在這一共同體的文化中。傳統法律文化觀念形態并不僅僅是時間投射在歷史長河中的浮光掠影,而是過去與未來之間那種延續性的意識與時間自我的沉淀,是反身向我們的祖先尋求向未來世界前行的啟示。它不僅僅記描述著我們過去如何對待法律、權威,也必將在同樣的領域影響著現在的我們。在運用我們自身的文化塑造我們自己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本民族自身的法律文化傳統,使得我們先于接觸“文本上的法律”之前,就已經獲得了關于什么是法律權威、什么是司法、什么是法律的知識。我們是在文化中獲得了關于法律最為重要的知識,而非是在法律的文本中。是我們自己特殊的文化形成了我們獨特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塑造了我們的法律人格,當移植而來的法律與我們自身的法律文化相背離或矛盾時,法律文化沖突就在所難免。
(二)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宗族”觀念導致沖突
不同于西方法律是圍繞著陌生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而展開的,我國傳統法律是圍繞著宗族這一獨特的社會關系而展開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在我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無法產生權利義務這一對被西方法律視為生命的概念,而將道德倫理與家庭倫理奉為整個法律的核心。在生活于宗族關系中人們的眼光中權利義務關系是那么的缺乏人情味,是那樣的赤裸裸。血緣關系使人們無論是對利益的追求,還是對由此產生的矛盾的解決都被包裹在倫理道德之中,從而具有了濃濃的人情味。
清末以降,清政府在強大的外在壓力作用下開始鼓勵工商,走上資本主義改良道路,導致農村原本的經濟結構遭到破壞,土地大量兼并、農村出現大量的閑散勞動力、農村人口出現流動,時至今日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建設,那種傳統意義上的依附于土地和血脈的宗族體系已經基本瓦解。但是,在中國社會,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一種類似于宗族社會的熟人社會關系依然繼續存在并且依然強大。可以說宗族關系不僅沒有就此退出歷史舞臺,并且在我國社會繼續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只不過是由臺前轉變到臺后而已,由舊有的單純血緣為紐帶的宗族轉變為以血緣和鄰里關系為紐帶的“宗族”。正如前文所言,法律文化的變遷相對于劇烈的社會變遷總是相對緩慢的,在許多法律無法觸及的社會空間,傳統法律文化依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我國較為落后的農村地區,在這些地區,社會依舊是一個熟人社會或者說“類宗法社會”。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社會生活更多依靠的是熟人之間的人際關系和習俗來調整的,舊有的習俗與倫理道德強烈的排斥著現代法律文化所提倡的權利義務關系。在權利義務關系與舊有習俗與倫理道德偶合的地方,它們相安無事,但一旦權利義務關系與習俗和倫理道德出現非偶合現象時,人們就會有意的規避法律而習慣性的遵循習俗和倫理道德。在熟人關系網絡中,大家如同在一種新的“宗族”關系中一樣互惠互利,相互依賴,誰都不敢獨立于整個“宗族”網絡之外。恰如中國的諺語所言“多個朋友,多條路”,在這一新的“宗族”之中人們依舊不敢輕易的碰觸和破壞人情關系這一底線,習俗與倫理道德依舊是人們在處理日常事務時首要遵循的行為規則。人們依然習慣采用一套更加靈活、特殊的以人際關系為脈絡的規則來處理日常生活中的事務而非通過現代法律中的權利義務關系來尋求問題的解決,或者說人們是在這種新的“宗族”社會文化中去定義和理解規制體系并運用日常行為規制的。
“在我們社會的激速變遷中,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2]正是這種鄉土社會的習俗和倫理道德規范與現代法治社會所倡導的以權利義務核心的社會規范之間的不適應造成了當前我國當前社會法律文化的劇烈沖突。
(三)傳統法律文化中“無訟”觀念引發沖突
與西方現代法律文化不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并不把法律訴訟視為一種和平解決爭端,對受侵害法益進行救濟的有效手段,相反往往盡力避免法律訴訟,將法律訴訟視為一種不得已的爭端解決方式。“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歷來奉行和諧、‘和為貴’的無訴價值取向,從古傳頌至今,對我國法律制度的發展和變革產生深遠的影響。在我國古代,‘和為貴’、‘能忍者自安’等法律文化思想廣為流傳。受這種思想的影響,當人們之間發生糾紛時,首先想到的是用傳統風俗、宗教禮法、倫理道德等規范來進行調整,從而達到所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理想狀態,忽視了法律的存在。”[3]這種無訟思想在官與民兩個層面導致了當前社會的法律文化沖突。首先,在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當中并不存在獨立的司法制度,往往地方最高行政官員同時也是地方最高司法官員,地方行政體系兼顧著司法體系的職能。“這種地方行政官員兼任司法官員的獨特形式使得司法目的往往屈從于行政目的,行政官員簡單、片面地將司法視為一種行政手段致使司法失去應有的獨立地位。”[4]對于地方官員而言無訟通常是一種值得夸耀的政績,是地方和睦治理得法的有力旁證,所以傳統的地方官員往往傾向于抑制訴訟。這一現象在今天社會依然十分常見,官員常常在總結工作時將訴訟數量下降視為一種值得夸耀的政績。這種對訴訟數量減少的夸耀不源于社會矛盾的真正減少,而僅僅是無訟法律文化的一種映射。在社會關系日益復雜的今天,社會利益沖突是傾向于增多而非減少的。法律作為一種公平的矛盾解決途徑,當更多的矛盾沖突被納入到法律體系通過訴訟解決的時候,意味著社會公平在更大的范圍內被得以實現。而反之著意味著更多的私力救濟的發生,意味著不不平等的概率在升高。或許我們可以將當下司法界的大調解也視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無訟理念的具體表現。其次,對一般人而言,在傳統法律文化無訟觀念的影響下現代法律意義上的民事關系沖突幾乎消解于宗族內部,只有當人們嚴重觸犯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刑法時,人們才會進入訴訟的領域。通過法律訴訟來解決問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看來是家庭或家族失和的表現,是家丑的外揚。無訟思想可以說被深深地嵌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觀念當中,在中國人看來訴訟是一種社會病態,不和諧的表現。就個人而言訴訟既是一件備受社會非議的不光彩事情,同時也是一件個人懦弱無能的表現。因為,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中只有當你無法運用自己宗族或個人社會關系去有效解決沖突的時候,你才會求助于法律。時至今日,中國人依舊深受無訟思想的影響,當沖突和矛盾發生的時候,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發動親朋好友,動用一切社會關系進行私力救濟,而非求助于法律通過訴訟的途徑解決問題。
二、法律文化沖突的整合功能
我國當前社會所面臨的法律文化沖突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異域文化間的對撞并非僅僅意味著混亂與沖突,同時也因為著新生與融合。這里所言的傳統法律文化并不是一個靜態概念,并不是單純的意味著對過去的繼承和保留,而是一種對死者或者過去的活的信仰。“傳統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在歷史進程中取得的確定形式的繼續性,這種連續性包含著兩種相互矛盾而又必須相互整合的因素,那就是保守的因素和變革的因素。”[5]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保守因素使傳統法律文化保持其固有觀念形態和制度形態連續性。催生了以新的利益關系為紐帶的熟人社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規則體系。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和傳承,它已經被內化到民族精神當中,成為中國人的一種潛移默化的行為規則,具有了超穩定結構。同時,傳統法律文化中所蘊涵的變革因素促使其不斷變遷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進而維持傳統法律文化的存在,使得傳統法律文化避免被高速發展的社會所淘汰依舊得以在當前社會發揮作用。而法律文化沖突正是法律文化中所蘊含的保守與變革兩種截然相反的力量之間達到平衡的媒介。一切在矛盾中展開,一切在矛盾中發展,并在矛盾中得以統一。沖突的力量打破了保守的壁壘使得變革得以發生,但沖突同時使得保守的力量影響了變革的速度使之無法完全偏離傳統文化的解釋框架。
法律文化沖突,無論是法律文化觀念沖突還是法律文化制度形態沖突都是在社會變遷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法律文化整合的現象。無論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還是西方法律文化又或是前蘇聯法律文化,無論其影響力的大小,他們都在當前的中國社會中共同存在,并影響著我國法律的運行。在法律文化的沖突中,各種法律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這種不同法律文化間的整合必然超越體用之別,并有機統一于我國現實社會之中,形成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法律文化。可以預期的是,這一整合過程必然孕育出屬于當代中國的法律文化。這種法律文化不必以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為體,但其中必然蘊含著中國文化自身的獨特風韻,也不必以任何外來的法律文化為用,卻應該具備那些人類法律文化中已然成熟的價值追求,并以對人的終極關懷為最終歸宿。[6]
三、結語
總之,當前中國社會所表現出來的法律文化沖突既可以視為傳統法律文化中保守因素對社會變遷的消極抵抗,也可以視為傳統法律文化中激進因素自我脫變過程中所經歷的陣痛,或者兩者兼而有之。中國法律文化的未來走向似乎難以捉摸,是固守傳統,還是全盤西化,或是在中體西用的范疇內騎墻而行,又或是走出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道路。但當我們回顧現實,超越文本與概念的范疇僅以實踐為標尺去審視法律文化的未來的時候。我們或許會發現固守傳統、全盤西化、中體西用都只是我國法律文化發展過程中蜿蜒的過程而非方向。市場化的經濟發展必然摧毀傳統中的流弊,將社會推入一個陌生人的社會,而堅守“中國人”這一定義的我們必然承載我們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或許具有中國時代特色的法律文化才是唯一的方向與目標。
[1]劉作翔.法律文化理論[M].北京:商務出版社,2001:31-32.
[2]王立民.法文化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72.
[3]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三聯書店,1985:46.
[4]楊顯濱.論當代中國法律文化價值的依然歸屬[J].河北法學,2012(2):137.
[5]羅揚.網絡與司法:困境與契機并存[J].河北法學,2013(1):185.
[6]李鵬程.當代文化哲學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