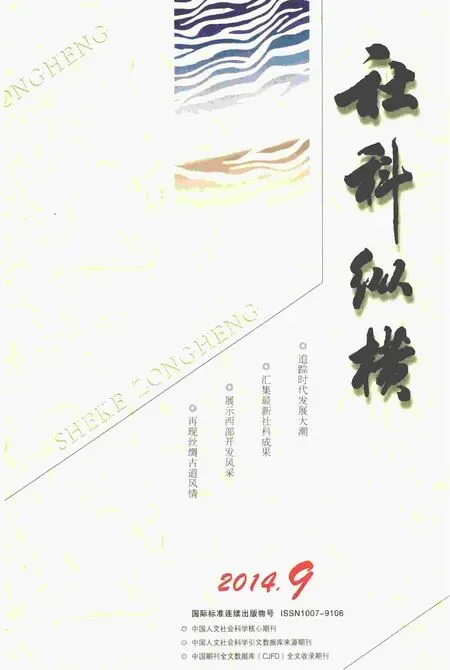論莫言小說歷史與虛構敘事的并置——以《生死疲勞》、《豐乳肥臀》為例
王 萍
(洛陽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河南 洛陽 471934;蘭州大學文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當代著名作家莫言自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他的眾多作品一時“洛陽紙貴”。其實,莫言的文學地位,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先鋒文學中就已凸顯。如他的小說《紅高粱》,由于電影媒介的傳播效應,一時被人們所關注,也得到了文學界的高度評價,被認為是先鋒小說的代表作,甚至也有說是新歷史小說的代表作。此后,他的諸多小說作品不斷涌現,尤其是長篇小說,更趨繁盛,如《檀香刑》、《四十一炮》、《蒜薹天堂歌》、《生死疲勞》、《豐乳肥臀》、《紅蝗》、《蛙》等小說。他把這些皇皇巨著,源源不斷地推向文壇,拋向讀者,使人應接不暇。總體看來,他的小說既對傳統有所繼承,又大膽借鑒西方現代藝術方法,采用民間敘述形式,對歷史、人物、時代、事件等給予合理而大膽的想象,呈現出歷史真實與虛構的并置敘事方式。本文僅擷取《生死疲勞》[1]與《豐乳肥臀》[2]兩部小說作為個案,對莫言小說的敘事方式給予細致地解讀和剖析,以此關注他對傳統小說和現代小說的敘事方式的藝術處理,也為當下小說的創作探新提供藝術探索的資源借鑒和啟悟。
一、生命形式幻象的訴愿
小說作為一種敘事藝術,它既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又是對創作主體想象虛構的展現,二者融合在一起才構成小說的敘事內涵。但一般來說,歷史敘事或現實敘事常常是主要敘事方式,虛構的敘事成分往往隱含于歷史或現實的敘事中。有關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關系,羅蘭·巴爾特、海登·懷特等西方文論家認為是相等同的,“歷史敘事=文學敘事=虛構敘事”[3](P181),簡化為歷史敘事等于虛構敘事,很顯然,這種等式是值得質疑的。如盧波米爾·道勒齊爾在《虛構敘事與歷史敘事:迎接后現代主義的挑戰》一文中明確說:“虛構的建構和歷史的建構都是可然世界,但歷史世界受到的限制并不會施加于虛構世界。”并承認,“虛構與歷史之間雜多而持久的交換”[3](P175)是存在的,“并不否定各種相互滲透的情況”[3](P194),但前提是要肯定二者的對立關系,并不是等同的。在莫言小說的敘事中,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并不是等同的,二者的關系呈現給我們的多是歷史或現實敘事與虛構敘事的并置(也有相互融合的時候),有時想象虛構的敘事部分更突顯,有評論者說這是莫言狂歡化敘事話語的張揚[4],當然這與創作主體的成長經驗、個性、文學觀、藝術構思,對歷史文化的認知,以及創作主體在把生活素材轉化為藝術形式的審美觀念等有關聯。文學藝術“是生活的反映,但在把生活轉化為藝術的過程中,作家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介。作家在把現實轉化為藝術的過程中,”現實“本身就是多種多樣的,而通過作家的真實探求和睿智的發現,就會使得藝術多彩紛呈。”[5]在莫言的許多小說中,我們明顯感覺作為創作主體,他在把歷史、時代、人物等轉化為藝術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人的主體性作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大膽的豐富想象。他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和《豐乳肥臀》,尤其彰顯了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并置藝術,融合了傳統與現代的藝術構思,傳達出莫言的審美認知和敘事風格。
長篇小說《生死疲勞》主要敘述了人生的六道輪回,表達了人對現實的認識和理想的渴求,實際也是通過對現實人生生命形式幻象的種種表現,揭示幻象背后的種種真實訴愿。這部作品的敘事方式是對文學傳統的一種借鑒,作品的結構布局采用古典章回小說體式,每章以主要內容的關鍵詞相連貫的句式標識出來,概述了內容要義,交代了主要人物、主要行為、主要場所、主要事由等,猶如讀張恨水的《春明外史》等通俗小說的感覺。各章標題用語整齊、押韻,多呈七言式,也有八言式、四言式。總之,各章標題概括各章要義,言簡意賅,各章標題連接起來,讀者就能對該小說作品的主要內容有所了解。
在敘述方法上,這篇小說多次采用長句、“象”字的比喻句,以及豐富的意象,如牛、馬、驢、糞便等,還有各種感官如各種知覺的連用,視覺、聽覺、感覺等并用,所有這些極大地調動了讀者的各種感官活動。再者,各種色彩詞的運用,如紅、黃、藍、黑、白等,則達到了電影的影像效果,甚至達到一種繪畫的功效。正如馮驥才所說:“文學是用文字繪畫”,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文字都是色彩。”[6]更何況這些色彩文字描繪出來的景象,更是一副五顏六色的人生圖景;還有“血腥”一詞的出現、“啊噢—啊噢”的反復出現,等等,大大激起了讀者的相應感官,使之產生強烈的即時效應。此外,作品還運用了回憶方式引出作品人物,如第一章引出馬文斗、白氏、迎春、秋香、黃瞳,及主人公西門鬧本人。對歷史的追蹤索源,如古來就有“不勞動者不得食”;“均分土地,歷朝都有先例”等等。作者還使用了大量的民間俗語,并且押韻、節奏流暢、意義明了。敘述結構上,根據人物的輪回次序,各章有序敘述。作品第一章交代故事的時間:1950年元旦。人物西門鬧是作品敘述人物之一,是一個勤勞、善良的地主,如作品寫到他每天早起去拾糞、掩埋“路倒”之人、雪中撿拾黃瞳等行為。接著第二章交代了另一人物藍臉的來歷、面貌等,從中可以管窺出莫言對農村生活的熟知。作品的敘述語言豐富多彩,簡潔明快,有節奏、有韻律,多俗語、諺語等民間語言。作者語言運用自如,信手拈來,其意也現,恰到好處,輕松詼諧中盡顯作者語言的狂歡化風格。作品前四章給人的感覺是:想象奇特,語言豐富,比喻形象,而且排山倒海地連續出現。但同時也給人以充滿殘酷、血腥、丑陋、惡俗的感覺,如人死屌不死、糞便、驢性歡等詞的運用,驢交配采用人的感覺敘寫,讓人感覺粗俗不雅。
作品在敘述歷史事實的同時,作者也讓讀者置于在敘述人幻想的想象中去解讀歷史。如20世紀50年代,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大事件,尤其文革中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描述和揭示,采用西門鬧(人)、西門驢、西門牛、西門豬等各自的視野,審視和觀察歷史中的人物和歷史的進程,以幻想、夢想等想象形式來揭露社會的現實,傳達出作者對歷史的闡釋和批判,展現了特定歷史中的風云人物,他們擁有濃厚的紅色革命思想,竭力擺脫身上的各種羈絆。如人物西門金龍的六親不認,過分張揚自己,展示所能以達到上爬的目的。小說故事性強,敘事時間成線性推進,敘述清晰,人物在故事敘述中彰顯了性格,人物所處的場景明確。莫言的這部小說,完全具備了傳統小說的三大基本要素:故事、人物和環境。三要素在整個小說中非常突出,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傳統小說三要素在故事中的呈現,其中融入了現代小說的諸多現代元素。如敘述視角的獨特和多樣,小說人物的別樣風采展現,語言形式的民間與現代的混融,在推延故事情節中顛覆和消解一些民間俗語的原意。小說體式的新穎(呈現代式章回體式,各章可以獨立,但合起來就構成了整卷或整篇),大膽想象歷史,傳達對歷史的思考和認識。所有這些現代元素有機融合在一起,呈現了莫言小說的獨特風格:大膽想象歷史的敘事風格。
作品在敘述形式上運用了隱含敘述者的插敘。在閱讀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文中多次出現了作者自己的名字及其創作的小說,猶如作者莫言本人完全置于小說文本之外,僅以作品敘述人物外的另一個敘述者的插話,在敘說其中的故事。莫言成為小說中的一個小人物,如《人死屌不死》、《黑驢記》等小說。小說從第三卷《西門鬧轉世西門豬》開始,明顯增加了作者自畫像的成分。莫言成了小說作品中一個竭力彰顯自己的小人物,出場的次數越來越多。當然,莫言是作品中的一個小丑式人物,是一個表現欲很強的小孩子。他不斷跳出來,極力表現自己,彰顯自我,以自認為能引起別人注意的方式表現自己,以便吸引人們,尤其是大人物的注意,目的是想謀求個位置。作品中,敘述人對莫言這個小人物的敘述,是用輕視的態度描寫他的長相和滑稽言行。作品還展現了他愛耍小聰明的一面,塑造出一個調皮搗蛋、表現欲強的、“絕不放過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的小人物形象。作者借此表白自己小說中的虛構歷史,明確自己的政治立場;同時也表現出自己對一些事實的不滿認識,暗含了作者批判的色彩。作品還用虛構幻想的形式展現出那些不合時宜的事情,以及它們對當時造成的巨大影響,它們給人們造成的無法估量的傷痛和錯誤。此外,作品還時不時地展現出文人的色彩,如“蓬蓽生輝……”,“有不速客三人來敬之大吉”,“月亮,月亮,我敬你一碗酒!”等等。當然,作品中的莫言并不完全等同現實中的作者。不過,他也擁有作者真實的影子,竭力地傳達作者對生活和現實的想象與虛構。通過他的言行,可以更直接、更清楚地表達對社會歷史與現實的認識和理解,正如魯迅小說中的“我”和其他人物,并不完全是作者本人和現實中的某個人物一樣,莫言作品中的人物也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7]。
敘述人不斷提及莫言及其小說,還有他對小說虛構的現身說法,甚至對莫言的行為給予客觀評價,如“莫言從來就不是一個好農民”,“這人生性好奇,而且喜歡想入非非”,等等,這也是作者在竭力表明自己的立場。小說中的歷史言說不可全信,讀者自己鑒別歷史的真假和是非,作者的立場在作品中借助敘述者之口,明確表明其政治立場:不反黨、不反毛主席,只是愛想入非非。這也是作者莫言處理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方式。在瑞典頒獎典禮上,莫言曾表明獲獎是作家個人的事情,不是頒給國家的。那么,創作也是他個人的事情,與政治沒有關系,小說只是作者對現實的審美認識和自己內心的想象表達,是傳達自己對歷史、現實、時代的認識和思考。
小說中轉世的動物皆是有頭腦、有智慧、有豐富思想的“人物式”動物,它具有強烈的觀察社會的主動意識,并以之審視社會中所發生的事情和事件,思索它們的來龍去脈。而獨特的靈巧思維是洞察社會人生的關鍵,也表達出作者本人對人物的言行和事物發展的看法和態度。小說中的民間故事,一個接一個地被作者道出;小說富有引力的情節,具有生活的典型性,含蘊了生活背后的深度思考。
總之,《生死疲勞》以生命形式的各種幻象,用虛構的筆法展現歷史的滑稽和時代風貌,人畜視野結合,以畜生的特點為基點,在與人相同的特點上運用夸張、擬人的修辭方法,對畜生給予極大的人和事的想象,賦予畜生以人的特點。并以此大膽想象虛構歷史的原貌,借此表達歷史給人們造成的身心創傷。如作品中群豬的交配,作者賦予其人的特點,并給予想象:公豬對象選擇的思考和自由選擇的得意,有處女豬、漂亮豬、風騷豬的爭寵表現。從中可以看出,有時作者完全給豬以人的特性,并進行大膽的想象、描寫和敘述。小說中的多個敘述者,一個個出場,但其中又夾雜著其他敘述者對事件的敘述缺陷進行及時補充跟進,使得故事的敘述更為完整,歷史更為逼近。莫言在這篇小說中通過歷史和虛構敘事的并置藝術,有力地展現了人的生命形式幻象背后的訴求和愿望。
二、時代女性形象的重塑
小說《豐乳肥臀》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以主要人物上官魯氏及其九個兒女為中心,展現了高密東北鄉人民抗戰的苦難歷史,以及延展近百年的中國歷史發展狀況。作品以上官魯氏的九個子女中唯一的兒子——上官金童為敘述人物,講述了幾個姐姐的不凡人生及其所處時代的復雜。其中也融入了隱含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聲音,更加全面地補充了上官金童不在場或不全面的敘述,不僅呈現了故事全面進展的情況,也凸顯了作者對社會現實人生苦難的理解和傳達,顛覆了傳統文學中對女性足不出戶的描寫,重塑了時代女性形象,表現她們強大的堅韌性格,對家族、對時代、對社會、對國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作用,她們不僅延續了家族的血緣,也大膽呈現了女性生命原始訴求的一面。
小說文本中上官家族的女性個個獨立、有主見、做事果斷、執著、大膽、雷厲風行,是當時時代中叱咤風云的人物,女性中又以母親上官魯氏為中心,展現了家族女性的風采。作品以“我”(上官金童)對乳房的崇拜和貪婪擁有,寫出了母親及幾個姐姐的偉大,與此同時,榮辱與共、集于一身的姐姐們都成了抗日時代中的風云人物。作品想象豐富,情節扣人心弦,懸念迭起,富有吸引力。小說語言豐富、細膩,多運用比喻、排比等修辭。情景場面喧鬧奪目,人物言行富有個性,尤其上官魯氏及其幾個女兒的描寫,富有獨創性,作品凸顯了她們的獨立大膽,果斷與執著,抗爭苦難的堅強意志和爭取愛情幸福的信念,也展現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女性大膽爭取個性獨立的時代特征。她們其實就是現代小說作品中的子君、春桃、莎菲等女性的社會獨立訴求的承續者,沖破了女性被動選擇獨立的窠臼,勇敢主動地爭取自己的愛情。并且,她們對愛情的追求,無論好壞,都無怨無悔,始終如一地跟隨所愛之人。心中之愛的堅定與執著,在她們身上盡情展現。作者以金童的出生、成長為線索,來詮釋抗戰時代中女性的巾幗風采,為祖國為自己所做的貢獻。她們有苦難,也有戰勝苦難的決心;有愛情渴求,也有追求愛情的膽量和力量;有民族苦難的意識,也有排除民族苦難的決心。只是,她們始終是以傾慕之人的思想為思想的,這也反映了她們獨立社會的狹隘意識。畢竟,作為農村女性已是女中豪杰了。她們的悲憤、苦難和命運,與時代緊密相連。
作品極力展現了抗戰時期國家民族的苦難和各方勢力的角斗。對日本人的兇殘野蠻表示強烈憤怒,對各方爭奪權力的表演深惡痛絕,百姓的遭殃與受難皆源于他們,百姓的命運大多掌握在這些人手中。戰勝帶來的災難,洪災等,使百姓流離失所,被迫離開家鄉避難。而處在這樣時代中的上官家族的女人們,人性與時代的縫合緊密。當時,國內各方勢力互相勾連,作品通過愛情展現各方的勢力,此消彼長,你方唱罷我登場。上官魯氏的時代苦難抗爭是傳統思想的正面映射,上官家族女人的自我追求彰顯了人生存在的價值,上官家族男人的卑瑣與無用展現了家族的衰敗。作品呈現給我們的是典型的陰盛陽衰,女性的強大強勢,男性的弱小弱勢,家族血緣的混雜,也窺視出女性性觀念的“開放”與追求。上官家族的女婿們個個是威風凜凜、叱咤風云的時代弄潮兒。他們有力量、有野心、有能力、有膽量抗拒時代的不幸,為國家、為自己。雖然有成王者、有成寇者,個個都成為時代的英雄。其實,作品通過男性的“偉大”來凸顯上官家族女人們的勇敢和堅強,重新書寫和塑造歷史中的時代女性形象。
上官魯氏九個子女的多血緣組成,彰顯了母親上官魯氏作為女性的傳統思想的禁錮與突破的交融與沖突,生男孩延續上官家族煙火,立足于上官家族,由于失去了實現眾望的可能條件,于是開放自己,目的爭取生個男孩。然而,直到第九個孩子的到來,才滿足了愿望;而此時,家族已失去了耐心。令人可笑的是:作者為其安排了一個混血兒,眾人眼中一看就知并非上官家族的后代,所以也未贏得在世婆婆的歡喜,但母親卻有了足夠的勇氣和力量繼續以后的生活。從此,民族的災難,國人自我制造的災難,以及自然災難,洶涌而至。充滿力量的母親表現出了驚人的堅強、睿智、偉大,帶領眾多子女們勇往直前,奮力活下來,直到迎來新時期的九十年代。活了近一個世紀的母親,可以說歷經磨難、千瘡百孔,雖然只剩下微弱的視力觀看世事變化,但終究見到了光明,擁有了老年有子的陪伴在身邊的幸福和心酸。兒子的不爭氣,并未讓母親對其棄之,而是寬容地接納落魄的老兒,并與之一起投靠基督的精神世界中。小說結尾,老娘與老兒相伴在基督教堂中的一幕,令人慨嘆也令人心酸。用盡一生的力量養護兒子,盡一切力量滿足來之不易之子的愿望,到頭來如此結局,這也是作品對男權中心主義者的極大嘲諷,作者在文中也傳達出對重男輕女觀念的顛覆和解構。但上官魯氏了卻了心愿,兒子則充滿愧疚,感覺只有回到母親身邊,才是最安全安穩的。無能卻善良的他,遭受了生活的打擊和小人的算計,也享受到了人生繁華富貴的待遇,最終失去了對抗和附和的力量和勇氣。與母親相比,已足矣。正如評論者張清華所說:“莫言是作為其中的一分子來觀察中國的民間社會的,他觀察中國人民在20世紀所經歷的苦難,不是作為他者來看,是作為感同身受的其中的一員來描寫的。”[8]所以,作品讀來感人至深,如文中人物的苦難描寫讓讀者深有同感。作品中子女們的不同血緣構成,也彰顯了時代的動蕩,各種力量的交融與較量。不同階層、不同身份職業的融合,構成了上官家族的子女身份,但有母親的共同血緣根系的存在。其實,這些構成預示了各種力量的爭權奪利。作品通過豐富多彩的語言表達形式,深化了作品的內涵。像歌詞、諺語、歌謠、廣告語、宣傳語等,語言存在的多樣化,體現了時代特色,也緩沖了作品的嚴肅色彩,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和調侃性。
這篇小說在敘寫上官家族女性的形象時,處處閃現了作者的豐富想象,作者善于運用人物的幻想來揭露社會現實、抨擊現實,傳達其社會認識,如作品用大膽的幻想揭示當下的黑暗。運用人物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的幻想式,來慰藉自己痛苦的心,如上官金童落魄時的幻想。作品以一個視乳為嗜癖的男兒,來敘寫中國九十多年的歷史進程,彰顯了女性在社會進程中的重要作用,消解了以往男人在社會發展中占據絕對位置的傳統思想。重解和重塑女性,也是男女各有力量、皆有可能一統天下的趨向。女人不可忽視,女人應當受到平等的對待。女人也是人,擁有人的一切特性,人的情感欲望、人的權利渴求、人的美好愿望等等。張清華在談到莫言小說時說“他脹破了社會學的倫理學的看問題的方法,他把所有的人物還原到人類學的視野里面,把人當做動物,當做生命,原始的生命。”[8]莫言小說竭力傳達和詮釋了對女性和時代關系的認識。總之,作品中豐富的想象力,語言表達形式的多樣性,敘述視角的多維度,敘事進程中的后置交代與補缺說明,使主要人物居于核心,上下線性引出其他人物。作品以敘述人物為主,穿插隱含敘述者和作者的聲音,全面在場式敘述故事發展,遵循小說故事、人物、時代環境的三大要素來安排故事情節。小說敘述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人物命運明晰,故事進程鮮明,人物雖然眾多,如馬洛亞、沙月亮、司馬庫、鳥兒韓、魯立人、孫不言、魯勝利、沙棗花、上官各弟等,但各有清楚的來去安排,根據時代的發展狀況和人物的成熟程度融合和分離二者。作品的主線圍繞上官魯氏的人生發展與時代在場的纏繞,上官金童的成長視野觀察和敘述人物和時代的發展,以此推動整個故事的進展。“豐乳肥臀”只是意象,包含女性的突出特征和上官家族女性的獨特性,以及與時代的對接點。作者借此歌頌母親、女性對社會的重大貢獻,在真實展現和虛構想象并置中一展女性的風采和魅力,顛覆和解構了傳統女性的保守、軟弱,重塑了時代女性的新形象。
通過上述的闡述和具體文本的詳細剖析,可以看出,這兩部小說各自展現的不同問題,前者主要是人對歷史的認識和想象以及對生命形式幻像的想象,傳達人生的種種訴愿,后者重在塑造歷史進程中時代女性新形象,顛覆以往小說中慣常的舊形象,但在藝術上它們都展現了作者莫言敘述的共同特點:歷史與虛構的并置敘事,一方面表現了歷史事實,一方面彰顯了虛構想象,既有現實主義手法,也有現代主義手法,是二者的有機融合,使作品的敘述藝術得以顯現。這是莫言努力對小說這種文體藝術進行創新和探索的結果。
其實,在莫言的其他小說中,這種并置的敘事方法的運用并不少見,如長篇小說《蛙》通過歷史的真實敘事,展現了歷史的現狀和種種奉為神圣的精神文化積淀,同時小說也通過大量的想象虛構出了姑姑在新時期的種種離奇表現,內心和精神的極度創傷,歷史敘事與虛構敘事的藝術方法在作品中得到了很好地表現和融合。《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紅蝗》、《天堂蒜薹歌》等等作品也運用了這種敘事并置的方法,如《紅高粱》中“我奶奶”中彈之后的幻象與她的具有傳奇色彩的婚戀故事并置在一起,在敘事節奏上也明顯緩慢下來,以便于二者有機融合在一起,凸顯敘事藝術的效果。在莫言小說中大量的歷史敘事和虛構敘事的并置,有力展現了作家的藝術駕馭能力,也表征著作家的藝術審美觀念,即把創作主體的審美認知在創作中得以凸顯和張揚。莫言的小說既有對歷史事實的真實再現,以歷史敘事的方法表現出來,又有對不合理歷史的理想想象,以虛構敘事的方法得以呈現,它們共同體現了莫言小說創作的傳統與現代融合的藝術認知,同時,也是他對歷史的審美認識和合理想象的藝術表現。
[1]莫言.生死疲勞[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莫言.豐乳肥臀[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3][美]戴衛·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M].馬海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李業根.論莫言小說狂歡化敘事研究[D].南昌大學,2007.
[5]孫中田.色彩的語像空間[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162.
[6]趙玫.藝術天空的閃亮[N].馮驥才和他的繪畫.光明日報,1993-05-22(5).
[7]魯迅.《出關》的“關”[A].魯迅雜文全集[C].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70.
[8]張清華.莫言小說特質及中國文學發展的可能性[EB/OL].2012-10-24,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2-10-24/653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