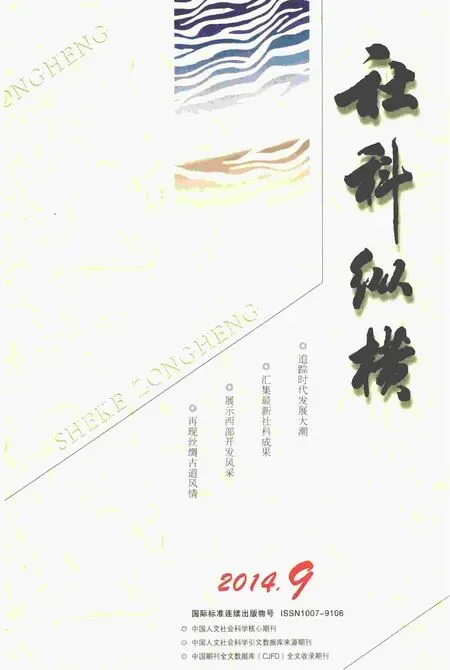淺析《三矢協(xié)定》
尹鉉哲 唐 烈
(延邊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學(xué)院歷史系 吉林 延吉 133000)
《三矢協(xié)定》是奉系軍閥與日本朝鮮總督府之間簽訂的關(guān)于東北朝鮮人管轄權(quán)的協(xié)定;這個協(xié)定的簽訂具有重要的劃時代意義。這個協(xié)定簽訂之后,奉系軍閥從原來對東北朝鮮人的態(tài)度以溫和為主開始轉(zhuǎn)變?yōu)橐浴拔淞Α睘橹鞯膹?qiáng)硬姿態(tài)。為什么在奉系軍閥從1919年7月完全控制東三省到1925年6月短短的幾年的時間奉系軍閥的態(tài)度就會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筆者認(rèn)為這種反差不僅是《三矢協(xié)定》②本身的內(nèi)容所要告訴我們的,更是《三矢協(xié)定》簽訂的背景和當(dāng)時的東北亞大的國際關(guān)系格局所決定的。
從這個層面上來看《三矢協(xié)定》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協(xié)定。但是經(jīng)過對相關(guān)學(xué)界動態(tài)的整理筆者發(fā)現(xiàn),學(xué)界對于《三矢協(xié)定》的研究可以說是鳳毛麟角,專門的學(xué)術(shù)論文沒有一篇,僅有研究同時代相關(guān)課題的論文涉及到《三矢協(xié)定》,但是書目也僅僅只有十幾篇,筆者所知道主要有:金昌國《一支最早的朝鮮族抗日武裝的建立與發(fā)展》,延邊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科版)1982年03期;石源華《韓國獨(dú)立運(yùn)動與中國》,1945-1995抗日戰(zhàn)爭勝利五十周年紀(jì)念集1995年;譚毅《萬寶山事件的遠(yuǎn)因近因與教訓(xùn)》,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guān)系——九一八事變70周年國際學(xué)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2001年;[韓]孫承會們920年代在滿韓人國籍問題的構(gòu)成與解決的探索》,“1920年代的中國”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2004年;呂秀一《簡述“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對東北朝鮮人的國籍政策》,東疆學(xué)刊2006年;彭懷彬《論奉天當(dāng)局對朝鮮移民開發(fā)水田的政策》,延邊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科版)2008年05期;許永吉《論東北地區(qū)朝鮮共產(chǎn)黨人加入中共問題》,中國朝鮮史研究會會刊——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十二輯)2011年以及權(quán)赫秀的《中國東北近代歷史與東亞的關(guān)聯(lián)》,東北史地,2013年02期。還有兩篇博士論文鄭光日的《日偽時期東北朝鮮族“集團(tuán)部落”研究》,延邊大學(xué)2010年和黃潤浩的《東北地區(qū)朝鮮共產(chǎn)主義者的“雙重使命”研究》,延邊大學(xué)2012年。至于專著,筆者所接觸到當(dāng)中,李洪錫的《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qū)領(lǐng)事館警察機(jī)構(gòu)研究——以對東北地區(qū)朝鮮民族統(tǒng)治為中心》,延邊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結(jié)合當(dāng)時的國際關(guān)系變動,有著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通過學(xué)術(shù)整理不難看出,學(xué)界關(guān)于《三矢協(xié)定》的研究還大有可為,由于筆者才疏學(xué)淺、水平有限,如觀點(diǎn)有失偏頗,歡迎指正。
一、《三矢協(xié)定》簽訂之前日本在東北地區(qū)的勢力發(fā)展
20世紀(jì)20年代的東北地區(qū)形勢比20世紀(jì)初期更加復(fù)雜,通過《間島協(xié)約》與《滿蒙條約》的簽訂,日本將俄國的勢力完全控制在了北滿,在與俄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過程中取得了相當(dāng)?shù)某晒ΑS滞ㄟ^“寬城子事件”扶植具有親日傾向的張作霖事實(shí)上統(tǒng)一了東北,這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完全占據(jù)了在東三省的主動權(quán),為進(jìn)一步侵略東三省進(jìn)而侵略全中國做好重要的準(zhǔn)備。
日本在支持奉系軍閥的同時,加緊對東三省的進(jìn)一步侵略活動。通過掠奪東三省的鐵路修筑權(quán)、自然資源和土地對東三省進(jìn)行立體式的進(jìn)攻。尤其是把擴(kuò)展同南滿鐵路相銜接的“鐵路網(wǎng)”放在首要位置。在1922年修通了鄭家屯至通遼的鐵路后,滿鐵急于東三省的西部擴(kuò)張,以為掠奪內(nèi)蒙古地區(qū)豐富的木材和煤碳等自然資源做運(yùn)輸準(zhǔn)備,試圖修筑鄭家屯至洮南的鐵路,為了達(dá)到這個目的,日本越過了名義上的北京政府,與張作霖做私下談判和交易,于1923年修通了鄭洮鐵路。1925年9月,滿鐵還提出了一個更具有野心的《滿蒙鐵路網(wǎng)計(jì)劃》,計(jì)劃用20年時間,以5.8億日元投資,修建35條,總長8828公里鐵路,準(zhǔn)備把侵略勢力擴(kuò)展到東北地區(qū)的各個角落。③日本早在20世紀(jì)初,就開始覬覦中國東北地區(qū)的豐富資源,1915年,利用清政府的軟弱無能,日本駐華公使曾導(dǎo)演出“天寶山合辦開礦契約”的丑劇。日寇無理強(qiáng)占掠奪天寶山礦產(chǎn)資源,從1916年4月開始,日本人飯?zhí)镅犹上群笳惺諠h、朝及其它民族的礦工達(dá)400多人,大肆采集高品位礦石,并安裝冶煉設(shè)備,生產(chǎn)規(guī)模曾達(dá)到日冶煉70多噸的情況。日本的東京經(jīng)濟(jì)雜志曾刊載文章說飯?zhí)镅犹稍?916年到1919年的四年間,從天寶山賺取了超過投資900倍的利潤。④進(jìn)入20世紀(jì)20年代以后,日本為了加快侵略東北的步伐,于1922年1月20日在奉天成立了東亞勸業(yè)株式會社(簡稱東勸會社)。東勸會社是由“滿鐵”、“東拓”、(東洋拓殖會社⑤)等與日本侵略密切相關(guān)的企業(yè)共同出資,其中的股東甚至還包括樸泳孝和李完用等親日朝鮮人。東勸會社成立之后,把掠奪中國東北的土地當(dāng)做主要業(yè)務(wù),方式則有通過各種契約占有土地、轉(zhuǎn)讓得到土地、收買土地、租地和托地等。⑥
通過與奉系軍閥進(jìn)行合作和將自己的勢力滲透到東北的各個領(lǐng)域的立體式侵略,日本已經(jīng)將全面侵略東北的準(zhǔn)備工作充分做好,接下來就是日本需要找一個像《間島協(xié)約》那樣的機(jī)會來進(jìn)一步介入東北的事務(wù),同《間島協(xié)約》的簽訂一樣,在東北的朝鮮人又給了日本一個“機(jī)會”。
二、《三矢協(xié)定》簽訂之前的東北朝鮮人分布狀況
在1919年朝鮮爆發(fā)反日的三一運(yùn)動之后,朝鮮總督府進(jìn)行了血腥鎮(zhèn)壓。由于朝鮮總督府大肆搜捕反日愛國志士,使得1919年以后朝鮮向中國東北的移民當(dāng)中又多了愛國的知識分子。同時,由于上世紀(jì)20年代開始,日本的人口急劇膨脹,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國內(nèi)對稻米谷物的需求猛增,為了防止國內(nèi)因?yàn)槿丝诤图Z食問題而發(fā)生混亂,日本從1920年開始在殖民地朝鮮推行產(chǎn)米增殖計(jì)劃。產(chǎn)米增殖計(jì)劃可以看做是日本為加快鮮殖民地化過程中的重要經(jīng)濟(jì)政策,該計(jì)劃的目標(biāo)就是把朝鮮變成日本的商品銷售市場、工業(yè)原料和糧食的供應(yīng)基地。⑦產(chǎn)米增殖計(jì)劃的實(shí)施使得大量的朝鮮農(nóng)民失去土地,淪為佃農(nóng),淪為佃農(nóng)之后依然要承擔(dān)諸如水利組合費(fèi)和其他土地改良費(fèi)等嚴(yán)重負(fù)擔(dān),這種嚴(yán)峻的生存形勢,逼迫更多的朝鮮農(nóng)民移民到“滿洲”來尋求生存之道。1919年以后的朝鮮向東北的移民當(dāng)中,與以往明顯不同的就是有大量的反日愛國志士為了躲避日本殖民者的鎮(zhèn)壓,遷入到中國東北境內(nèi)。至于這一時期朝鮮移民的分布情況間島地區(qū)占大部分,并且分布的區(qū)域也有大范圍的擴(kuò)大,在中國東北的朝鮮移民分布狀況為:奉天省169514人、吉林省379876人、黑龍江省5500人,熱河特別區(qū)域813人、關(guān)東州815人、內(nèi)蒙古988人、北間島329391人,共計(jì)886897人。⑧這一時期遷入的朝鮮入主要是通過茂山、會寧、鐘誠、慶源、慶興等口岸進(jìn)入中國境內(nèi)。
與以往相比,在20年代,進(jìn)入南滿的朝鮮移民也大幅增加,這主要與這一時期該地區(qū)的水田發(fā)展有較大的關(guān)系。除了鴨綠江以北的丘陵地區(qū)像安東、恒十二、通化、撫順、柳河等地也有大量從事水稻種植的朝鮮移民。由于在20年代前半期,在南滿地區(qū)奉系軍閥與日本經(jīng)常發(fā)生各種關(guān)于土地商租權(quán)和朝鮮人雙重國籍問題的紛爭,并且奉系軍閥與日本人的關(guān)系也是時好時壞,不是十分的穩(wěn)定,加之當(dāng)?shù)氐刂鞯谋P剝,所以這一時期還有大量的朝鮮移民從南滿遷入北滿或東蒙地區(qū)。由于北滿屬于俄國的傳統(tǒng)勢力范圍,所以在這一地區(qū)日本人的勢力較難深入,加之這一地區(qū)開發(fā)程度比南滿低,所以大量的從南滿遷入北滿的朝鮮移民和從朝鮮國內(nèi)以及俄羅斯沿海州等地為了生活遷入北滿的朝鮮移民一起,為水稻在北滿的種植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xiàn)。
從1920年代朝鮮移民的分布格局我們不難看出,朝鮮移民的分布有明顯的從南向北發(fā)展的趨勢。這種趨勢方面說明這一時期的移民數(shù)量比以往增長較多,導(dǎo)致東滿、間島和南滿等地?zé)o法接納,另一方面有為數(shù)不少的朝鮮移民從南滿遷入北滿,也說明了南滿對朝鮮人的政策相比間島和北滿地區(qū)更為殘酷和高壓,導(dǎo)致大量的朝鮮移民即使在南滿有了自己所開墾的一小塊土地也無法生存。尤其是《三矢協(xié)定》的簽訂給了奉天當(dāng)局以懲治不逞鮮人為借口,大肆盤剝廣大朝鮮移民,成為朝鮮移民北上的一大原因。而日本原本寄希望于簽訂《三矢協(xié)定》能夠和奉天當(dāng)局在不逞鮮人即共同抓捕反日的朝鮮人方面達(dá)成共識,但是事與愿違,日本與奉天當(dāng)局的出發(fā)點(diǎn)不同就決定了即使達(dá)成《三矢協(xié)定》該協(xié)定也不會得到很好貫徹落實(shí),還成為了奉日關(guān)系當(dāng)中的一大不穩(wěn)定因素。
三、結(jié)論
《三矢協(xié)定》與其他的在國際關(guān)系當(dāng)中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協(xié)定與條約等一樣,具有自身的“價(jià)值”,這種所謂的價(jià)值就是一個協(xié)定能夠在一定時期內(nèi)對國與國之間的關(guān)系的走向產(chǎn)生重要的影響。關(guān)于《三矢協(xié)定》對這一時期的奉系軍閥與日本的關(guān)系和“名義上”⑨的中日關(guān)系的走向均產(chǎn)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奉日關(guān)系當(dāng)中,《三矢協(xié)定》簽訂之前奉系軍閥與日本之間的關(guān)系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裂痕,從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之后張作霖在想問鼎北京政府實(shí)權(quán)的思路下,采取了對日外交的強(qiáng)硬政策。日本對此也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外交回應(yīng),后來二次直奉戰(zhàn)爭之后,奉系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實(shí)權(quán),在“郭松齡反奉事件”⑩中,日本人以在東北修筑鐵路和土地商租權(quán)等為代價(jià)提出與張作霖簽訂《日奉密約》,張作霖出于現(xiàn)實(shí)需要,只得答應(yīng)。從《日奉密約》的簽訂過程可以看出,此時張作霖與日本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進(jìn)入了表面和睦私下矛盾叢生的階段了。而《日奉密約》簽訂第二年簽訂的《三矢協(xié)定》在日本方面的考慮,原本是既可以使自己在東北通過朝鮮人事務(wù)而更多插手中國的主權(quán)事務(wù)又可以通過與奉系軍閥合作來緩和一下雙方之前已經(jīng)有些緊張的關(guān)系。但是,在《三矢協(xié)定》簽訂之后,隨著“五卅反帝愛國運(yùn)動”在全國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張作霖也不大可能冒著天下之大不韙繼續(xù)加強(qiáng)與日本人的合作。再者,《三矢協(xié)定》主要的針對對象是在東北的朝鮮人,張作霖可以以東北朝鮮人為征稅和盤剝的對象,并且當(dāng)時朝鮮人當(dāng)中的反日志士在某種程度上還與張作霖有契合點(diǎn),所以奉系軍閥雖然與日本簽訂了有損中國主權(quán)的《三矢協(xié)定》,但未完全執(zhí)行。這點(diǎn)從《三矢協(xié)定》的部分內(nèi)容當(dāng)中就可以看出,《三矢協(xié)定》的第五條內(nèi)容為“中國官府應(yīng)逮捕朝鮮官憲指名之韓黨首領(lǐng),即行引渡。但是奉系軍閥出于維護(hù)自身統(tǒng)治利益的需要,在協(xié)定的貫徹執(zhí)行方面是大打折扣的。甚至奉天當(dāng)局在日本人抓捕了朝鮮人反日志士之后還有過從日本憲兵手中將反日志士搶回并且釋放的例子。
通過解讀當(dāng)時中國國內(nèi)的形式發(fā)展情況看,并結(jié)合日本對中國東北地區(qū)的侵略始終以朝鮮人作為“先導(dǎo)”以及協(xié)定簽訂之后的效果與目的的嚴(yán)重“不相符,足以證明張作霖對日本的政策確實(shí)存在兩面性。并且這種兩面性是和張作霖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相聯(lián)系的。由于在《三矢協(xié)定》的執(zhí)行和其他如“滿蒙新五路的問題”上沒能滿足日本的要求,和以后中國國內(nèi)“國民大革命”形勢的發(fā)展導(dǎo)致張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岌岌可危,張作霖在內(nèi)外交困的形勢下拒絕接受日本的條件,最終1928年6月4日凌晨命喪皇姑屯火車站。
注釋:
①全稱《關(guān)于取締不逞鮮人的朝鮮總督府與奉天間的協(xié)定》,是1925年6月11日奉天省警務(wù)局長于珍與朝鮮總督府警務(wù)局長三矢宮松在奉天秘密簽訂的協(xié)定。該協(xié)定的內(nèi)容參見孫春日《中國朝鮮族移民史》,中華書局,2009年,P311。
②一般以1919年7月日本利用制造“寬城子事件”的機(jī)會,迫使北京政府解除吉林督軍孟恩遠(yuǎn)的職務(wù),任命張作霖的心腹孫烈臣擔(dān)任督軍為標(biāo)志,認(rèn)為張作霖完全控制了東三省。有關(guān)“寬城子事件”可參照http://ccwb.lnews.cc/html/2012-11/26/conte-nt-279779.htm,2013-12-12。
③參考日本國際政治學(xué)會:《太平洋戰(zhàn)爭人內(nèi)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1卷第36頁。
④參考http://hanyu.iciba.com/wiki/363432.shtml,2013-12-12。
⑤http://baike.baidu.com/link?url=2N9zcAbQVDYMDNDLxAw5KNPIN-5fg8jxIWZJjT-k64uovsigDk025hJTIzx-rPyXZqg-
RcPMNJGChPisLou-,2013-12-12。
⑥參考孫春日《中國朝鮮族移民史》,中華書局,2009。
⑦參考孫春日《中國朝鮮族移民史》,中華書局,2009年,P250—256。
⑧牛丸潤亮《最近間島事情》,朝鮮及朝鮮人社1927,120—122頁,轉(zhuǎn)引自孫春日《中國朝鮮族移民史》中華書局2009,P277。
⑨之所以稱之為名義上的,主要是指中國這一時期處于軍閥混戰(zhàn)的混亂局面當(dāng)中,北京政府并沒有實(shí)際控制中國,并且日本所扶植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后來也由于與日本發(fā)生矛盾而在皇姑屯事件當(dāng)中被炸死。
⑩奉系將領(lǐng)郭松齡因?yàn)槎沃狈顟?zhàn)爭后利益分配不均和反對張作霖的某些政策起兵倒戈的事件,該事件最終在日本人的幫助下以郭松齡夫婦被誅殺而告終。
[1]潘喜延.張作霖與日本的關(guān)系[J].學(xué)習(xí)與探索,1980(02).
[2]任松.張作霖與日本“滿蒙鐵路交涉問題”考略[J].遼寧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社版),1982(06).
[3]陳崇橋.關(guān)于張作霖的評價(jià)問題[J].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1988(04).
[4]陳崇橋,胡玉海.張作霖與日本[J].1990(01).
[5]何應(yīng)會.試論張作霖與日本的關(guān)系[J].黑龍江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0(08).
[6]王冠鴻.張作霖對日外交評述[D].吉林大學(xué)碩士論文,2004.
[7]呂秀一.簡述“九一八”事變之前日本對東北朝鮮人的國籍政策[J].東疆學(xué)刊,2006(03).
[8][著]李洪錫.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qū)領(lǐng)事館警察機(jī)構(gòu)研究——以對東北地區(qū)朝鮮民族統(tǒng)治為中心[M].延邊大學(xué)出版社,2008.
[9]張文俊,申曉云.論張作霖與日本關(guān)系的雙重兩面[J].歷史教學(xué)(高校版),2009(04).
[10]許銀珠.日本侵略朝鮮半島時期(1910—1945)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朝鮮人移民研究[D].吉林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0.
[11]茅文婷.愛國主義視角下的張作霖對日關(guān)系[J].黑龍江史志,2010(09).
[12]孟悅.張作霖對日態(tài)度芻議[J].東北史地,2011(03).
[13]張巖.東北地方政府對萬寶山事件的應(yīng)對研究[D].遼寧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2.
[14]黃潤浩.東北地區(qū)朝鮮共產(chǎn)主義者的“雙重使命”研究[D].延邊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2.
[15]劉東.關(guān)東軍與張作霖[D].東北師范大學(xué)碩士論文,2012.
[16]辛圣鳳.朝鮮人的滿洲移民史研究[D].延邊大學(xué)博士論文,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