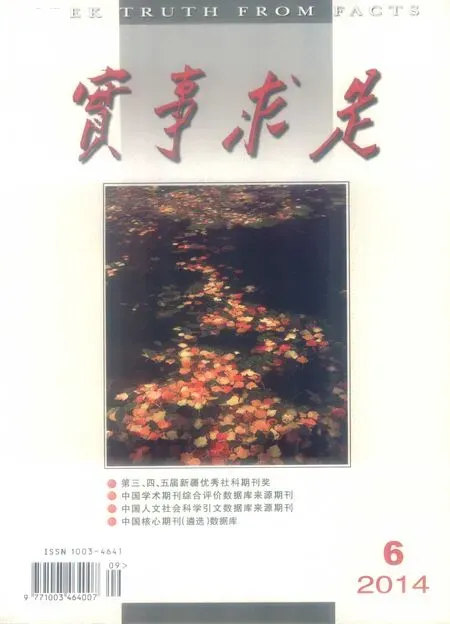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
劉嘉堯
(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0)
經濟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
劉嘉堯
(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南開封475000)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認為,我們既要從人的實際發展需要出發,又要從自然的需要出發,強調要堅持人的主體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統一。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重要內容,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具有特殊性和脆弱性。西部地區構建生態文明,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為理論導向,以西部地區生態和社會構成的現實情況為基本依據,探索一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自然觀的重要內容,對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國西部地區面積為660余萬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積約占14.9%,草場面積約占48.1%,耕地保有面積占6.8%,濕地面積占2.8%,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點區域。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影響人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1]近些年來西部地區各級政府雖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卻總跳不出“局部改善總體惡化”的現實情況。馬克思生態倫理思想中關于人化自然觀的理念,為我們確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奠定了基礎。要改善我國西部地區的生態發展模式,必須立足西部地區的實際,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為指導。
一、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對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倫理價值導向
馬克思生態倫理思想中關于人化自然觀的理念,為我們確立正確的生態價值觀奠定了基礎。面對當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惡化的情況,我們首先要對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重新認知。在學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即“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過于強調以人自身為中心的理念,認為人類利益是一切問題的中心,如果自然存在物對人類失去了價值,那么對人來說它就沒有意義。“非人類中心主義”者則恰恰相反,他們強調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中應該尊重自然,與自然為伴,主張消除人類的主體性地位,主張抽象的“萬物平等”。
新中國建國初期,尤其是“大躍進”前后我們的生態意識是“向自然開戰”。這種生態意識指導下的實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生態問題。實踐證明,這種“極端人類中心主義”是死胡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生態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找到了快速發展的契機和平臺。但是有些地區簡單地把“開發”理解成“開挖”,把發展理解成為簡單的生產總值數字的增長。這些行為導致了生態系統的退化及環境污染的加劇。針對這種情況,很多學者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把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扭轉成“非人類中心主義”,提倡自然與人是完全平等的,其理論基礎是超功利主義的自然觀。
“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在西部民族地區有著較好的傳統文化基礎。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人口較多且呈現聚居狀態,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如藏傳佛教、原始崇拜等宗教文化中非常強調萬物平等、保護自然等思想內容。但我們也該理性地看到,這種“非人類中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會將人和自然的關系孤立起來,忽略了人對自然的主觀能動性。“非人類中心主義”看似解決了人和自然最根本的矛盾,但實際上這種解決矛盾的方法并不適合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語境,是一種消極的處理模式。西部地區的生態壞境如果只靠單純的維持和保護,靠自然本身的恢復能力來達到原先的水平,需要一個漫長的周期。另外,西部地區生態資源是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資源支撐,不利用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是不現實的。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在利用資源的同時,一方面保持生態的良性發展,一方面又可以為我們國家的建設提供有力的支持。這需要我們在“人類中心主義”和“非人類中心主義”中找到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在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可以找到相應的價值指導。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認為,我們既要從人的實際發展需要出發,又要從自然的需要出發,強調要堅持人的主體性和自然的先在性相統一。馬克思提出了“人化自然觀”的理論,詳細闡述了人與自然間的辯證關系,它所貫穿的不是一般的“人類中心主義”意義上的人本主義,也不是今天狹隘的自然中心主義意義上的反人類中心主義,而是人本主義意義上的生態主義。
在馬克思看來,要真正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以單純的人道主義或單純的自然主義作為理論基礎,都是難以勝任的。我們要將人道主義充分發展以至包含了自然主義的全部合理思想,上升為一種自然人道主義;使自然主義充分發展以至包含了人道主義的全部合理思想,上升為一種人道自然主義。[2]只有如此,才能為建立人與自然的合理關系奠定科學的理論基礎。
在這個過程中人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以及可能給自然帶來的正面與負面的影響,遵循自然規律,按自然規律辦事,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共同進化與和諧發展。在實踐中,人類需要做到超脫自身需要的狹隘束縛,從整個生態系統的利益出發,去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和自然萬物共存共榮。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樹立了一種新的生態價值觀: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人類是處于自然生態系統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為了人類的永續存在和健康發展,人類既要關注和追求人類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也要尊重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發展權利,還要在發展生產、提高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更加合理、科學地對待自然,保護環境,從而更好地協調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實現地球上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對“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揚棄的過程,指導我們建立新的“生態——人類中心主義”指導思想。
二、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西部地區生態問題解決的社會化路徑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強調:“人們會重新感覺到,而且也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但是要實行這種調節,單是依靠認識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對我們現有的生產方式,以及和這種生產方式連在一起的我們今天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3](P519)可見,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解決生態難題的一個重要因素。人的實踐活動作為人的本質力量的感性實現形式,在這里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是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前提。人們總是通過一定的社會結合方式與自然界打交道,“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4](P344)正是通過社會關系的整合,人們才克服了單個自然人所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是實踐活動的存在基礎,并規定著人與自然關系展開的方式、性質與前景。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人與自然之間生態關系矛盾的解決,有賴于對不合理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矛盾解決和生態民主缺失的完善。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角度,還是當今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都要求我們將處理好社會關系作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的基本前提,重視環境正義和社會公平建設。社會制度構建與社會公平民主是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解決生態問題的一個基本視閾。結合馬克思的觀點與西部地區生態實踐的經驗,以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為目標,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相應的完善。
首先,要完善西部地區生態民主,尤其是基層生態民主。美國生態政治學家丹尼爾·科爾曼在其著作《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中講到:“我們之所以強調基層民主,因為我把基層民主視為生態社會的根本特征和轉變活動得以取得成功的中心環節。我也十分強調由社群為本的經濟推衍而來的合作和社群概念。在此意義上的社群將成為社會責任、可持續性、權力放下、尊重多樣性和生態智慧的組成要素。”[5](P9)
在一個真正的生態社會,我們強調的是生態權益清晰,決定生態未來分權化的民主環境,讓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機構制度將權力留在行之有效的、離個人家園最近的基層。在西部地區生活的民眾,最了解他們的環境現狀與發展趨勢,有關的決策權和監護權應當掌握在他們的手里。基層生態民主的完善可以更好地降低民族地區因生態問題而產生的不必要的群體性事件,當民意達成一致的時候,生態“暴力”事件就會泯滅在萌芽階段。
其次,關于國家權力和西部地區生態社會的良性互動方面。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政府應當秉持“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允許公民社會在這個領域中決定自己的生態社會發展。這個公民社會的組成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本地的少數民族群眾,也包括非政府組織成員,既可是關注生態環境的學者,也包括環境公益企業。西部地區生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需要政府把握方向,一方面需要不同的聲音,這是我們當今提倡社會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實現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需要國家權力和公民社會的不斷磨合與諒解。但我們要認識到,建立一個長久的、穩定的生態文明制度,需要這種生態政治層面的調試。只有當國家權力與公民社會真正實現了良性互動,才能對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注入持久的動力。
三、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與西部地區生態產業的發展
不可否認,近十年西部地區工業發展所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速度是驚人的,但在財政數字突飛猛進的時候,我們卻看到那日益枯萎的草原和傷痕累累的山脊。如何從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轉變為綠色生態產業模式,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中關于“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理念,為我們確立正確的產業發展模式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的物質交換無法循環和持續會同時危害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人類的生產活動中,一旦這種“物質變換的過程”超出了自然的實際承載能力,必然會影響自然的正常物質循環和能量循環,從而引發人與自然的對立和沖突,[6]這便是生態環境危機產生的本質原因。因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如何有效地平衡“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進行了詳細地闡述,他強調,要“把生產排泄物減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進入生產中去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7](P117)可以看到,馬克思所談到的這些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過程,正是一種“再利用”或“再循環”的過程。它依據一種“資源——生產——再生資源”的新陳代謝模式來實現物質的不斷循環,減少人類社會線形物質代謝對生態系統的壓力,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8]當今,我們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從其實現基礎上來看就是通過改變傳統工業化生產方式、消費模式以及經濟增長方式,恢復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正常物質循環,消除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裂縫,使人及其社會的發展始終保持在自然所能承載的范圍之內,并與自然之間形成一種動態的、可持續的平衡。
在馬克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藍圖中,無論是人與自然不可分割的辯證統一思想、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思想,還是生態問題解決的社會制度變革思想等,都是當代西部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源泉。我們應當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思想,確立西部地區生態建設正確的價值導向,通過完善生態民主和制度建設等社會化路徑來解決相應的生態問題,通過傳統產業升級改造,重構西部地區生態產業體系,形成西部地區的綠色發展模式。
[1]清華大學生態環境保護研究中心.西部生態現狀與因應策略[EB/OL].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12-02/114521571368.shtml.
[2]黃斌.馬克思生態自然觀的當代價值[J].理論探索,2010(01).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丹尼爾·科爾曼.生態政治:建設一個綠色社會[M].梅俊杰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
[6]趙成.馬克思的生態思想及其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02).
[7]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嚴文波.馬克思生態倫理思想的科學內涵與現實意義[J].鄱陽湖學刊,2012(06).
責任編輯:哈麗云
A81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4.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