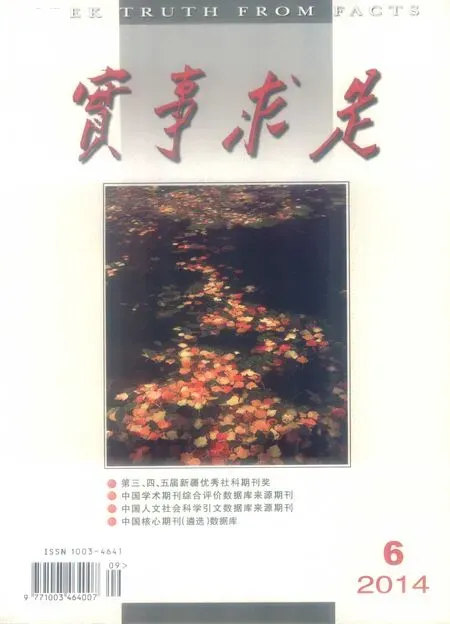論中國現代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中的文化精神
陳德璽
(惠州學院 建筑與土木工程系 廣東 惠州 516007)
文化
論中國現代國家治理能力建設中的文化精神
陳德璽
(惠州學院 建筑與土木工程系 廣東 惠州 516007)
現代國家治理是當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國家治理不能疏離于文化,必須彰顯文化精神,體現民族價值情趣。“文化”介入國家治理能有效規避人治和法治的諸多弊端,需要在繼承中激活傳統文化基因,在創新中展布現代文化精神,在對接中開辟后現代文化路徑,在引領中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國家治理 治理模式 文化精神
2014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拋出了一個當前亟需破解的重大現實課題,即如何建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他說,“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歷史任務,就是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1]怎么“定型”?這是一個突破口。作為一次嘗試性的探討,筆者認為,習總書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價值體系,堅守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必須發揮文化的作用”[1]的觀點極具政治智慧,循此思路,并認為大國的治理不能疏離于文化,必須彰顯文化精神,體現民族價值情趣。
一、傳統文化中國家治理的幾種模式
“觀乎天文察乎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立于天地之間催生了“文化”。而所謂“文化”即是指人們生活方式的凝結,在時空變遷中形成的一定群體所擁有的行為模式和社會運行的內在機理,它規范著人們的生產生活和一切交往行為。依照雅思貝爾斯的觀點,有史以來,公元前800至200年間,世界范圍內相繼產生了古希臘羅馬文明、古埃及文明、中華文明等文明形態,形成了所謂的“軸心時代”,它的影響一直延續至今。其實這就是我們所談論的傳統文化。其中不乏飽含深邃治國理政的理念和思想,可以看作是這一體系的先河和經典范本。比如古希臘的柏拉圖設想出了《理想國》,中國的《禮記·禮運》提出了“天下為公”的理想模型,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出了“小國寡民”的治理思想,近代以來的啟蒙思想家則主張“契約論”等。
1.國家治理的遵德性而為模式。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柏拉圖的“理想國”理論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所建構的“理想國”可以看作是世間之物對“理念”原型的模仿,雖然不盡然與“理念”相符合,但卻是最完美的,也是最符合不同階層本性的社會秩序,因而也可稱這樣的國家為“正義國家”。因為整個國家由不同的階層構成并各司其職。柏拉圖認為,“我們的國家如果安排得當,那就是完善的。[2](P110)這些不同的階層分有了“智慧”“勇敢”“節制”和“公道”等四種美德。由于柏拉圖的階級地位,他的治理理論更傾向于貴族政治,所以他說“這是治國的知識,體現在統治者身上,”“它是妥善謀劃的國家,真正智慧的國家。”[2](P110)但擁有這些知識的人是“國家里最小的這一部分”,[2](P110)也即是除非哲學家當了王,“集權力與智慧于一身”,“否則國家是永無寧日的”。[2](P118)而這正是今天我們所呼吁的“頂層設計”、“系統思維”。但柏拉圖畢竟是沒落貴族思想理論的代言人,所以他的很多觀點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思想文化水平不相符合,比如他規定,一個好的城邦,其下轄人數必須為5040人,這些人口又歸屬于59個部落。盡管如此,應該說他在西方思想史上比較自覺并全面地討論了國家治理的問題,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毫無疑問,“國家治理”必須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一部分,按照職責與能力相匹配的原則,整合政治資源,從而達到理想的治理效果。
2.國家治理的禮法權信模式。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國家治理理念可謂百家爭鳴,各抒己見。在《管子·牧民》中指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順天意而為之,多予少取,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3](P2)還談到治國須“明鬼神”“祇山川”等,從中不難看出,這一主張含有濃厚的愚民色彩。在《商君書·修權》中則更進一步提出,“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3](P5)“法”為君臣所立,即政府草擬以公布天下,“信”為君臣所遵守,即政府行為必須言行合一,至于“權”,商鞅將其詮釋為“權術”。在諸家治國思想中,儒家應該說是獨樹一幟的。禮法融通,以禮為上,輔之以仁德之治,則“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3](P11)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儒家以“損益”手法構想出了一個“大同社會”,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3](P17)也即是說,公權力不僅僅操之于政府之手,相反,權力屬于全體人民所用,人民積極參與國家管理,社會自然一片祥和之氣。這一點,似乎中西之間是共通的,正好呼應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可見,國家治理在深層次上即文化精神上是互通的。
3.國家治理的處無為之事模式。老子主張無為而治,在他看來國家治理并不是什么不可克服的課題,相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問題的關鍵在于,圣人是否能夠體“無”。“無”不是什么都沒有,而是形而上學的最高理念,其價值意蘊與“道”和“德”相通。從執政者的角度來看,他的施政理念就是“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圣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4]正所謂“無為”故“無所不為”,而民則能自所為之,圣人可垂拱而治,天下太平無事,功效自然顯現。基于此,老子進一步構思出理想的社會形態,即“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4]照此來看,似乎老子要人們退守到文明的原初狀態,并使一切都回歸于“小”,其實不然,老子思想的深邃之處就在于以“退”為“進”,讓人從繁雜的“有為”之中解縛出來,理順事理而依憑人之本性并加以引導之,從而達到治理的目的;他所說的“小”也并非實體的弱小,而是統治者加諸于百姓的過度的訴求,須從百姓沉重的負擔中剝離,所以老子批判地指出,“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4]而若能依照萬物“道德”一理的方式去治理,則必定是“治大國,若烹小鮮”。[4]
4.國家治理的權責相對等模式。嚴格意義上來講,“法治”和“法制”這一對概念并非中國本土文化催生的,而是近現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引入的“舶來品”。回顧歐洲啟蒙運動的成果,在理性主義的文化語境下孟德斯鳩和盧梭為國家治理特別是現代國家治理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根據孟德斯鳩的觀點,“任何國家都有三種權力:立法,執行有關國際法事務之權,執行有關公民法事務之權。”[5](P45)這即是“三權分立”最早雛形,日后逐漸演化為立法、行政和司法民族國家治理的理論框架并延續至今。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將整個國家資源依照不同的屬性給予區分,條塊分離,但又相互制衡,在權力制約的均勢中推動國家治理。同期的盧梭,人文情懷更加厚重,由“人生下來是自由的,可是處處受到束縛”,[5](P66)論述了人由“自然狀態”向文明狀態轉變的必然性,人有向往社會生活的訴求,并要求有“社會秩序”,它是“一項其他權利充當基礎的神圣權利。然而這項權利并不是自然的產物,它是建立在一些約定上的。”[5](P67)“約定”既不是來源于神賜,也不是來源于自然,而是一定社會階層的人們共同的意志和意思表達,具有廣泛的約束力。它不能讓渡,不可分割,主權在民,換言之,人民享有絕對權力,一旦這一公意被政府扭曲,則人民可以將之收回并重新授權。很顯然,在國家治理中,主體是人民和政府,客體是公共資源即公權力,遵循這一約定機制,可以有效節制公權力,確保權力始終為民服務。
二、不同文化資源在國家治理語境下出場
不同的自然條件、不同的生產方式以及不同的群體和個體差異形塑了不同的文化類型,這些文化類型在歷時性和共時性上既遵循文化發生、發展和演化的一般規律,也以其特殊性開辟生存空間。可以說,正是文化的異質性才讓人類文明大放異彩,同時,這種特性也對當時乃至后世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產生深刻影響,甚至是導向性作用,因而不能忽視。在中國進行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今天,應充分挖掘輝煌燦爛的傳統文化資源和吸納人類文明的積極成果。
1.舊邦維新,在繼承中激活傳統文化基因。常言道“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道出了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數千年延續的深刻道理。“維新”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思想命脈,或者說是民族意識的深度自覺。怎么“維新”?老子有一番體悟,叫作“為學日益,為道日損”,[4]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損益”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不難理解,治國安邦之道,古往今來,多少賢良先哲日三省悟尚只得其經略一二。可見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但中華民族貴在能“學”。一部五千年文明史,可供學習和參考的治國理政思想可謂汗牛充棟,有道家的“無為而治”,有儒家的“禮樂”“賢德”之治,有墨家的“非攻”“兼愛”之治,也有法家的“隆禮”“重法”之治,等等。其中,有可學者,也有不可學者,也即我們必須以批判的眼光,結合當下的時代需要,各有側重。另一方面,也必須有實踐的能力,學能否為真學、能否為真用,需要回歸生活,由人的行為去檢驗。這一點,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是不存在疑問的,老周隱循,是為了跳出三界煩擾體悟天道以教世人;孔孟周游列國,為的是推廣他們的仁政主張;墨翟拒楚,為的是阻止非正義戰爭帶給百姓的災難;商韓立法,為的是鞏固新生社會階級的現實利益。總體上來看,他們的思想和理論都富含有強烈的應世而為傾向,不做無病呻吟的偽學問。這啟示我們,要推動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就必須真學、真懂、真用。
現如今,傳統文化話語空間被擠壓,以一種“異化”的方式,乃至扭曲的形式茍延殘喘,長久以往,必定導致民族文化精神的基因斷裂和碎片化。當務之急是遵循文化發展規律,加大保護和開發力度,以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喚醒民族優秀文化記憶,從而激活民族文化基因,助力當下的國家治理能力體系建設。
2.深耕固本,在創新中展布現代文化精神。“文化”是一個生命體,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它有原始的生長點,有營養的吸收成長階段,有成熟輝煌階段,也有衰落頹廢階段。對于傳統文化而言,不同的文化形態所經歷的發展和演化時間不一定是同步的,也即有的成熟得早,有的較晚。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每一種文化形態其實都比較早熟,乃至于呈現出一些現時代社會發展才具有的個別特征。所以學界對此比較贊同,認為中華文化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但沒有喪失生命力,相反,在一次次歷史變遷中得到傳承。但這也不是絕對的,環顧一下“軸心時期”的幾大文明形態,至今依舊存在的僅有中華文明這一孤本,這究竟是歷史要讓中華文明“獨孤求敗”,還是要見證自身返古開新呢?歷史不容假設,但卻允許實踐。中華文明在實踐中得以生成,其源頭活水乃是現實生活,也即它首先是生活的,其次才是理論的。這提示我們,中華文明雖然是傳統的,但并非是守舊的。
今天,由資本裹挾的市場化和信息化穿插的現代化已然強勢登陸中華這片土地,可是我們沒有報之以仇外心理,而是以開放、歡迎的姿態擁入現代化。但必須警惕,現代化本身蘊藏著風險,從哈貝馬斯“現代性未完成的規劃”中可以看出,我們還不能坐享其成,尤其是不能將傳統文化當成故紙堆打包統統扔進歷史的垃圾桶。坦率地說,中國今天的現代化之路,付出的文化代價已然超出所得,歸根到底還是民族文化命脈的根子沒有維護好,從而導致在新道路上顧左右而言他,猛回頭才發現已偏離正軌太遠。所以,必須呼吁,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背景下,文化建設的重點一定要“開新”,才能對癥下藥。否則,你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我也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就失去區分度,而實際上支撐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外衣的內襯則是民族文化及其精神。
3.模式轉換,在對接中開辟后現代文化路徑。美國文化學者本尼迪克特提出了“文化模式論”,在她看來,人類行為方式存在多種選擇性,但具體到某個民族、部落或氏族,他只能選擇諸模式中的某部分,而這種選擇往往內含了自身的價值判斷。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數千年苦心經營的傳統文化,其實就是他們一整套價值觀的體現。其中,儒家文化與道家文化有別,道家文化有別于法家文化,但這種差別遠遠不及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所以說,世界的改造,并非在無“前見”和無價值深度的平面上展開,而是一定的人們試圖將自身的文化客觀化并渲染他者的一種“意向性”活動。
因此,促進模式轉化是民族文化“適者生存”的進化論選擇路徑。雖然這種轉換并非一帆風順,但我們必須提早啟動,而且也可以不必重走“卡夫丁峽谷”的老路。或許在此時談論后現代對中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具有促進作用為時尚早,但卻沒有必要隱晦后現代已經來臨,而且我們正經受著它帶來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后現代抑或現代性之后,其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非線性、異質性,在個別情況甚至帶有前現代的痕跡。在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語境中,后現代提示,宏大敘事情節必須受到節制,要更加關注特殊群體和個體的存在感,關注他們的現實利益和價值訴求,盡可能弱化由推動建設作用激發的“反體系”力量的沖擊。
4.核心統領,在引領中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所有文化資源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最年輕的,也是生命力最強盛的一支。就文化發揮作用的機會而言,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傳統文化以及現代文化資源等,機會是均等的,但由于文化景觀必定不會是無價值深度的平面,正如前文所言,文化模式都帶有價值判斷,所以,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又必然要超出機會均等的界限,發揮核心統領作用。所謂核心統領,即是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諸多文化資源中占主體和主導地位,這是捍衛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必然邏輯。
所以,中國建設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實質是對國家政治資源的整合,激發機體活力,而其動力源泉一則來自于體制內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則來自于厚重文化背景中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它的作用,主要是引導性和提示性的,然而一旦失去這一方向指引,文化場會混亂不堪,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實踐成效也會被抵消。
綜上可知,不同的文化資源在國家治理體系語境下出場,各自所發揮的作用應有所不同,各自發力,共同助推這一體系的順利建設,從而實現自身歷史形態和價值作用的時代化。
三、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從以上四種傳統文化視野中的經典國家治理模式以及不同文化資源的治理功能的轉換中可以看出,“文化”以一種政治哲學智慧和在世精神介入國家治理,不僅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也具有現實的操作性。可以肯定地說,“文化”(文化治理)是繼“人治”和“法治”兩種治理理念和模式之后的第三條道路,這種選擇能有效規避“人治”和“法治”的諸多弊端。
1.文化有助于凝聚現代民族精神。在現代國際關系中,主體是民族國家。而一個國家雖地域有大小,實力有強弱,唯獨在民族精神上是相對等的。也即是說,自近代國際關系法的第一個藍本《維斯特伐利亞條約》[6](P574)簽訂以來,所有民族國家均享有參與國際關系的資格。我們認為,所謂的國際資格,實質是“國格”,指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被認可度。進而言之,一個民族是否被認可,不唯在法律上,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認同。而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是否被國際社會認同和接受,關鍵不在于世界怎么看,而在于本民族自身的民族精神的凝合度。因為他者認可你前提是,首先當事者得認可自身,否則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因而,民族文化精神對于國家治理具有提綱挈領和“牽牛鼻子”的作用,它是一個民族“特定價值系統、思維方式、社會心理、倫理觀念、審美情趣等精神特質的基本風貌的反映”。[7](P3)目前,對中國民族精神比較一致看法,是彰顯人文主義情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8](P5)“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8](P18)以及由此演化出的以民為本、務實躬行、友愛簡樸等。這是傳統文化語境中民族文化精神。新時期,這一精神得到轉換和升華,在黨的十八大上將之表述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崗、敬業、誠信、友愛”二十四個字,[9]前八個字主要定位于宏觀的國家層面,中間八個字定位于中觀的社會層面,后面八個字則定位于微觀的個體層面,很好地詮釋了新時期的中國精神,同時也能熔鑄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之中,實現鋼性整合向柔性整合的轉變,更深程度地凝聚改革共識,優化政治體制改革結構,提升改革實際成效,實現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2.文化有助于變遷民族生活方式。在傳統社會及其文化背景下,一般而言,生活方式具有超穩定性的特征,以至于政治上層建筑發生了劇烈的變遷,依舊能維持原狀平穩運行。這一點在中國社會數千年的歷史演變中體現得很充分。中國傳統文化是基于農耕文明,而農耕文明的根基則是血緣和姻親關系,推而廣之就是家國同構,統治者具有強烈的小農意識,所以數千年來奉行“不違農時”的生存理念,經營“以農為本”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交往方式。在個人身上,君權和父權是唯一權威,產生了強烈的人身依附;在社會上,皇權不下鄉,主要倚重門閥氏族和鄉野豪紳以正統思想和土地囚困百姓;在政治上則推行集權制和宗法制,層層滲透和整合社會階層;在文化上合百家言論定儒學于一尊,采取舉孝廉、科舉制等舉措收攏仕人。總之,自然經濟、氏族政治、科舉取仕、儒家文教在傳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從而釋放了制度惰性,嚴重阻滯了生產力和文化的進步。但從深層次上加以審視,文化即生活方式并非一成不變,在內外因條件的作用之下,或快或慢地也會發生變革。時下,我們推進市場改革,著力于民主政治建設,發展主流價值引導的多元文化,其用意正在于促進生活方式的變遷。
3.文化有助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以其先鋒隊的角色,積極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團結和帶領各族人民反抗外來入侵,爭取了民族獨立;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人民共和國;進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過“十年浩劫”后迅速扭轉方向,積極改革開放,獲得了巨大成功;從而開辟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新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的取得,具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雙重必然性。從理論上來說,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到蘇聯,經歷第一次轉換,實現經典理論向革命實踐的轉變;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由于忽略自身特殊性及人類發展規律的一般性葬送了社會主義政權;中國也因為效法蘇聯而付出了沉重代價,但能從民族國家的實際出發,及時醒悟挽救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實際深度融合,催生了兩大理論成果。從實踐上來看,中國共產黨人大膽實踐,在凝聚民族智慧的前提下,首先是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并取得勝利;其次是及時推進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再次是推進二次改革,也即新時期的深化改革,這一時期以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為目標。可見,中國共產黨在執政實踐中,將革命、改革和發展結合起來,不搞“一步到位”,也不搞“二重唱”,而是實現“二”而“一”的融通,馬克思主義不斷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生活方式的根基。
4.文化有助于實現民族發展目標。黨的十八大勝利召開,新一屆領導集體履職,遂而拉開了新一輪中國改革的序幕。隨后,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基本陳列,并發表了“中國夢”的主題講話,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10]緊接著是重走鄧小平南方改革的路子,并拜謁改革設計師鄧小平先生銅像,表示了不遺余力推進和深化改革的決心;之后又視察武漢提出必須處理好深化改革過程中的五個關系。其實,無論是“中國夢”闡述也好,還是啟動“二次改革”也罷,其目的都只有一個,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11]這即是“兩個百年”目標的時代表達。翻開中國近代史,羸弱的國家治理能力致使中華民族飽受摧殘,無數革命先烈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這既是革命意志的高度體現,更是民族復興意識即文化自覺在行動上的踐行。作為一種時代強音和文化意識,就是希望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打造出適合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引導億萬人民群眾朝著既定目標奮進,力爭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實現小康社會的階段目標,在建國一百周年之際初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個目標無比宏偉,惠及十三億人口,沒有強大可靠和歷久彌新的精神動力支持難以實現。很顯然,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提出,契合了這一時代語境,而文化精神則成為檢驗這一體系建設是否到位的試金石。
[1] 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EB/ OL].2014-02-18,http://www.ccps.gov.cn/pictures/201402/t20140222_45510.html.
[2]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M] .北京:商務出版社,2007.
[3] 成汝信·從政文鑒[M] .廣州:廣大人民出版社,1993.
[4] 道德經.
[5]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下[M] .北京:商務出版社,2007.
[6] [英]諾曼·戴維斯.歐洲史[M]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
[7] 李宗桂·傳統與現代之間——中國文化現代化的哲學省思[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8] 周易: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10] 習近平.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奮勇前進[EB/ OL].2012年11月29日,http://www.gov.cn/ldhd/2012-11/29/content_2278733.htm.
[11] 學習《習近平關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論述摘編》[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3/1203/c64387-23722539.html.2013-12-03.
責任編輯:哈麗云
G120
A
10.3969/j.issn.1003-4641.201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