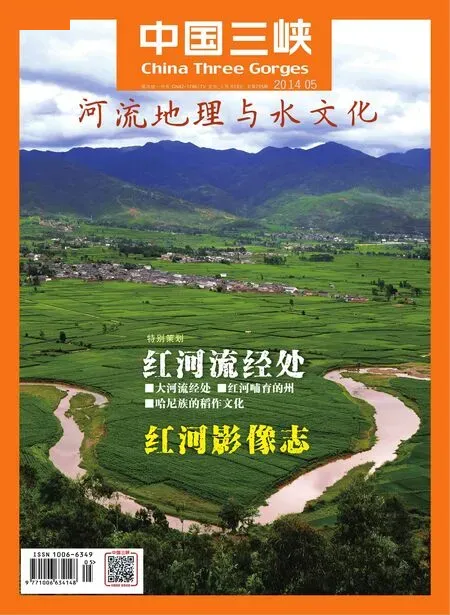沅水第三條河岸
沅水第三條河岸
文/談雅麗 圖/李佑喜 編輯/柳向陽
水馬船聲出洞庭
我們不是刻意去尋訪河流,但湘西之行,自北向西,走的高速公路,時斷時續(xù)有一條白色錦緞跟隨——是沅水。過沅陵后溯水而上王村,又是沅水支流不離不棄地陪伴。越野車上看到的清江是酉水,橫跨其上的大橋名為芙蓉鎮(zhèn)大橋。過了幾日,坐火車去湘黔邊境的鎮(zhèn)遠(yuǎn)古城,一路與沅水支流舞陽河親密接觸著,山是青山翠谷,水是碧水長流,更早這些地方都叫五溪蠻。五條溪流鋪織的蠻夷之地,然而我走過之處,山民個個都純樸良善,背著背簍上河堤下河岸。河畔處處殘有水馬驛站的傳說和遺跡,但是,車水馬龍的繁華已在時光的淘洗中暗淡下去了……
沅水是一個何其巨大、支脈相連的水系,走向沅水水網(wǎng)的歷史,就仿佛進(jìn)入一場春秋大夢,水馬驛之大夢則始于明朝。明朝的法律大典《明會典》記載說:“自京師達(dá)于四方設(shè)有驛傳,在京曰會同館,在外曰水馬驛并遞運(yùn)所。”自古以來驛站有水驛、陸驛和水馬驛三種,沅水江畔多設(shè)水馬驛,既可河運(yùn)又可陸運(yùn)。每六十里至八十里設(shè)馬驛一所,每所備馬三十匹、六十匹、八十匹不等。水驛在沖要的地方,每所備船十只、十五只、二十只不等,每船有船夫十名。水馬驛站是沅水江畔商賈如云的交通大網(wǎng),類似現(xiàn)代穿山越嶺的高速路或是火車道。

云霧之山,沅水之源。攝于貴州黔東南。
每當(dāng)曙光漸染,碼頭上絡(luò)繹不絕的商人在馬驛和水驛里進(jìn)行著商賈買賣,他們把一個水運(yùn)時代推向了極致和頂峰。沅水或其支流兩岸的古鎮(zhèn),鎮(zhèn)遠(yuǎn)、鳳凰、乾州古城、洪江、古辰州(現(xiàn)常德)等都是依著水馬驛形成的繁盛城池。
沅水江畔最重要且最遠(yuǎn)的水馬驛在鎮(zhèn)遠(yuǎn),鎮(zhèn)遠(yuǎn)依沅水支流舞陽河而建。當(dāng)年,由西往東的客商在鎮(zhèn)遠(yuǎn)登舟遠(yuǎn)行,入沅江過洞庭遠(yuǎn)涉東南沿海,而由東溯流而上的客商到達(dá)鎮(zhèn)遠(yuǎn)便棄舟登車,開始在山巒相連的陸路中顛簸穿行,走施秉、黃平,最終可穿越云南,直奔緬甸、印度。一條舞水,穿城而過呈“之”形流向,東接湖南黔城。《湖湘地理》中《溯水篇》就曾考證,在距黔城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清水江和舞水在此相匯而成了沅水。水運(yùn)碼頭的商船以鎮(zhèn)遠(yuǎn)形成重要的水驛和馬驛。1878年,清知府汪炳敖寫下過“辟開重驛路,緬人騎象過橋來”,是指當(dāng)時在水馬驛做生意的異國人。古代鎮(zhèn)遠(yuǎn)與云南之間的陸驛有二十多個,即使在現(xiàn)在的縣境內(nèi),仍有水驛站12個。正是這些驛站與碼頭,連接了古南方的“絲綢之路”。
從沅水一路而下洞庭,南來北往的水馬驛站在各個古城河邊交會。武水邊的乾州古城有十八條石級碼頭通向萬溶江,辰州府則又有大河街、小河街、老碼頭等通向河運(yùn)和街市,從這些碼頭把湘西的桐油、土堿、藥材、青蔗、牛皮及各種土產(chǎn)山貨用小篷船運(yùn)往外地;又把外地的布匹、棉紗、糧食、鹽巴、紙張及日用品運(yùn)往沅水周邊大大小小的城市鄉(xiāng)村。

水天一色。

古老的石階,勤勞樸實的人民,他們依山而生,依水而長。攝于貴州天柱縣三門塘沅水源頭。
大江為主脈,設(shè)大驛站,微小支流的毛細(xì)血管上,遍設(shè)水碼頭,如同一個漁網(wǎng),經(jīng)脈相連,流動奔涌。如云的水馬商業(yè)貿(mào)易演繹出許多動人的傳說,甚至在沅水一個不起眼支流注入的紅旗水庫邊,我也聽到過關(guān)于茶鹽老街的傳說。茶鹽老街是肖伍鋪一僻靜小鎮(zhèn),明清年間靠河而建一座水馬驛,專門從事山民和湖民的鹽茶貿(mào)易,因而形成了一座熱鬧的集鎮(zhèn)。據(jù)說遠(yuǎn)道賣鹽的伍姓姑娘與當(dāng)?shù)刭u茶的肖姓小伙因茶鹽貿(mào)易互生情感,從此喜結(jié)連理,繁衍后代,將茶鹽生意越做越大,集鎮(zhèn)從此得名為肖伍鋪鄉(xiāng)。當(dāng)我們穿越塵囂,聽到這些驛站的野史傳聞,歷史仿佛翻到另一頁,在紙背后,藏了水馬驛站流傳著的涂滿陽光歡笑的歷史。
時光的滌洗是無形的,當(dāng)我在鎮(zhèn)遠(yuǎn)、乾州古城、茶鹽老街行走,再也找不到人流如織的驛站碼頭;踩得發(fā)亮的青石板早已坍塌;孤獨的十八級臺階不再通向任何商船;大河街小河街失去姓名影蹤;沒有誰再演繹水馬驛的愛情傳說;系船纜繩早已腐爛在哪個朝代;茶鹽糧物通過火車飛機(jī)運(yùn)往了更遠(yuǎn)的遠(yuǎn)方。
但是沅水和她的支流還在靜靜流淌著,也許,只有她們會在某些靜夜里傾聽著遠(yuǎn)處傳來的得得馬蹄聲了……

沅水河邊,捕魚歸來的漁民。
江水中靜靜浮出的光陰
我是一個深深懷舊的人,喜歡沉浸在流逝的時間片段里。在被世人遺忘的角落,我總是希望有某個瞬間——能夠讓時光倒流,回到我曾經(jīng)歷或從未經(jīng)歷的過去場景。
很多年來,我傾慕大大小小的古鎮(zhèn)老街。我行游于此,因為古鎮(zhèn)老街是可以找到光陰流痕的地方。也許在茶馬古道千年的青石板上,多少馬蹄、車轍和行色匆忙的腳步輾過,它被歲月磨得光滑發(fā)亮了,如一扇記載過去的書頁,沒有人再去讀懂它的滄桑。有時候下雨,古鎮(zhèn)沉陷清寂,從青石板一閃一閃的光亮中,我能找到時間隧道那個神奇的入口。從那里我能看到更多過去的生活幻象,我便能記下那些不可多得的瞬間畫面。
古鎮(zhèn)是藏納時間之所,它使人想起自己的前生。隔壁人家鏤空照壁上有一幅梅蘭竹菊的木畫,斜對著的暗紅雕花窗上,一對展翅欲飛的蝙蝠。黃昏落巢的斜陽照映這幽暗的圖畫,如果石桌上正有一壺碧螺春暖了我的唇舌,此時我就能走入過去——那里有前清女子恬淡度過一生的繡樓,有小橋流水掩映的郎情妾意,或者是炊煙繚繞的普通臨水人家……
我固執(zhí)地在古鎮(zhèn)上尋找著一些東西。有一年在云南麗江的水車邊聽到了納西古樂,有一年在貴州鎮(zhèn)遠(yuǎn)的舞陽河觸到了車水馬驛,有一年在吉首乾州看到了萬融煙云,有一年在千燈古鎮(zhèn)拾到零星雨意,有一年在湘西鳳凰感到情不自禁,有一年卻是在流水鎮(zhèn)——我要寫下的就是叫流水的古鎮(zhèn)。
“風(fēng)過流水已無影”。因為水庫蓄水,流水鎮(zhèn)已永遠(yuǎn)地沉沒在了江底,當(dāng)我從高懸的堤壩上,遠(yuǎn)看碧藍(lán)得透明的江水,想象這個古鎮(zhèn)。對我來說,流水是所有古鎮(zhèn)的縮影,是我想要盡力挽留卻沒有辦法留住的。
關(guān)于流水,已鮮有人知道它的舊事,在書中網(wǎng)上我沒有查到任何相關(guān)記載,只有一些細(xì)枝末節(jié)道出它在世間的淡淡水影:比如流水居民曉蕓會唱一些特別的民間小調(diào);比如某天中午我遇到的流水餐館,供應(yīng)著金黃土豆、方塊臘肉、大碗酸菜,這都是流水人家最常見的吃法;比如移居山下的流水移民,他們?nèi)哉f“咱是流水的”。
古鎮(zhèn)是一個謎了。它曾經(jīng)被五條小河相圍,到處是潺潺水聲,在修建水庫蓄水后,移民造了一個新鎮(zhèn),五條河從此變成五個無聲針管,流水聲停止,五個針孔的水流注入水庫。一切美好的,因為急促地消失,人們便閉口不談,仿佛從來沒有存在。
這一天,當(dāng)我站在堤壩上,俯看碧藍(lán)江水飛濺出輕俏的浪朵,我有一種沖動:我想復(fù)活它!我想用詩歌復(fù)活沉陷江水的千年古鎮(zhèn),讓它依附我的精神世界的吉光片羽而存在。我以從前游歷古鎮(zhèn)聽到的、看到的、觸摸的、感覺到的為建筑古鎮(zhèn)的磚瓦木石,以深沉的愛重構(gòu)那個嫻靜之鎮(zhèn)。我確信自己在堤上片刻就已找到神奇入口。借此我回到流水古鎮(zhèn),記載著逐漸遺忘的瑣碎人事和愛恨情仇……
更多寂寞是因往事會淡泊,所愛之人會在生命中丟失。我喜歡的一首英文歌叫《昔日重現(xiàn)》,我覺得重現(xiàn)就是一種精神的回歸。曼德爾斯塔姆在隨筆中說:“詩是掀翻時間的犁,時間的深層,黑色的土壤都被翻在表層之上。我喝干這昏暗的空氣像喝盡昏暗的水,時間被犁翻起;那枝玫瑰曾是這片土地。”當(dāng)時間被犁翻起,那雕花窗曾是古鎮(zhèn),橋下紅鯉、橋邊銀杏、橋頭栗木舸……皆為流水古鎮(zhèn)。恍惚間——它有自江底靜靜浮出永逝的光陰。
“認(rèn)出的瞬間足以使我們感到甜蜜”,對我而言,在某些神奇的瞬間,詩歌能帶動靈魂而無所不往。它使我脫離沉重的肉體找到精神的寬闊通道,在時光隧道中往復(fù)穿梭,我是自由、明亮、舒展而飛揚(yáng)的,我確信我能想到人們所未曾想到過的,我能見到人們所渴望見到的——一切。
追尋遠(yuǎn)逝的陬市古鎮(zhèn)
陬市是被時光完全毀壞的一座古鎮(zhèn)。
這座曾依沅水而繁華的小鎮(zhèn)約有五百多年歷史。明清年間,此地水路通達(dá),是湘西北最重要的水馬驛站。當(dāng)年水驛站沿河設(shè)木棑坊,木棑坊將從沅陵上游崇山峻嶺間流下來的小木筏改扎成大木筏,或?qū)⒕d紗、稻谷轉(zhuǎn)運(yùn)到貨輪上,一路浩浩蕩蕩南下或是北上,往洞庭湖,入長江,隨長江走三峽,去往各處航運(yùn)碼頭,最遠(yuǎn)到海上,去往海外。
當(dāng)我來到古鎮(zhèn)尋古覓今,幸運(yùn)的是,在人群中找到了在陬市生活了七十多年的兩個老居民,謝西元和鄢和清。隨著古稀老人的滔滔訴說,古鎮(zhèn)已然消失的歷史,歲月的鴻泥雪爪,慢慢浮現(xiàn)在一條河流之上。
我們從大碼頭開始,仿佛找到了時光隧道的某個入口,輕易地走進(jìn)過去的光影里。
大碼頭臨沅水,位于陬市最東邊,陬市現(xiàn)存三個碼頭中,唯大碼頭還存有一些歷史遺痕。明清年間的石頭臺階還在,上面長滿青苔和水蔓,大樹蔭涼,映照蒼青色的沅水。
大碼頭被商賈河運(yùn)稱之為官運(yùn)碼頭,負(fù)責(zé)迎送官家客船。當(dāng)年的京漢居,建有木樓三棟,最底下為飯鋪茶肆,中為戲樓,最上為歇息打尖的客棧。官家客商從碼頭下來,在京漢居聽?wèi)蚝炔瑁R船聲的疲倦便消聲杳跡。大碼頭還存有字跡模糊的“湘航客運(yùn)站”等幾個紅字,湘航公司自1998年改制后宣告破產(chǎn),職工們搬離碼頭,剩下幾棟搖搖欲墜的破房子。
往大碼頭沿堤向西而行,很難想象這座毫不起眼的大堤曾是十里繁華場,在謝西元老人的訴說中,沅水兩岸停靠的木棑幾乎鋪滿了沅水河,兩岸有無數(shù)的吊腳樓,沈從文先生在《湘行散記》中也多次提到了這些吊腳樓。
吊腳樓設(shè)有堂班和窯班,堂班和窯班里有來自上海、江西、武漢的美貌女子,堂班為戲樓,窯班為煙花樓。民國時,一塊光洋可換來一夜風(fēng)流。許多從沅陵木排上一路漂過來的木排工,領(lǐng)完工餉,就在窯班將一路來的孤獨消空。吊腳樓上有他們相好的女子,他們揮霍口袋里叮當(dāng)作響的銀元,據(jù)說很多船工因此領(lǐng)到錢餉后又空手返回。
民國時陬市曾有三大名樓,一為爽心樓。老人謝西武的祖父是該樓的樓主,一樓設(shè)飯鋪,二樓為戲臺,三樓為窯班。謝老祖父是陬市的保鎮(zhèn),相當(dāng)于現(xiàn)在鎮(zhèn)長,是家境富裕的一鎮(zhèn)諸侯。另為翠谷樓和大雅樓。翠古樓樓主姓向。傳聞此樓為不義之財所建,向姓主人在沅水貨船上結(jié)交了同年同月同日李姓老庚,生意往來,相交甚密。一日,李老庚將木材運(yùn)抵陬市,因思家心切,便把木材等貨物寄在向主家。李某回家途中病亡,數(shù)日后其妻來到向家,打聽貨物下落,不小心透露李某病死的消息。向主人便將貨物私吞,冷臉打發(fā)庚妻回到湘西。某日,向主人回家,見李老庚好端端坐于堂屋,大吃一驚,李老庚悠悠地說:“我來收寄存的貨”,言畢消失不見。當(dāng)月,向主人得一子,驚嚇之余,將自己的財物與私吞的財物分成兩份,私吞的財物修樓一座,翠谷樓。其子后成敗家子,家產(chǎn)被揮霍一空,翠谷樓亦被抵債。
我們來時兩樓都已消失,不見片瓦只磚,兩位樓主的后人悠閑地在陬市的茶肆里打紙牌,過去的歲月都已不值一提了。從明清到民國,從民國到抗日,從抗日到解放前,陬市鎮(zhèn)最終毀于解放前的一場大火。日本兵在常德狙擊戰(zhàn)里點燃的大火燃了幾天幾夜,最終把沿河而建的木樓焚燒一空,一座古鎮(zhèn)因此在烈火中消失無影。
我見到陬市河堤上的碎石場,巨大的轟鳴聲把我從夢境中驚醒,河邊青草依依的堤岸,人去樓空的湘航公司,都如恍然一夢。
老人平靜的述說中有關(guān)于亭子的一段記憶。亭子是陬市鄉(xiāng)民傳統(tǒng)的娛樂場地。節(jié)日時在老街上用手抬著巨大的戲臺,那些紙制的人,皮偶戲,都在亭子里表演。當(dāng)我們在臺下看戲,看著看著就忘記了身在何處,忘記了水馬船聲、吊腳樓上女子咿呀的哼唱,忘記了大火,也忘記了后來修筑的堤,把澧家洲、鸕鶿洲、揚(yáng)洲完全隔離開來,澧家洲的斷橋變成了小巷,鸕鶿洲變成了擁擠的大街。沒有人再記得從前,兩位老人也已記憶模糊。
往古街回去的路上,我有幸找到了一段完全破舊的青墻,我悄悄地經(jīng)過了這最后的遺跡,也悄悄地從時光隧道中走了出來。
夷望入江
如果把沅水分成上游、中游、下游三段的話,我覺得夷望溪注入沅水的入江口可以當(dāng)作下游的真正開始。我需要充分的時間去觸摸河流的肌膚,而不是去想象河流,當(dāng)我在河邊,內(nèi)心的情感得到真正的沉淀,并且結(jié)晶。這是一個美好的、讓人激動的過程。
我去夷望溪并不是在江水最完美的季節(jié),一個月來,湘楚大地夏雨滂沱,我們的越野車過桃源縣城后右轉(zhuǎn),便進(jìn)入了曲折的山路。經(jīng)過的兩個鄉(xiāng)鎮(zhèn)——深水港、泥窩潭,都是逢二趕集的日子,狹窄的水泥路上擠滿來來往往的山民。年歲大的山民背著背簍緩行,年輕的則騎著摩托車呼嘯而過。鎮(zhèn)中心街道上全都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物什,西瓜香瓜成堆堆在路邊,剃頭鋪生意正好,包子鋪里熱氣騰騰,花花綠綠的衣服涼鞋擺了一地,路邊還有長長的案板,一塊塊大肥豬肉擱那案板上。小堆的金黃苞谷,推車?yán)锩装椎奶鹁啤I矫駛冊诼愤呥汉然蚴歉`竊私語,顯得和諧閑散。
車過凌津灘,我們才時斷時續(xù)地接近沅江,因為江流在山形中時隱時現(xiàn),我們的視線也一會兒開闊,一會兒閉窄,想捕捉這明黃的飄帶,卻又不知它在哪里。等走過山路十八彎,翠綠楠竹和一叢紫穗蘆葦在路邊頻頻點頭時,興隆街就近了,隱隱我聽到了沅水撲撲的心跳聲,它仿佛在等待我的到來。



泛綠的淺灘,黃燦燦的油菜花,打撈水草的農(nóng)民奏響一曲春的樂章。
因為漲水,沅江變得開闊,滔滔江水濁黃,流速略急,江面時而皺褶,時而平整,似一匹黃色的錦緞鋪開在碧山秀水間,顯得氣勢恢弘,它的濁流中不時有紅色的挖沙船發(fā)出一聲聲低沉的吼叫。我們乘當(dāng)?shù)匾凰页运苌畹臋C(jī)帆船,溯沅水而上,直達(dá)夷望溪頭。陽光很烈,但江風(fēng)清涼,更清涼的是江兩岸翠綠的風(fēng)景。天空湛藍(lán),白云縷縷,從河心望向河面,水面倒映著的岸影和山色呈明黃和灰黑。水漲后略有回落,使江邊的楊樹、楠竹、蘆葦、荊棘、桑葚貼近水面的部分露出一小片灰白的泥印。翠綠中,時而現(xiàn)出紅屋頂瓦房,或是藍(lán)屋頂樓房,或是一間木屋,旁邊碼頭上站著一名紅衣少女,這都是翠色中引人驚訝的亮色調(diào)。
遠(yuǎn)遠(yuǎn)的對面,有一個黑點,過一會兒,看到一艘小船,聽到機(jī)器的聲音,響聲越近,船越大,看到船內(nèi)的男人,一剎那的照面,那船與我們的船擦身而過了,不知他們從哪里解繩,也不知他們將停靠在哪里,順著他們的船在水面留下的痕跡看下去,眨眼功夫,河流就把一切洗得干干凈凈,只留下一船高談闊論的人看著江水和兩岸。
船過無痕啊!而江水卻給了河岸無窮盡的痕跡。一個水中洲渚在江中清晰可見,洲渚的右邊是夷望溪,左邊是沅水,如果繼續(xù)溯水而上,我們會到達(dá)沅水的中游,上游——也許那里有王村、洪江鎮(zhèn),也許是辰溪、瀘溪或是沅陵古鎮(zhèn),也許是北溶鎮(zhèn)、麻伊伏。如果向下,就會像當(dāng)年的沈叢文一樣,神往于香草香花的沅洲,如果過沅洲,也許能遇見“朝發(fā)枉陼兮,夕宿辰陽”的楚逐客屈原。“沅有芷兮澧有蘭”,我們甚至可以“乘舲船余上沅兮”,去尋找岸邊的蘭草。
我們停船泊舟,順山而至夷望山頂,俯看著夷望溪與沅水交匯的剎那,溪水和沅水有著同樣的濁黃質(zhì)地,如同母子,一個細(xì)弱些,一個寬厚些。對峙的山峭如同沅水張開的雙臂,迎接孩子撲入她的懷抱。江邊盤繞一條細(xì)細(xì)的公路,在闊大的江面上纖細(xì)而柔韌,仿佛要向遠(yuǎn)方飛了過去。
對河流而言,她的支流、兩岸的樹、她滋養(yǎng)的生靈都是有生命的,當(dāng)支流注入沅水時是支流的一種結(jié)束,然而這樣的結(jié)束卻是回歸,是另一個水聲滔滔的開始。在夷望溪,我理解的沅水第三條河岸的意義,是河給予生命無盡的肉體的和精神的自由。

沅江邊,濃霧中,若隱若現(xiàn)的常德城恰似海市蜃樓般美麗。
洞庭鷺影
經(jīng)過濤聲的滌洗,呼吸蘆葦蕩的氣息,天越來越藍(lán),風(fēng)中帶有夏天的熱氣,我們的眼睛也越來越亮,是沿途的青蔥將我們變成濕地一只只小動物,沒有翅膀,只有張揚(yáng)著的笨拙肉身,船載著我們緩緩地爬行著,沿著湖水,我們看到了兩岸密不透風(fēng)的黑楊林。
這是一叢還沒有被水淹沒的林子,黑楊是生命力極強(qiáng)的一種樹,每年他們被水淹沒的時間有近一個月,大水退了,他們?nèi)匀换钪譅渴值模θ~間漏下點點陽光。在這塊濕潤的黑土地上,我們的歡笑聲驚動了林子里成千上萬的白鷺,他們大雪片一樣飛起,沿著湖堤成群地飛動,我們禁不住用掌聲呼應(yīng)他們的飛翔,鷺鳥自船后落下,安靜,另一群又飛起,他們依水飛行,沒有飛到天空上,只是在林子中盤旋著落下,仿佛大雪飛起后又落回了枝丫間。
經(jīng)歷流光回雪的一段路程后,林子漸漸稀落,但有江洲不時出現(xiàn),洲上有青草地,一群黑色的水牛在青洲上悠閑地走著,這里的世界從來都是他們的,天光晴好,青草豐美。在牛背上,在草叢里,在大湖邊,站著一種灰黑色的水鳥——牛背鷺,這似乎是一種專為牛群而活著的鳥,也是洞庭湖唯一不以魚類為食的鳥類,它們相伴著牛群,過著與世隔絕的快樂生活。

上:清晨,外出捕魚的漁民徜徉在畫一般的美景中。

下:晨霧中,河灘上,野鳥自由翱翔,家畜自由覓食。
我們的船在日頭下航行,天氣炎熱,不時有飛躍出水面的魚兒。沿途我們遇到了一些漁船,最多是鸕鶿船,一排嘴喙突出、羽毛灰黑的大鳥站在魚桿上,守船的漁夫安閑地等待收獲,我們也遇到過小木船,牽著一張張漁網(wǎng),逶迤而行。我知道,在水下也有另一個洞庭湖的世界,就是數(shù)不清的魚類王國。據(jù)介紹,水中有一百多種魚類,青鯽鯉鳊,還有小到細(xì)如銀針的銀魚,有額上一點紅的狀元鯽,有燦若晚霞的胭脂魚,有猛如冒雨頂霧飛離水面的烏鱧,有靜如處子的沙鱧。
我們進(jìn)入西洞庭湖的萬畝蘆葦蕩,除了水道,我們身陷于蘆葦?shù)暮Q罅恕LJ葦只有兩種簡單的分類,一類是寬葉,可以包棕子吃,一類是窄葉。細(xì)細(xì)地隨風(fēng)搖曳,蘆葦站在水中,洞庭湖一節(jié)節(jié)退水,蘆葦?shù)纳碜由嫌幸欢瓮怂蟀咨哪酀簦翊┲咨棺拥墓媚铮缓笫乔啻涞闹Γ啻涞娜~,青翠的表情,青翠的笑聲,這兒的一切都是翠的。蘆葦遮住了我們的臉,遮住了我們的船,遮住了我們的歡笑嬉語,也許慢慢地,我們也變成了其中青翠的一枝,融入到西洞庭的浩浩蕩蕩之中。
洞庭湖分為東洞庭、南洞庭和西洞庭,東洞庭在岳陽,是當(dāng)年范仲淹書寫《岳陽樓記》的地方。人們想到洞庭湖常常只想到岳陽,其實洞庭湖包含著更多的涵蘊(yùn)和內(nèi)容,是很多人無法真正了解的,比如此處的西洞庭,它的濕地養(yǎng)育了無數(shù)的植物、魚群和水鳥。西洞庭湖的水鳥有夏候鳥和冬候鳥,有的夏天飛來度夏,有的冬日飛來越冬,炎夏之中我們看的最多的夏候鳥就是白鷺、蒼鷺和鶿鷺。這里是蘆葦?shù)奶焯茫彩曲橒B的天堂。
在洞庭湖的楊柳嘴,是澧水和沅水的南支合流的地方,沅水清澈,澧水混濁,兩水合流處形成一個明顯的分界線。我們的船沒有經(jīng)過合流的分界,只在分界附近的楊幺水寨停留,然后駛往了洞庭煙云。洞庭煙云是西洞庭最廣闊的地方,萬頃波濤一直延伸到天際,在水天之中航行,風(fēng)起云舒,濕潤的湖風(fēng)吹來的水霧灑在臉上,白鷺將翩飛的影子映在一望無際的湖面,順著萬里煙波的湖上行走,可以順?biāo)碌竭_(dá)南洞庭和東洞庭,可以溯水而上到達(dá)沅水,澧水。它如此寬闊,信任著萬事萬物的自在和美,人間的小悲歡都不值一提。
當(dāng)我順著沅水河行走,到達(dá)入湖口,經(jīng)過巖汪湖,到達(dá)目平湖、洋淘湖,我覺得我自己也越走越寬,河流影響到了我,也影響我的人生,它使我不再局限于自我的小情緒,而是在自然中,從最細(xì)小的流動到越來越寬大,越來越渾厚,直成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