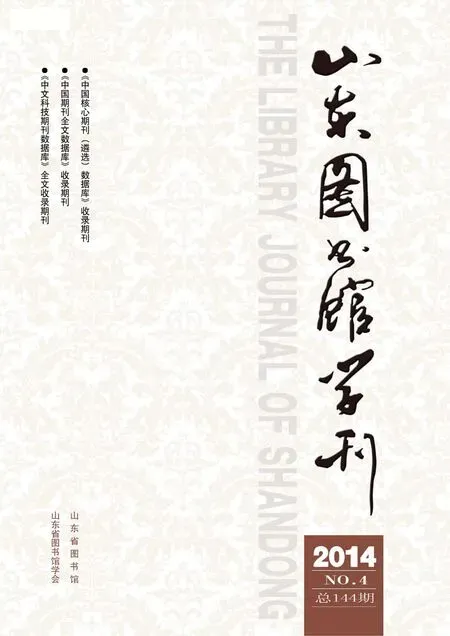“但求解古人故舊之沉郁”
子 張
(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32)
三月卅一日,下午先后為研究生和大一新生講授近代印刷出版業之發達,晚間卻忽然收到寧文兄短信,告知來新夏先生剛剛在這個下午過世,年九十一歲,并準備于《山東圖書館學刊》下期組織紀念,問我可否寫點什么。
雖然我與來先生既不熟悉,亦無往來,但又覺得確有某些話要說,故立時回復寧文兄,答應寫段文字略表悼念之意。
來先生鼎鼎大名,我總是知道的,可因為專業離得稍遠,往還的機緣也就不容易碰到。沒想到2006年春天,我應約赴天津南開大學參加詩人穆旦的學術研討活動,竟然邂逅了這位著名的前輩學者。先是他來看望和我同住一室的海寧學者陳伯良先生,彼此簡單交流幾句,我始知他乃浙江蕭山人。翌日會議開幕,來先生出席了開幕式。而會議期間他是否有過發言,我已記不清楚了。
前年初夏某日,也是寧文兄短信告知,來新夏教授學術思想研討會暨九十華誕慶典在蕭山舉辦,約我帶本書去請其簽名。惜我手頭只有來先生主編“中華幼學文庫”并作序之一種《雜字》,想想遠不夠“粉絲”級別,遂作罷。但還是當即乘車趕到蕭山賓館,見到了寧文、韋泱諸兄,寧文甚至為我預留了一套紀念品,包括一幅“壽”字掛軸、一幀“中國郵政”紀念封、一本中華書局版精裝《友聲集——來新夏教授九十初度暨從教65周年紀念集》,以及一部樸廬書社印制的繁體豎排《來新夏隨筆選》。盡管第二天未再赴會,卻因了寧文兄的邀約,倒一下子有了若干與來先生有關的物品,便再也不能說與來先生無緣了。
我于來先生之史學、目錄學、圖書館學乃至寫作成就,近乎盲者,實在無由置喙。然讀過他的《懷穆旦》一文,卻感到文章雖短,感慨甚深,由此或可觸及到來先生心路之一隅。
來先生曾自謂其散文隨筆“不外三類”:一曰觀書,二曰窺世,三曰知人。“觀書所悟,貢其點滴,冀有益于后來;窺世所見,析其心態,求免春蠶蠟炬之厄;知人之論,不媚世隨俗,但求解古人故舊之沉郁。斯固可謂冷眼熱心之作,亦我食草出奶之本旨。”(見《人生也就如此》)
我以為,《懷穆旦》一文,正是一篇“不媚世隨俗,但求解古人故舊之沉郁”的“知人之論”。
生前寂寞無盡,死后享譽日隆,是一切人格高潔、藝境超前詩人的普遍命運,穆旦自不例外。而世俗之人,卻既可以與俗世同謀冷落詩人于前,復可以攀附詩人榮名以自售于后,實則前倨后恭,皆非本心,功利之欲使然耳。
而來先生此文,卻并非那種借光自賞的投機之作,他反反復復強調的,只是希望在面對穆旦的光榮時,別忘了穆旦后半生所遭遇到的厄運和苦難。
之所以出此言,是因為來先生在“文革”時期,曾經與穆旦由較遠而較近,由同命運而成為在一起打掃校園和廁所、清洗游泳池而近距離接觸的難友,因此成為穆旦受難史中某個時段“唯一的見證人”。故而來先生表示:“為了讓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較完整的記述,后死者應該擔負起這種追憶的責任。”這正是此文的意義所在。
文章既對穆旦“文革”前十幾年在南開的遭際有所陳述,更對穆旦于“文革”初期幾年進一步的淪落作出了有力的見證和描畫,令讀者像是親眼看到了身處苦難深處的詩人影像。其中當然也有來先生自己對穆旦的印象,比如:“后來當我讀到他的全集時,那種才華橫溢的詩才與他在游泳池勞動相處時的形象怎么也合不起來。他有詩人的氣質,但絕無所謂詩人的習氣。他像一位樸實無華的小職員,一位讀過許多書的恂恂寒儒,也許這是十來年磨練出來的‘斂才就范’”。1970年,二人分別被解送到不同的地方“勞動改造”,直到四年之后才又開始在校園里偶爾碰到。限于嚴酷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形勢,這自然也算不上什么深度交往,然畢竟遭際相似,彼此心有戚戚,能夠相互談談詩歌甚或彼此寬慰幾句,已經極其難得了。看得出,兩人性情有差異,而穆旦長來新夏五歲,故而穆旦常處在“囑咐”、“開導”地位,也是可信的。
在文章后半,來先生也有疾言厲聲為穆旦抱不平的陳辭,那就是對有關方面對穆旦錯案平反一再拖延的憤怒:“錯誤決定何其速,而糾正錯誤又何其緩?”
也許從這里,讀者可以感覺到來先生更為幽深的感慨和疑問。一個竭盡全力熱愛祖國的詩人,何以長期遭到嚴酷的打擊和折磨?何以“生前的二十幾年,幾乎沒有一天舒心日子”?“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我能從來先生的話中品味到一種濃濃的苦澀。來先生說:“穆旦喝盡的苦酒給生者帶來了許多理不清的思考。真正希望穆旦喝盡了苦澀的酒,把一切不該發生的悲劇一古腦兒擔走”,這其實也是所有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心聲呵……
謹以此文表達對來新夏先生的敬意和悼念。
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甲午三月初四,于杭州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