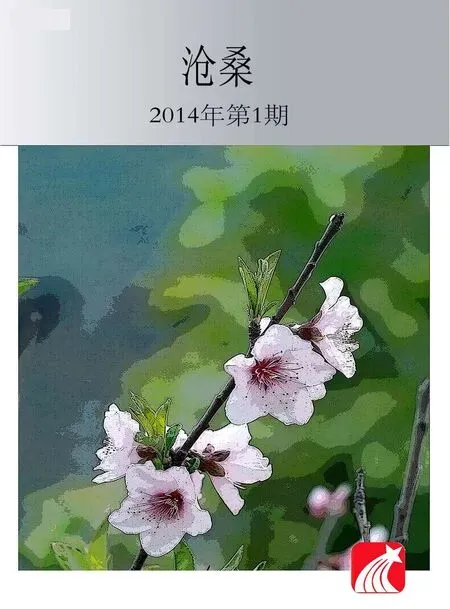十六國時期北方民族的漢化進程
魏振國
十六國時期北方民族的漢化進程
魏振國
民族融合自古以來就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北魏統一以前十六國時期的漢化是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組成部分。五胡入駐中原的同時,其自身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也開始了封建化。十六國時期民族的漢化不僅鞏固了自己的統治,甚至為后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以往人們只注重了這一時期的戰爭動亂,卻對少數民族自身的漢化進程論述甚少。
十六國時期 少數民族 漢化 民族融合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長期分裂動蕩的歷史時期。十六國政權是指東晉永興元年(304)匈奴人劉淵建立漢國,到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9)。北魏統一中原前的135年間,先后有匈奴、羯、氐、羌、鮮卑5個少數民族建立的16個割據政權,史稱“十六國時期”。這些少數民族在曹魏、西晉年間就已遷居黃河流域。各民族之間交錯雜居,各民族之間的相互交流也比較頻繁,民族融合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主流。由于北來的少數民族受中原漢族先進的生產方式、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影響,民族融合又以少數民族的漢化為一大趨勢。本文主要來探究這一時期少數民族漢化的進程。
一、少數民族上層自身的漢化
由于五胡遷往中原在曹魏、西晉時期就已開始,所以十六國政權的創立者,從小就受漢文化的熏陶,自身漢化進程也比較深。史載漢國的劉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1]劉淵第四子劉聰,“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余篇,賦詩五十余篇。”[2]后趙的建立者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閑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3]前燕的建立者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4]。南燕的建立者慕容德,“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5]前秦的建立者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祖)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6]后秦的上層姚襄,“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7]由此可見,胡族上層自身的漢化程度很高,他們好學,喜歡讀儒家的經史,善詩文、書法,深得儒家的治國方略,使他們按照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規范考慮經國要務,有利于他們推動漢化的進程。
二、政治組織上以夷化夏
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以后,自身的政權體制落后于中原的政權體制。為了維護他們在中原的統治地位,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重用漢人的知識分子,借鑒漢民族封建制度的先進成分。其一,在官僚制度上,匈奴劉聰當政時,“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置左右司隸……單于左右輔……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馬景位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8]。再看羯族后趙政權,石勒稱帝后,“論公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9]。這些封爵也繼承了傳統的封爵方式及稱號。到石虎當政時,已下書曰:“吏部選,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10]說明石虎當政時完全繼承西晉時的官制,與中原無差別了。我們可以看到隨著中原強大的封建政治體制對少數民族政權的影響,少數民族政權的官制在逐步漢化。其二,在社會組織,經濟生活上,“由部落變成編戶,是胡族社會上的一個進步,之所以有這個進步是與漢人接近,接受漢文化的結果”[11]。慕容暐時期,“令諸軍營戶,三分共貫”[12]。都是稱戶,而不以少數民族的部相稱。苻堅時期:“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13]姚興時,“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14]通過這些可以看出,少數民族政權以戶為基本單位進行統計,社會組織顯然由部落進化成編戶。在經濟生活上,采用封建賦稅制度。前趙的建立者劉曜時,“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15]。石勒攻占襄國后,“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資二匹,租三斗”[16]。采用田租戶調的方式,明顯的漢化。其三,在官吏選拔上,十六國君主大都能打破民族界線,招納和吸收大批漢族知識分子參與新朝政治。如石勒轉戰河北時,“陷冀州郡是,堡壁百余,眾至十余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及引張賓為謀主,始置軍功曹,以刁鷹、張敬為服股,夔安、孔長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陰、桃豹、吳豫等為將率。”[17]他稱帝后,又“重禁胡人,不得凌侮衣冠華族。”[18]之后又用九品官人法來選拔漢人。張賓死后,石勒曰:“機不虛發,算無遺策,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19]說明張賓在石勒政權中受到重用及所起的重大作用。再如苻堅時期的王猛,“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20]。著重強調王猛在政權建設中的重大功績。
三、經濟生活上的農本思想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業不僅關系到民生,還關系到國家穩定、強弱、戰爭勝負等大計。在地理上我國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為界,其東南為太平洋及印度洋季風影響的濕潤地區,其西北為東南季風影響較少的干旱地區,是我國農業和畜牧業的分界線。十六國的少數民族居住在400毫米線的西北地區,以畜牧業為主,而漢族居住在東南地區以傳統農業為主。當十六國的少數民族入駐中原之際,他們深受中原先進的農耕經濟影響,繼承了漢民族以農為本的重農思想。前燕慕容皝執政時言:“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谷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苑園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令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百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余者還農。溝洫灌溉,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各盡水陸之勢。”[21]可見他的重農思想,積極發展農耕經濟,并督促地方官員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羯人石勒稱趙王后,“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于是重制禁釀,郊祀宗朝皆以醴酒。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22]注重安撫流民,保護農業生產。前秦苻堅執政時期更是積極發展農業生產,“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親耕籍田,其妻茍氏親蠶于近郊。”[23]針對關中干旱少雨的特點,“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徑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收瀆。”[24]從而增加了糧食的產量。致使前秦經濟一度恢復發展,“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道樹櫆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于途,工商貿販與道。”[25]呈現一派小康氣象,前秦正是憑借這種國力,一度統一了中原。十六國胡族政權的重農思想與實踐,不僅有利于戰爭年間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也通過生產方式的轉型與農業技術的交流,有力地促進了西北各民族的漢化和封建化進程,從而為后來北魏統一中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四、思想文化上的德天尊儒
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論斷: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縱觀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歷史很能說明這一問題。內遷胡族統治者深刻認識到要想在中原有長遠的統治,必須把漢族文化作為治國安邦的統治之術。自西周以來,歷代漢族帝王即宣揚天命,以維護自身統治的正統性和神圣性。這一傳統被少數民族所繼承,諸如漢國建立者劉淵,“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鬚擢鱗而至祭所,六天乃去,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26]后趙君主石勒降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中庭,見者咸異之。”[27]前秦君主苻堅出生時,“其母茍氏當游漳水,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28]十六國諸胡族君主借助中原的天人感應說來神化自己的地位,最終鞏固自己的統治。此外他們還大力興辦學校,學習中原的儒家文化。前趙時期的劉曜,“立太學于長樂宮東,小學于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于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29]后趙時石勒,“立太學,簡明經善文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增置宗文,宗教,崇儒,崇訓十余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一人,弟子一百十五。”[30]石勒還“親臨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31]前秦對儒學更為重視,“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修釋奠焉。”他經常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32]前燕慕容皝時期,“賜其大臣子弟為者號高門生,立東庠與舊官,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33]由于尊儒重教之風,少數民族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鞏固了他們的統治。
結論
十六國時期的漢化是魏晉南北朝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來蒙古的漢化不能與其同日而語,元代曾經是中國歷史上的強盛王朝,然而成吉思汗彎弓射雕的勁氣在他的后人手里留下一種蔑視文化的粗陋與狹隘。蒙古貴族沒有文化,他們分民族為四等,置漢族與賤類,并且鄙視知識分子,以儒生掛名俘籍,倡優畜之。讀書人久視為登天之梯的科舉,在蒙古人眼里是并不值錢的。這種做法本身就挖掘了一道社會鴻溝,使他們的根無法深深地扎進中國的社會和歷史。而十六國少數民族的君主并不如此,他們君臨中國的過程,同時也是自身漢化的過程。他們自覺地繼承前代的政治制度,而且接受并提倡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為北魏的統一,隋唐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礎,甚至為當今的民族政策的制定,為我們今天的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
[1][26]晉書·劉元海載記[M].中華書局,1982.
[2][8]晉書·劉聰載記[M].中華書局,1982.
[3][9][19][22][31]晉書·石勒載記下[M].中華書局, 1982.
[4][21][33]晉書·慕容皝載記[M].中華書局,1982.
[5]晉書·慕容德載記[M].中華書局,1982.
[6][13][23][24][25][28][32]晉書·苻堅載記上[M].中華書局,1982.
[7]晉書·姚襄載記[M].中華書局,1982.
[10]晉書·石季龍載記上[M].中華書局,1982.
[11]萬繩楠.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
[12]晉書·慕容暐載記[M].中華書局,1982.
[13]晉書·苻堅載記上[M].中華書局,1982.
[14]晉書·姚興載記上[M].中華書局,1982.
[15][29]晉書·劉曜載記[M].中華書局,1982.
[16][17][27][30]晉書·石勒載記上[M].中華書局, 1982.
[18]晉紀十三·中宗元皇帝中[A].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76.
[20]晉書·苻堅載記下[M].中華書局,1982.
魏振國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碩士研究生
(責編 高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