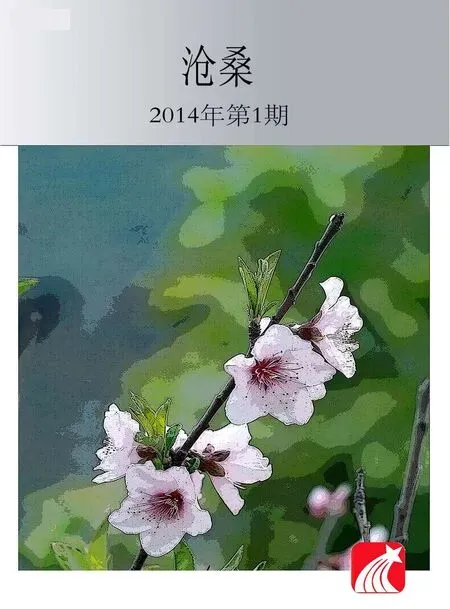《汾州府志·平遙編》序
來新夏
《汾州府志·平遙編》序
來新夏
平遙冀有貴先生,能文善書,為三晉名士,與我以文字相結識殆二十余年,時有切磋,頗得收益。新編方志事業,冀先生以才名,為當局借調,主編《平遙縣志》,殫精竭慮,黽勉從事者多年。1999年春成稿時,該縣副縣長李全祥與冀先生偕來寒舍,征求意見,并請作序。因其情真意切,乃允讀其志,并為作序。是年夏,我應邀親赴平遙考察,見其于維護古城,頗多善策,而境內留存舊物古跡,所以多有。觀其城而讀其志,于其敘古城事不足,似有微憾。緣今修新志,自有體例,古城勝景,不過新志數十篇章之一門,難以饜民眾之需求。于是在交談中,我曾建言說,平遙古跡如此之多,何不別撰古域志,既能為全省通志備份,更可作宣揚古城文化,備導游指南。我不過信口一言,而李、冀二先生則耿耿于懷,時在念中。經多方奔走,終于在2001年春得獲立項,責成晉中市史志研究院負責,由冀有貴先生主編,經年而稿成。題曰《平遙古城志》,為今修志書開縣級古城志纂修之先河。
平遙于世紀前后成二志,皆出冀有貴先生之手,誠為難得。冀先生于編纂縣志過程中,得讀平遙舊志多種,于舊志情況了若指掌。平遙修志自金始修《平遙圖經》以來,歷明至清,共修志九次。計金志一種,明志四種,清志四種。金、明二朝志均佚,獨清康熙十二年、四十五年,乾隆三十五年及光緒八年四志,尚散存各方,但使用頗多窒礙,幸2004—2005年該縣重新影印康熙二志及光緒志等三種各數百冊,幾近全璧。而明志一無所存,時使冀先生引以為憾。
冀先生于主編《平遙縣志》嘗不時翻閱《汾州府志》,平遙為汾州屬縣之一。府志中又有平遙專編。經相核校閱,參以專家考證,盡悉府縣志書之關系。蓋萬歷《汾州府志》之內容皆采自萬歷初之《平遙縣志》,而乾隆《汾州府志》亦采自乾隆《平遙縣志》。冀先生以為,茍將其各自輯出,則前者可補明志之佚缺,后者可解難求之困惑。設由萬歷、乾隆二府志中,別裁《平遙編》,另成一書,則為平遙之縣志傳承,增光添色,固非僅僅補益缺憾而已。
明萬歷三十七年《汾州府志》經李裕民先生點校,清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經馬夏民先生點校,糾謬正訛,條理編次,皆具勞績。而李裕民先生為萬歷三十七年《汾州府志》所寫之點校前言尤見功力。李先生對該志作了優缺點的公允評述,并有所考證、論辯,非一般點校前言可比。冀先生有鑒于此,久有心于二志之擇錄,自成一書,以補平遙明志之佚缺。惟以公私猬集,簿書鞅掌,難得空閑,蹉跎遷延,郁為心結,待時而動。
去冬今春,冀先生為疝疾困擾,手術后臥病、養病,殆將數月,瑣務屏除,較有空閑,書生故態,未能稍泯,遂抱病重理舊業,病愈而書告成。其堅韌不易之志,天人共鑒,足令人欽敬。冀先生于詳閱慎錄過程中,抽繹編錄原則三,頗有參考價值。一曰關于節選內容,將府志中分散在各卷目中的平遙內容,分別照原樣一一擇錄,以利讀者;二曰編錄體例,在盡量保持原卷目體例不變的前提下,酌情對少數卷目適當合并與調整但無損原志內容;三曰校勘編注,府志重印時李、馬二先生曾于各卷卷屬設“校勘記”,冀先生編錄時,若見有小誤者,即加注釋與訂正,立“編者注”于“校勘記”之后,于提高原府志專篇質量,極有裨益。當前各地整理舊志者頗多,有重印者,有點校者,有重加整理校勘者,有以舊志改編新著者,而從上一級志書中擇錄其屬縣某、重加編錄成一書者,則未之見也。冀先生此舉,當為首創,或可為后來者示范,我將拭目以待,是為之序。
辛卯盛夏寫于南開大學邃谷,行年89歲。
來新夏 中國地方志協會學術委員南開大學 教授地方文獻研究室 主任
(責編 高生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