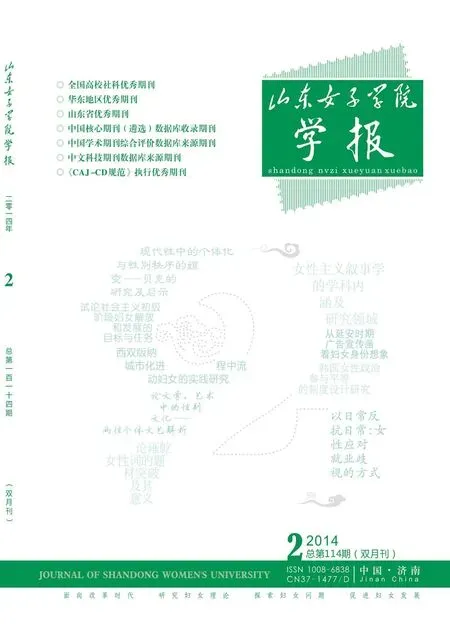西雙版納城市化進程中流動婦女的實踐研究
章立明
(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轄一市(景洪)兩縣(勐海和勐臘),是瀾滄江流出云南南端的最后一塊陸地。西雙版納的城市化是20世紀中國現代性的一個縮影,景洪城是外來移民的主要流入地,如果以1979年為界,可以把1950年以來進入景洪的移民分為計劃流動和自發流動兩種類型。本項研究始于1999年,在隨后10年的田野工作中,作者收集了計劃流動和自發流動婦女的30個案例,通過對這30個案例進行分析,可以揭示出不同階段不同民族的流動婦女是如何及怎樣嵌入城市的。
一、流動婦女嵌入城市的背景
正如吉登斯認為的,“現代的城市往往就是傳統城市的所在地,而且看上去它們似乎僅僅是舊城區的擴展而已,但事實上,現代的城市中心,是根據幾乎完全不同于舊有的將前現代的城市從早期的鄉村分離出來的原則確立的”[1],而且伴隨著現代性的是,“社會關系從地方性的場景中挖出來并使社會關系在無限的時空地帶中再聯結”[2],移民城市景洪城的興起本身就是一個極好的例證。
20世紀70年代格蘭諾維特在波拉尼的嵌入性(經濟關系嵌于社會關系之中)基礎上,提出“強關系”和“弱關系”說,認為弱關系是個人獲得發展機遇的重要來源。然而,邊燕杰的研究證明在中國社會的求職過程中強關系的作用要更大一些[3]。聚焦西雙版納流動婦女的性別案例,可以發現在計劃流動中起作用的是強關系,而在自發流動中則是強關系與弱關系交替發生作用。
“把婦女當作一個群體和穩定的分析范疇加以利用是成問題的”[4],因此不同時期進入景洪的婦女們首先是異質性的。例如在計劃流動中,來自湖南的漢族婦女與西雙版納州勐海和勐臘山區的哈尼族婦女能夠在國營農場定居下來并成為城市居民,而在自發流動中,任何族群的流動婦女都很難能夠獲得景洪市戶籍并且在當地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其次是能動性的,無論是來自四川、貴州、墨江、鎮沅的漢族婦女,還是來自勐臘、勐海壩區的傣族婦女,以及山區的哈尼族婦女,其個人自身資源相當有限,不足以支撐她們的流動并嵌入城市社區,但是“在適應周圍環境時,個人會有不同的資源可供使用,其中有他們自身的資源、核心家庭的資源、擴大家庭的資源,甚至鄰居朋友的資源,或更寬廣的社會資源。在依賴族人的策略中移民是利用核心家庭以外的親戚資源以適應環境;依賴同輩的策略則運用同輩及相同社會背景的人的資源進行調適;依賴自己的策略則依靠自己及核心家庭或外界非人情關系的組織資源。”[5][6][7][8][9][10][11]因此,這一階段婦女在流動過程中并非只依賴某種單一的資源,而是對族人、同輩和組織資源的交替使用。
二、1979年前景洪的計劃流動婦女
景洪的城市化過程,是傳統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邁進,即從邊陲到邊界的轉換過程,而這一過程也是一部各族移民進入西雙版納的邊疆開發史。歷史上的西雙版納地廣人稀,“十二版納全境……每平方公里現僅有居民八人”[6],1949年以前,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漢族人口總數為5000人,僅占其全境總人口的0.26%。
西雙版納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獨特的氣候條件,使其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后計劃移民的目的地之一。1950年以后,中央政府對西雙版納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歷史調查,1953年1月,成立了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1956年,在全州實施和平協商土地改革,在傳統勐制度所依托的土地制度瓦解之后,中央政府開始著手在西雙版納建立國營農場,因為新中國成立后,很多戰略物資受到西方國家的禁運和封鎖,其中就包括橡膠及其制品,所以,中央政府便開始在西雙版納這個被認為是世界植膠禁區的熱帶地區北緣引種三葉橡膠。從1955年起,中央政府在整個西雙版納地區共建立了10個大農場,形成一個以橡膠—甘蔗—水稻種植為主的邊疆屯墾區,到1993年,整個西雙版納農墾系統人口達到了14.23萬人[7],在移民人口稠密的農場四周形成了星羅棋布的大小集市,大大推進了景洪的城市化進程,景洪成為一座依托屯墾而形成的新型移民城市。
由于景洪城市化的主體是國家,政府通過戶籍、就業、商品糧、住房等管制措施嚴格限制非計劃移民人口進入農場,而納入計劃移民的人口一旦進入農場就能獲得景洪市非農業人口戶籍,在就業、住房、糧油副食、勞保教育、福利、醫療保健等方面享有由國家財政統包統分的權利,因此,直到1980年止,從某地居民的實際戶口數就可以準確計算該地人口流動的數目,這就是強嵌入的極好說明。此外,1980年以后,地方政府還通過農場這樣高度化的行政組織,對其職工實施有效的計劃生育管理,這一實施狀況明顯地左右著個人日常活動的私密性,即使是對那些并寨進場的哈尼族也不例外,而非農場職工的當地少數民族則不必受此限制。
1950年代初期,由中央政府出臺了一個龐大的計劃移民方案,也就是要遷移大量的青壯年人口到西雙版納,因此,農場職工主要由以下幾類人員構成:
第一,由部隊士兵就地轉業成為農場職工,以軍事化的兵團建制從事農業生產,如組建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
第二,內地移民,即從中國東部農村把大量青壯年農民轉移到西雙版納從事農業生產,這就挑戰了那種認為計劃移民人口的教育水平要高于一般水準的觀點[8],因為移民們并沒有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主要從事的還是農業生產勞動。1959年,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和湖南—云南兩省的協議,湖南省醴陵、祁東兩省的青壯年移民共21939人(其中家屬8649人),于1960年分批次到達西雙版納的10大農場。由于故土難遷,這些移民大多自行結伙返鄉,直至1963年,返鄉潮才基本平息。1966年,部分已返回原籍的移民再次回到版納農場,另外更有若干湖南籍青年農民自行前往農場謀事,但因其不屬于計劃移民,并無糧戶關系遷入農場,只能在農場做臨時工,到文革后期,他們才在農場落戶,成為農場的正式職工。
第三,下鄉知識青年。從1969~1973年,約有10,000,000~15,000,000中學生從各自家鄉來到北方和西部,他們中的一部分也到了西雙版納的10大農場。最初的設想是讓他們從此扎根農村不再回到城市,當然,他們中的絕大部分都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返回到各自的家鄉。
按照計劃移民計劃,未婚的移民婦女以職工身份進入農場,這樣男女職工人數相當,婚配嫁娶就可以在農場內部解決了。由于占農場職工大多數的是30~50歲的男性青壯年,在這種性別比例懸殊的情況下,要解決農場職工的婚配就成了大問題,當時的政策是鼓勵他們回到原籍去找未婚妻或者結婚,承諾他們的家屬將擁有景洪市非農業居民戶口,可以在農場就業。當然一般情況下,她們只能做農場的臨時工,后來情況發生變化,由于移民返鄉和知青回城之后,橡膠農場的割膠工作季節性強,時間長且工作量大,這部分已婚婦女才開始逐步走上農場工作崗位,以后逐年轉為農場的正式職工,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單位人,享有工休、勞保、醫保、養老退休金等福利保障,她們的子女們也享有在農場內部優先招工,頂替退休父母親工作的權利,這種具有照顧性質的用工制度在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最為常見。
“我有5個孩子,3個在農場工作,大女兒在三分場搞婦女、團委和工會工作,二女兒在一隊干衛生員,三女兒是割膠的,四女兒在景洪打工,小兒子在二分場門口修車。我老婆原先是跟著我來農場管膠地的,一開始每天才得0.53元,后來轉成了正式(職)工,年齡大了就讓三女兒來頂替,現在她一個月的退休工資有1000多(元)。”(孫某,2005,春)
換句話來說,正是戶籍、票證供應和單位制度等制度性設置為計劃流動婦女和她們的子女提供了基本的社會保障,1992年,在西雙版納的整個農場系統最后一次招收正式職工后,至今都沒有再招收新職工,職工子女的就業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成了一個老大難問題。
由于生活在農場這個單位社會中,在婦女也頂半邊天的主流話語中,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的宗族社會的支持意義逐漸淡化。以張氏宗族為例,現在整個東風農場屬于醴陵東鄉河溪張氏宗族成員的移民就不下300人,他們在湖南時分屬亨—功—昂—江—濟5個房份,到了景洪之后,宗族成員除了參加小孩滿月、周歲、婚喪嫁娶等活動外,他們之間平時很少來往。在父系繼嗣中,修譜工作是一項重要活動,但農場的張氏族人對修譜的態度并不一致,有人根本就不愿上譜[9],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也不想承擔對此的出錢與出力義務,現在的張氏族人所看重的是作為衣食保障的單位人身份,而并非宗族成員身份。因此,作為單位人而存在的女職工,脫離單位對她們來說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農場減員增效時期,被分流出去的大多數女職工即使外出打工,也都還在農場保留著工資關系和人事關系。
建立國營農場和推進西雙版納的城市化,對于境內各少數民族婦女的傳統身份格局也產生了深遠影響。1970年代末隨著大量知青回鄉,農場勞動力出現短缺。1979年勐捧農場決定從當地哈尼族中招聘一批工人,補充到農場的職工隊伍中,于是將與農場相鄰的一些村寨整體并進農場。在1979~1997年,先后有15個哈尼族村寨被一次性劃入農場,凡是16~35歲的男女勞動力全部成為農場正式職工,享受工資、戶口、糧食供應等城市居民待遇,現在勐捧農場職工中共有24個少數民族,其中哈尼族最多,占全場總人口的30.8%,職工總人數的28.9%[10]。
三、1979年后景洪的自發流動婦女
自從1979年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極大發展,在計劃流動停止的同時取而代之的是日益興旺的自發流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西雙版納獨特的民族風情和亞熱帶旖旎風光,吸引了中外游客的紛至沓來,旅游市場的興起加速了景洪的城市化建設步伐,但是國家仍然控制著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一系列資源要素,也就是說,自發流動就等于流動婦女們脫離了戶籍、身份以及與地域和原制度有緊密對應性的關系等中國社會最重要的要素,而這些要素并沒有因為市場的介入而不復存在,因此,自發流動并沒有如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是零嵌入,而呈現的恰恰是格蘭諾維特所說的弱嵌入狀況。
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現代化理論來說,它們能夠部分地解釋流動過程中發生了什么,特別是現代化理論提出流動過程其實是現代社會和非現代社會的連接點,即通過信息和技術來實現從農村勞動力向市民身份的轉換。從訪談材料來看,流動婦女的動機不外乎為了獲得更好的教育條件、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這也就容易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流動婦女要爭相涌入并不算特別發達的邊陲城市——景洪。當然,從更寬泛的角度來講,流動動機還包括向上流動、社會交往和求得身份認同,這已為作者和其他相關研究所證實,因為流動婦女進城的動機已經由當初的到城里吃苦掙錢再返鄉補貼家用,上升為希望能夠在城市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和實現從農業戶籍向非農業戶籍的市民身份的轉變。
自1995年以來,少數民族婦女流動人口的比例一直較高,而且她們中的絕大多數是青年人,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景洪的移民婦女并沒有像珠三角一帶的打工妹一樣進入工廠,或者成為北方城市常見的街頭商販、餐館服務員和駐家保姆之類,她們通過購買戶口、技術移民、婚姻流動、撿荒務農4種方式進入景洪并想以此長期生活下來。
第一,購買戶口。雖然外出務工是自發流動的主要動機,但是單一的勞動者身份,并不能為她們自動地成為城市居民提供可能性,如果以市場行為來實現身份的轉換則要容易得多,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直接購買城市戶口。當然,相對于直接購買城區非農業戶籍的昂貴費用來說,購買城市近郊區村寨的農業戶籍則要便宜許多,因為一旦城區擴大時,凡符合條件的近郊村民會一次性集中轉為城市戶口。2008年,筆者在景洪市郊的曼龍匡做戶籍統計時,發現有10多戶漢族共30多人舉家遷移住在曼龍匡,而且全是常住戶口。當筆者向村里的戶籍員提及此事時,他說:“這些人誰也沒見過,平時也不住在村里,都是各個方面的關系戶,上面有人打招呼就給上戶口了”,其實這些外來移民就是以購買戶口的方式來實現異地遷移的,當然,他們不能就此提出享受和曼龍匡村民一樣的年終分紅和宅基地等待遇。
第二,技術移民。對于農業戶籍的居民來說,在2000年之前,他們可以被國營工廠招工,或者從大專院校畢業后由國家統一分配工作,自動實現由農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的身份轉換,特別是后者可以稱其為技術移民,也就是說,如果作為技術型人力資源的話,移民們通向城市的道路要平坦不少。當然,近些年的大學生就業難也證明這一條路并非坦途,因為,這其中的很多人還得依托親友等強關系才能找到好工作,這種在技術流動中起作用的非技術因素,使得學術界對此往往是毀譽參半。
第三,婚姻流動。20世紀90年代以后,西雙版納的旅游業直接催生了與民族風情旅游相關的就業崗位,如歌舞表演的演員和按摩服務中的按摩員。少數民族成員的就業經歷和社會經歷表明,相對于漢族婦女來說,她們要在城市獲得優質的就業機會是很難的,不僅存在著漢語交流能力缺乏的問題,還有文化認同上的因素。當然,少數民族婦女選擇具有比較優勢的就業崗位,如能歌善舞的傣族婦女以民族舞蹈演員的身份就業,而會一手按摩絕活的哈尼族婦女則選擇了按摩員的職業。
曼龍匡是一個距景洪市區2公里的傣族村寨,主要向外來移民提供出租房屋和轉包土地等業務,而曼廳公園就緊鄰該村,它曾是召片領的御花園,景洪市主要的趕擺場和重點旅游景點,公園里每天都有3場免費的歌舞表演,17個女演員多在16~19歲之間,她們當中除了3人是曼龍匡本村的,其余的14人都來自勐臘縣的曼飛龍和勐海縣等地,她們就租房居住在離工作場所不遠的曼龍匡。每當游客觀看傣族女孩們的歌舞表演時,就有13~14名身著哈尼族服裝的少女為男女觀眾進行肩、背、手、頸和頭部的按摩。在傳統的哈尼社會中,人們用按摩來表達他們對家中長輩、宗族長者、遠道而來的貴客的敬意,而曼廳公園的按摩以分鐘計價,20元/20分鐘·人。
那么,如何從少數民族村寨挑選合格的歌舞演員和按摩員進入旅游市場呢?田野調查發現,傣族與哈尼族婦女的流動主要是依賴組織資源和同輩資源,即由各旅游服務公司和演出團體派出自己的員工以老庚①身份,來到勐海和勐臘的傣族、哈尼族村寨向適齡女性游說并承諾其成為公司一員后所能得到的待遇。在經過短期的就業培訓后,最漂亮最有才華的女孩子成為該公司的正式員工,上崗從事表演或按摩工作。由于旅游市場起伏波動,歌舞表演本身又是青春行業,因此員工們的流動相當頻繁,一般每批次也就在公司呆上1~2年,就再次分流到城市的其他服務行業中去了,如在民族餐館表演歌舞等。
由于這些女孩子年齡大多在20歲以下,當初從農村出來時,沒有誰會一下子就想到要結婚嫁人的事,她們就是想多掙點錢,出門長點見識什么的,但是要在青春行業中長期就業是不現實的,因此想要長期在城市中生活下去,通過與社會地位較高的男性締結婚姻關系成為她們留在城市的另一條捷徑。雖然這些女孩子年紀輕,不少人都有著較好的身體資本,但是直接嫁給有城市戶籍身份的男性,對于她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也是不可行的,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嫁給像曼龍匡這樣準城市社區的男青年。
玉某,傣族,21歲,一家4口住在勐臘縣尚勇鄉靠近磨憨口岸的寨子里,因為姐妹倆都長得很漂亮,1997年前后,她們被云南民族村招到昆明做傣族舞蹈演員。在昆明待了一年多,姐妹倆都返回了景洪,她自己先在景洪的傣味餐廳跳舞,結識并與曼龍匡的巖某結婚,婚后其戶口就從家鄉勐臘遷到了景洪的曼龍匡。現在夫妻倆在公園里共同經營冷飲和鮮榨果汁攤點,在99’世博會前,每天都有400~500元的收入,而2003年以后,生意就時好時壞,但總的來說,與勐臘老家單純的務農收入相比,現在的收入還是要高很多(2006,秋)。
當然,在西雙版納通過婚姻流動嵌入經濟收益好的準城市社區,在實際上也有相當的操作難度,并不適合所有未婚的年輕女性。由于西雙版納歷史上的民族、等級、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傣族實行的是民族等級內婚制,也就是說傣族男子潛在的婚配對象是同等級的傣族女子,漢、哈尼等其他非傣族的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
第四,拾荒務農。對于移民婦女中的已婚者來說,實際上也喪失了通過婚姻流動的可能性,因為她們大多在30~40歲之間,通常是帶著家里的幾個孩子從農村來到景洪,扎堆地租住在像曼龍匡這樣的近郊村寨。一般來說,她們中的相當一部分是依托與農場職工的各種關系來到景洪的,許多人往往一住多年,有的是因為身邊還有上學的孩子,有的則因為不知道回鄉后還能干什么,再說頻繁的流動只會帶來更大的不穩定和更少的收入。
雖然在調查中她們說自己是為了子女的教育而來的,即通過子女特別是男孩子的讀書上進來改變全家人的狀況,但是在田野中并沒有獲得實際案例支持,特別是近10年來,由國家來統一分配畢業生就業已不可能,所以,她們的這一希望要實現起來也是極其渺茫的。
陳姓婦女一家四口從鎮沅鄉下來投靠在東風農場工作的大伯,正上中學的大兒子因為大伯的關系可以在農場中學借讀,由于沒有景洪戶口,每年都要交一筆不菲的贊助費,從3000~5000元不等,如果還要繼續上高中的話,費用就更高了,如果不上的話,那么這些年的投入就打了水漂。由于她丈夫也沒有找到正式工作,所以,一家人就在曼龍匡租下一間只有十幾平方米的房子住下……而她十多歲的小女兒從來就沒有上過學,每天早上就隨蹬小三輪的父母外出拾荒,下午再返回出租屋把垃圾分類歸并,等待價格合適時再賣出(2008,秋)。
就像杰卡對北京流動婦女的調查顯示的,作為已婚婦女,流動婦女們的首要工作是家務勞動,其次才是外出掙錢[11]。當孩子們一個個長大了,她們也想找一份工作來改善家里人的生活條件,但是她們的年齡、學歷和具備的技術技能都達不到城市工作的要求,即城市的就業機會和工作性質是排斥她們的,她們能找到的都是低薪水、工作量極大的和極不穩定的工作,所以,她們更多地嘗試各種能夠掙錢的生意。
由于自發流動階段的流動類型不一而定,既有從鄉村到城市的,也有從鄉村到鄉村的。特別是后者,在近年來也很普遍。由于家鄉的土地少產量低,大量的農村居民來到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西雙版納又干起了老本行,向曼龍匡人承包土地種菜供應市場。
行走在曼龍匡,和當地居民交談,他們的第一句話往往是“你可要租房子?”“你租哪一家的房子?”如果在菜地、在窩棚邊遇到種菜人,他們會問“你可要種菜?”“你也出來找工做?”租房和種菜是曼龍匡村民和移民經濟生活中的兩宗大事。流沙河繞曼龍匡而過,每年雨季河水泛濫帶來的豐富泥沙,成為種植蔬菜的天然肥料。景洪分為干季和雨季,菜農們在干季種南瓜和四季豆,雨季種辣椒和番茄,其中景洪種的小米辣最為著名,好年成的小米辣可賣到7~8元/kg,1畝地能有5000元的純收入。當年成好收入多時,菜民們就在村里租房子住;而年成不好、菜價走低時,他們就退掉村里的房子,在菜地邊搭一個窩棚住下,等待來年的好運氣。因為租土地的租金往往要提前支付,一般是3年一次交清,再加上澆地的水費、種子錢、農藥費和化肥等項支出,還沒有算上自家的勞動力成本,菜農們就已經處于虧本狀態了,實在是沒有余錢來支付房費了。
王某夫婦倆是墨江人,2000年聽說私人可以承包東風農場的土地,就從家鄉來到景洪,但是人生地不熟的,他們在景洪找不到擔保人,農場的地就包不下來。既然來也來了,他們一家四口就在曼龍匡住下了,包了村民的7畝地種辣椒。結果,2002年菜價就倒了,“(昨天)摘了200公斤(辣椒),才賣了200多元,3畝地的(收成)才賣得5000塊,還不到原來一畝地的錢,成本都找不回來啰……”“一家四口一時半會地也回不去(老家)了,(雖然)墨江的戶口還沒有銷,(可承包的)土地已經被村上收回了,自己沒有牛,再去租地來種的話,幾年都找不到1000塊,現在的(景洪的)日子苦是苦點,慢慢等菜價再升上去,才能翻本……”“沒得辦法的事,沒有本錢,不種菜也做不了什么”。他們的兩個十多歲的女兒就一直輟學在家,幫著母親守窩棚、摘辣椒、做家務,忙出忙進地儼然就是兩個小“大人”(2008,夏)。
對于漢族或哈尼族移民婦女來說,曼龍匡是一個在語言、文化、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異質性很強的社區。雖然移民婦女們都不得不學會簡單的傣語來和房東交流,比如包地費、房租金、水電費,還有就是打聽院子里什么地方可以用來堆放撿回來的垃圾,要不要再另外交錢,除此之外,曼龍匡的村民們與移民婦女之間并沒有多少共同話題,也沒有一起參加的社會活動,所以彼此之間的認同感差,也很難產生相應的信任感。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不同流動類型對于移民婦女獲得城市身份的難易程度是不同的。在計劃流動中,對進入農場職工行列的湖南漢族及其家屬子女,對農場附近并寨入場的哈尼族及其家屬子女來說,國家政策賦予了他們城市居民身份的強嵌入;而在自發流動中,除了購買城市周邊農村戶口的經濟行為外,投資移民和技術移民對普通移民婦女來說也是不現實的;而婚姻移民雖說是一種受到鼓勵的生存策略,但是這條捷徑也不是對任何民族的婦女都可行的;至于說通過父母投資子女教育來改變家庭命運的話,也存在經濟投入高和回報率低的問題……總的來說,弱嵌入給了移民婦女太多的選擇機會,而現實則反映出她們并沒有多少選擇余地的困境。
既然中國現階段既沒有計劃流動的強嵌入,也沒有完全市場化的零嵌入,因此,移民難以嵌入城市的事實就不能只歸因于移民的個人行動選擇,而忽視國家在宏觀層面上的公共政策取向,特別是移民婦女還將在中國社會中長期扮演重要角色。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長期以來對經濟的關注開始讓步于對民族和性別議題的關注,而且這一問題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緊迫。因此,國家應該通過宏觀政策和行政干預,提高農村婦女的教育水平,保障婦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是使農村婦女成為城市化受益者的關鍵。世界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研究顯示:婦女多受一年教育可以使其在未來的收入增加15%,農村婦女接受教育年限增加了,不僅具有經濟效益,而且還具有重大的社會效益,如可增強婦女參與社會的能力,能夠提高中國城市化的管理水平和質量等。
注釋:
① 老庚是同年生的同性朋友,男性有男性的老庚,女性有女性自己的老庚,它是一種同性的小群體,這是一種基于經濟與社交需要而產生的同性聯盟,老庚不受地域的限制,它是擴大人際交往的有效方式。
參考文獻:
[1]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6.
[2]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趙旭東,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19.
[3] [美]邊燕杰.找回強關系:中國的間接關系網絡橋梁和求職[J].張文宏,譯.國外社會科學,1998,(3).
[4] 王政,杜芳琴.社會性別研究選譯[C].北京:三聯書店.1998.365-366.
[5] 王春光.流動中的社會網絡:溫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動方式[J].社會學研究,2000,(3).
[6] 李拂一.十二版納志[M].臺北:正中書局,1955.178.
[7] 劉隆.西雙版納國土經濟考察報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141.
[8] Robyn Iredale, Naran Bilik, Fei Guo.China’sMinoritiesontheMove,SelectedCaseStudies[M].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Sharpe, Inc,2003.46.
[9] 和淵.西雙版納:二十世紀整合中的中國邊疆[D].昆明:云南大學,2001.
[10] 尹紹亭,等.雨林啊膠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45-48.
[11] Tamara, Jacka.RuralWomeninUrbanChina,Gender,Migration,andSocialChange[A].AnEastGateBook[C]. A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M.E. Sharpe, Inc,200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