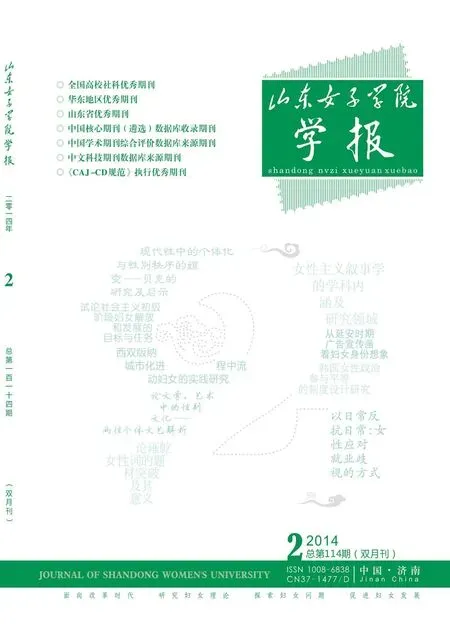論文學、藝術中的性別文化
——兩性個體文藝解析
申 林
(山東女子學院,山東 濟南 250300)
兩性文化差異體現在文學藝術上的異彩紛呈,是由其根深蒂固的性別文化體驗和性別認知的時代背景所決定的。要探索性別文化在文學藝術中的呈現,首先要了解何謂性別,何謂性別文化,以此來認識這種二元化的性別并立所衍生的多元文化現象,以及與之共存的意識形態和認知元素。在探詢文化中的性別差異時,不單以性別本身為基準,還要考慮時代背景與歷史坐標。顯然,性別文化是由性別本身界定的;由性別差異愆出不同特點的文學藝術作品來,從而彰顯出男女相異的文化指向及人性品格。
性別是人先天的生物屬性,是“物競天擇”的自然選擇,是兩性各自獨有且不可替代的生理差異。夸大或抹殺這種差異都是主觀、片面和非科學的。如何客觀認識男女間的性別差異,正確處理性別差異同人類文明發展的關系,是性別文化研究所探討的問題。
男女性別同人類社會的關系,是人類繁衍生存的基礎,也是社會發展最基本、最普遍的關系,由此而派生的性別文化則是人類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性別文化是關于人的性別屬性在社會關系中界定的倫理觀念和行為準則,是為男女所分別限定的所思、所言、所行、所覺的范圍,并與之相適應的家庭生活模式、文化藝術范疇以及生產組織結構,即所謂“社會性別”。這種“社會性別”是在人類歷史變革中客觀生成進而逐步完善的。
縱觀性別文化史可以看出,它是在同父權、男權、“男尊女卑”觀念的斗爭中,奮力追求和諧、平等的演進過程。這種不平等首先是女性性別“劣勢”向社會生產活動“劣勢”的演變,繼而是性別的社會分工差異導致社會價值分配的錯位。這種不平等的價值分配觀念最終導致了男女間的不平等甚至是對女性的“壓迫”。性別文化自階級社會以來,就以“男尊女卑”的等級觀念相繼打造出男女有別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準則。在“男陽女陰、男剛女柔、男外女內、夫唱婦隨”等由來已久、約定俗成的傳統理念中,漸漸形成了男主女從的模式。
在歷史的長河中,從奴隸制、封建制時期,直至近代,女性都被父權、男權所奴役。如《禮記·曲禮》上說:納女子于天子曰“備百姓”。那時的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是物,她們的命運掌握在男性手中。婦女在男性作品中的形象也是處于被欣賞把玩、支配品評的地位。“性”及性的快樂似乎都是男人的話題,而女性關于性的感受,無論快樂或是不快樂,往往均被冠以“淫蕩”,從來都是禁忌的話題。這種性別歧視不單體現在對女人生理的態度上,在社會輿論、倫理道德、權利規范等領域皆是如此。近代儒者梁漱溟曾說:女人的任務在身體上,不在頭腦里。尼采說得更為露骨:女性的一切價值歸結于生育。
女性在文學藝術領域更是沒有彰顯個性與感受的話語權,因而,文學作品中主人公的性別往往會置換和逆轉:女扮男裝、男扮女裝和男性角色女性化的情形司空見慣,比如南北朝樂府《木蘭詩》,后來也多見于戲劇和小品;梅蘭芳男扮女相的京劇,或徐玉蘭扮男相的滬劇,后來甚至發展成為傳統戲劇藝術中的普遍形式。南宋詞人李清照,其作品詠情抒懷、細膩婉約,但其暗含的無奈與傷感,卻深深打上了封建時代性別文化的烙印。
即使在主流認識上確立了男女平等的性別觀念,但在一定時期內,文學藝術仍存在某種矛盾性和特殊性。如巴金小說《家》中的鳴鳳、瑞玨、梅,曹禺戲劇《雷雨》中的四鳳、侍萍,《北京人》中的愫方等。她們精神高潔,富有犧牲精神,以恪守愛情為天職。作品把中國男性文學傳統中“佳人”與“母親”相分離的兩類理想女性整合為一體,打造出理想的愛與美的道德牌坊。
隨著社會進步、科學發展以及生產方式的逐步改變,社會分工正逐步打破性別界限。婦女走出情感與家庭的小圈子,男女在同一起點上實現就業,隨之帶來了婦女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的改變。近代以來,婦女自由解放的呼聲越來越高,事實上的改變比任何歷史時期都巨大。在此背景下,“女性主義”者通過“去社會性別”表達了消除社會性別差異,實現男女社會地位與價值分配平等的訴求。在文化藝術領域,女性則融合自身對現實和傳統的批判,架構富有個性的女性文化空間,確立自身的女性文化價值觀。人的自然性別一旦同社會性別得以剝離,任何因性別差異而被社會歧視的人,都將找到自己挑戰社會不平等待遇的視角和理由。先進的性別文化,是正視性別差異,尊重自然法則,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追求性別和諧與精神自由,充分實現自身訴求,實現女性在社會中享有同男性平等的權利與機會。這既是先進性別文化的基本內涵,也是批判落后性別文化的立足點。
上世紀90年代,女性文學創作開始引起社會的普遍關注。在文學藝術創作領域,男性文學藝術作品往往關注宏大題材,氣概豪邁;女性文學作品則關注身邊瑣事與情感體驗,往往給人以情感關照有余、時代風云描摹不足的印象。較之那些侃談時事風云與沉溺于理性思辨的“男性大手筆”,有些女性的“小敘事”“小情調”則更細膩感人,沁人心脾。作品本身也彰顯了女性文學藝術的獨特價值與無可替代性。解析兩性個體文藝的差異,不應以品評孰優孰劣為前提,而陷兩性于相互爭勝的對立與爭執中。
以王安憶、林白、池莉、陳染、徐小斌為代表的女性作家,在這一時期的文壇上頗具影響。她們以各自獨特的女性視角,拓展了文學的審美表現空間。之后又出現了衛慧、棉棉等被稱為“用身體寫作”的女作家們,她們直白地書寫自身,從反觀自身性別出發,憑借良知賦予的勇氣,通過對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描述,試圖向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中的男性特權宣戰,以此來掙脫強加給女性的宿命,確立并構建以女性為主體的文藝語境。作品所反映的精神指向,負載著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內涵,對男性中心主義的解構成了作者的寫作理想,個性化的寫作回歸到內心與真實。
翟永明等人的“女性自白詩”以女性對本體生理環節的關注,抒發了女性獨具的性別體驗和糾結的情緒。繼而,張欣欣作品《在同一地平線上》則聚焦男女之間的糾葛,展現了兩性在文化背景上的對撞和各自愿景與現實之間的沖突。王安憶系列小說《錦鄉谷之戀》《荒山之戀》《小城之戀》,描寫主人公在不同環境體驗中的欲情萌動和潛意識活動。這些作家雖然沒有觀照社會重大問題,但她們卻話語相通,與個性相逢,深入兩性權力關系話題,探討文學無法回避但卻視為“禁忌”的領域。20世紀末,陳妍音、向京、陳羚羊將身體帶來的感受作為寫作載體;尹秀珍、崔岫聞則以女性的思維和情感來敘述或記錄女性群體的命運。
這一時期,女性作家的視野更加開闊,兩性之間的認同感逐漸擴大,倫理道德及社會風尚較之以往更為寬泛實際、更為人性化、更具包容性。社會的開明和個性的釋放,贏得了女性生活方式多元化的選擇,反映于女性文學藝術創作中,其表現內容和表達形式擁有了更為廣闊的展示空間。女性文學中的多元化發展勢頭,也反映在女性造型藝術中。
在以往的造型藝術中,女性所擔當的是女紅刺繡、剪紙窗花、描龍畫鳳的民間藝術家角色,即使她們有大家閨秀和才女的學養,也只能深閨吟詩,暗繡鴛鴦以寄怨情,無論如何也不能正視自身的感受與表達。真正的藝術表現領域,似乎專屬于男性文人、士大夫和男性藝術家。
近年來,隨著性別平等意識被喚醒,女性藝術家開始重新思考精神的、身體的、內在的、意識的話題,她們正視自己的感受,直面自己的訴求,追求藝術表達的人性化與個性化。她們嘗試顛覆傳統、沖破禁忌,尋求自我的表達方式,以不懈努力索求性別文化的話語權,力圖確立女性藝術表達的主體地位。她們同時以多變的策略吸引媒體及大眾的關注,大膽探索女性在藝術領域中的無限可能性,以拓展多元藝術表達空間。她們力爭與男性藝術家共生并進、平分秋色、融入時代主流文化之中,在層層糾葛的復雜互動關系里,形成虛實不悖的新感覺、新現實、新表達。其客觀結果是使其作品內容更貼近個體真實感受,作品風格更為現代前衛,作品面貌更加新奇而多元。
男性畫家朱新建的《美人》系列,在傾慕女性的肉體美的同時,提煉出表達欲求的典型樣式。那輕柔而極具彈性的女體線條,既是對女性生命形態的贊美,也是對女性傳統“社會性別”文化的另類形象化解讀。女性畫家申玲的《粉床》系列,則把現代夫妻之間的性愛隱秘以及夫婦身邊瑣事以夸張的手法裸陳于畫面。她以調侃式幽默、感情化色彩濃厚筆觸,表現了生活中平淡愉悅的性愛,營造了一個都市“伊甸園”的夢想。蔡錦的《美人蕉》系列,則通過對蓬勃植物的血紅表現,暗喻女性的生殖力支撐了人類的繁衍。向京的作品《你的身體》,通過木訥、迷茫、猶疑等切片的重構,造就了一個男性光頭、女性裸露的雙性氣質的身體文化。這被她動容地描述為“身體是對腐朽靈魂的一次震撼”,是道成肉身的一種社會文化形態,與奧尼爾的“我們的身體就是社會的肉身”的觀念不謀而合。作為一種觀念的表達,其所展現的裸露傷疤的女人身體、失色的眼神、遲鈍的靈魂、坦然敞開的女性生殖器,一切由譏諷與詼諧帶出了女性受傷的身體文化。這些作品是她認為的自雕像:“她是人的痕跡,情感的力量,粗糙的、感性的、本質的東西。”這似乎在說,身體承擔的是一種原始抒情的符號。
與此同時,被譽為材料美學的準身體的物質形態,也進入了女畫家的視線。比如施慧的《老墻》,她用柔軟而脆弱的紙漿,塑造出如同男性身體般偉岸而渾厚的古城墻。充滿歷史想象力的古城墻,是文物的碎片,還是文明的紀念碑?它似乎旨在道明:性別身份的定位,是在潛意識中選擇自我,決定自我,采取男性生存方式還是女性生存方式的過程。另一位女畫家陶艾民,執拗地走遍鄉村收集搓衣板,“搓衣板”是鄉村女人辛苦勞作的見證。她作為生活在都市的知識女性,因為追思的使命感,而去探尋女人的過去,反思女性的今天。她創作的《女人河》《女人經》《一個女人的長征》等作品,既守護了女人辛苦的歷史,也昭示了女人今日與明日認知上的區別。
而女畫家俞紅的作品《日常生活》系列,則不急不躁,在平淡中悠然守候著屬于女性的人生本位。她將自己的日常生活片段,詩一般地娓娓道來。畫家以“一滴水能反映太陽光芒”的滿足感,精心而從容地打點著屬于自己的生活,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我們這個飛速旋轉的數字社會。女畫家夏俊娜的作品《浮生》系列,以時光流轉為線索,采用唯美的手法,表現了都市白領的審美情態。畫中淑女窈窕、幾凈窗明、暗香浮動,營造了一個處處溫馨、超然的世外桃源鏡像。
在當代異彩紛呈、靚麗鮮明的女性文學藝術作品中,無論是反叛的激昂,哀怨的傾訴,還是生命的贊頌,唯美的表達,她們都以各自的獨特視角,淋漓地書寫著對人性本真的追求,對生命的深刻體驗,以其自覺的性別文化意識和性別魅力,彰顯了女性個體中先進的性別文化理念及時代特征。
然而,在“性別文化”萬象更新的背后,也不難看到,當下大眾道德素質良莠不齊、價值取向錯綜復雜的現實。傳統腐朽觀念、西方墮落文化和奢靡享樂之風仍在侵蝕著社會和人的靈魂。加之大眾文化品味尚待提高,經濟利益與精神價值之間的矛盾日顯突出,諸多問題仍然存在。因而,單單以女性的個性釋放和潛意識的表達來確立性別文化形態,難免會產生新的困惑與矛盾。重塑先進性別文化價值體系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尚處探索階段,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