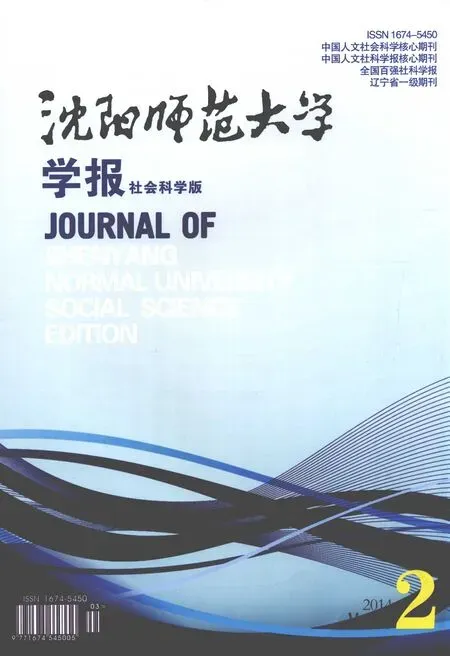文化自覺視閾中的駢文理論
——以《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比較研究為例
馬驍英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110036)
文化自覺視閾中的駢文理論
——以《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比較研究為例
馬驍英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110036)
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在文化學、社會學、人類學領域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這一命題,對我們在當代文化語境中,研究駢文理論的創新發展、現代轉化,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分別是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終點和起點,如果我們以文化自覺的視角,對《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就可以發現,駢文理論自身具備著創新發展、現代轉化的宏觀條件和巨大可能性。
文化自覺;駢文理論;《四六叢話》;《文心雕龍》;比較研究
費孝通先生在《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中寫道:“‘文化自覺’的意義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這一命題,對于當前駢文理論研究的方向、出路、反思、轉型、重構,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文化自覺,要求駢文理論研究者,對于自身研究領域,具有清醒而深刻的自知之明。這種自知之明將使駢文理論研究者認識到:駢文,這種最具中國特色的、為中華所獨有的、崢嶸一千余年而長期占據文壇主導地位的文體,在經歷了濫觴于先秦、萌芽于秦漢、形成于魏晉、鼎盛于六朝、蛻變于唐宋、中衰于元明、復興于清代的漫長發展歷程之后,由于時代形勢、社會氛圍、文化思潮的變遷,自近代至今,再三衰變,陷入了空前的危機與窘境,生存空間屢遭蠶食,無處立足,幾近消亡;曾經最具應用性和實用性的,上至朝廷典誥,下至民間啟札,公私文翰,無所不用的駢文,如今淪于被封存在故紙堆中,無預于現實,無關乎時事,與時代脫節,被當作文物的尷尬境地;與駢文創作相伴生而又影響、引導著駢文創作的駢文理論,也隨之同樣陷入了以古釋古、自說自話、墨守藩籬、以古為牢、無涉于當今、自絕于現代的理論困境。對擺脫困境、解決危機的渴求,迫使駢文理論研究者,以文化自覺的視角、觀點、立場、態度,重新審視整個駢文理論領域,尋求駢文理論向著現代意義進行自主轉型的可能性,尋求駢文理論作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的自主抉擇的可能性。在以文化自覺的視角重新審視整個駢文理論領域時,《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無疑是這種審視與關注的重中之重。它們二者分別是中國古代的系統而完善的駢文理論的終點和起點,體現著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最高成就,是中國古代駢文理論領域中的兩座遙相呼應的高峰。以文化自覺的視角,對《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進行比較研究,以文化自覺的觀點,探討《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從中發掘出駢文理論現代轉化的宏觀條件和各種可能性,無疑是最能切中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研究的現實發展和未來方向的肯綮的,無疑是研究、推動駢文理論現代轉化的最有效途徑。而就《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的比較研究而言,通過文化自覺的角度研究《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從中探索駢文理論的現代轉化之路,也無疑是《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比較研究的最現實意義。
一、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在近現代的現實困境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云:“儷文、律詩,為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駢文,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土壤所孕生出的特產,以漢字的單音獨義、伸縮自由、浮聲切響的特質為溫床,生根發芽,枝繁葉茂,成長為中華文化園圃中特有的文壇奇葩,它以對偶表現視覺之美,以聲律表現聽覺之美,以用典表現含蓄之美,以藻飾表現繁富之美,集中反映了華夏文藝的美學特征和中國文化的特有內蘊。駢文理論,與駢文創作相伴生,以中國文化獨特的“生命體驗”式的思維方式和“天人合一”式的文化價值觀念為指歸,借助于批點、案語、文評、文話、筆記、叢談、選本、序跋、論說、書信等外在形式,對駢文的成因、特征、技法、分體演進、流變發展、作家作品以及駢散關系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探討,闡釋了駢文所獨具的內在文化意蘊,形成了一整套獨特的范疇、方法、觀點、術語,構成了一個完整圓通、自給自足、獨具魅力的感性體驗式的理論體系。
如此富有民族特色而為中華所獨有的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在世界各國文化交流、對話、溝通日益頻繁深廣的近現代,本應大放異彩,發揚國光,走向世界,“與外域文學競長”而續寫輝煌。然而,現實卻并未如此。在近現代,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江河日下,一蹶不振,不僅“與外域文學競長”成為遙不可及的癡念妄想,就連維持自身生存都已難以為繼。駢文,在文學領域,雖有余緒尚存,不絕如縷,但其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在文壇上已無實際地位可言;駢文理論,雖仍有著作問世,但皆泥古貴古,以古釋古,不知變通自新,格局氣象日蹙,幾近無人問津,無人關注。究其原因,一是由于當時的駢文作者,過于偏重“六朝式”的駢文形式技巧,過度講究關于形式美的清規戒律,而忽視了現實功利,沒有發揚唐代駢文所具有的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沒有將唐代駢文經世致用之義與當時救亡啟蒙的社會現實相銜接,沒有將當時救亡啟蒙的現實生活內容引入駢文創作,而當時的駢文理論研究者,也沒有根據時代的發展、思潮的新變為駢文理論擴容,沒能為駢文理論引入嶄新的時代氣息,而只是繼古人之筆法,述歷朝之陳跡,守前代之咳唾,這些都導致了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無法與時俱進;二是由于駢文本身具有著“貴族文學”的色彩,駢文寫作要求深厚的學養、廣博的知識和卓越的才性,駢文作品要求精美、典雅、含蓄、富麗,這使得駢文極易淪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文化玩具,使得駢文極易成為曲高和寡的陽春白雪,使得駢文難以實現通俗易懂,使得駢文創作難以為普通民眾所掌握操作,使得駢文的接受、使用群體日益狹窄,使得駢文在為社會生活服務、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方面愈顯笨拙、力不從心,而當時的駢文理論研究者也沒有指出能讓駢文降低姿態、貼近民眾、服務現實的有效途徑和可行辦法,這些都導致了駢文創作、駢文理論與現實、時代相脫節,無法獲得新生。由于以上兩個原因,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沖擊之下,在“俗語文學”“白話文運動”“文學改良”“文學革命”的沖擊之下,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在近現代走向了式微與沒落,陷入了以古為牢、作繭自縛、無法自我更新、無力重新振興的困境、迷途、死局。面對這種局面,倒是既非駢文名家又非駢文理論專家的政治活動家,顯得旁觀者清。維新志士譚嗣同,針對近代駢文的困境,清醒地點明了其弊端,并振聾發聵地指出了其革新之路。針對近代駢文過度偏重形式技巧之弊,譚嗣同在《三十自紀》中寫道:“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認為駢文不應僅僅局限于對“四六排偶”的形式技巧的追求,而應當去追求能夠適應嶄新時代生活內容的新體例,應當去賦予自己嶄新的時代風貌和時代氣息。針對近代駢文脫離民眾、不切實用、固步自封、封閉保守之弊,譚嗣同在《報章文體說》中寫道:“去其詞賦諸不切民用者,兼容并包,高挹遐攬,廣收畢蓄,用宏取多”,認為駢文應放低姿態,貼近民眾,切合實用,為現實生活服務,指出無論是駢文創作還是駢文理論,都應當以開放的胸懷包容吸納各種嶄新的時代因素。譚嗣同的駢文革新之論,至允至當,然而可惜的是,一人之獨醒,難以改變舉世之昏昏,在整個近現代,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仍然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二、文化自覺視角的選取及其對駢文理論的重要意義
當今時代,救亡已經完成,啟蒙持續深入,隨著教育與知識的普及,大眾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精致、淵深的傳統文化知識不再為少數人所獨享;學術環境、學術氛圍的改善使研究者對發掘、整理、振興傳統文化抱有極大的熱情,投入巨大的精力;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使文化界迫切尋求最具民族性的文化樣式,以推向世界;“漢語熱”的不斷高漲,使外國友人負笈來華,尋求獨具魅力的漢語文化精品。這一切都使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瑰寶和漢語文化獨有精品的駢文的復興,成為了可能。時代在呼喚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走向新生,走向復興。
然而在中外文化交流比近現代更加頻繁深入、社會轉型形勢比近現代更為復雜嚴峻的當今時代,應該如何推動駢文走向復興呢?局限于古典意義的以古論古、墨守成規絕對不行,埋頭在自身小圈子里自我玩賞、自我陶醉、自娛自樂、單打獨斗絕對不行。我們必須尋求一種既能發掘、發揮、弘揚自身傳統文化優長又能以清醒的文化反省意識來認識到自身不足,既能將自身優秀傳統文化介紹給世界又能以開放的心態吸納各國文化之優長以彌補自身不足,既能將自身傳統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打磨為稀世的文化珍品又能使傳統文化精華適應時代、切合實用、為社會現實生活服務、被社會大眾所掌握的嶄新視角,來全面審視、研究駢文理論,使之現代轉化,從而引導駢文創作在新的時代里走向復興。這種嶄新的視角,就是“文化自覺”的視角。
費孝通先生在《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中指出:“‘文化自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對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首先要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觸到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條件。”
以文化自覺的視角,研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的駢文理論,要求我們以清醒的自省精神,全面審視、梳理駢文理論的整個歷史發展脈絡,緊緊把握其來龍去脈和逐漸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內在意蘊,深刻認識其優長與不足,揚其長而抑其短,并且做到溫故知新,從駢文理論的歷史發展脈絡中發掘傳統與現代之間的接榫之處,以中國文化的“維新”本能,推動駢文理論在發揮原有文化優長基礎上的主動自我更新,以求得其進一步發展,使之適應日新月異的時代與環境;同時還要求我們在與西方文化進行交流時,敏銳意識到中西文化的鮮明差異,清醒認識到二者各自的優勢與缺陷。基于這種清醒而客觀的文化判斷,確定駢文理論現代轉化的正確走向,不妄自菲薄,不盲目轉型,而是確立自主地位,增進自主能力,做出自主抉擇,既能以包容開放的心態,博采眾長,補己之短,又能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獨立自主地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在與各國的廣泛文化交流中,將自己獨具魅力的文化神韻展現在世界面前。
三、《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的比較研究進入文化自覺的視野
在文化自覺的視野中,全面審視、梳理駢文理論的整個歷史發展脈絡,勢必要求我們選取駢文理論發展史上最能體現中國駢文理論特色的、最具集大成意義的代表性的駢文理論經典著作,加以研究、分析、闡釋,以便為文化自覺視閾中的駢文理論研究,提供豐富的歷史資源和優質的理論資源。于是,《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自然而然地進入了我們的“文化自覺”視野。
清代孫梅《四六叢話》與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遙相呼應、雙峰對峙的兩座理論高峰。《文心雕龍》是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和以駢文來寫作理論的起點。其《麗辭》篇,不僅從修辭的角度入手,探討了駢偶的產生原因、發展過程、主要形式以及存在的弊端,而且在駢文創作方法論的理論層面上,深入地探討了在文章寫作中如何使用駢偶的問題。其《事類》、《聲律》、《情采》諸篇,則分別深入研究、論述了駢文創作的用典、音韻、藻飾等重要理論問題。謝無量先生的《駢文指南》,高度評價了《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駢文盛于六朝之際,而論其體制,較其優劣者,以《文心雕龍》之書為最備”“,劉勰《文心雕龍》譏評古今文章得失,其中雖合詩賦雜筆而言,要以近于駢文者為多。況彥和之時,為文競尚聲音比偶,觀《雕龍》之持論,則于駢文之秘奧,可以思過半矣”。《四六叢話》是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和以駢文來寫作理論的終點。它是自《文心雕龍》誕生以來直至清代,在駢文理論批評領域中最系統、最豐富、最完備的著作。它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發揮著“集大成”和“總收束”式的重要作用。其概括諸家之功,推闡精微之力,《文心》以降,罕有其匹。錢基博先生《駢文通義》、劉麟生先生《中國駢文史》都高度評價了《四六叢話》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駢文通義》云“:談駢文者,莫備于烏程孫梅松友《四六叢話》”,《中國駢文史》云“:批評駢文之書籍,至孫梅《四六叢話》而始告美備。”更為重要的是,《文心雕龍》與《四六叢話》,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絕不僅僅是簡單的一首一尾、一始一終,它們之間具有著息息相通的血脈聯系。《四六叢話》的作者孫梅,對劉勰的《文心雕龍》滿懷著高山仰止之思、踵武繼蹤之意。他在《四六叢話·卷二十二·論十四》敘論中寫道:“賦家之心,包括天地;文人之筆,涵茹古今。高下在心,淵微莫識。爾其徵家法,正體裁,等才情,標風會,內篇以敘其體,外篇以究其用,統二千年之汗牛充棟,歸五十首之腎擢肝,捶字選和,屢參解悟。《宗經》、《正緯》,備著源流,此《文心》所以探作家之旨,而上下其議論也。”在《四六叢話·卷三十一·作家四·三國六朝諸家》案語中寫道“:彥和探幽索隱,窮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彥和此書,實總括大凡,妙抉其心。自陳、隋下訖五代,五百年間,作者莫不根柢于此。嗚呼盛矣!”其心向神往、追比前賢之意,溢于言表,同時,也確實見之于行動。《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從駢文成因論(文章駢化過程論)、駢文特征論、駢文分體演進論、駢文流變發展論、駢散關系論、駢文作家論、駢文技法論(對偶、用典、聲律、藻飾)等各個方面,對《文心雕龍》進行了全面而出色的繼承,充分吸收了其理論精華,并且在繼承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發展和駢文諸體的新變,作出了很多杰出的理論創新。正由于《四六叢話》,在駢文理論方面,對《文心雕龍》的這種杰出的繼承與創新,因而,自《四六叢話》誕生時起,便有人將其與《文心雕龍》相提并論,甚至認為其較《文心》更勝一籌。清陳廣寧《四六叢話跋》云“:劉勰之《文心雕龍》,不過備文章,詳體例,從未有鉤玄摘要,抉作者之心思,匯詞章之淵藪,使二千年來駢四儷六之文,若燭照數計,如我夫子(孫梅)之集大成者也。”清許應《重刊四六叢話跋》云“:《文心雕龍》之體例詳矣,然鉤抉玄要,精妙簡賅,不得是書(《四六叢話》)以疏其節目,分別枝流,則高遠而無階梯也。“”文化自覺”這一命題,高度重視文化的歷史性,認為中國文化具有著注重、強調“世代之間的聯系”(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的特點,指出“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在歷史的連續性中創造文化”(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史上,《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正體現了中國文化的歷史性特質。
在文化自覺的視野中,對《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進行比較研究,研究《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研究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有助于我們撥開紛繁復雜地籠罩在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發展歷程之上的由現象、事件、思潮組成的重重迷霧,直接地、迅捷地抓住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核心本質、核心特色、理論品格和獨特魅力。如果我們以文化自覺的視角,細密入微地全面審視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核心本質、核心特色、理論品格和獨特魅力,就會發現,它們與“文化自覺”這一命題的基本要求,是完全符合的。這說明,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在理論靈魂的層面上,是完全具備著實現自身的文化自覺和現代轉化的條件的。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核心本質、核心特色、理論品格和獨特魅力,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通變適時,發展創新,與時偕行,二是在堅持“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的基礎上開放包容,海納百川,博采眾美。下面,讓我們在文化自覺的視閾中,對二者加以闡釋。
四、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通變適時、與時偕行的理論品格
“文化自覺”的觀點認為,文化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創新,適應時代的變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走向現代轉化,“文化是流動和擴大的,有變化和創新”,“中國傳統文化里強調一個重要的道理,即文化只是作為一個環節,本身要維持,也要創新”(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并更新了‘傳統’”(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
以文化自覺的視角,審視《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可以發現,它們一脈相承地體現了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通變適時、與時偕行的理論品格,與“文化自覺”的關于發展創新的基本要求若合符契。
《文心雕龍》非常重視創新、發展對于文學的重要意義,明確指出了文學創新、發展的必然性和內部規律,“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可久,通則不乏”,“文辭氣力,通變則久”“,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文心雕龍·通變》)“,至變而后通其數”(《文心雕龍·神思》)。《文心雕龍》十分強調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社會的變遷之間的緊密聯系,認為時代風氣、社會氛圍的變化會深刻地影響文學發展,“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世漸百齡,辭人九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蔚映十代,辭采九變”“,質文沿時,崇替在選”(《文心雕龍·時序》)。《文心雕龍》認為,文學的發展具有與時俱進、推陳出新的顯著特征,文學必須根據時代的發展,因應時代的需要,隨時做出變化調整和自我更新,“變通以趨時”(《文心雕龍·裁》),“抑引隨時,變通會適”(《文心雕龍·徵圣》),“與世推移”(《文心雕龍·時序》),“隨變適會”(《文心雕龍·章句》)。《文心雕龍》認為,文學的創作實踐活動,本身就具有著求新的內在需求和內在動力,“辭務日新”(《文心雕龍·養氣》),“英華日新”(《文心雕龍·原道》)“,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文心雕龍·總術》)。《文心雕龍》認為,文學的與時俱進、變化發展,是繼承與創新這兩個因素的統一體,文學的發展,既有源遠流長的一面,又有日新月異的一面,明確指出了繼承與創新這兩大要素之間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文心雕龍·物色》)“,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文心雕龍·通變》),“該舊而知新”(《文心雕龍·練字》)。
《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全面地、創造性地繼承了《文心雕龍》的關于文學應當適應時代發展而不斷求新的觀點,并在繼承的基礎上作出了突破和創新。《四六叢話》認為,文學的面貌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呈現變化,“三統遞嬗,尚質亦尚文”(《四六叢話·卷二十八·總論二十》敘論),因此,駢文的創作者必須深明“質文升降之故,風雅正變之由”(《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以便根據時代的要求,及時調整文風。《四六叢話》從宏觀上論述了駢文伴隨時代發展而不斷創新的重要性,指出駢文應當順應時變,“相推相衍,遞出新奇”(孫梅《四六叢話自序》),做到“通變以盡神”(《四六叢話·卷十三·章疏六》敘論),在繼承與創新的辯證關系方面,駢文應當“迥越前古”(《四六叢話凡例》),“獨開生面”(《四六叢話·卷二十一·記十三》敘論),“杼軸新意”,“獨出巧意,不蹈古人”(《四六叢話·卷二十七·談諧十九》敘論),“必也盡遺窠臼,別出機杼,始可揚古調以賞音,進文心而奏績也”(《四六叢話·卷十四·啟七》敘論)。《四六叢話》又從微觀上論述了駢文創作具體實踐中的創新的重要性,指出駢文在具體創作層面,應當“琢句彌新,遒文間發”(《四六叢話·卷六·制敕詔冊四》敘論),“新巧以制題”,“進退遞新其格”(《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追求“新裁”(《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新制”(《四六叢話·卷十四·啟七》敘論),認為駢文的文體風格應當因時而變,做到“體屢遷而惟變所適”(《四六叢話·卷二十六·雜文十八》敘論)。在強調發展、創新的同時,相應地,《四六叢話》也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對僵化、守舊、陳俗的堅決反對的態度。《四六叢話》明確反對“繩墨所設,步驟所同”(《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指出“門面習套,無復作家風韻”(《四六叢話凡例》),對“臭腐陳言”(《四六叢話·卷十·表五》案語)厭惡至極,堅決主張“刊落陳言”(《四六叢話·卷十三·章疏六》敘論)。《四六叢話》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創新的觀念對于研究駢文發展史具有重要意義,指出“識鮮通變,亦無以枋選”(《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認為,如果缺乏應時而變、創新發展的文學理念,是無法掌握、權衡、研究作為“駢儷之淵府”(《四六叢話凡例》)、“駢體之統紀”(《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的《昭明文選》的,又指出“《解嘲》、《答賓戲》,問對雄奇,《漁父》之深趣也,冰絲一掬,而杼軸日新”(《四六叢話·卷三·騷二》敘論),認為,駢文發展史上的優秀作品,無不是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發展而不斷開拓創新的結果。《四六叢話》又開創性地提出了,發展、創新的觀念對于駢文理論寫作具有重要意義,指出駢文理論著作在體制、體例的設置方面,應當像《文心雕龍》那樣,勇于“創例”(《四六叢話凡例》),認為,駢文理論的寫作,只有將繼承性的“考訂”與飽含著發揮、創見的創新性的“發明”緊密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粲然可觀”(《四六叢話凡例》)的理論水平,在駢文作家論方面,《四六叢話》對“作家姓氏、爵里,稍引史傳,附以論斷,見知人論世之義”(《四六叢話凡例》),充分強調了時代、社會的發展變化對于駢文作家、駢文創作的深刻影響。
總體看來,《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通變適時、與時偕行的理論品格,完全符合“文化自覺”的關于發展創新的基本要求,有力地證明了駢文理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創新、走向現代轉化的可能性。
五、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的在堅持“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的開放包容、博采眾美的核心特色
“文化自覺”的觀點認為:“要認識和把握中國文化的特點,就要考察我們文化中的‘天人觀’的獨特性。”(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著重‘天人合一’的傳統。這里的‘天’字應作為‘自然’解。”(費孝通《文化論中人與自然關系的再認識》)中國文化具有著“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渾融感應、凝聚整合。“天人合一”最基本的涵義,就是充分肯定自然界和人的精神的統一,充分關注人的行為與自然界的協調,充分強調人與世界之融合。“天人合一”,強調天人相類,主客相通,融人心于萬物,化天性為德性,從而實現主客合一、物我合一、二元合一。“天人合一”,主張心物一元,將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渾然為一,認為人與世界息息相通,融為一體,世界是人心與天地萬物的徹底融合。“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是潛藏在中華文化異彩紛呈的眾多文化現象之下的最精微的內在動力和思想基礎,是中華文化不斷發展的內在思想源泉,是中華民族文化特質的典型表現。“中國文化傳統尤為推重的‘太極’之說,就是指二合為一的‘天人合一’的終極狀態。我們一向反對無止境地用‘物盡其用’的態度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主張在自然、歷史和社會中找到適合人的位子。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終極狀態,追求一而二、二而一的融會貫通。”(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
“文化自覺”的觀點指出,在文化的交流、對話中,應“保留自己的特點,同時開拓與其他文化的相處之道”(費孝通《對文化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的思考》)。“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講:‘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費孝通《關于“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觸、碰撞、融合中,研究者必須擺脫各種成見,敞開胸懷,以開闊的視角、開放的心態、博大的包容性,超越自己文化的固有思維模式,來深入觀察和領悟其他族群的文化、文明。在跨文化的交流和溝通中,構建起新的更廣博的知識體系。”(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文化上的唯我獨尊、固步自封,對其他文明視而不見,都不是文明的生存之道。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世界文明共存共榮的根本出路。”(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中華民族在形成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進程中,積累下了融匯百川、對不同文明兼收并蓄的寶貴經驗。”(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因此,在面對西方“天人對立”“主客二分”的文化精神所派生出的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態和理論形態時,中國文化完全有能力在堅持“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的基礎上,獨立自主地作出自己的文化抉擇,“博采眾長,開闊胸懷,拓寬思路,啟迪靈感”(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最終通過文化互補共贏,實現“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費孝通《“美美與共”和人類文明》)。
以文化自覺的視角,審視《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可以發現,它們一脈相承地體現了中國古代駢文理論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和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文化胸懷,與“文化自覺”的關于在堅持“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基本要求若合符契。
《文心雕龍》高度重視“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指出,“天人合一”意識是中國古典藝術理性的基本意識,認為,中國古典藝術理性高度強調與天地自然和諧統一的人在藝術中的本體地位。《文心雕龍·原道》從“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出發,對于與自然渾融一體的人的藝術本體性,作出了生動而詳明的闡釋:“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龍》認為,與造化自然和諧統一、渾融無間的人,實為“五行之秀”“天地之心”,代天地而立言,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了自己與天地造化融為一體的和諧至美的境界。《文心雕龍》進一步指出,在藝術構思的過程中,“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體現為一種“神與物游”《文心雕龍·神思》的精神狀態;而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則體現為這樣一種情況,即創作主體并不把藝術作品僅僅當作一個外在的冰冷的客體來創造,而是把藝術作品作為主體生命、靈魂的延伸,在藝術作品中注入創作主體的生命,使主客渾融一體,使藝術作品成為靈動的、有血有肉的、生機勃發的、蘊含著主體生命體驗的、擁有神髓聲氣的生命體,“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文心雕龍·附會》)。
《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充分地繼承了《文心雕龍》對“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的關注,并作出了自己的創新。《四六叢話》在首篇開篇便開宗明義地標舉出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在文學領域的靈魂性地位,高度彰顯了“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在文學誕生、發展歷程中的重要意義,“文之為言,合天人以炳耀”(《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四六叢話》進一步指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可以使駢文創作在藝術風格上達到一種主客、天人“渾然和同”(《四六叢話·卷二十三·銘箴贊十五》敘論)的完美境界。《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繼承了《文心雕龍》的關于“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使藝術作品成為主客渾融的有血有肉的充滿生命力的生命體的觀點,以“風神”“氣骨”“神形”等本用來形容人的充滿生命意蘊的范疇來闡釋駢文創作,“興寄篇中,百讀而風神自得”(《四六叢話·卷三·騷二》敘論),“采珠數言之精當,氣骨非常”(《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而意古,體峻而骨堅”(《四六叢話·卷十八·碑志十》敘論),“神離形合,則魚目之無光”(《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四六叢話》創新性地提出,“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可以使駢文創作達到主觀人力刻意經營與天地造化自然之美的完美統一,可以使駢文創作者的雕琢、藻飾、用典、協韻達到毫無斧鑿之跡、做作之態的如同自然天成般的化境,可以使駢文作品體現出“妙若天成”(《四六叢話·卷六·制敕詔冊四》敘論)、“妙極天然”(《四六叢話·卷二十八·總論二十》敘論)、“構局渾成”(《四六叢話·卷四·賦三》敘論)、“千洗而無痕”(《四六叢話·卷二十八·總論二十》敘論)、“有天成之章句”(《四六叢話·卷十八·碑志十》敘論)、“賁若化工之肖物”(《四六叢話·卷六·制敕詔冊四》敘論)、“卷舒之態自然,襞積之痕盡化”(《四六叢話·卷十三·章疏六》敘論)、“運于手而不知”(《四六叢話·卷六·制敕詔冊四》敘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四六叢話·卷十·表五》案語)的藝術風格。
《文心雕龍》積極主張,文學創作者應當具有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和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懷,應當在“乘一總萬”(《文心雕龍·總術》)的基礎上,在掌握、堅持、標舉自己的特色和靈魂以應付、適應、融匯、支配各種情況、萬般變化的基礎上,兼容并包地吸納多元異質文化因素,為自身服務,實現“眾美輻輳”(《文心雕龍·事類》)、“驅萬途于同歸”(《文心雕龍·附會》),而絕不能狹隘地“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文心雕龍·知音》)。
《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忠實地繼承了《文心雕龍》的關于文學創作者應當具有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和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胸懷的觀點,并作出了自己的創新。《四六叢話》的作者認為,不同的文化因素之間,“淄、澠不必盡合”(《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駢文創作者在面對多元文化因子時,應當以“博綜”(《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的心態,兼收并蓄地吸納“他山之瑜瑾”(《四六叢話·卷一·選一》敘論),從而使不同文化因素融會貫通于駢文創作者筆下,“化秦、越如一家”(《四六叢話·卷十七·書九》敘論),最終實現駢文作品“體包眾善”(孫梅《四六叢話自序》)、“集茲眾美,蔚為大觀”(《四六叢話·卷二十一·記十三》敘論)的完美狀態。總體看來,《四六叢話》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完美地體現了中國古代駢文理論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和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文化胸懷,完全符合“文化自覺”的關于在堅持“天人合一”文化精神的基礎上兼收并蓄、博采眾長的基本要求,有力地證明了駢文理論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吸收、借鑒多元文化合理因素,從而走向現代轉化的可能性。
六、結論
“文化自覺”的觀點,為中國古代駢文理論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指明了自主轉型、發展的宏觀方向。在“文化自覺”的視閾中,近現代駢文創作走進困局的原因,是引導駢文創作的駢文理論依然停滯在以古論古的狹小天地內,陷入了以古為牢、不知新變的思維定勢,而當今時代,駢文創作與駢文理論走向新生與復興,成為了學術發展與文化發展的必然,成為了文化交流與對話的需要,成為了時代的呼喚,時代要求引導駢文創作的駢文理論,以高度的文化自省精神,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優長和不足,在保留自身基本特色的同時,走出泥古桎梏,與時偕行,吸收嶄新的時代因素以豐富自己的理論,為自己擴容,在與外域文化進行互動、溝通、交流時,不僅要堅持自身的核心特色、理論內核以保持獨立自主,更要兼容并包地廣泛吸收多元文化的合理因素、優秀成果以拓寬自身理論的解讀、闡釋途徑,豐富自身理論的內涵與外延。以“文化自覺”的觀點看來,時代對駢文理論的這種要求,不僅并不苛刻,而且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是駢文理論完全有能力實行的。因為,在“文化自覺”的觀點看來,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其杰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自身內在地、天然地完全具備著實現上述要求的條件,這些條件由于日久年深、歲紀綿邈而逐漸被歷史的塵埃所掩蓋,現在是借“文化自覺”之力把它們發掘出來以利于駢文理論創新發展的時候了。在“文化自覺”的視閾中,對《四六叢話》與《文心雕龍》進行比較研究,探索《四六叢話》的駢文理論對《文心雕龍》的繼承與創新,可以發現,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其杰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具備著通變適時、發展創新、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和在堅持“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的基礎上開放包容、海納百川、博采眾美的核心特色。這完全符合“文化自覺”的關于發展創新和在堅持文化特色基礎上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題中之義,完全符合當今時代對于駢文理論的上述要求。因此,透過“文化自覺”的視角,我們可以肯定地指出,以《四六叢話》和《文心雕龍》為代表的中國古代駢文理論,在理論靈魂的層面上,充分地具備了實現自身現代轉化、引導新型駢文創作的宏觀條件。在“文化自覺”精神的指引下,獨立自主而又博采眾長地推進自身的現代轉化,是駢文理論創新發展的必然趨勢。
[1]費孝通.費孝通全集[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2]馬林諾夫斯基著.文化論[M].費孝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3]于景祥.中國駢文通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4]孫梅.四六叢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5]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6]張世英.天人之際[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責任編輯 楊抱樸】
I207.22
A
1674-5450(2014)02-0092-05
2013-11-03
馬驍英,男,遼寧海城人,遼寧大學古代文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