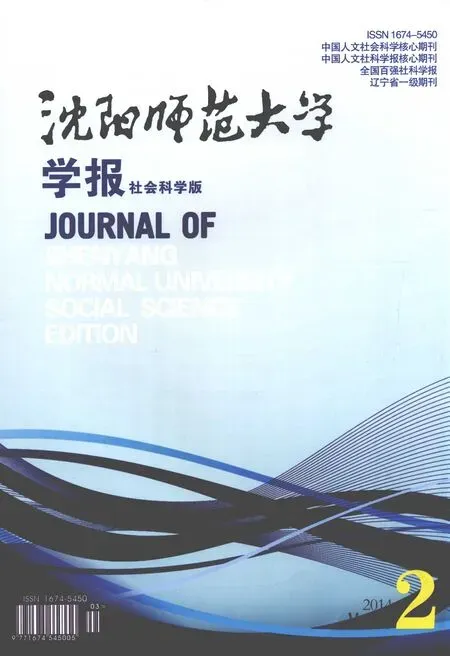論流貶文化的歷史地位
葉淑香
(鐵嶺市濕地研究所 歷史地理研究室,遼寧 鐵嶺 112000)
“流貶文化”是古代中國衍生的一種特有文化,它是以歷史上所實行的流刑制度和貶謫制度為依存,以流貶地為生存空間,以流人文化和貶官文化為內涵實質,以區域本土文化為基礎,以中原先進文化為核心的特色鮮明、獨立成章的一個文化單元。流貶文化反映了被流放、被貶謫人員的悲慘境遇、心路歷程和苦難生活,在中國浩瀚的歷史文化長卷上繪下了濃重凄美的色彩。同時,它也極大地豐富和提升了流貶地的文化內涵。正是因為有為數眾多的流貶人員的到來,才使得當地的經濟文化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一、流貶文化及其構成
歷朝統治者將其所判定的罪犯流放、貶謫到邊遠蠻荒之地以懲罰和實邊,因而,在這些地區聚集了大量的流貶人員。他們中很多人是知識分子,這些人帶去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對當地的開發和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并與當地居民共同創建了五彩繽紛、多元駁雜的流貶文化。作為歷經數千年的流貶文化,是中華燦爛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淀豐厚為不可多得的文化遺存。
所謂流貶文化即是指被流放、貶謫人員在同自然界和社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其至少包含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人員構成。這里的被流放人員既包括被統治者判定為有罪而流徙之人,也包括被統治者強行擄至邊地以實邊之人。此處之所以用“判定”表述,是因為被流放的人員當中雖然絕大部分確確實實是刑事犯罪人員,但也不可否認其中有不少無罪、無辜之人,他們有的是被人排擠、受人誣陷的官員,有的是和平居民和無辜百姓。因此,用“判定”一詞更為客觀和準確。這里的被貶謫人員是指因忤怒皇帝,得罪當權者,或違反朝儀禮法,甚至違法犯罪而被貶黜流放的官員,其中亦不乏有蒙冤之輩;二是時間跨度。早在上古時期,我國就有用流放措施處罰官員的做法,而官員貶謫至少可追朔至戰國時期。《尚書·舜典》云:“流宥五刑”,帝堯曾“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至清朝,流貶懲罰才隨著封建王朝的覆滅而終止,其歷時之長可以說是與我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相始終的;其三,地理區域。流貶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懲罰,因此,流貶地大多選擇在邊遠偏僻的蠻荒地區,主要包括西北絕域、西南煙瘴之地、東北苦寒之地和嶺南瘴疬蠻荒地區。最后是成分內容。流貶文化由流人文化和貶官文化兩部分構成,且特指流人和貶官于被流貶時期在流貶地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
二、流貶文化的形成原因
流貶文化的形成與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存在著緊密的聯系。一方面,在古代中國,統治者非常重視官吏制度,尤其重視對官吏的整肅機制。在這一機制中,對官吏的懲治是一項重要內容。官員所受到的懲治多種多樣,流貶是其中較為常見的懲罰形式,可以說,流貶在中國古代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官員被流貶的原因很復雜,有的是因犯罪受罰,有的是因得罪權貴受罰,有的是受親朋連坐受罰,有的是因黨爭受罰,有的是因觸怒龍顏受罰,也有為追求公理公正而遭迫害的。在這諸多原因中,黨爭和觸怒龍顏是導致官員受到流貶處罰的兩個重要原因。黨爭是統治集團內部爭權奪利的宗派斗爭,當權臣得勢時,與其相對立的政治勢力則會經常遭到排擠打擊而被貶謫、流放乃至誅殺。在中國,君主專制是延續了2000年之久的官僚政治體制,其重要特征即是皇帝個人專斷獨裁,其極具隨意性和突發性。在專制制度下,任何臣子都隨時隨地有可能因觸怒龍顏而被流放和貶謫,只要與皇帝意志相悖,只要忤逆皇上圣旨,就有可能“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因此,流貶文化產生的深刻根源是專制制度。另一方面,在傳統社會里,科舉制度將中國文人與政治聯系在一起,科舉成為士人們改換門庭和身份的最佳選擇和途徑,學而優則仕成為他們實現自身價值的終極目標和畢生追求。然而,官場是殘酷和無情的。表面上官場沒有劍影刀光,沒有腥風血雨,但卻暗藏玄機,波詭云譎,險象環生,充滿了嫉妒、仇恨、機詐和權謀。官場從來就是政治斗爭的代名詞。迂腐的文人士子們進入官場后,由于不諳官理,雖才高八斗,滿腹經綸,卻遭人妒忌,受人排擠,往往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仕途的失意、慘遭流放和貶謫的命運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官宦士子在品嘗了被流貶的苦難與艱辛之后,頑強抗爭,或建功立業,造福一方;或苦讀不輟,治學不息;或寄情于山水,訴說悲腸,成傳世佳作。這樣,在專制統治下的殘酷的政治斗爭中,經過“士”與“仕”的碰撞,被流貶人員對人性思考、對制度反思后的智慧結晶——“流貶文化”便形成了。也正因為流貶文化的誕生伴隨著廣大流貶人員的辛酸和辱痛,自強不息的抗爭精神、憂國憂民的憂患情懷、鞭撻時弊的批判意識、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便成為了流貶文化的鮮明特征。
三、流貶文化的歷史地位
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流貶文化產生了重要作用和影響,占據著不容忽視的歷史地位。
古代中國的流貶地多選在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環境險惡、經濟文化落后地區。流貶人員中絕大多數人在經過了短暫的悲憤、彷徨、消沉、痛不欲生之后,積極主動地融入當地社會生活,對當地全面開發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有的通過農耕和軍屯生產,開墾了許多荒地,不僅增加了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而且促進了農業發展,對當地的經濟繁榮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明朝戍守遼東的軍士多為“謫發”的流人,他們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通過他們的辛勤勞動,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遼東屯田已達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洪武末年,遼東上交的屯糧不僅做到了“強兵足食”,而且“頗有贏余”。正是這些流人用自己的雙手開發東北,建設東北,使得土曠人稀、荒涼榛莽之地,逐漸變成經濟發達地區。在流貶人員中,有很多是來自中原的博學才子、文壇精英,他們或迫于生計,或為情志所致,開館授徒,著書立說,在傳播中原先進文化方面占有一席之地。如楊慎在謫戍云南期間,專心讀書、講學、著書,寫就著作180余部/篇,現存有《滇程記》《滇載記》《滇候記》《南中集》《南詔野史》《云南山川志》等,對后世影響很大,也成為后人研究云南的重要史料。此外,東北流人所寫的地方志著作如方拱乾的《絕域紀略》、楊賓的《柳邊紀略》、吳臣的《寧古塔紀略》、方式濟的《龍沙紀略》等,不僅是研究寧古塔地區歷史的重要地方文獻,也是研究黑龍江省和東北歷史的重要歷史書籍。更為可貴的是,有些貶官雖身處逆境,卻能勤政為民,造福一方。如因“諫阻迎佛骨”而先后被貶刺潮、袁二州的韓愈,中國文學思想史上杰出人物,為政期間,興利除弊,政績斐然:他驅鱷除患,化民成俗,贏得當地百姓的廣泛贊譽,以致“潮州山水皆姓韓”;他興書院,開民智,倡文風,十幾年后,袁州誕生了江西第一個狀元——盧肇,至唐朝中后期,袁州更贏得“江西進士半袁州”的美譽;他修筑堤防,鼓勵農桑,使潮州農業自唐以后及至宋代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潮州社會經濟的發展。再如一代思想文學宗師柳宗元,在被貶永州時,積極參與辦學,熱心指導后生,史稱:“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在刺柳期間,柳宗元鑿井取水,釋放奴婢,開荒植樹,重修孔廟,創辦學院。據《柳州縣志》載:“有唐柳子厚開此邦之文教”“建學宮,崇圣教……而喬野樸陋之風一變。”此外,他還教民“種禾、養雞、蓄魚,皆有法,民益富”,使“民業有經,公無負租……豬、牛、雞、鴨,肥大蕃息。”正是有如韓愈、柳宗元這樣的貶官的到來,才增添了像袁州、永州這樣原本默默無聞的蠻荒之地的文化內涵,提升了它們的歷史文化地位。因此,流貶人員對當地的開發和建設功不可沒。
統觀古代中國眾多流貶人員,其所取得的成就幾乎涵蓋了文化的所有領域,在文化的諸多方面他們都頗有發展與建樹,以至形成了各自有著自己風格與特點的流派。囿于篇幅,下面僅引文學、書法、哲學三領域為例作以說明。在文學上,有代表北宋最高成就,在文學史上占據卓越歷史地位的蘇軾。蘇軾一生經歷了三次大的貶謫:先貶黃州,再貶惠州,繼貶儋州。這三次貶謫成為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三個里程碑,黃州尤其如此。黃州五年是蘇軾創作高峰和才華最橫溢時期,其巔峰之作“兩賦一詞”——《赤壁賦》《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和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文精品諸如《定風波》《卜算子》《浣溪沙》《臨江仙·夜歸臨皋》等,都創作于這一時期;在寓惠的兩年零7個月里,他寫下了近600篇(首)的壯麗詩篇,以致“一自坡公謫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因此,一句“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便成為蘇軾對自己一生最貼切、亦最真實的詮釋。在書法上,有與蘇軾、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的黃庭堅。黃庭堅在被為“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和被“復除名,羈管宜州”期間,“不以遷謫介意”,仍不懈堅持書藝,形成了其行草書取勢尚意的獨特風格,如小字行書如運筆圓轉流暢,沉靜典雅的《史翊正墓志稿》,大字行書如與蘇軾《黃州寒食詩帖》合稱“雙璧”的《黃州寒食詩卷跋》、被譽為天下第九行書的《松風閣詩帖》,草書如恣肆縱橫、龍蛇起舞的力作《李白憶舊游詩卷》等都成為中華書畫寶庫中的瑰寶,對后世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在哲學上,有明代著名哲學家王守仁。其在被貶至貴州龍場任驛丞時創建的“身心之學”即“心學”成為我國哲學思想史上一個頗為重要的流派。該學說提出了“心即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的主張和“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學命題,建立了“心”“理”“良知”三者一體的心學體系,其所強調的個性化發展和對個體創造力的調動及對個人意愿的尊重,對后世社會影響深遠。正是這些流貶人員創造了獨具特色的流貶文化,它以其凄美與瑰麗為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人之偉大,常見于危難中。流貶文化所蘊含的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沉重深廣的憂患意識和濃厚熱切的愛國情懷,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流貶者群體既要忍受邊地之艱難與險惡,更要飽受歧視、凌辱和迫害,在此雙重壓力下,他們中有的人摧而不折,不但沒有意志消沉,反而在困厄中奮發向上,有所作為,于不知不覺中影響著周邊的人們,并漸漸地形成一種獨特的人文思想,甚至在他們離開之后,還在他們曾生活過的地方薪火相傳,成為一種生活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人生觀。如蘇軾雖然屢次遭貶,但每次都能悠然樂觀地面對,并創作了大量的名篇佳作,表現出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這種在逆境中建功立業的進取精神,為后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啟示和巨大的精神財富。特別是那些雖遭流貶厄運,卻仍矢志不渝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政治主張,念念不忘百姓疾苦、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流貶人員尤為令人欽敬,如范仲淹在貶謫中所發出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曠古名言,千年來一直影響和教育著后人,并已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楷范。他的詩文及人品在當時和后世得到極高的評價。其好友韓琦評價他說:“竭忠盡瘁,知無不為……天下正人之路,始公辟之。”受儒家思想影響,中國古代士大夫向來胸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即使遭貶流放,也心存報效國家的愛國情懷,他們或撰寫詩文,頌揚愛國軍民抗擊外國侵略英勇事跡,或直接參加反侵略戰爭,保家安邦,或以死明志、以死報國,他們的愛國情操永遠是激勵中國人民奮勇前行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責任編輯 曹 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