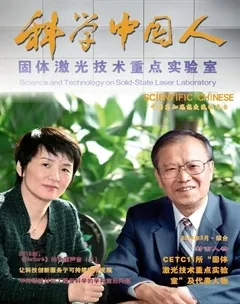從醫救人 惠院強科
良醫處世,不矜名,不計利,此其立德也。
——題記·摘自《臨證指南醫案·華序》
古語有云:“心不如佛者,不可為醫;術不如仙者,不可為醫”。醫生,這個以人為本的特殊職業,在被賦予神圣光環的同時,也承載著生命與希望的重托。海軍總醫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區阜成路6號,在新建內科大樓的神經內科主任辦公室里“坦蕩真誠”和“醫德自然”兩塊牌匾拉近了我們與受訪專家戚曉昆的距離。經過片刻時間的等待,我們見到了戚曉昆教授。他剛從病房查房回來,略帶些許疲憊的神色,卻依然有著親切的笑容。
在這個數九的冬日里,聽他娓娓道來,感受他救死扶傷的溫情,聆聽他把希望播撒人間的祈愿。他讓人看到了一位真正被無數患者贊譽為“信得過的好醫生”,用近三十年的鞠躬盡瘁、愛患如親,書寫了醫者大愛無邊的情懷和無私奉獻的精誠風范。風輕云淡、寵辱不驚之間,他讓我們的訪談變成了一次對生命的朝拜和參悟。
習醫問學,
拾級而上的求學往事
神經內科是研究神經系統疾病的臨床醫學。主要診治腦血管疾病、偏頭痛、頭暈眩暈、腦部炎癥性疾病、神經免疫性疾病、癲癇、癡呆、神經系統變性病、代謝病與遺傳病、脊髓病、周圍神經病及重癥肌無力等肌肉病。主要檢查手段包括神經影像學、神經電生理學、神經生理學、神經免疫學、神經組織病理學,以及分子基因生物學檢測等。
1981年秋,戚曉昆考入第四軍醫大學醫療系。1986年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軍區,進入北京軍區總醫院進行住院醫師輪轉培訓。1989年考入解放軍軍醫進修學院師從于朱克教授,攻讀神經病學碩士研究生,1991年又以優異成績獲得轉博資格。讀研期間,他勤奮好學,借助解放軍總醫院這個很好的平臺,感覺如魚得水,臨床工作與科學研究同步進行,白天晚上稍有空余時間就拼命啃書本,喜歡研讀臨床神經病學及神經影像學,特別是對于神經系統疑難雜癥方面書籍的鉆研,更是達到廢寢忘食的程度!他還借助醫學英文詞典翻閱了大量國外神經科期刊及醫學典籍,自行設計并實施神經免疫相關課題,1994年順利地取得神經病學臨床醫學博士學位。此后,該研究課題繼續深入,并獲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
當問到為什么要選擇神經內科作為自己奮斗的方向時,戚曉昆教授的回答似乎“合情合理”。于“情”,是他弟弟本身患有癲癇,每當看到弟弟抽搐時,就渴望為弟弟以及像他那樣的病人解決病痛之苦,于是上大學時選擇了從醫之路;于“理”,是因為大學期間,對神經系統富有邏輯推理定位定性分析及神經系統疾病復雜的發病機制頗感興趣,符合他一貫勤于思考的性格。
戚曉昆的導師朱克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神經病學家、神經病理學家、軍隊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談起朱克教授,戚曉昆滿懷敬佩與感激;“他對待學生不僅傳授知識,同時教導我們做人的道理。他經常對我們學生說,對待工作和學習上的自我要求標準要高一點,生活標準要低一點,做到淡泊名利。這種人生觀與價值觀深深地影響著我。”
耳畔常縈教誨聲,難舍難斷恩師情。導師嚴格的要求培養了戚曉昆嚴謹的邏輯思維與判斷力,而導師的人格魅力與修為更是深深影響著他的從醫思想和人生態度。在導師的教誨下,博士畢業后的戚曉昆仍然堅持不斷地學習,不僅掌握了扎實的現代神經免疫學、神經影像學和神經病理學的基礎,同時,還能及時掌握國內外神經科發展的前沿信息,開展與臨床緊密結合的科研工作,特別是在脫髓鞘病等神經免疫性疾病的診治及神經影像方面積累了較深的造詣,二者相結合,成功診斷并治愈了許多神經系統疑難病患者。其中,部分患者輾轉國內多家大醫院均被診斷為“腦腫瘤”,但戚曉昆教授借助其扎實的神經內科專業知識,經細致的影像學閱片后,為患者做出了準確臨床診斷——“中樞神經系統瘤樣炎性脫髓鞘病”,不僅治愈了患者身體上疾病,也為患者消除了心理上的陰影,同時,也避免了因誤診所采取放療或開顱的不良預后。近年來,戚教授還多次出國參加學術交流并走上講臺,與世界頂尖的專科大師“對話”,并與日本、歐洲等著名學者建立了良好的學術交流關系。
仁心仁術,
懸壺濟世的從醫足跡
部隊是一塊特種鋼,而軍醫應該是特種鋼中最優質的部分,它們都需要不斷地冶煉。做為軍醫要像大浪淘沙一樣不斷地去除思想上的雜質,而留取精華。
——戚曉昆
“腦血管病,譬如腦梗死和腦出血等,是神經科醫師均應掌握的常見病與多發病。它作為臨床研究而言,既復雜又簡單。復雜在于醫學界對其研究了近二百年,也不能阻止腦血管病的發生與發展,現已成為威脅中國老年人健康的頭號疾病;而簡單又在于腦血管病的診斷與治療相對簡單。”戚曉昆還向我們介紹到,在我國,腦血管病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2008年中國第三次死因調查中,腦血管病占到22.45%,是頭號殺手。為此,戚曉昆早在15年前就開展了旨在挽救腦梗死、腦出血患者生命,改善其遠期預后,提高患者生存質量的多種診療措施:開展早期神經功能康復治療,建立以神經專科的卒中監護、早期床旁神經功能康復為主的卒中治療中心(使腦血管病患者能夠得到系統化、個體化的綜合治療)。但是,戚曉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神經系統免疫疾病、代謝病及變性病,尤其是中樞神經系統的炎性脫髓鞘疾病。
發現我們聽到這個深奧的醫學名稱后疑惑的眼神,戚曉昆解釋說:“中樞神經系統脫髓鞘病患者的中樞神經系統傳導纖維可出現多個部位的髓鞘脫失,就好比電線的皮脫掉了一樣,但與之不同的是,神經纖維信號的傳導主要是包在外周的髓鞘,而不似電線中心的“金屬絲”。這種疾病的患病往往反復多次發作,且人群主要以中青年為主,不僅患者自身很痛苦,而且使整個家庭都承受著相當的精神與經濟負擔。”
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醫學專業問題上開始了對戚曉昆懸壺濟世之路的探尋,走進了戚曉昆的勇敢、樸實與蘊含責任與擔當的從醫之旅。
攻克醫學堡壘,勇者的智慧與果敢
假瘤樣脫髓鞘病(tumefactive demyelinating lesion, TDL),也稱瘤樣炎性脫髓鞘病(tumor-like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diseases, TIDD)是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一種較為特殊的脫髓鞘病,也是CNS炎性假瘤中的一種。
近年來,TDL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多為個案或少數病例的報道。目前,國內對該病的臨床及影像特點觀察研究比較淺顯。隨著近年影像技術發展及腦活檢術的應用,發現該病罹患人數并不在少數,特別是其臨床、影像等方面與腦腫瘤有諸多相似之處,臨床中二者易于混淆、誤診或誤治。即使是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及影像科的資深專家有時對TDL及腦腫瘤的鑒別也有一定困難。
如何及早判斷患者是否患有TDL,從而提高該病患者的治愈率是目前每一個從事神經內科的醫生都不容回避的問題。近年來,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神經內科醫生和團隊都向這個“堡壘”發起了進攻,戚曉昆便是其中一員。以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為平臺,他一直為攻克這個堡壘而不遺余力。
早在2008年的第一屆亞洲神經病理大會上,戚曉昆就總結了18例TIDD的臨床影像特點,并受邀第一個進行大會發言,引起了與會專家共鳴,受到好評。近來,在首發課題的資助下,戚曉昆及其同事對TDL與腦腫瘤進行了詳細的對比剖析,總結了病理證實的60例TDL及70例腦腫瘤患者的臨床、影像資料,并做了細致的對比性研究,對TDL及腦腫瘤的臨床鑒別提供了有益的臨床經驗,以供研究神經內外科及影像科等相關專科醫師在TDL的診斷與鑒別診斷中進行參考。
除了TDL,戚曉昆還擅長診斷和治療多發性硬化、格林-巴利綜合征、不典型病毒性腦炎、多系統萎縮、頭暈眩暈癥、以及某些神經心理障礙疾患;尤其擅長診斷神經科的少見病及疑難病,為此,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
在不斷超越自我、敢為人先的精神下,戚曉昆在醫學的道路上不斷前行,近年來共承擔首發基金課題3項,其他課題多項。每年多次受邀參與中華醫學會繼續教育部和中國醫師協會等諸多繼續教育學習班授課;另外,自2001年以來,獨自承辦了共9屆全國神經疾病臨床進展學習班,講授國內外神經疾病臨床診治進展。2011年4月做為高級訪問學者赴瑞典卡洛琳斯卡醫學院學習訪問3個月,并在該院基礎部進行講座。2013年做為大會主席承辦了第十四屆全軍神經內科學年會及第十屆中瑞國際神經科學學術大會。
在臨床及科研工作中,戚曉昆不僅勇于開拓和實踐,也善于對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提煉,共發表論文300余篇,主編專著3部,參編20余部。其中,《炎性脫髓鞘病的基礎與臨床研究》獲得軍隊科技進步二等獎,《線粒體腦肌病的臨床及相關基礎研究》獲得軍隊醫療成果二等獎,另有6項臨床研究獲軍隊醫療成果三等獎。
心系治病救人,仁者的樸實與情懷
“每次門診,一上午能看20多個病人。”由于戚曉昆的工作認真負責、服務周到,國內越來越多的患者慕名前來就診。“戚主任人好,醫術也好,找他看病心里踏實。”每當說起戚曉昆,病人們都是贊不絕口。
戚曉昆說,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神經科大夫,他的構成需要是合格的神經專科大夫,加上下列三種主要的成分:部分的心理學者、部分的影像學者、部分的病理學者。
在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疑難病會診和危重病人搶救過程中,總能看到戚曉昆的身影。在越來越多的醫師依賴高精尖儀器檢查的今天,無論是在門診,還是查房,戚曉昆都是聽診器、叩診錘從不離手。他對病人的體格檢查,就像教科書一樣規范。在診斷病情時,他總是耐心詢問,仔細傾聽,認真檢查。“細微處見真章”,很多時候,就是在與病人細心的交流中,他發現了隱藏在疾病背后的蛛絲馬跡,從而發現導致疾病的“元兇”,最終找到科學的治療方法。在救治病人時,他憑借高超醫術,不放過任何一個救治希望的可能,《給生命一次機會》就是CCTV-10《科技之光》欄目對他妙手回春使一個危在旦夕昏迷的大學生起死回生故事的報道。在專家門診時,有些患者病情復雜,需要重新詢問病史,全面查體,他就不怕麻煩地一頁頁、一項項地閱讀化驗和影像檢查報告,審慎思考,把相應的診斷治療措施向病人或家屬進行耐心細致的解釋,絕不會幾句話就把病人對付走,多年如一日,他總是成為門診走得最晚的醫生。
“作為一個醫生應具備耐心、認真、虛心、執著的態度,所謂耐心是指要學會傾聽他人的述說,所謂虛心即不恥下問,所為認真即指對工作及其相關事情一絲不茍,所謂執著是指對未知或不解有著強烈地解決的愿望;作為一個醫生應具備仁慈寬容、關愛體貼、果斷機智的素質。所謂仁慈寬容是指對待患者就像長者對晚輩那樣大度和包容;所謂關愛體貼是指對患者要向對自己的親人一樣,有無私奉獻的精神;所謂果斷機智是指對病情的判斷處置要迅速、準確,而且要善于靈活應對突發事件;最后,作為一個醫生還應具備能甘于寂寞、不畏困難、任勞任怨的特殊素質。”從醫三十年,戚曉昆對于如何做醫生這一命題有了越來越深刻的理解。
心中有夢,
五彩斑斕的科室未來
人生的目標與追求,實際上也是人生最高級的需要,即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但我認為,人活著實際上就是為他人而活著。我的人生觀就是要像朱克教授那樣對待工作、學習與生活,淡泊名利,不追求物質享受。
——戚曉昆
不辭辛勞強科室 耐心傳授育人才
1994年,戚曉昆來到海軍總醫院工作。斗轉星移,幾經變遷。戚曉昆至今仍清晰地記著初到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工作時的情景。
“雖然來之前已經有了心理準備,但是現實條件還是超出了我的預期。醫生一共只有九個人,床位21張,當時神經內科還跟呼吸科合在一起,未獨立成科,科室沒有像樣的實驗室,只能做簡單的血流變學檢查。”
確實,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后是當時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的真實狀況。面對困境,戚曉昆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責任。盡管科室發展的困難是客觀存在的,但他相信,思路決定出路,只要高度重視、深入研究、堅持突破,就會成為發展的新基礎、新平臺、新動力。
在他的帶領下,經過十余年地努力,海軍總醫院神經內科近年來醫療技術力量發展迅速,現擁有畢業博士7名(含在讀2名)、碩士5名(含在讀3名)。主任醫師職稱2名,副主任醫師職稱4名。目前,科室已發展成為了第二軍醫大學和南方醫科大學臨床神經病學博士與碩士培養點,以及解放軍醫學院、安徽醫科大學、大連醫科大學神經病學碩士培養點,另外,還是北京市神經內科住院醫師培訓基地、全軍神經疾病護理示范基地、國家藥物臨床試驗驗證基地。2013年戚曉昆教授還當選為中華醫學會北京醫學會理事;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委員會委員;全軍神經內科專業委員會神經免疫及神經肌肉病學組組長、北京醫學會罕見病學組委員等十余項任職;還擔任《中國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病學雜志》副主編、《中華神經科雜志》、《中華內科雜志》等十余種期刊的編委。
科室現有病床82張,還擁有獨立的神經肌肉病理室、神經免疫診斷室,配備先進的德國萊卡冰凍和石蠟切片機,可以進行神經和肌肉的病理檢查。神經免疫實驗室可開展多項京內僅少數醫院可進行血液與腦脊液的實驗室檢測,如:寡克隆區帶、24小時IgG合成率、髓鞘蛋白(MBP等)、水通道蛋白4抗體、神經節苷脂抗體等的檢測;同時,借助神經外科的立體定向技術可以進行腦的病理檢查。通過這些檢查可以為就診的患者提供較為全面和完整的輔助診斷檢查,更好地為患者提供診斷服務。
由于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很高,科室長期重視該病診治研究,在缺血性腦血管疾病的治療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特色治療方案。通過卒中單元與神經康復的完美結合,使得腦血管疾病患者得到最大程度的恢復。另外,科室還在部分少見疾病(如:多發性硬化、視神經脊髓炎、多系統萎縮、同心圓硬化、瘤樣炎性脫髓鞘病等中樞神經系統變性疾病、線粒體腦肌病等遺傳代謝病)的研究以及眩暈的診治方面的均已形成鮮明的自身特色。再有,科室對神經疑難病癥診治有獨道之處,目前海軍總醫院神經系統疑難病多學科聯合會診中心已開展5年半余,已經會診1800余例疑難雜癥,糾正了很多錯誤診斷,數十名病入膏肓的患者重獲新生。這種以神經科、病理科、影像科聯合在一起的會診模式為患者帶來了福音,并受到業內專家的認可及廣泛好評。
盡管臨床、科研以及管理工作繁忙,戚曉昆仍不遺余力為科室培養年輕醫生,他總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堅持讓一個個年輕醫生脫穎而出。在技術上,他既嚴格要求又大膽放手。雖然臨床工作很忙且雜,他卻堅持每天帶領醫務人員交班。在每周進行查房過程中,他經常手把手的示范,及時糾正學生不正確的體檢手法,有時利用休息時間耐心地為學生在實踐中遇到的疑難問題解惑,盡可能提高學生們的動手能力。
對年輕醫生來說,戚曉昆既是良師,也是益友。他總是言傳身教。率先垂范,告訴他們如何做好醫生、學會做人。他總是以自己的經驗教訓為例證,讓年輕醫生少走彎路。每次學習歸來,他總是毫無保留地將新知識與同事分享,學以致用,不斷躬耕,把理論轉變為能力,大膽創新,讓最新醫學技術造福于病人。
科室的后起之秀邱峰從碩士開始就一直跟隨在戚曉昆身邊,如今已有十余個年頭。在他眼里,戚曉昆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超人”,他每年都要審閱幾百篇文章,兼任很多學術期刊的編委。即便如此,他對學生的論文修改還總是親力親為,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連中間語法標點符號的調整,思路的理清,他都會詳細地跟學生解釋。
“我愿盡余之能力與判斷力所及,遵守為病家謀利益之信條,并檢除一切墮落和害人行為,我不得將危害藥品給與他人,并不作該項之指導,雖有人請求亦必不與之……”這是兩千多年前,古希臘醫生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行醫三十年來,戚曉昆始終將這段誓言奉為自己懸壺濟世的圭臬,一心一意踐行著“大醫精誠”的醫家精神。
戚曉昆不是不累,而是對工作太熱愛,太投入。他只要進入工作狀態,精力就高度集中,就忘記了疲憊,忘記了休息,更忘記了自我。他對自己的定位是“當一輩子醫生”,這個從踏入軍營就有的夢想,至今未曾改變。“不管工作條件、環境、技術條件怎么變,夢想都不會變。”而他也經常和廣大年輕人分享了自己一路走來的心得,“堅持、勤奮,就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