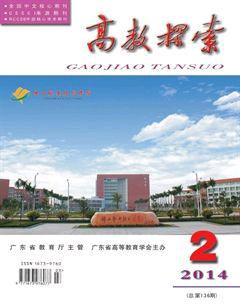高校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策略分析
朱海龍+楊韶剛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簡介:朱海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2012級博士生,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講師;楊韶剛,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510006)
*本文系廣東省2012年“十二五”教育規劃課題青年項目“價值與行動:高等教育國際化與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研究”(項目批準號2012JK131)的成果之一。 摘要:多元文化時代的強勢崛起掀起了多元價值觀相互沖突、滌蕩與重構的浪潮,世界諸國都在此番浪潮的推動下主動調整著高校價值觀教育的方略。作為我國高校道德教育核心內容的價值觀教育也正面臨著現實困境,其中既有緣于價值相對主義的道德判斷難題,也有“不接地氣”的價值觀教育模式尷尬。多重困境的存在急需教育策略的超越。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結合的理念超越,“從做中學”與道德價值判斷融合的路徑突破以及教育主體間聯合的創新模式等成為當前價值觀教育突破困境的可取策略。
關鍵詞:困境;超越;高校;價值觀;教育策略多元文化時代的不期而至招致的結果必然是多元價值觀的激蕩、沖突與重構。正如馬克思在一百余年前斷言的那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形成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此番情境下的高校價值觀教育尤為重要。它決定大學生能否獲得價值批判的精神利器,能否習得走向終極幸福和享用一生的道德價值觀。誠然,我國當下的價值觀教育依然面臨困境,探求從困境走向彼岸的超越理應成為積極的教育關照。
一、 現實的困境:價值判斷難題與教育模式缺陷并存(一)多元文化時代的判斷難題:價值相對主義
多元文化時代的來臨使人們體驗到了短暫欣喜,之后轉瞬之間便被拋入到價值選擇的困境之中,即如何審視價值相對主義的判斷態度,如何在魅影重重的多元文化背后尋得可以享用終生的絕對價值,從而走向幸福人生。這對當下的高校價值觀教育和涉世未深的大學生而言都是一個艱難的現實課題。眾所周知,文化是價值觀的載體。多元文化浪潮送來了世界不同民族、國家豐富文化資源的同時,多元價值觀也裹挾而來,其中不免魚龍混雜,亟需做出清晰的價值判斷。然而,高校價值觀教育還未做好全面準備,大學生的價值判斷能力也還遠未達到入木三分的力度,面對光怪陸離的各式價值觀容易一葉障目,既無法洞察多元價值觀的優劣,也不能對自身民族價值觀進行深刻剖析,最終變成一個似是而非,一切皆可的“好好先生”,而幕后推手就是價值相對主義的評判態度。“似乎突然之間各種形式的相對主義又受到青睞。我們對科學的本質,對異族社會,對不同歷史時代,對宗教和文學文本進行考察時,都會聽到一個聲音在告訴我們,并不存在“‘硬事實,相反似乎‘什么都行。”[2]不可否認的是,價值相對主義雖然打破了強勢文化獨尊論,倡導文化平等主義,力求文化寬容,但其踐行的相對主義判斷準則卻直接造成了價值邏輯混亂,演化成了生活中的無標準,大學生和社會都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判斷底線,社會價值秩序將從此隕落。大學生考試作弊、貸款違約、偷竊、甚至毒殺室友事件的頻繁出現也就不足為奇。美德倫理學家麥金太爾犀利地指出:“道德行為者從傳統道德的外在權威中解放出來的代價是,新的自律行為者的任何所謂的道德言辭都失去了全部權威性的內容。各個道德行為者都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論或等級制度的權威的約束來表達自己的主張……”[3]告誡之言依然縈繞于耳,如若對價值相對主義聽之任之,今天的大學生勢必成為“失落的一代”或馬爾庫塞言下“單向度的人”,實現高校價值觀教育的超越也只能是永遠看不到盡頭的一席春夢。
(二)“不接地氣”:高校價值觀教育模式的最大尷尬
毋庸諱言,當前高校價值觀教育模式的最大尷尬就是“不接地氣”,即與火熱的現實生活脫離,不能熟稔地游走于多元文化的熱潮之中,大學生仍然局限在課堂里接受價值觀教育。在這看似非常精妙的教育設計中并不缺乏豐富的道德價值內容和頗具教學經驗的教師,也不缺乏先進的教學設備,唯獨缺乏的正是價值觀教育的核心要素,即真實生活情境和大學生的情感參與。由此看來,無論是大學生個體價值觀的養成還是社會整體道德風尚的建構都將無法徹底實現。
·教師與學生· 高校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策略分析 就發生論的視角而言,價值觀的生成始點在于生活,生活是大學生價值觀生成、培養與升華的唯一現實源泉。馬克思依據社會關系的基礎對人的本質做出了史無前例地精準判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所以,大學生的價值觀不能僅僅體現在抽象意義上,還要還原到現實生活中去,從生活中去建構、升華價值觀。列寧也強調說:“訓練、培養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學校內,而與沸騰的實際生活脫離,那我們是不會信賴的。”[5]因為生活規定了大學生作為人的存在和價值觀作為精神的存在,“規定了他們是誰;不只提供了他們在自由社區可以建立的關系,也提供了可以讓他憧憬去發現的相互關系;不只成為個體的一個特征,也成為了他們認同的構成部分。”[6]正是生活造就了真實的存在,賦予大學生砥礪道德責任,培養道德判斷力和道德行為力的真實環境和現實素材。縱觀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雖然自建國以來歷經多次改革,取得了斐然的成績,但教育走不出校園的尷尬卻未有本質改變。因為沒有生活的檢驗,大學生尚無法在多元文化裹挾的多元價值觀面前做出有效的價值判斷,只能在精神層面“建構”自己的價值觀卻無法在生活中實踐,學習的結果更多地是知行分離,甚至還會適得其反地造成信仰危機。著名倫理學家樊浩教授在《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中披露,經過全面調查統計發現:“29%的大學生認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的影響變小了,50%的大學生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變小了,41%的大學生認為共產主義的影響變小了。”[7]調查結果必須引起警醒。在生活中進行價值觀教育,讓生活成為價值觀教育的教材,這在世界范圍內已經成為教育共識,也理應成為我國大學生教育過程中的必需介質。
另外,價值觀的培養離不開情感因素的參與。因為在價值觀形成過程中,不僅需要理智對是非、善惡、美丑做出直接的價值判斷,還需要情感的介入以便對其形成認同。如果在價值觀教育過程中剝離道德情感,一味地講授道德知識,只能使大學生在真實的道德情境面前麻木不仁,既不能培養完整的、健康的價值觀,也不能造就鮮活完整的人,使當下的價值觀教育成為遠離真實,不接地氣,曲高和寡的“精神花瓶”。媒體中早年爆出的清華大學生硫酸潑熊和近年來不斷映入眼球的新聞事件,諸如大學生戲弄精神病人,欺辱同學甚至毒殺室友等等無一不反映出大學生道德情感缺失的弊病,這也正是高校價值觀教育亟需改進之處。
二、 走向超越:高校價值觀教育的應然策略(一) 道德知識與道德行為結合:高校價值觀教育的理念超越
價值觀教育作為高校道德教育的核心內容,包括兩個重要的維度:即道德知識和道德行為。道德知識主要是告知大學生什么是善惡,美丑,真假,正義與非正義等等,一般理解為德目,是人類走向終極幸福的前提條件;道德行為是在生活中踐行德目,通過大學生的自身行為體驗,完成對道德價值的認知,生成道德情感與道德認同,由此建構與升華自我的價值觀,它是大學生擁有德性人生的必要條件,二者同時具備才能形成完整、真實、健康的價值觀。西方德性倫理的源頭人物亞里士多德對此就有前瞻性認識,“美德有兩種,即心智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心智方面美德的產生和發展大體上歸功于教育;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習慣的結果”[8]。這里的“習慣”,就是生活中的行為,就是“做”的意義,通過行為去校驗道德價值的真實與否。作為價值觀教育的規律性認知,這一點西方與東方有著高度的相似性。《論語·里仁》中就曾有“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的觀點,強調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就應該少說多做,升華自我的道德修養。《論語·學而》中也提出從日常生活中實踐德性的必要性,要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理學大師朱熹更加關注行為對道德知識以及德性養成的意義,要求從小入手。他說:“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習成,而無捍格不勝之患也。”[9]諸如此類,無不說明行為與認知之間不可分割的規律性意義所在。
不可否認的是,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依然疏離于古代先哲們早已認知到的教育規律之外。面對以價值相對主義為代表的各路思潮的強勁挑戰,超越當下的不足便成了必需的文化自覺。由于深受原蘇聯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影響,我國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一方面非常注重道德知識的教授,尤其注重政治價值觀教育,主要是以“兩課”教育為主要載體,教育主體是德育教師,方法則主要是“美德袋”式的灌輸講授,教學內容缺乏生活氣息,大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受到了一定的制約,另一方面卻又忽視了道德行為的教育。如此以來,學生從生活中建構價值觀的正常途徑就被阻斷,剩下的只有政治價值觀內容的講授。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和不易操作性特點,大學生更多地是通過強迫記憶的方法記住了基本的價值內容,目的也是希望通過考試,與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準則沒有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對如何學以致用自然也就無從下手。由此可知,如若要超越當下價值觀教育的不足,就必需在注重道德知識教育基礎上,拓寬教育內容,納入并加強道德行為教育,尤其是對大學生道德行為的評價,建立以價值觀為介質,從道德知識到道德行為之間的對應參照體系,使他們的行為可以從學校延伸到社會,使大學生在此參照體系下踐行、校正自我的價值觀。學校和社會則可以在此參照體系下對他們進行及時有效的行為評價:道德行為要予以肯定,以此強化形成固定的行為模式;對非道德行為則要嚴厲批評,及時校正。在此參照體系下,學校、社會、大學生三者之間形成了有效的交往溝通,大學生也開啟了對道德價值真正的自我探索,而不是像以前那樣被動接受“美德袋”式的價值觀教育。
令人欣慰的是,面對當前的不足,教育界已經清醒地意識到了問題所在,并且進行了諸多改革,如設立大學生社會實踐學分,組織大學生暑期“三下鄉”活動,進入福利院慰問孤寡老人、弱勢群體,深入社區做民生調研等等,增加大學生在社會基層實踐德性的頻度,以此提升價值觀教育的實效性。但此類教育活動階段性突出,制度性和長期性都還不足,尚不能保證大學生在完整的生活鏈條中通過自我行為去驗證道德知識的價值真理。所以,亟需建立一整套完整、細致、操作性強的制度以超越當前的教育不足。
(二)“從做中學”與道德價值判斷融合:高校價值觀教育的路徑突破
早在1927年,著名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就在《教學做合一》一文中指出:“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是先生;在教上學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系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系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說,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教,學也不成學。”[10]此言入木三分,指出了教、學、做三者不可分割的本質聯系。這恰恰也是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的方法瓶頸:教師無法從做中講授什么是價值觀,學生更無法從做中學到什么是令人格完善、道德高尚的價值觀,只能是從“美德袋”中抽取道德價值觀內容講給學生聽,原本需要通過從做中學的鮮活教育頓時之間變成了思想上的寂靜空響,全然失去了鮮亮的教育色彩。陶行知在幾十年前指出的教育弊病不應該在生活育德已經成為共識的今天還繼續存在。必須從教育路徑上謀求突破,堅持在做中學的同時結合道德價值兩難判斷,既給大學生提供多元文化視域下從做中學的通道,也賦予他們提升道德判斷的方法。
大教育家夸美紐斯的話意味深長:“德行是由經常做正當的事情學來的。”[11]這里有兩層含義,首先,道德價值觀是從做中學來的,生活是不可替代的途徑;其次,要由道德價值判斷去決定是否“正當”。做還是不做,以及怎樣做,只有把從做中學和道德價值判斷結合起來,才能解決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途徑和培養的方法問題,保持良好的價值判斷力。正是如此,陶行知特別提出:“從生活中發生出來的困難和疑問,才是實際的問題;用這種實際的問題來求解決,才是實際的學問。”[12]只有在做的過程中才能遇到道德價值判斷的真實“困難和疑問”,而解決這些困難和疑問的過程,為高校價值觀教育提供了真實的情境和有效的培養方法,所以亞里士多德也認為“道德是一種在行為中形成正確選擇的習慣”[13]。
我國目前的高校價值觀教育尚未建立從做中學的教育平臺,道德價值判斷的教育方法則更為少見,大學生最需要的指導缺失了。僅從教材而言,主要是依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馬克思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中國近代史綱要》、《形勢與政策》為介質的政治價值觀教育教材;在方法上主要運用講授式,缺乏道德價值判斷的教育,尤其缺乏道德兩難判斷教育方法。大學生不能在課堂中體驗能到兩難判斷的沖擊力,也無法提高價值判斷水平。所以,課堂教學中可以更多地運用一對一辯論、小組討論、兩難情境模擬表演等方式講授;教材中則可多體現生活情境中的道德兩難沖突,讓大學生從教材和教法中都能夠體驗到價值判斷的困難和魅力,啟發他們自我思考,提升道德認知能力。
(三)借鑒的力量:高校價值觀教育的文化勇氣
當下正值多元文化強勢崛起之時,它也促使文化因子在世界各國、民族之間頻繁交流互動。任何國家希冀對此視而不見,在與世隔絕的文化真空環境下完成自我文化生產都是一廂情愿的烏托邦。對朝氣蓬勃的大學生而言更是如此。他們對放眼看世界的欲望是如此強烈,網絡資訊科技發展又是如此神速,大學生手指輕輕一點就可以完成世界的“遨游”。此情此景下,高校價值觀教育是挑戰與機遇并存。可以通過多元文化的交流積極借鑒他國長處,彌補自我不足。它既是對當下高校價值觀教育的努力回應,也不失為一種自信的文化勇氣。
社會學家格里芬說:“中國可以通過了解西方世界所做錯的事,避免現代化帶來的破壞性影響。”[14]多元文化時代為我們的價值觀教育提供了一個了解他國經驗教訓的良好契機,因為多元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動態多元開放的系統,高校價值觀教育的理念、內容、方法、成果、師資等因素在國際間交往和流動,在比較中體現優勢,暴露劣勢,我們完全可以秉持批判中繼承,反思中吸收的態度借鑒他國的可取之處,用以改進、提升自我的教育。縱觀歷史,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生成過程就是與多元文化接觸、砥礪、革新的過程,并不缺乏向異質文化借鑒的勇氣和智慧。比如說,早在隋唐時期,自印度大陸傳入我國的佛教很快在相互借鑒的基礎上與儒學和道教完成了本土化的融合,成為我國的主要宗教。時至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早期現代化學制“癸卯學制”,就是在借鑒美國以及學習日本、德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新中國成立后的教育則是大量借鑒當時的教育強國原蘇聯的理念、體制、方法,甚至包括教材,使得孱弱的教育迅速跟上了世界的步伐,紀律精神和集體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與此同時,世界諸國之間也在全球化的交往過程中相互借鑒,積極吸收。如1947年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就是參照美國道德教育的經驗建立的,而美國的《國防教育法》則是在比較學習原蘇聯教育目標、體制和方法的基礎上確立的。凡此種種,不勝枚舉,但無一例外地說明在多元文化的生態環境中積極借鑒吸納他國的優秀教育成果是自我提升的催化劑,而我國當下的高校價值觀教育既擁有開放包容的傳統文化基礎,又有多元文化的現實交流平臺,所以,借鑒他人之長理應成為一種教育選擇。
(四) 教育主體間的聯合:高校價值觀教育的模式創新
高校價值觀教育的系統性、復雜性、變動性與長期性決定了教育主體應有的多樣性,不同主體因其所長發力于一處,又通過主體間的聯合形成穩定強大的合力,成為我國道德教育模式的創新方向,助推教育實效性的躍升。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主要通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展開,依托高校課堂教學完成,教育主體是高校和教師,至于社會、家庭以及學生的自我教育功能并未被設計進來,教育主體間的聯合也未曾實現,造成無形教育資源的極大浪費,制約了價值觀教育的隱性力量發展。
由于“學校教育處于社會本位”[15],學校必須擔負起道德教育和公民訓練的使命,而且這種訓練的根本在于共享的價值觀之中。所以,我國一直以高校作為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重要的、其至是唯一的制度化場所,長期倚重學校道德教育的途徑,缺乏與社會、家庭和大學生的和諧互動,致使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原本不高的實效性在家庭和社會中被消耗。美國品格教育靈魂人物托馬斯·利考納曾指出:“新式價值觀教育要取得長久成功,必須依賴學校之外的力量:學校和社區應當共同努力,來滿足孩子們的需要,并促成他們的健康發展。”[16]這道出了教育主體間聯合的必要性。在此過程之中,大學生從高校回到家中就進入了父母主導的教育和督導體系,從家庭中走出步入社會或社區時,又得到社會所樹立的道德楷模人物的榜樣示范意義,并在大學生破壞了群體認同的道德準則時給予及時的輿論批評和懲罰,引起大學生的道德反思,從而實施自我道德教育,如此往復,形成良性循環,值得我國認真借鑒。
國學大師梁漱溟說:“家庭在中國人生活里關系特見重要,人盡皆知;與西洋人對照,尤覺顯然。”[17]大學生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員,他們的價值觀教育如若沒有家庭作為教育主體的參與也就失去了中國社會獨特的倫理教育資源,難以對大學生產生深入靈魂的教育作用——畢竟家庭給他們提供了進行思維和道德價值判斷的基本背景,塑造了他們的精神歸屬。然而,社會作為另一教育主體則為高校價值觀教育提供了砥礪道德責任和檢驗道德行為,培養道德判斷力的真實環境與現實教材,讓價值觀教育回到了生活。有鑒于此,我國高校近年來也在不斷嘗試把學校價值觀教育和社會教育聯合起來,鼓勵大學生踐行中國傳統道德價值觀,如參加“三下鄉”活動,慰問孤兒、空巢老人等弱勢群體,參加社會公益活動,爭當志愿者,就業面向“西部志愿者”、“三支一扶”等。盡管如此,依然是治標不治本,難以形成系統化、精確化、制度化的互動機制。亟需制定一套操作性強、有明確制度或法律保證的教育體系,使大學生在學校的道德表現能夠讓家庭和社會知曉。社區則為他們實踐價值觀提供現實機會和場所,對其不足之處進行及時校正:社區建立大學生道德檔案,給予分數評定,并定期將其表現反饋至高校,由此形成互動。同時,激勵大學生自我以及朋輩群體進行價值觀反思,煥發出自我教育和朋輩教育的積極作用,使價值觀教育真正從外部教育轉化成內部教育,實現康德言下的道德自律。這樣,高校價值觀教育才算落地生根,也必將結出豐碩的道德果實。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2][美]查理·伯恩斯坦.超越客觀主義和相對主義[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2.3.
[3][美]阿拉斯戴爾·麥金太爾.德性之后[M].龔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87.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5]列寧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
[6]Michael Samdel.Liberalism and the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150.
[7]樊浩,等.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784.
[8]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A].張法琨.古希臘教育論著選[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17.
[9]題小學·晦庵先生朱文公選集(卷七十六)[M].臺北:大化書局,1985.116.
[10]陶行知全集(第2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2-43.
[11][捷克]夸美紐斯·大教學論[M].傅任敏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167.
[12]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42-43.
[13]周輔成.西方倫理學名著選讀(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311.
[14][美]大衛·格里芬.后現代性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M].馬季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16.
[15][德]O·F·博爾諾夫.教育人類學[M].李其龍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4.
[16][美]托馬斯·利考納.美式課堂——品質教育學校方略[M].劉冰等譯.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152.
[17]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北京:學林出版社,2000.26.
(責任編輯于小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