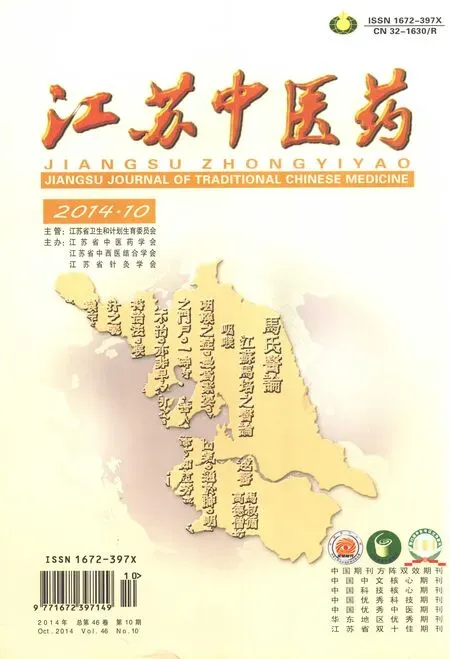烏梅丸治愈疑難寒熱病驗案2則
俞俊薏
(紹興市中醫院,浙江紹興 312000)
烏梅丸治愈疑難寒熱病驗案2則
俞俊薏
(紹興市中醫院,浙江紹興 312000)
失眠 惡寒發熱 烏梅丸 驗案
烏梅丸出自漢代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由烏梅、細辛、干姜、黃連、當歸、附子、川椒、桂枝、人參、黃柏十味藥組成。方中烏梅為君,味酸、澀,性平,具收斂之性以清降相火,《神農本草經》認為其有“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等功效;合黃連、黃柏之苦寒,可益陰清熱、降氣除煩;佐附子、干姜、桂枝、川椒、細辛溫三陰經之寒而不燥;人參、當歸,健中以培補氣血。全方寒熱并用,攻補兼施,現代常被用來治療寒熱錯雜、虛實互見的疑難病證。筆者近來在臨床上遇到兩例以寒熱為主要表現的病患,經服烏梅丸(改湯劑)后,迅速取得明顯療效,服膺于經方療效之余特整理以與同道分享、研討。
1 病歷摘要
1.1 寒熱失眠案
樂某某,女,39歲,公司職員。2014年4月6日初診。
主訴:半夜后發作寒熱往來,并因此導致不寐2年余。患者2年多來每到半夜后即出現寒熱往來,持續1至3小時不等,發作時無其他不適,發完后幾如常人,因寒熱發作,導致失眠,即便寒熱結束后亦僅能淺睡。長期睡眠不足導致精神狀態差,工作效率低,健忘,時常出錯,痛苦不堪。曾陸續在多家正規醫院的西醫、中醫處求診,終因短時內毫無改善而作罷。既往易得口腔潰瘍,常有痛經,易焦躁,冬季四肢不溫。刻下:面色萎黃,納食基本正常,大便偏溏,舌淡紅、苔薄黃,脈沉細滑。予烏梅丸改湯劑煎服,處方:
烏梅15g,制附子9g,細辛6g,干姜9g,花椒6g,桂枝9g,黨參12g,當歸6g,黃連6g,黃柏15g。3劑。
4月13日復診:訴服藥當晚寒熱等癥即明顯減輕,后兩日均未發,因上班原因未及時復診,后又發過1次,然僅1小時左右,今求鞏固。再予原方稍增劑量續服,處方:烏梅15g,制附子12g,細辛6g,干姜9g,花椒6g,桂枝12g,黨參15g,當歸6g,黃連6g,黃柏15g。5劑。至7月因發現乙肝小三陽再來求診時訴上證未再發。
按:此病診治之點睛之處正在于半夜后發作寒熱往來,寒熱往來之表現常見于少陽與厥陰二經,為樞機不利的表現,而病發于半夜后,即子丑相交之時,而持續1至3小時,則多在丑時,正是厥陰經氣旺盛之時,此時發病則可知病與厥陰有關。再看患者平素癥狀,口腔潰瘍、失眠、焦躁為相火偏旺,痛經、四肢不溫、面色萎黃、便溏、舌淡、脈沉為脾腎虛寒之象,合而觀之,從部位看為上熱下寒之證,依虛實論為虛實夾雜之病,故決定投用烏梅丸寒熱并用、攻補兼施,竟得立竿見影之效,經年之病數日而痊。
1.2 不明原因惡寒發熱案
楊某某,男,34歲,公司職員。2014年4月23日初診。
主訴:反復惡寒發熱3月余。患者3個多月來,常無明顯誘因下出現惡寒發熱,有時一日數次,有時數日一次,一般持續半到1小時,伴全身乏力、自汗、四肢酸楚、便溏,常易出現口腔潰瘍。曾在西醫處檢查血常規、生化等,未有明顯異常。也在中醫處服過中藥,而觀前醫處方有桂枝湯或桂甘龍牡湯加減,有小柴胡加減,有補中益氣湯加減或導赤散加減,療效均不佳。刻下:患者納食一般,夜寐欠佳,小便偏黃,舌黯紅、苔薄黃,脈沉細。予烏梅丸改湯劑煎服,處方:
烏梅15g,制附子12g,細辛3g,干姜9g,花椒6g,桂枝12g,黨參15g,當歸6g,黃連12g,黃柏15g。5劑。
5月7 日復診:訴前方服完后,未再發寒熱,四肢酸楚明顯緩解,大便稍成形,口腔潰瘍近段時間未發,唯仍時有汗出,問是否需再服藥。囑予虛汗停顆粒及玉屏風顆粒善后,并囑其注意休息,勿過勞累,飲食清淡,忌煙酒、辛辣煙熏、冷凍冰鎮、黏膩食品及炒貨。
按:本案患者非典型烏梅丸證,其寒熱表現為惡寒發熱而非寒熱往來,且無明顯厥陰經見證。但所幸前醫的診治過程為筆者排除了許多類似證的可能。粗看紛繁復雜的臨床癥狀,經仔細推敲辨證,則可見寒熱錯雜、虛實互見的病機。口腔潰瘍、尿黃、苔黃為有熱;便溏、脈沉為寒;乏力、自汗、四肢酸楚、脈細為氣血虧虛,衛外不固,筋脈失養。綜合其寒熱、虛實又以脾氣虛及心肝火旺為主,故稍重附、姜、桂、參振奮脾運,促進氣血之生化;加大黃連用量,以清降心肝之火。故諸證得愈。復診時僅余自汗一證,乃脾肺氣虛所致,為減其煎藥之苦,故以成藥及生活調養善后。
2 討論
烏梅丸可算最耐人尋味的經方之一。仲圣于《傷寒雜病論》中用以治療蛔厥,晉唐一直沿襲,待到宋代以后,醫學流派興盛,才不斷有人從其藥物組成去探討其對應治療病機,逐漸樹立其厥陰病主方,治療寒熱錯雜、虛實互見病癥的地位。已故“傷寒泰斗”劉渡舟教授在其著作《傷寒論十四講》[1]中說:“它(作者注:指厥陰病)應是陰陽錯雜,寒熱混淆的一種疾病,方為正論……為此,凡臨床見到的肝熱脾寒,或上熱下寒,寒是真寒,熱是真熱,又迥非少陰之隔陽、戴陽可比,皆應歸屬于厥陰病而求其治法。”經方大家黃煌教授也在其《經方100首》[2]中提到:“烏梅丸的真正定位應該是厥陰病的主方。厥陰病即是凡寒熱錯雜、虛實互見、氣血失調等疑難證候的綜合概括,而本方的組成則是寒熱并用、攻補兼施、融酸甘苦辛四味為一體的雜合而治……在腹痛、嘔吐、下利等消化系癥狀以外的疾病中,此種寒熱錯雜往往更是判斷是否使用烏梅丸的重要線索。”
筆者所治兩例中第一例證候較為典型,既有典型癥狀又有厥陰經氣旺盛之時發病的特征性時間表現,其可判定無疑。但一時囿于越地多濕,吾人多脾虛濕阻,用熱易濕熱上火,用寒易傷脾致瀉的固定思維,僅先以3劑投石問路,患者又未及時復診,致未能一舉而克,所幸再次調治后即獲痊愈。第二例雖缺乏厥陰定位性表現,但綜合紛繁的癥候可見寒熱錯雜,虛實夾雜之病機。又因有前例之經驗,故徑用5劑而惡寒發熱之證除。可見應用經方當膽大心細,或抓主證,或符病機,就當徑直投用,必能桴鼓相應,立得顯效。
[1]劉渡舟.傷寒論十四講.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72
[2]黃煌,楊大華.經方100首.2版.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251
編輯:吳寧
R255.9
A
1672-397X(2014)10-0056-02
俞俊薏(1981-),男,醫學碩士,主治中醫師,從事內科雜病及腫瘤的中醫藥診治研究。yuzuzi1981@163. com
2014-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