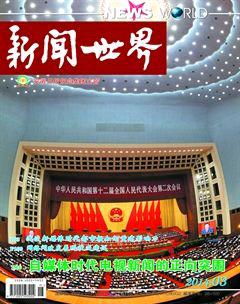評論性節目主持語言特點分析
宋秋怡
【摘 要】本文以白巖松在《新聞1+1》中評論性的主持語言為范本,分析白巖松的電視語言觀及新聞評論主持語言表達風格,即具有貼近性、感性與理性的結合、引導性和記者化,并探討了新媒體背景下既符合大眾傳播規律又具有正能量的新聞評論主持語言。
【關鍵詞】白巖松 貼近性 感性與理性 引導性 記者化
一、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的特點及其對主持人的要求
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在中國50多年的電視歷史中屬于“后來居上”的一種節目類型。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對電視新聞節目的需求不僅僅停留在知道某一新聞事件,還想在節目中看到聽到針對這一新聞事件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于是,主持人言論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喜愛,一些思想政策水平高、被受眾認可的著名主持人成為受眾依賴的“意見領袖”。目前,在全國(大陸地區)范圍內《新聞1+1》在電視評論性新聞節目中可以說是首屈一指,在CNTV網絡電視臺上,欄目介紹是這樣寫的:從時事政策、公共話題、突發事件等大型選題中選取當天最新、最熱、最快的新聞話題,還原新聞全貌、解讀事件真相,力求以精度、純度和銳度為新聞導向,呈現最質樸的新聞。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欄目以新聞事件為基礎,以對新聞事件的解讀和分析為特色,通過電視化的表現手段,在宏觀上提供正確的輿論導向,微觀上提出具體的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中央電視臺副臺長孫玉勝在其《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中提出“電視是一種‘主持人媒體”的觀點,認為主持人的存在使媒體與受眾的傳播還原到了人際傳播的原始階段,主持人成為電視表達親近性和實現交流的一個載體。這一“載體”在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中的作用更為突出。
二、白巖松電視新聞評論主持語言表達特點a
1、貼近性
白巖松在主持節目時,經常以一個“故事”作為節目的切入點。“故事”的“主角”往往是自己,并且“主角”在故事中的地位往往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一樣,尤其是在那些有負能量的新聞事件中,他總是把自己同那些心靈上受傷的人綁在一起。這樣很容易拉近自己與受眾之間的距離,尤其是那些與新聞事中當事人有著相同或相似境遇的受眾。
2011年10月19日,《新聞1+1》播出了題為“這個‘綠色不環保”的節目,開頭是這樣的:
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在進演播室之前呢我究竟是戴一個紅色的領帶還是一個綠色的領帶我猶豫了一下,最后呢我還是選擇戴一個綠色的領帶。但是戴完綠色領帶心里又有點含糊,會不會有很多的觀眾朋友會認為我是一個不太好的主持人,跟戴紅領帶的主持人比較起來呢我比較差。當然這只是一個開玩笑的語言,我是故意戴上綠色領帶的,戴上這條領帶其實是特別想跟西安一所小學剛上小學一年級就戴了綠領巾的孩子們說上兩句話“白叔叔也戴過綠色的領帶,但是呢,不意味著咱不好啊,咱們相當棒,非常好,而且跟戴紅領巾的孩子一樣棒。當然了,你們比白叔叔還棒!”為什么我要嘮叨半天什么綠領帶綠領巾紅領巾呢?來,咱們看!
在這期節目的開頭,貼近性通過白巖松的角色置換表現出來。“綠領巾”事件曝光后,各大媒體蜂擁而至,對這一事件重復報道,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對那些帶著“綠領巾”孩子的二次傷害!多報道一次就是往孩子們受傷的心靈上多撒一把鹽。同時作為主流媒體中口碑、信譽度皆高的欄目要對這一熱點新聞事件不聞不問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做到避免二次傷害或是把傷害降到最低是一個負責任媒體必須考慮的因素。白巖松故意選擇一條綠色領帶,并且把自己等同于那些孩子,反問自己是不是不合格的主持人。眾所周知,白巖松在主持人領域不僅合格,而且是一名很出色很成功的主持人!這樣一來,那些戴過綠領巾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就更容易消除對這一報道的抵觸心理,也不覺得戴綠領巾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同時,這樣拉家常的語言,消除了與受眾之間的距離感,使新聞事件中校方的規則制定者也很容易接受。因為電視是一種居家媒體,在自己的家里,難道有人會愿意請一個“家庭德育教師”,站在自家客廳里,甚至是站在自己的床前來教訓自己嗎?他們當然不愿意,盡管他們確實有錯。
主持人語言的應用是受眾與節目之間的紐帶,語言具有貼近性,節目才能夠具有親和力和全民性。貼近性的語言表達容易贏得受眾的信任感,溫和、不居高臨下的態度使白巖松的新聞評論主持呈現出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
2、感性與理性的結合
感性與理性在評論性新聞節目中是統一的。理性的主題要由感性來實現,感性的人物要做理性的梳理。《新聞1+1》在對理性事件進行解析時,多數是以感性的語言為切入點。
例如2011年10月11日,《新聞1+1》的節目主題是《如何用母語來訴說》,從節目的標題來看這是一個感性的表達手法,但內容是對于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教育及發展在社會轉型期遇到的挑戰和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與思考。節目里白巖松是這樣引入主題的:
我的爺爺只會說蒙語,一句漢話不會說。我的爸爸蒙漢兼通,因為他是他們那的第一代大學生。到我這呢,可以說一些蒙語,比如吃、喝這些等等都沒有問題,能說一些也能聽一些。但是平常基本是用漢語來主持節目。到了我兒子的時候蒙語他完全一句話都不會說,但英語說得不錯。你看四代人,可能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背景,我格外關注母語,各個民族的母語在我們的這種變遷時代當中這樣的一個發展。臺灣有一位著名的詩人叫席慕容,她是蒙古族。有一首著名的詩,后來變成著名的歌詞《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在里頭有這樣一句,我相信很多人唱到它的時候都會格外地被觸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少數民族。那句歌詞是:雖然不能用母語來訴說。因此這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究竟現在我們的民族語言教育發展到了一個什么樣的階段,面臨哪些挑戰,存在哪些問題。帶著這樣一系列的問號回到了我自己的家鄉。來,從呼倫貝爾的一所小學開始說起。
節目開頭,白巖松從自己的爺爺到自己的兒子四代人對母語掌握和使用程度講起,故事化的開頭感性地切入,增強了節目的可看性。接著通過一句理性的總結表達了一種語言的消失僅僅用了四代人的時間,令人深思。之后又提煉出臺灣詩人席慕容的詩句“雖然我不能用,不能用母語來訴說”,表達了對少數民族語言教育及發展的憂慮。自己一家四代人的故事是感性的,詩人的表達也是感性的。但幾句總結性的語言就使節目得到了理性的提升,巧妙地用感情的語言把理性的提升表達出來。
3、引導性
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為觀眾報道新聞、分析事實、發表評論,是傳播意見性信息的節目。主持人對節目的主導能力可以說是節目的重要資源。同樣以2011年10月11日的節目為例,節目最后提到對少數民族語言的繼承與發展的辦法時,白巖松給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問題以及應對問題的一些建議性的方法:
真正要思考的是如何激勵更多的少數民族的學生愿意從小學開始就學本民族的語言進行教育,這恐怕要從將來入大學,尤其是就業方面讓他們成為受益者而不是吃虧者;有更多的選擇而不是只是一個狹窄的空間。不能只在生存的這個比如說內蒙古自治區而是想去北京、上海等等上大學的時候會更有吸引力,在就業的時候口會更寬,它自然就愿意學了。比如內蒙古自治區這兩年在招收公務員考試的時候,就設了蒙漢語都招,這樣的話呢尤其蒙語試卷答題這就增加了吸引力,但這有多少人呢,需要全社會去共同思考。
4、記者化
孫玉勝根據自己及身邊同事多年的工作經驗總結出“記者—名記者—主持人—名主持人”這樣的理念。他認為只有長期的采訪經歷,主持人才能準確判斷什么信息值得放大,什么信息應該放棄;采訪對象透露的什么問題值得窮追不舍,打破砂鍋問到底,什么話語應該及時打斷,免得偏離主題;同樣的事實從什么角度分析更與別人不同,更有利于深入挖掘;事實與背景之間存在什么關系,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樣的結論等等。的確如此,白巖松的記者生涯,鍛煉了他的文字功底,培養了他非凡的洞察力和新聞敏感性,完善了他的知識構架,養成了嚴謹的工作態度。正因為有了以上諸多記者素養,白巖松在主持評論性節目時才能準確到位地把真相和事理挖掘出來,在碰撞和思索中與受眾價值取向產生共鳴,融傳媒意圖、受眾視角、個性特色為一體。
結語
在一檔直播的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中,白巖松的主持語言極富有“養分”,承載的內容豐富、深入,表述的觀點或事實具有啟發性,常常引人深思或讓人有所感悟。并且能把口語和書面語有機地結合。同時,在新媒體背景下,白巖松也能恰當地融合諸多網絡語言元素,在進行合理的信息解讀和正確的輿論引導前提下迎合觀眾的需要,增加節目的可看性,進而提高節目的收視率,使節目能夠達到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機統一。
語言的貼近性拉近了節目與觀眾的距離;感性與理性的有機結合增強了節目的可看性;引導性升華了節目的主題,充分發揮了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傳播意見性信息的功能;記者化增強了觀眾對白巖松主持人身份的信任感。這四個特點強化了白氏主持風格,四點有機融合,是白巖松深受廣大群眾好評的重要原因,也有效地保證了評論性電視新聞節目的權威性和可信性。□
參考文獻
①羅莉:《當代電視播音主持教程》[M].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
②孫玉勝:《十年——從改變電視的語態開始》[M].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
③鄒煜、馬力、夏中南:《追尋新聞的深度——白巖松與〈新聞周刊〉》[M].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
④姚喜雙,《功力、能力、親和力:主持人成功的關鍵》[J].《言語交際》,2011(9)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