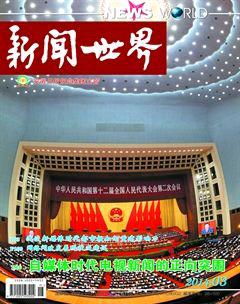淺談新媒體時代都市報如何重建影響力
陳婉婉
【摘 要】新媒體出現(xiàn)給傳統(tǒng)媒體帶來巨大沖擊,它打破了對資訊的壟斷或者相對壟斷,降低了信息生產(chǎn)和傳遞的門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都市報
新年伊始,上海《新聞晚報》停刊。回顧2013年,憂傷迷茫困頓頹唐焦躁的情緒纏繞著國內(nèi)大批紙媒從業(yè)者。其間,行業(yè)大腕的轉(zhuǎn)型,報紙成為“古典媒體”等論調(diào)在微博和朋友圈內(nèi)的廣泛流傳,暗合并放大著這股情緒。
情緒的成因多元,既有紙媒人在報社內(nèi)外的際遇,又夾雜著理想、榮譽、收入甚至求偶等形而上甚或形而下的考量,以及橫向與縱向的比較。
這種情緒,促使大批紙媒人真正開始對未來進行思索。
都市報的盈利邏輯
擴版、專刊、特刊、厚報、彩印,發(fā)行、廣告、福利翻番……在所謂的“黃金十年”里,都市報人確實體味著某種狂歡。
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內(nèi),都市報的從業(yè)人員大幅增加。大量年輕人走上采編或者經(jīng)營崗位,按照前輩開創(chuàng)的模式工作。這種慣性驅(qū)動下的滾動,使得很多年輕的都市報人不曾真正思考過都市報的盈利邏輯。
一家報社,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是什么?一家報社,又靠什么來掙錢?很多人的答案會是:報社生產(chǎn)內(nèi)容(新聞),產(chǎn)品形態(tài)為報紙;報紙靠廣告掙錢。
我想換個視角來看看。不妨拿個其他類型的企業(yè)做對比。一家飲料企業(yè),全年銷售一億瓶飲料,飲料單價為一元,那么總營收為一億元。一家都市報,全年發(fā)行40萬份,一份報紙定價100元。這家報社的總營收又是多少呢?是40×100=4000萬元么?顯然不是。所以,從市場交易或者說是某種“等價交換”的角度來看,在銷售環(huán)節(jié)中被“賣”出去的產(chǎn)品并不是報紙本身,當然也就不會是內(nèi)容(新聞)。
在過去和現(xiàn)在(不代表未來一定還是這樣),都市報社對外出售的,其實是廣告版面。所以,報社確實是在靠廣告掙錢。不過,有意思的是,廣告的定價高低和銷量多寡卻與報紙的內(nèi)容優(yōu)劣及發(fā)行寬窄直接相關(guān)。
綜上所述,一家都市報在過去和現(xiàn)在的生存之道其實是這樣的:由內(nèi)容和發(fā)行共同形成的某件東西有價值,能變現(xiàn)。我們姑且稱這件東西為:影響力。
新媒體如何瓦解了都市報的影響力
如果上述邏輯成立的話,2013年國內(nèi)都市報普遍遭遇廣告量直降,其實源于都市報的影響力在下滑。
新媒體一直被視為傳統(tǒng)媒體的掘墓人。但是,新媒體是如何消解了傳統(tǒng)媒體過去如彼強大的影響力呢?
新媒體出現(xiàn)給傳統(tǒng)媒體的最大沖擊是,它打破了對資訊的壟斷或者相對壟斷,降低了信息生產(chǎn)和傳遞的門檻。受眾的選擇愈多,對媒體的要求愈高。此時,都市報在內(nèi)容制作上的粗放,帶來不利影響,部分優(yōu)質(zhì)內(nèi)容無法第一時間刊發(fā),各家媒體之間內(nèi)容同質(zhì)化、口水化嚴重。
都市報在內(nèi)容制作上的粗糙粗放以及盲目,開始收獲惡果。按照大多數(shù)觀點的論調(diào),我們可以把內(nèi)容區(qū)隔為UGC(用戶生產(chǎn)內(nèi)容)和PGC(專業(yè)生產(chǎn)內(nèi)容)。按說,報社的采編團隊應(yīng)該生產(chǎn)PGC,但是當博客和微博這樣的自媒體平臺興起后,都市報人悲哀地發(fā)現(xiàn):高手原來在民間。
不久前,創(chuàng)新工場的創(chuàng)始人汪華在騰訊網(wǎng)媒體高峰論壇上作了題為《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下的新媒體》的演講。他認為,在移動互聯(lián)的大背景下,依然不變的是,“有深度、高質(zhì)量的專業(yè)內(nèi)容依舊有價值,不會被UGC(用戶生成內(nèi)容)完全替代”。這句話,堅守“內(nèi)容為王”的人都認可。然而捫心自問:我們生產(chǎn)的內(nèi)容真的深、高、專嗎?
知名電視節(jié)目《中國好聲音》的“教父”、燦星制作總裁、復(fù)旦大學(xué)新聞學(xué)專業(yè)畢業(yè)生——田明,將《中國好聲音》的成功概括為這樣一句話:即“我們只是掌握了中國電視娛樂的一種議程設(shè)置”。他繼而談到,議程設(shè)置能力是媒體爭奪的根本。當BBS尤其是微博產(chǎn)生后,網(wǎng)絡(luò)媒體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奪取了話語權(quán)。微博,已經(jīng)成為新聞的發(fā)酵廠、新聞事件衍進的舞臺。
在微博誕生4年時間里,這樣的傳播脈絡(luò)屢見不鮮。比如,陜西發(fā)生交通事故(事件)+網(wǎng)友發(fā)現(xiàn)安監(jiān)局長車禍現(xiàn)場微笑(用戶介入)=局長微笑被質(zhì)疑(新事件)+網(wǎng)友圍觀,并有人扒出局長戴名表(用戶介入)=安監(jiān)局長涉嫌腐敗……
在這樣的流程中,微博不再只是一個二次傳播的媒介。用戶和信息的交織,推動著事件的發(fā)展,不僅不斷帶走受眾的注意力,還牽引著傳統(tǒng)媒體尾隨跟進。
@武大沈陽用另外一種表述即“輿論的核心力量”談過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如果說傳統(tǒng)媒體是由七大系列掌控(新華系、人民系、南方系、央視系、其他央媒系、專業(yè)媒體系、地方系),那么在社交媒體時代,核心輿論力量包括:突發(fā)事件爆料系、公知系、娛星系、政務(wù)微博系、官媒系、市場媒體系、專業(yè)自媒體系、水軍營銷系、管理平臺話題策劃系、海外網(wǎng)戰(zhàn)系……
當大V們歆享著批閱奏章的快感時,都市報人正集體無意識地追隨著網(wǎng)絡(luò)的熱點做文章。
因此傳統(tǒng)的報刊發(fā)行,在這個時代更全面的稱謂應(yīng)該是“市場推廣”。在受眾對單一媒體依附感越來越弱的今天,傳統(tǒng)媒體本身也迫切需要自我包裝,需要立體推廣。特別是,推廣一定要解決讀者是誰、讀者在哪兒的問題,使得推廣的指向性更加明確,并能反哺內(nèi)容生產(chǎn)并提升廣告精度。
新媒體的出現(xiàn),讓人們獲得信息的途徑相當個性化、社交化、移動化,因此都市報的精準定位難度較大。
都市報如何重建影響力
《新聞晚報》元旦停刊再次敲響了傳統(tǒng)紙媒的警鐘,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wǎng)專欄作家徐達內(nèi)為此寫下了《紙媒的黃昏》。當都市報人看到那首“十年青春空飛揚,人未老,報先亡”的《江城子》,無不思考著報社改革的方向。
當商人去推銷產(chǎn)品的時候,首先得考慮產(chǎn)品的用戶群是誰。報紙也是這樣,讀者中可能既有高大上的需求,也有下里巴人的需求,最終要明確的是報紙要針對什么人,要針對讀者什么樣的具體需求和具體場景。
報紙送到讀者手中,不代表流通的結(jié)束。而是繼續(xù)要通過數(shù)據(jù)去跟蹤,做數(shù)據(jù)訪談,反復(fù)多次下來,報紙會真正抓住用戶的導(dǎo)向,不斷修正報紙內(nèi)容產(chǎn)生方式、內(nèi)容本身和內(nèi)容遞送方式。說白了,就是用戶導(dǎo)向,快速迭代,數(shù)據(jù)驅(qū)動。
在新媒體時代,每一個讀者從廣義上來說可能是媒體潛在的后備作者和內(nèi)容產(chǎn)生者,而每個人之所以到某個媒體上去讀內(nèi)容,他需要的可能不僅僅是一個單向的信息接收,而是需要的是一個雙向的交流,需要一個社群的歸屬感,需要一個內(nèi)容再導(dǎo)入的二次解讀,需要一個真正的活在一群人中的有共同的感覺。因此,作為傳統(tǒng)媒體的都市報,需要很好地去引導(dǎo)和經(jīng)營讀者,培育報紙和讀者之間的交互。
舉一個例子,是最近網(wǎng)絡(luò)上很火的暴走漫畫系列,它的創(chuàng)作團隊是針對于草根用戶群的,它有自己的用戶群定位和自己的社區(qū)氛圍,它想要考慮做流量和發(fā)行的時候,會考慮“我的最終用戶在哪里”,“我的最終用戶每天干什么事情,用什么樣的產(chǎn)品”,“用戶在哪里的話,我的內(nèi)容就到達哪里”,“我們的用戶在貼吧上,要保證我們的內(nèi)容在貼吧上;我們的用戶在微信上,要保證所有的內(nèi)容出現(xiàn)在微信上;如果用戶在微博上,我們就要做到微博上。這還不夠,我們還要做成APP,客戶在哪里我們就用各種辦法去到達他”。
同理,都市報的發(fā)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更需要建立長久的“流量觀”,即發(fā)行者每周都要去發(fā)現(xiàn)讀者在哪里,新的讀者流量來源在哪里,每周都要想辦法去做像產(chǎn)品一樣,不斷的迭代,增加新的內(nèi)容管道,不斷的跟蹤,發(fā)現(xiàn)什么內(nèi)容讀者反饋更好、傳播率高。再反過來根據(jù)反饋,不斷修正報紙采編內(nèi)容。□
(作者單位:安徽日報社)
責(zé)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