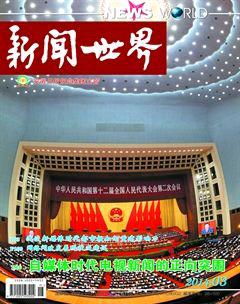對現代社會風險的反思
陳瑤
【摘 要】在現代社會中,風險無法預見、消除但風險發生概率可以被降低。作為一種危險的可能性,如何有效進行風險傳播、判斷風險發生概率顯得尤為重要。本文以PX群體事件為例,從國內媒介的敘事方式、技術專家的言論、政府公關、受眾的風險認知等多個維度的相互作用探討群體性事件發生的背景原因,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PX事件 風險傳播 政府公關
一、現代社會的風險傳播
2012年10月22日寧波鎮海發生PX群體性事件,在此之前有廈門PX事件、大連PX事件、福建PX事件等。對于此類群體性事件的歸因,我們不能籠統的將市民“散步”看做是一次由群體暗示與感染引發的群體極化運動,也不能片面地將市民“散步”當做由謠言引起的非理性行為。PX群體性事件屬于“人造風險”。郭小平認為,“人造風險”是反思的現代性條件下風險類型,是由人與知識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由科學技術的進步所造成的,風險結果常常無法預測。①現代社會風險是伴隨現代科技進步出現的,為了將社會風險值降低至零而不去發展科技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我們可以進行有效的風險傳播,進行風險評估與監測從而降低社會風險發生的概率。
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認為風險社會和人為的不確定相聯系的風險概念,指的是一種獨特的“知識與不知的合成”。一方面是在經驗知識基礎上對風險進行評估;另一方面,則是在風險不確定的情況下決策或行動。②我們需要注意的是:進行風險評估的主體——學科專家——因為風險評估路徑或評估角度不同——風險事件的評估結果可能會有所差異甚至大相徑庭。從廈門大學中科院院士的觀點(PX屬危險化學品和高致癌物,對胎兒有極高的致畸率)到中科院化學專家的言論(二甲苯就物質本身而言屬于低毒,其危害性應該可以控制),加劇了“行動者”的不確定性。在這里,“行動者”可以是政府決策者、媒體從業人員、化工企業管理者以及受眾等。
廈大中科院院士的觀點被《中國經營報》報道后,頗具爭議的風險議題很快被手機、微博、論壇等媒介迅速傳播,“原子彈”、“畸形兒”、“白血病”成為PX的關鍵詞,因為“風險傳播在知識信息中可以被改變、夸大、轉化、削減、隱匿,極易為知識政治所左右”。③之后就引發市民“散步”,導致政府與公眾關系緊張。在風險社會中,不同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并且力圖從這一研究框架內尋找一些解決方案。
二、風險社會中不同行為主體間的社會關系
在風險社會中,PX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是不同行為主體間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復雜社會關系的背后必然存在制度性以及結構性壓力。在這里,我們著重分析PX群體事件中媒介、技術專家、政府以及受眾的認知、態度、行為,并給出相關建議。
1、媒介的敘事方式
媒介在新聞價值的框架內進行風險傳播時,往往會把最具戲劇性、沖突性的內容單獨“拎出”以達到“吸睛”效果,這種做法不利于受眾全面、深度了解風險事件。2007年《中國經營報》報道廈門大學中科院院士關于PX有劇毒的觀點,單一的“權威”信源、單一的報道角度以及戲劇化的敘事內容(致癌物、致畸率)馬上引起受眾關注,在其他媒體的跟進報道下,受眾對PX迅速定性致使PX遭到“污名化”。“污名化”過程包括三個向度:第一個向度是通過媒體的風險傳播,造成高風險的認知,使風險被無限放大;第二個向度是風險報道中涉及的人、技術、產品、地域等被媒體標記,并被劃歸為危險性物質;第三個向度是出于風險的媒介化放大和標記,改變了上述人、技術產品、地域的原有特性,使人們在遭遇他們時,產生了思想上的抵觸和行為上的對抗。④
PX經過《中國經營報》的風險傳播,造成受眾對PX高風險的認知,小魚論壇、《鳳凰周刊》再將風險進行放大,使得受眾對PX產生認知偏差——受眾只知道PX有劇毒,但對于劇毒產生的環境條件、化工企業的控制方式以及政府的風險評估等一概不確定。在《中國經營報》報道中,PX被定性為“劇毒”,“白血病”、“畸形兒”、“原子彈”成為PX的關鍵詞,受眾對其產生抵觸情緒,本能地采取行動自衛。
大眾傳媒單一地傳播某一位技術專家的風險信號,風險信號中的核心詞匯又被其他媒介(論壇、貼吧、微博)繼續放大,這種對風險事件的失衡報道方式勢必會引起群體對PX“過敏”。
所以,大眾傳媒在進行風險傳播時有必要遵循平衡報道原則。孫培旭認為:“平衡就是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因素時,還要顧及其他因素,特別是相反的因素;在突出報道一種主要意見時,還要注意點出其他意見,特別是相反的意見。”⑤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大眾傳媒對風險事件時效性的追逐與風險事件平衡報道原則在某種情況下相悖,所以,這就需要不同的大眾媒介對風險事件進行多元分析,多角度發聲,為受眾提供不同的“側面像”而不是言論報道一邊倒。當然,媒體對風險事件的全面了解也需要一個過程,所以在其進行風險事件傳播時有必要注明“文中所述僅代表XX個人觀點,事件全貌有待進一步考究”。
2、技術專家的言論
技術專家的地位在風險傳播中舉足輕重,其言論會影響受眾對周遭環境風險認知的判斷。當廈大中科院院士表明其觀點時,在PX處于最具爭議的時間段中并未或極少出現其他技術精英的不同聲音,導致受眾“鄰避”效應的形成。在五年之后的寧波PX事件中,就算大眾傳媒極力引用其他意見領袖的多元言論也無法迅速消除受眾的風險疑慮、重構受眾風險認知。在某種情況下,還會引起極少數受眾的厭惡反感情緒——面對大眾傳媒在不同時間段的“悖論式”報道,受眾很容易將當前社會現實、自身處境、政府政策與利益掛鉤。
受眾對提供風險信號的媒介和專家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如果這二者出現失衡,社會就會陷入高度緊張之中。在現代社會中,提供、解釋信息的符號系統和專家系統可以相輔相成:大眾媒介需要引用專家觀點支撐報道內容,而專家言論也有必要通過媒體渠道進行廣泛傳播。媒體傳播不同專家的“對話”可以推動受眾對風險事件的全面了解。
3、政府公關
風險是一種潛在的危機,威脅越大,人們對其控制的欲望也就愈強烈。在現代風險社會中,公關是政府必備素養。在寧波PX群體事件中,區政府發布的“說明”以及負責人的言論(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嚴格履行審查程序)、市政府堅決不上PX項目的決定以及新聞發布會的召開等都是政府應對風險事件的公關措施。但是,從受眾對PX環境風險認知的角度上看,政府公關效果差強人意——PX項目的遷址暗示著政府因為理虧以及迫于輿論壓力而做出讓步。
現代公關之父艾維·李認為要告知民眾以真相,要信奉“凡有利于公眾的才有利于組織”,人民之所以心懷偏見乃是因為未能獲知充分真相。⑥政府必須傳達給受眾的真相是——PX危害性可控、PX風險發生概率低。政府應該真誠主動地建構對話模式與公眾平等協商,譬如及時利用本地媒介進行風險知識的傳播而不是指責民眾行為魯莽等。
4、受眾的風險認知
在廈門PX群體性事件爆發期間,媒體的突然“失聲”、技術精英的一家之言(PX劇毒)、政府的做法(遷址)使受眾談“PX”色變。受眾對當地化工企業的安全監控能力以及PX風險的發生概率不確定,使其對周遭風險認知產生偏差,從而導致社會摩擦。公眾“散步”行為的背后隱藏著風險社會下的集體認同心理,是在環保主義的邏輯下進行的維權運動,受眾的風險認知能夠對其態度、行為產生能動效用。令人欣慰的是,在寧波PX群體事件發生后,《鳳凰周刊》、《新京報》、《環球時報》以及《人民日報》等一系列媒體積極作出深度報道與評論,受眾不僅對PX風險有了理性認知,而且增強了政府的公信力。
結語
現代社會風險作為科學技術進步的“衍生品”,應當被正確認知,我們不能僅僅了解社會風險的危害程度,更要科學分析其發生概率。媒體對PX風險事件的全面了解需要一個過程、受眾重構風險認知需要一個過程、政府進行風險評估與監測也需要一個過程,這就加大了風險傳播的難度。妄圖建立獨立的監察機構去預見風險是一種徒勞。但是,在對不同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進行考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更加理性地認知風險從而避免做出沖動的決定,采取盲目的行動。□
參考文獻
①郭小平,《風險傳播與危機傳播的研究辨析》[J].《Media Time》,2013-2
②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再思考》[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4)
③杜建華,《風險傳播悖論與平衡報道追求——基于媒介生態視角的考察》[J].《當代傳播》,2012(1)
④[美]珍妮·X·卡斯帕森:《風險的社會視野》[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0:152
⑤孫培旭:《論新聞報道的平衡》[M].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
⑥Ray Eldon Hiebert:Courtier to the crowd: the story of Ivy Le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relation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P.157
(作者:湖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13級傳播學碩士)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