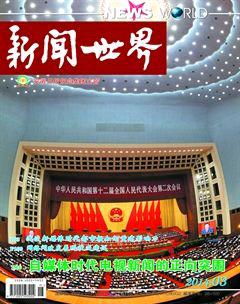淺析社會化媒體上個體的內在和外在表現的差異
常寧
【摘 要】人在現實中總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各個角色也都有相對應的人格,但一個人的“多重人格”總是被統一在外在的表象之下。網絡的匿名性使人們將自己在工作和生活之外隱藏的不為人知的性格多元化地展現在網絡上,表現出了不同的網絡人格。然而,社會化媒體的真實、透明、快捷等特點,在讓人們享受了“自夸”式的內容分享之后,又重新開始壓抑“多重人格”,帶上“假我”面具參與各種社會化媒體活動。a
【關鍵詞】社會化媒體 人格 個體
人格也稱個性,這個概念源于希臘語Persona,起初主要是指演員在舞臺上戴的面具,類似于中國京劇中的臉譜,后來心理學借用這個術語用來說明:在人生的大舞臺上,人也會根據社會角色的不同來換面具,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現。面具后面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真我,即真實的人格,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①
也就是說,一個人可以在生活、工作以及社會中根據環境的變化表現出多重的人格。如果換個角度來看,一個人受制于自身以外的外界環境的壓力,以“多個人”的角色存在,這些角色把一個“真實”的自我或人格隱藏起來。這些角色可能會有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性格,那么我們或可以將這些不同的表現稱為一個人的“人格分裂”。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的外在表現往往因為社會環境而趨于統一,比如,受制于社會道德、人情世故、人際關系,這樣真實的自我也被壓抑起來。或許一個人內心有一些小邪惡,有一些“自私”,有一些利我的想法,但是,因為大環境的文化,因為工作生活或角色的需要,這個人可能要表現出“大公無私”、“大好人”、“處處為他人著想”……而這個人的真實人格和真實需要卻長期被統一在這些“面具”下不敢表現出來。否則,他就會被帶上“異己分子”“不友好”“自我”“太個性”等帽子,而被社會系統中其他人“孤立”。所以,一個人的“多重人格”必須在這種情形下統一成一個外在的“面具”。
當然,這里的“人格分裂”并不是醫學上所指的病態,而是反映現實中人長期的在生活或社會中的生存狀態。不可否認,在網絡出現以前的傳統社會,一個人的“人格分裂”是受環境限制和自身壓抑的,必須帶著一個與自身身份相符的“虛偽”面具“假裝”著生活。即使有“多個人格”(真正的自我、外在的自我、角色的自我),但這些“人格”卻被控制在統一的面具下,處于“假死”的狀態。
一、“人”被綁架在外在現實“關系”之下
那么何謂“人”?如果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的話,對于“人”的表述,中西方有明顯的不同或完全相反。
在西方新教文化下產生的存在主義認為:一個人只有從所有社會角色中撤出,并且以“自我”作為一個基地,對這些外鑠的角色做出內省式的再思考時,他的“存在”才開始浮現。如果他缺乏這道過程,那么他就成為了一個沒有自己面目的“無名人”。②
而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孫隆基是這樣解釋“人”的。“中國人認為:‘人是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體現的。他是所有社會角色的總和,如果將這些社會關系都抽空了,‘人就被蒸發掉了。”③
對于這個解釋,筆者是認同的。在我們的文化里,如果一個人脫離了我們所謂的“社會關系”“人情”“世故”“別人的肯定”,那么這個人在我們看來是沒有“存在”的,會受到異樣眼光和評判的。也就是說,一個人是為“他人”而活的,一個人做事前首先會潛意識里考慮是不是“被別人接受的”“會不會得到贊許的”“會不會符合他們判斷標準的”……“人”是被“各種關系”來定義的。而最終的結果恰恰是忽略了真正“自我”的發展,或沒有“自我”。但在整個環境中,一個人并不會意識到這一點,反而將“假我”認為就是自己本身,認為“假我”才是對的。“真我”處于極度隱秘和壓抑狀態。
這樣看來,一個人確實存在“多個人格”的需要,但這些人格卻隱匿在現實環境 “統一”的面具下。因為“人”被綁架在外在現實“關系”之下,而為了某種目的(比如虛榮、作秀、獲得好感、維護名利……),這種綁架會越來越牢固,也被“關系”挾持得越來越緊。
二、網絡匿名性使個人的“多重人格”得到釋放,“真我”呈現
在網絡匿名時期,“真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展現,并且與帶“面具”的“假我”并不沖突。比如,一個人可以將那些不敢在現實生活中表露的私密情感,在網絡上盡情揮灑,以達到內心真我狀態的寧靜。人們在去社會化的狀態下自由地表達思想和觀點,不用擔心被人指責和鄙視,不必刻意地將自己的言行限制在某個框架內,以求自我的釋放和減壓。
因此,網絡出現后相當長的一段匿名期,給個人的“多個人格”的展現提供了寬松的土壤。這種“人格分裂”對網絡最初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給網絡環境帶來了一些嘈雜的聲音,但是,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多個人格”的展示對個人自身的“真實”發展是有好處的,一個人至少是按照符合自己身體或心理“意愿”來行事的,在“真我”狀態下,至少沒有按照“他人目光”來“作秀”。而這一時期,一個人的“真我”和“假我”的多個人格出現了并存狀態。
三、社會化媒體讓個體的“多重人格”消失
以真實“關系”為基礎的社會化媒體出現后,個人的“多個人格”再度消失。因為人們必須面對極具傳播力的社會化媒體,極盡所能的將“不好的狀態”隱藏起來。人們又重新面對比真實社會“關系”更復雜的網絡,并且這種關系以真實為基礎,且影響力廣泛,個人的“個性”“言行”都要“小心行事”,以符合統一的“價值觀”和所謂的“道德標準”,而社會化媒體上的“關系”帶給個人的壓力其實要比現實社會大得多。
因此,個人的“多個人格”重新統一到“假我”的面具下。而此時,個人的真實人格的發展停滯了,或者個人對何謂其“人格”感到不確定。
四、社會化媒體上,個體人格狀態的重新統一
社會化媒體的透明、真實和公開等特點改寫了互聯網的虛擬性。每個虛擬的人不再虛擬而是真實存在,個體的“多個人格”徹底隱藏起來,所謂的“暢所欲言”其實可以說是某種“秀”,秀生活、秀幸福、秀慈善、秀各種“好”……即使秀的是“不好”的東西,也要在某個允許的范圍內(個人虛榮心、名利、社會標準、政治),要維護自身的身份和真實關系,否則就會受到“懲罰”。
社會化媒體和現實的距離越來越近。個人迫于社會化媒體透明、真實和公開的壓力,個人為了“保全自身”或“樹立良好形象”,重新壓抑“真我”人格,并極力修飾自我言行以進行“自夸”和“自我防御”。
所謂的“自夸”是指在社會化媒體上,個體隨時隨地對自我或周圍狀態的“播報”,以求引起他人的注意或贊同,達到一種“自我炫耀”和“自我表現”的心理平衡。這樣的結果是,社會化媒體上“自夸”的信息越來越多,所有的信息都有被個人包裝在“面具”下的傾向。而所謂的“自我防御”則是指,在社會化媒體上任何不謹慎的自我表現都會給自身帶來麻煩,這必然會引起人的防御心理,而防御心理又讓個人盡量隱藏不為人知的真我人格。
所以,社會化媒體上的個人以各種“真”“善”“美”的姿態出現在基于關系的圈子里,個體人格狀態被統一在某個“框架”內,這個框架是由我們的深層文化所定下的基調:我們以他人來行事,和他人統一,我們為“取悅”他人。
五、“單一”人格狀態蘊含的文化內涵
人們的“偽裝”都是為了和社會評價、他人關系、他人的看法等保持一致,因為怕被排斥在“正常的系統”之外,這個“正常的系統”正是由我們的文化來定義的,而不是由個人從自身內省的角度出發,從真正的理性出發去判斷何謂好壞是非。大家都說好,即是好的,即便自己有些不情愿。人云亦云,大家都做的就是對的,如果不跟風反而怕被孤立。個體容易被集體意識同化,個體此時的人格被統一到集體人格中,在集體中表現出無意識,個體失去了本我的價值。
所以,我們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求生存”“求發展”的,個人可以犧牲真正的自我人格發展,以求和大環境協調,表現出大眾都有的單一的人格狀態。而當社會化媒體出現后,所有的正負能量都被放大無數倍,人們受制于更強大的壓力,讓曾在網絡匿名時期短暫出現的“多個人格”現象消失了。
因此,社會化媒體出現后,其真實、透明、快捷等特點,讓人們在享受了“自夸”式的內容分享之后,又重新開始壓抑“多個人格”,帶上“假我”面具參與各種社會化媒體活動。□
參考文獻
①《人格的特征》,http://www.wqx-
lw.com/portal.php?mod=view&aid=455.
②③孫隆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26
(作者: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博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