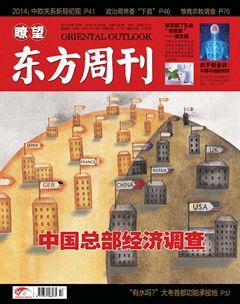讓地方百姓共享資源寶藏
陳融雪


在全世界黃土沉淀最深厚的地方,甘肅慶陽將自己定位為“新型資源型城市”。
2013年,長慶油田油氣產量超過大慶油田成為中國第一大油田。作為長慶油田的誕生地和主產區甘肅慶陽的市委書記,夏紅民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表示,慶陽不僅儲備有48億噸油氣,亦有2360億噸的煤炭資源儲備,相當于開灤煤礦的17倍、兗州煤礦的64倍、大同礦區的50倍、撫順礦區的100多倍。
隨著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的發現,以及國家關于《陜甘寧革命老區振興規劃》的出臺,被譽為“隴東糧倉”的慶陽提出,打造煤炭和油氣兩個千億元級產業鏈。
按照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董樹文2010年率院士團考察該地時的估算,慶陽已發現的資源量折現總價值為4420萬億元,260萬慶陽人,人均擁有17億元的資源價值。
外界很容易拿來與“17億元”對比的數字是,2013年,慶陽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6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僅4888元。事實上,慶陽全市八個縣區都是國家或省級貧困縣。
而這兩組看上去不那么“閃亮”的數字,還是過去一年間財政向民生大力傾斜的結果---在甘肅省內,前者增速第二,后者增速第一。
“慶陽最大的優勢是資源,最大的困難莫過于破除城鄉居民收入低的短板。”夏紅民毫不避諱。
“幾年前,我們的財政收入在省里還是墊底的。現在,財政收入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在全省第二。”他說,“是時候考慮如何讓人民更多地分享發展的紅利了。”
2014年,是52歲的夏紅民到慶陽工作的第二年,到甘肅工作的第八年。
從農業部到國家質檢總局,再從北京到甘肅,擔任甘肅省長助理6年后主政慶陽,如此履歷,使得他能以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地方發展。
“資源型城市”如何脫胎換骨
對于“資源型城市”的慣常病灶,夏紅民很清楚:一是一業獨大、一企獨大,能源產業流金淌銀,卻流不進當地百姓的飯碗;二是能源枯竭后山河破碎,生態崩潰。
在連續兩年的全國兩會上,他的議案堅持圍繞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做文章。
他提出發展交通,建議加快修建銀川到西安的鐵路以及稅收屬地化管理。這條縱貫慶陽的鐵路已經立項,“去年是希望加快前期工作,這次希望盡快開工”。
另一個重要議題,則是如何讓當地百姓分享能源寶藏的效益。
在2013年的議案中,夏紅民算了一筆賬:2012年,慶陽石化公司繳納四稅39.65億元,長慶油田2012年在慶陽境內實現所得稅約12.04億元。數字可觀,但央企不是在當地注冊且獨立核算的一級法人,地方無法得到收益。
夏紅民建議借鑒國家對內蒙古自治區的扶持政策,對在慶陽老區境內進行能源開發的中央企業分支機構實行稅收屬地化管理。
議案推進并不樂觀。“財政部的答復是,現行國家稅法規定,央企的稅收只能交到中央。內蒙古的先例暫不推廣到全國。”
他打算兩條腿走路,一邊繼續爭取政策,一邊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實現部分稅收的屬地所有化。
如果爭取到央企稅收屬地化的政策落地,他計劃將增加的財政收入更多投向民生。
“去年的統計,慶陽還有貧困人口60萬,占農業人口的26%,全市有444個村是省定的貧困村。”
夏紅民說,目前對貧困地區的投入,主要用于改善基礎設施、發展特色產業和培訓新型農民。“現在全市還有十萬戶群眾住在危房危窯中,目前國家對農村危房改造的補貼是一戶補12000元,遠遠不夠。”
把資源優勢變為富民平臺
《瞭望東方周刊》:慶陽是甘肅省唯一的革命老區。你從中央部委到甘肅再到慶陽,感受如何?
夏紅民:大家說起甘肅,印象中是飛沙走石的戈壁灘,但慶陽是黃土高原。紅色資源和民俗文化豐厚。
這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地下有石油、煤炭、天然氣;地上有黃土原面最大、黃土層最厚的世界第一大黃土原---董志塬;在陜甘交界的地方還有770萬畝子午嶺林區---這個林區所在的山脈與子午線方向一致---是黃土高原上最大的水源涵養林。
這里飄揚著中國共產黨紅色根據地的旗幟---陜甘邊革命根據地,1934年11月7日,西北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就成立在華池縣南梁鎮,第一任蘇維埃政府主席是習仲勛,那時他才21歲。劉志丹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瞭望東方周刊》:慶陽2.7萬平方公里土地,其中2萬平方公里地下有油、煤、氣,長慶油田產量已超過大慶。目前預估這些資源能用多少年?
夏紅民:確切地講,長慶油田2013年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油田,覆蓋陜甘寧晉蒙五省區,而慶陽一個市以660萬噸原油占整個長慶油田原油產量的四分之一。
慶陽油氣資源儲量是48億噸,已經探明9.8億噸。這是什么概念?長慶油田在慶陽開采了40年的油,一共采了6300萬噸。
慶陽的煤炭資源預測儲量是2360億噸,目前已經探明215億噸。這又是什么概念?一年挖出一億噸煤,可以挖200年。
“十二五”后,慶陽的原油產量將達到一千萬噸,煉化能力實現一千萬噸,煤炭生產能力實現一千萬噸。圍繞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我們規劃了兩條千億級循環經濟產業鏈。
一是石油天然氣綜合利用的千億元產業鏈,主要做開采、煉化、化工,以及化工產品的后加工。一是煤炭綜合利用的千億元產業鏈,主要做煤制氣、煤電、煤化工和冶金、材料等,發展循環經濟。
相比河南、山西和內蒙古這些傳統能源產地,我們是后發的,并且末端產品不同---比如煤炭,我們會發展煤電、煤制天然氣、煤制肥等。這兩個產業鏈建成后,將成為甘肅和整個西部的重要能源化工產地。
《瞭望東方周刊》:你在慶陽工作快兩年了,目前最關注的問題是什么?
夏紅民:慶陽的發展現狀是一方面發展迅速---GDP和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城鎮化水平低、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低是突出短板。endprint
在甘肅省內,按照GDP總量我們排第三位,按財政稅收和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我們排第二位,按傳統能源資源的保有量來說,我們排第一位。
慶陽現在財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前列,但過去曾是全省最窮的地區。隨著礦產開發和工業提速,財政領先跑起來了。但是慶陽的老百姓還很窮。我們現在有條件可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
兩個思路,一是政府花更多精力,把扶貧攻堅、改善民生作為重點---去年這方面開支占市財政支出70%以上,所以農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分別為全省第一和第二;一是把資源儲量和開發的優勢變為老百姓創業就業的平臺。
避免一業獨大、一企獨大
《瞭望東方周刊》:資源是慶陽發展的最大優勢,資源型城市如何健康發展?
夏紅民:全國資源型城市有個通病:一業獨大,一企獨大。
我們這里狹義的一業就是以石油為主的產業,一企就是中國石油---長慶油田和慶陽石化都是中石油的,中石化的華北油田稍晚一些也進入了慶陽。廣義的一業就是傳統能源資源產業,一企就是能源資源開發央企。
這些企業是高效益、低用工的現代企業,和普通老百姓關系并不大,這就造成了兩張皮---產值稅收上去了,城鄉居民的收益卻沒有同步跟上。
和前幾年比,現在我們整體的經濟實力看似大了,人民的收入卻還很低。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思考把資源儲量轉化為經濟效益,在整體經濟做強做大的同時,把富民放在突出位置,把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作為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重點。富民強市同等重要,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要把富民放在第一位。
常規做法是向企業要錢要物,要他們捐資辦學、送水、修路。作為大型能源資源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回報社會,固然是必須的,但這種做法不是長久之計,我們不能老靠企業捐款來推動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們想到,以產業融合來促進地企協調發展---企業做核心業務,而打井、修路等輔助工作,以及為油田服務的產業,能不能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來搭建民間平臺,招商引資,鼓勵當地企業和群眾創業就業。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來講,政府怎樣搭建民間平臺?效果怎樣?
夏紅民:長慶油田和慶陽石化都是中石油的一部分,開采煤炭的是華能、大唐、華電、國電等央企,這些現代企業和我們當地百姓的發展對接不緊密。于是慶陽市政府就成立了一家地方國有企業---慶陽能源化工集團。
它在能源勘探開發、能源利用開發、鉆采工程服務、機械制造維修、融資擔保等五大領域和央企對接,又對社會開放,有資金、有技術、有設備的,都歡迎入股。這五個子公司不是國有,誰力量大誰就控股。通過產業的融合發展帶動地方工業體系的建立,同時為慶陽老區群眾搭建創業就業平臺。這實際上就是在做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截至2013年底,慶陽能化集團已經吸引民間資本入股2.5億,實現工業產值6.3億元,營業收入8.6億元,上交稅收3880萬元,直接解決就業6000多人。
比較典型的是在鉆采服務方面,整合了112家民間鉆井隊,以前散兵游勇,質量、安全、效益都沒法保障,但現在都能做到了。
寧愿不要GDP也不能破壞生命之源
《瞭望東方周刊》:慶陽正在由傳統農業大市向能源大市轉型,而其所處的黃土丘陵亦是典型的生態脆弱區。慶陽的生態環境如何?
夏紅民:資源開采確實會對生態造成影響。尤其是這40多年的石油開采,先期工藝落后。以前打井是垂直井,一口井要占三四畝地,套管技術也落后,就造成了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植被的破壞---有的地方群眾門前有水不能喝,水里有油花,只能到很遠的地方挑水。有的井場附近的植被破壞了,沒法種地。這些污染很難修復,現在主要是防止發生新的破壞和遏制它的發展勢頭,并不懈地進行恢復。
《瞭望東方周刊》:你曾表示,未來慶陽的發展不會走犧牲生態和環境的老路。目前對環境的治理和修復投入如何?
夏紅民:污染治理不能完全看數字。現在一部分是當地政府投入,根據需要,財政投入一年好幾個億。另一部分是企業,誰污染,誰治理,誰影響,誰修復。以長慶油田為代表的資源開發企業在環境治理方面也盡了很大努力。
總的來說,生態治理考慮兩個層次:一是保護,把破壞降到最低;一是對已有的破壞進行修復。
首先,我們對敏感地區、脆弱地區嚴格按照國家主體功能區的規劃,對部分地區禁止開采。比如770萬畝子午嶺林區,是黃土高原的水土涵養區,堅決制止破壞和禁止開采。我們寧愿不要GDP,也不能破壞這個生命之源。
第二,創新開采技術。比如現在開采石油打的是水平井,進到油層可以水平延伸,單井覆蓋面和采油能力相當于以前的三四口井,地表占地面積也大大減少了;又如鉆井技術和井筒套管技術創新,以前的套筒容易滲漏,現在完全封閉,地下污染也減少了。
第三,所有的礦區都有嚴格管理措施和應急預案。比如在線監控,每一個輸油管道的閥門點都是計算機全程控制,任何一點滴漏都能在終控室即時反映出來。
扶貧扶出來的基層民主新機制
《瞭望東方周刊》:據悉,民主決策新機制正在慶陽農村廣泛推廣,比如鎮原縣的村民以杏核為選票,民主投選當地發展上馬的項目。請問這樣的民主實踐是如何發起并展開的?
夏紅民:這又要回到之前說的發展短腿:城鄉居民收入低,貧困人口多,貧困程度深。
從2013年開始,我們突出把扶貧攻堅當作重中之重,又發現了農村工作中的“兩張皮”現象---干部和機關花了很大的精力去給群眾辦事,但是群眾不滿意,不配合,還有意見。
這個問題怎么解決?我們采用了“參與式扶貧”的做法---把黨委政府對群眾的關心幫助與群眾的所思所想結合起來,做群眾最盼望最急需的事。
以前的做法,往往是搞建設“一刀切”---說搞水就都搞水,說搞電就一齊搞電,說修路就都修路,簡單化、主觀性地安排項目。現在我們要聽群眾的意見,點上的事就在點上解決。這才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問政于民、問計于民。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怎么做?老百姓滿意嗎?
夏紅民:開村民大會,推行“兩議一監督”---村里要做什么事,由村黨支部、村委會提議,召開村民大會決議,最后由村民監督委員會監督。
去年開大會的時候幾百口人在大太陽下曬著,老的少的都聚精會神。這是老百姓在自己做主決定自己的事情。
比如說修路,這個不是修國道省道,不存在征地問題,就要老百姓自己挪樹拆房、先整理出路基,買水泥沙石、請施工隊由政府補貼。以前同樣是為群眾修路,占地和挪樹就很麻煩,群眾講各種條件不配合。
為了做好這項工作,我們健全了組織體系,在村委會下面成立了若干農民的能力小組。
比如基礎設施能力小組,負責修路的組織監督和實施;產業發展能力小組,負責種蘋果,養牛羊;還有教育培訓能力小組、婦女工作能力小組和矛盾糾紛排查協調小組,大部分群眾都根據自己的特長進入了組織。
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對我們的工作提了更高要求。我在寧縣有個聯系村,村里的基礎設施能力小組給我寫信說:“書記你上次來,村民大會決定了修路,說是修6米寬,現在我們看這個路只有4米寬。這是不是偷工減料?”
我要縣里查怎么回事,原來規劃的標準是路基6米寬,其中的硬化路面4米 ,所以沒有錯。但這也反映了一個問題,說明我們的技術標準宣傳不到位。反過來也說明群眾的監督意識很強,監督作用發揮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