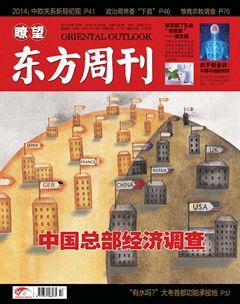幻想、墮落和野蠻
【美】菲利普·卡普托


1965年3月8日,那時的我還是一名年輕的步兵,我跟隨海軍陸戰隊遠征軍第九旅的一支營在峴港(越南港口城市)著陸,這是美國派去印度支那半島的首支分隊。
本書主要憶及了1965年至1966年間,我服役海軍陸戰隊的經歷。本書末尾附上一篇我撰寫的后記,簡要講述了美國撤離的故事。兩次事件相隔不過十年,然而美國帶著恥辱從越南撤退,想想當年入侵越南時我們的信心滿懷,比照之下,似乎隔著整整一個世紀之久。
那時的美國貌似無所不能
對于那些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尚未成年的美國人而言,那段歲月恐怕難以揣測---舉國上下都沉湎在驕傲自豪和過度自信的情緒里。我們旅的3500名士兵絕大多數出生在“二戰”期間,或是“二戰”結束不久后,他們身下刻著那個時代的烙印,那個年代到處彌漫著令人熱血沸騰的氣氛,加之年少輕狂,我們帶著滿腦子幻想來到海外。
年輕人往往對戰爭一無所知,因此便心馳神往。
“捫心自問,你能為國家做些什么?”肯尼迪向我們發出的挑戰點燃了我們內心深處到異國他鄉大干一場的理想,我們不由自主地穿上軍裝。那時的美國貌似無所不能:她仍舊可以宣揚自己屢戰屢勝。我們也堅信自己肩負使命,要將美國的政治信念傳播到世界各地。與18世紀末的法國士兵如出一轍,我們自認為在“這場必勝的戰局”中,我們絕不會是失敗者。
因此,三月潮濕的午后,我們背著行囊和步槍,行走在水稻田里,心中暗想,越共分子很快就會乖乖就擒,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是崇高善舉。行囊和步槍依舊在我們肩上。然而那種信念,不復存焉。
我們曾藐視那幫農民游擊隊,事實上,我們的敵手意志堅定、不懼死亡,死亡名單每周都在增加,鮮血淋淋令人不敢直視,有了這些發現之后,我們先前的壯志酬酬徹底崩塌。八月,曾被視為驚險刺激的遠征變成了一場讓人心力憔悴、無的放矢的消耗戰,我們不再為了心中崇高的理想而戰,只想保住性命。
曾幾何時,我希望自己不過是一次傳統戰爭的退役老兵,為了某項事業,經歷過熱血戰火和具有歷史意義的戰役,而不是翻來覆去的伏擊和交火。然而,我們沒能經歷諾曼底或葛底斯堡,沒能經歷那些史詩般的沖突,從而決定軍隊甚至國家的命運。
在一瞬間拋掉了幻想
我們的戰斗,絕大部分只是為期數周、料想之中的等待,期間還舉行莫名其妙的演練,我們穿行在熱帶叢林里和沼澤地里,練習危險的搜人行動,那里潛伏著狙擊手,不停地“襲擊”我們,還有各種惡作劇般的陷阱,要將我們一個個拿下。
我們的日子枯燥乏味,時不時會有大范圍的搜捕破壞任務,這時我們才能稍微提起精神。不過,歷經駕駛領隊直升機在某著陸區落地的狂喜之后,往往是日復一日頂著炎日行軍,靴子陷在泥土里,火辣辣的太陽恨不得燒掉我們的頭盔,在遙遠的樹林里,看不見的敵人對我們開火。
北越軍與我們為數不多的正面交火,是我們僅有的興奮時刻;不是尋常意義的那種興奮,而是近乎癲狂的與人接觸的激動之情。隱忍數周之久的緊張情緒,終于在那短短的幾分鐘內得到爆發---喪失理智的暴力,撕心裂肺的尖叫,極盡所能的辱罵。手榴彈發出陣陣爆炸聲,自動步槍快速射擊聲久久回蕩。
這種交火除了每周新添數位逝者,再沒有別的成果,軍事史上不會有記載,西點軍校學員們也不會拿來當教材。盡管如此,它們卻改變并教育了身處其中的我們;在這些漸漸被人遺忘的短暫交火之中,我們學會了有關恐懼、膽怯、勇氣、苦難、殘酷和戰友的古老教訓。最為重要的是,在一個習慣將自己視為永不隕歿的年歲里,我們認識了死亡。
曾經的幻想,最后不知去向,而對于尋常百姓,那種幻想則是在年復一年的分期付款中逐漸磨滅。我們是在一瞬間將那幻想拋諸腦后,不過數月,我們從少不經事蛻變成年,并且過早步入中年。見過了死亡,意識到凡夫俗子不可逾越的有涯命數,讓我們在青年時代便留下了不可痊愈的傷痛,就像早在娘胎,外科醫生的手術刀就劃了我們一刀。然而在當時,我們這一群人超過25歲的寥寥無幾。離開越南之時,我們一個個奇形怪狀,年輕的肩膀上,頂著一顆滄桑的腦袋。
平民世界看起來如此陌生
我本人是在1966年7月離開的。十個月之后,我完成了北卡羅來納州一支步兵訓練連指揮官的任務,這次光榮使命終于讓我從海軍陸戰隊退役,也讓我逃過了早夭在亞洲的命運。我心中慶幸,像是一個負罪累累的犯人被判了緩刑,然而不到一年,我便懷念起那次戰爭。
我所認識的其他退伍軍人也坦陳自己有相同的情結。不論怎樣,我們對越南有種古怪離奇的眷戀,更為令人詫異的是,我們甚至希望能夠重返越南。戰斗依舊在繼續,不過重返越南的渴望不是源自所謂責任、榮耀和犧牲的愛國情懷,也不是如同傳說那樣,過來人要讓年輕后輩踏上滿身創傷甚至死亡之旅。其源頭,是想看看我們的變化到底有多大,我們經歷了雨季之苦,艱苦巡邏,在炙熱的著陸地區,日夜擔心敵人來襲。
和不曾有此遭遇的人相比,我們究竟有多少不同。我們與他們鮮有共性。盡管后來我們恢復了平民身份,不過平民世界看起來如此陌生。我們不屬于這個世界,我們也不屬于那個世界,我們曾在那里戰斗,我們的戰友曾在那里犧牲。
我親歷了那時的反戰運動,我努力調和自己的反戰情緒和懷舊之感,最后卻無功而返。后來,我終于認識到,這種調和毫無可能;我無法和反戰運動的那些朋友們一樣,他們毫不妥協地反對戰爭。因為我曾參與戰爭,于我而言,戰爭不是一個抽象議題,而是切膚的情感經歷,是我人生中最不可磨滅的一筆。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緊緊包裹著我的思想、意識和情緒。
轟轟雷鳴在我耳中卻是大炮發射;雨點墜落,讓我回想起前線一個個渾身濕透的夜晚;走過樹林,我便不禁尋找警報線或警惕伏擊……我可以像那些意志最堅定的反戰人士一樣高聲抗議,可我卻無法否認戰爭曾吞噬我,那遭遇,既令人厭惡,也令人癡迷;既悲痛慘烈,也欣喜若狂;既慘不忍睹,也動人心弦。endprint
本書是想捕捉現實中模棱兩可的地帶。任何一個曾戰斗在越南的人,如果他誠實坦率,便會不由自主地承認,他樂在其中,戰爭對他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種樂趣詭異難明,因為其中混雜著相當程度的苦楚。
炮火硝煙之下,一個人離死亡越近,他的生存能力就越強,陷入恐懼驚悚極限的同時,內心的意氣風發到了極致。腦筋轉得更快,意識更為敏銳,立刻感受到陣陣愉悅癡迷。這種精神上的興奮猶如吞食了毒品。這東西也會上癮,相形之下,生活中其他東西所帶來的喜或悲不值一提。
越南戰場無疑是對一代美國士兵的嚴峻考驗,他們被聚集在這里,共同面對死亡、困境、危險和恐懼。
徹頭徹尾的殘暴野蠻
越南戰爭和美國參加的其他戰爭的區別在于---徹頭徹尾的殘暴野蠻。這種殘暴野蠻讓為數眾多的美國士兵---家住阿華州農場的善良純樸的孩子們---屠殺平民和囚犯。本書最后一章將聚焦這一問題。我的目的不是要供出如同謀殺的同犯,而是希望以我本人及其他幾人為例來說明,因其本質,戰爭能讓一個本是精神正常的人變得扭曲失常。
對諸如美萊村屠殺等殘暴事件最為常見的解讀有兩種:一種是種族主義論,即認為美國士兵覺得殺害亞洲人易如反掌,因為在他們看來,亞洲人根本算不上人類;另一種則是聲稱人生來就有暴力傾向,只要有戰爭作為借口,屠殺本性就會被暴露。
絕非是人性本惡---除非說人人心中都住著惡魔---不過當人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斗爭時,則會顯示出惡的一面。越南戰爭是兩種最苦楚戰爭的結合體---內戰和革命,另外還加之叢林作戰的兇險。早在我們到來之前,20年的恐怖主義和手足相殘,已經讓這個國家的道德圖譜沒剩下多少可值得頌揚的東西。
不論是以原則之名還是出于復仇,在越南戰場上,暴行簡直和彈殼、鐵絲網一樣,見慣不怪。我們旅的海軍陸戰隊士兵絕非生來殘酷無情,不過自抵達峴港,他們便立即認識到,在越南,一旦落入敵手,就休想被善待。得不到善待,自然也就不愿善待他人。
有些時候,戰爭唯一算是高尚情操的戰友情誼往往也是最殘酷罪行的源頭---為遇害的戰友報仇雪恨。有些戰士無法承受游擊戰的壓力:戰爭的一觸即發讓他們不得不隨時高度警惕,總覺得敵人無處不在,無法區分平民和敵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以至于哪怕是最細微的挑釁,都能讓他們喪失理智,大肆殺戮,如同一臺迫擊炮。
有些則出于對生存的極度渴望而變得冷酷無情。自保是人類本性中最根本也最強大的精神,能讓成人變得膽小怕事,但是在越南讓人在面對潛在威脅的情況下,也開始義無反顧地無情殺害。我所在排的一位中士平時和悅可親,他曾和我說:“中尉,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還在家等我,為了回去和他們團聚,我不在乎自己殺了哪些人,殺了多少人。”
威斯特摩蘭將軍(General Westmoreland)的消耗戰策略也大大影響了我們的行為。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占領地區或是守住關口,而是閉眼殺人,越多越好。像堆積木一樣堆累他們的尸體。勝利取決于尸體數量,殺敵少了就輸了,戰爭成了一道算術題。隊長面臨巨大壓力,必須上交大量的敵人尸體,他們便下令給隊員。于是乎,平民也被當作北越軍。“只要是死人,只要是越南人,那就算作北越軍。”這已經成了叢林作戰的經驗法則。所以,有些人后來藐視人命,嗜血如魔,也就不足為奇了。
美國社會的一面鏡子
最后,還有氣候特征和國家條件的因素。
我們長達數周之久留在偏遠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樣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識、望不到邊的稻田和雨林。瘧疾、黑尿熱和痢疾雖然不像以前的戰爭那般會奪人性命,仍然會傷人健康。干燥季節,烈日炙熱難耐,雨季時節,大雨不歇,我們被淋得全身麻痹。
白天,我們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軍,樹林深幽,我們不得不謹小慎微。夜晚,我們蹲坐在泥濘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螞蟥一根根拔出來,還要警惕敵人從鐵絲網那頭的暗處向我們開火。
位于西貢和峴港的指揮部吹著空調,離我們似乎有千萬里遠。我們不是平白無故稱美國為“他界”:它遙遠得猶如在另一星球。我們的周邊,沒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沒有教堂,沒有警察,沒有法律,沒有報紙,也沒有任何的監管力量,如果沒有監管,恐怕地球上的好人要減少95%。
印度支那半島的叢林似乎處在創世之初,道德倫理和地理條件都放眼荒蕪。在那里,無人監管,我們領命殺人,面對可怕的敵人,我們的人性也喪失殆盡。墮落與否只有審視一個人內心深處的道德價值網,以及所謂性格的特質。有些人沒有這張網,直線墜落,在他們的靈魂深處,潛藏著害人之心,恐怕他們自己都從未發覺。
越南戰爭的絕大多數美國士兵---至少我所認識的那些人---無法被簡單劃分為好人或壞人。他們都有著大體相當的兩種本性。我曾親眼所見,今天他們對越南人民友愛同情,第二天便一把火燒了整個村莊。他們和吉卜林(Kipling)筆下的英國大兵一樣,不是圣人,“也不是流氓,不過是與你如出一轍的兵營一分子”。這也許就是為何當美軍暴行被公之于眾時,全美社會一片嘩然,然而同時卻忽略了另一面:美國士兵不過是美國社會的一面鏡子。
我們在戰爭中失敗了,再怎么反對,那些死者也不會復活,只會令人回想起漢堡高地(Hamburger Hill)和石頭山(Rockpile)的血流成河。
也許,本書能讓下一代免遭戰火的再度浩劫。
不過,我沒信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