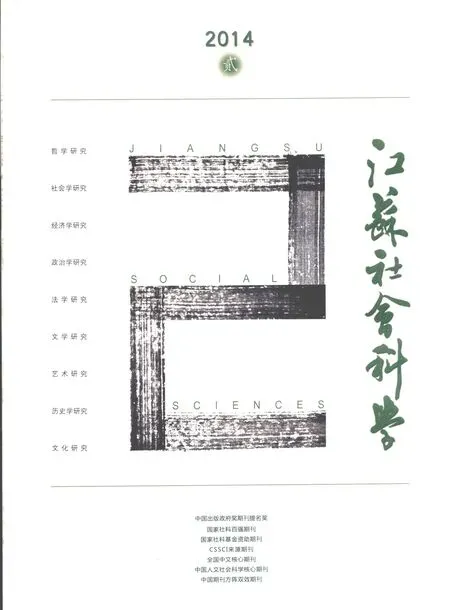界限與紛爭: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反思
——歐洲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研究
陳 軍
界限與紛爭: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反思
——歐洲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研究
陳 軍
古典與反古典、傳統與反傳統、固守與革新之類的論爭是歐洲文藝復興與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的主旋律。文類發展觀、界限觀以及等級觀是彼此具有邏輯相關性的有機統一體,大凡在發展觀或界限觀問題上的守舊派都是崇尚傳統文類的高等級地位,而革新派又多傾向于認可新型文類的高等級地位。悲喜混雜劇、喜劇的存在合法性及其等級因此獲得巨大改觀。古今論爭有助于還原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原貌,反思和沖擊其權威地位,彰顯出變化中的文類發展觀、文類界限觀以及文類等級觀等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的特征,為西方詩學的發展、突破與轉型,提供歷史契機和理論準備。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是由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向現代文類理論發展、轉型的重要序幕和必要過渡。
古今之爭 文藝復興 新古典主義 文類 悲喜混雜劇 喜劇
長達千年的中世紀像一道沉重的鐵柵,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開創的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發展戛然而止,文學及詩學蜷伏于神學的淫威之下。文藝復興像一記重錘,砸開了宗教神學的鎖鏈,拂去了古希臘古羅馬詩學經典封面上厚厚的塵埃,“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金字在久違的曙光照耀之下熠熠生輝。然而,歷史決非過往的簡單重現。具有共同理論來源且思想輪廓大體一致的文藝復興時期和新古典主義時期[1]凱瑟琳·埃弗雷特·吉爾伯特、赫爾穆特·庫恩在合著的《美學史》中點評意大利文藝復興和法國新古典主義兩時期美學發展特點時說道:“兩國批評家的思想,不僅大致輪廓是一致的,而且來源也是共同的。”(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頁)的文類理論,雖說是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重新在場,但是歷史發展規律注定了這種在場必然與紛爭、喧囂同行,而這種紛爭與喧囂,也自然構成了對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反思、檢討與解構。
一
伴隨著文藝復興時期伊始的各文類作品創作的興盛與繁榮[1]在莎士比亞著名悲劇《哈姆萊特》第二幕第二場,作者借波洛涅斯之口介紹戲伶時說道:“他們是全世界最好的伶人,無論悲劇、喜劇、歷史劇、田園劇、田園喜劇、田園史劇、歷史悲劇、歷史田園悲喜劇、場面不變的正宗戲或是擺脫拘束的新派戲,他們無不拿手;……無論在演出規律的或是自由的劇本方面,他們都是唯一的演員。”(《莎士比亞著名悲劇六種》,山東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304頁)文學創作的興盛以及古典文類法則的因素從此處不難窺見一斑。,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重新在場必然面臨一個問題:兩者之間的歷史和洽性是否仍然還存在?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對于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指導作用安在?而這些無不涉及到文類發展觀。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抑或是新古典主義時期,盡管涉及到敘事詩(史詩)、騎士文學(小說)、戲劇(悲劇、喜劇)眾多文類,但是都呈現出類似的兩種相反意見:一種傾向是認為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各項規范應當繼承并堅持,至多是作微調;一種傾向是認為古典文類理論有其現實針對性和適用性,文類理論在新時期應當發展創新、與時俱進。
文類發展觀問題表現于敘事詩(史詩)上,基拉爾底·欽提奧和明屠爾諾之間成為針鋒相對的一組論敵,引發了西方文論史上第一次“古今之爭”。針對當時意大利作家阿里奧斯陀創作的新型的傳奇體敘事詩《羅蘭的瘋狂》,欽提奧給予積極首肯,他認為包括荷馬、亞里士多德、維吉爾等人的理論和實踐都是圍繞“單一情節為綱的詩,而不是遵照歷史方式敘述的詩”,因而亞氏“對于寫這類詩的詩人所規定的一些界限并不適用于寫許多英雄的許多事跡的作品”[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頁,第186頁,第188-189頁,第189頁。。再有,今人和古人使用不同語言、不同寫作方式,各有其優秀作家和作品,故而敘事詩這種文類的規范內涵“應該遵照用我們自己語言寫作的最好的詩人所指點的路徑走,他們在我們語言里的權威也不亞于希臘拉丁詩人們在他們語言里的權威”,而不應該“受亞理斯多德和賀拉斯所定的規則約束,”它“會妨礙詩超出前人所界定的范圍,只能沿著老祖宗們所指的那條老路走”。如果這樣做,不僅是可笑的,也是“辜負自然所給的資稟”[3]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頁,第186頁,第188-189頁,第189頁。,與作家應有的判斷力和創作才能背道而馳。明屠爾諾則厚古薄今,無比堅決地抨擊了這種文類發展觀,認為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締造者享有無上的絕對權威,他們是根據“希臘人和拉丁人當中最高尚的詩人”的作品制定出敘事詩(史詩)文類規范,而當下所謂“傳奇體敘事詩的發明者卻是些野蠻人”,他們與前者的聲望可謂霄壤之別,無法做到“使我們寧可相信他們而不相信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4]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頁,第186頁,第188-189頁,第189頁。。同時,明屠爾諾又認為盡管文類眾多,但指導它們的規范與原則是唯一的,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是亞氏和賀拉斯創立的“真正的詩藝”,“真理只有一個”,“曾經有一次是真的東西在任何時代也會永遠是真的。……時代盡管推移,真理總永遠是真理。”[5]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5頁,第186頁,第188-189頁,第189頁。這就否決了文類規范內涵發展創新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這里有必要略加補充說明的是,與明屠爾諾既有聯系又相區別,同時期的意大利文學理論家斯卡利格提出一種以史詩為文類代表的、比較特別的原型規范理論,認為史詩文類的規范內涵是源頭,是原型性標準,一切其他文類的規范內涵都源于此:“各種事物都有一個美滿的原型,可以作為其余一切的模范或標準。史詩……具有其余種種詩歌的標準,所以它們可以以它為規范的原則。……引申出統轄其余各種詩的創作的普遍規律來。”[6]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頁。雖說都是肯定史詩文類規范內涵的永恒性質,但一個是強調史詩與其他文類共通的規范特征,一個則是強調史詩的文類規范特征對于其他文類的淵源角色。
文類發展觀問題表現于騎士文學(小說)上,塞萬提斯與宗教神甫教父一派也呈對立之勢。塞萬提斯創作了與傳統風格迥異的騎士小說《堂吉訶德》,這樣一本“亞里斯多德做夢也不會想到,圣巴錫耳永遠不會想到,西塞羅從來不曾聽到的”另類騎士小說,于是遭到了宗教人士的大肆抨擊,認為“和那種同時可以娛人而又可以教人的道德寓言完全兩樣”,責備其雖欲供人消遣,卻嚴重缺乏真實,充滿著“許多荒謬絕倫的東西”,“對于公眾幸福實在是有妨礙的”[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一言以蔽之,“向來制作這種書籍的人,竟置卓識與義法完全不顧的,就尤其應該受指斥”[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然而,文類規范內涵的創新帶來的客觀審美效果,也令宗教人士無法回避,在抨擊的同時也不禁贊賞其優越之處,認為在荒謬絕倫之間展露出的縱橫捭闔、天馬行空的創作自由,少去了過去創作上的幾多羈絆,有助于作者情思的充分宣發:“我剛才對于這類書籍雖然力予排斥,實在這一類書籍也不是沒有好處,好處就在于它們供給作者一片豐富的園地,可以盡量發揮他們的才情;……這種作品的自由,對于無論何種體裁的作者實都有利”;更是不免惋惜地抱怨說,如果這些“荒謬絕倫的東西”的發明者稍稍注意學習和利用傳統騎士文學的“義法”,“那么他們在散文上的成就,就可以做得詩歌上希臘羅馬二王的勁敵了。”[3]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幾乎要把新型騎士文學的作者抬高到荷馬和維吉爾的高度了。
當然,此段時期文類發展觀問題的探討熱點尚不止上述二者,還有悲劇與喜劇兩大文類。包括上文提到的欽提奧、塞萬提斯以及維伽、錫德尼、高乃依、圣·艾弗蒙、莫里哀、德萊登、布瓦洛等一批人都投身到了關于戲劇文類發展問題的論爭之中。其中如欽提奧、維伽、高乃依、莫里哀等人的《狄多》、《熙德》、《太太學堂》、《達爾蒂夫》諸作更是置身論爭的漩渦中心。對于加諸其上的非難與攻擊的駁斥,為闡述文類發展觀提供了歷史契機。為論說之便,我們不妨引用一段欽提奧記錄的當時一些人對于其悲劇《狄多》的種種非難:
現在,我要談談對我這作品的種種非難。第一點是:如果我寫這悲劇是用散文而不是用詩體,那會更好些。第二點是:亞里士多德反對在悲劇中使用神明。第三點是:把適合于悲劇舞臺的劇本分成幾幕幾場是欠妥的,因為古希臘作家從未這樣做過,而戲劇創作的法則和正確規律應該取自希臘人,亞里士多德就曾美滿地作出這些規律。第四點是:非難者不贊成使用許多個劇中人。第五點是:人物談及自己的話有失體統。第六點是:我在《狄多》中沒有寫出《俄狄浦斯王》那樣的形象,而亞里士多德就是從該劇取出誡條,視若完美悲劇的金科玉律的。第七點是:《狄多》太長了,不適宜于上演。[4]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
從其中“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這些高頻出現的字不難看出,在戲劇文類的發展觀問題上,一派傾向于認為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具有永恒價值,不可隨意僭越,否則就要受到批評。例如,在宗教人士眼中,嚴格按照古典主義文類規范創作的作品屬于正經戲,而把那些肆意違反所謂“三一律”的劇作稱為“荒謬絕倫的東西”,“深惡而痛絕”!把后者與“荒唐”、“愚昧”、“野蠻”[5]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相連。最為典型的例子莫過于莫里哀。由于其將喜劇主要表現對象由下層低賤之人改變為社會上有頭有面的所謂“正人君子”,違反了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規范要求,就像其本人所說的“本喜劇,大家議論紛紜,它長期受到冷遇;它所嘲笑的那些人已經肯定地表明他們比起我們以前觸動的任何人在法國更有勢力”[6]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頁。;“精通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的那些人,一下子就看出這出喜劇違反藝術的全部法則。”[7]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因此遭到了惡意攻擊,諸如“從來沒有看過再壞的東西”、“沒有價值”、“充滿色情”、“豈有此理的戲”、“沒有一個地方不糟糕”、“傷風敗俗”、“這是法蘭西的恥辱”[8]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08-209頁,第211頁,第210-211頁,第45頁,第212、213、214頁,第286頁,第275、276、278、281、283頁。等等,甚至被禁演。其他如德萊登、布瓦洛、錫德尼等人也從不同角度主張要恪守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及其規范,宣揚一種靜止不變的文類發展觀。
與之相反,另一派則認為,無論從作品形式、內容,還是從審美接受效果來說,文類的規范內涵都注定與世相推移、由人而創新。例如,欽提奧在列舉了對他作品的種種非難之后,逐一進行了反駁。認為任何文類作品的創作都要“合乎詩人寫作的時代的要求”、“符合我們這時代的慣例”,所以“離開亞里士多德所訂立的清規戒律”亦屬正常,如果處理得當且審美效果出色,采用眾多人數、杜撰悲劇情節以及采取雙線情節安排等與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相悖、“所持的見解與亞里士多德的不相同”的做法都是值得大力肯定的,而且他還從辯駁策略上指出,“我所以這樣做也是依照古人的先例的,因為誰都知道,歐里庇得斯的悲劇開場就不像索福克勒斯的一樣,而且,我曾說過,羅馬作家布局的方法也是不同于希臘作家的。”[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51、54頁,第254、264、259、254、257、265-266頁,第271、273頁。這就從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內部實施了釜底抽薪式消解。又如維伽在總結整理本國喜劇創作原理時,也旨在彰明文類規范內涵的發展本性,他指出,盡管“西班牙所編寫的喜劇全都違反藝術”[2]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第83頁,第84頁,第87-88頁。,盡管喜劇把帝王納入題材范圍,盡管喜劇沒有把事情限于一天之內,盡管西班牙喜劇“并不是按照世界上最初發明喜劇的人所相信的作法,而是按照許多蠻漢所用的方法”[3]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第83頁,第84頁,第87-88頁。,“冒犯”了亞里士多德“他老人家”[4]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第83頁,第84頁,第87-88頁。,但是它們得到了觀眾的擁護和喜愛,并自信把自己的寫作要求和原則譽為“從古代的藝術里得不到的”“至理名言”[5]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第83頁,第84頁,第87-88頁。!高乃依為了回應法蘭西學院和教會人士對于其劇作違反古典主義文類規范以及“三一律”要求,他立足當時社會發展現實,質疑了戲劇表現對象范圍以及“三一律”原則等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當下合法性,例如他提出:“亞里斯多德規定喜劇只是摹擬低下而狡猾的人物。我不能不說,這個定義并不令我滿意”;它只適合和屬于亞氏所在的時代,“對我們的時代說來,這個定義便不完全正確了”;“關于地點的一致,我從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的言論中沒有發現任何指示”;以及“我懷疑在適合亞里斯多德所舉出的各種條件的悲劇里也可能實現這種情欲的凈化”。所以他認為,我們“不必再踏古希臘人的足跡”,雖然古代悲劇只描寫少數家族的命運,但是“在以后的若干世紀中,我們得到的充分材料足以超越這種范圍”,“在戲劇中也沒有必要只表現國王一類人的災難,其他階層的人的不幸也能在舞臺上找到它應有的地位,只要它們是很有意義的、很不尋常的”。文類的規范內涵應該是發展變化的,文類的規范內涵在不同時代應當得到豐富和完善,他說:“我不善于在新的要求下更好地適應古代的規則,我不懷疑找到新的方法;只要他們經過實踐的考驗而獲得成功的,例如在我的作品中所采用的那些得到成功的方法,我便決定遵循它們。”[6]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51、54頁,第254、264、259、254、257、265-266頁,第271、273頁。實踐永遠是檢驗理論效用性的唯一標準,機械、固執地囿于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使之教條化,只能窒息文類鮮活的生命力,只能阻礙文學史健康發展的步伐。這一點在圣·艾弗蒙那里得到了充分論說:“我們既不過分推崇古人,也不過分歧視當代,因而我們也不會再以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得斯的悲劇作為當代戲劇創作的唯一典范了。”“想永遠用一些老規矩來衡量新作品,那是很可笑的。”自信通過新時代作家的努力,一定能夠創作出無愧于現時代的偉大作品[7]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51、54頁,第254、264、259、254、257、265-266頁,第271、273頁。!
綜上可見,自進入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發展觀的討論通過敘事詩(史詩)、騎士文學(小說)、戲劇等文類的創作是否應當遵奉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金科玉律而全面展開。論爭陣營分為明顯的守舊和革新的對立兩派,兩者勢均力敵,古典主義文類理論顯現出較為強勁的歷史勢能。然而,終因守舊派有違歷史發展規律,從而在其立論和論說上不免留下明顯的硬傷。例如號稱“巴那斯的立法者”(圣勃夫語)的布瓦洛在恪守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永恒性的同時又認為這種永恒性并非不可打破:“一個雄健的詩才,/當他逸興遄飛時是怎樣激昂慷慨,/藝術的束縛過嚴,便打破清規戒律,/從藝術本身學到放開無束無拘”[8]布瓦洛:《詩的藝術》(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頁。,認為只有靈感狀態中的天才方才是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克星,在其欲抬高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初衷之余,孰料又不免矮化了自身所處的時代。而且,在其反駁貝洛勒反崇古的信中這樣說道:“您那樣大聲叫喊反對古代作家,究竟有什么動機嗎?你是害怕人們摹仿他們就會壞事嗎?但是事實相反,我們法國最大的作家們的作品的成功正要歸于這種摹仿,您能否認嗎?高乃依從哪里得來他的最美的筆調和最偉大的思想去創造亞里斯多德所不知道的新型悲劇?……在這些劇本里,他越出了亞里斯多德的一些規則。”[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以高乃依創作出違反亞氏文類規則的新型悲劇為例駁斥貝洛勒的目的是達到了,但是“新型”、“越出”等字眼又再一次擊碎了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永恒性的神話。另外,守舊派據以反對文類發展觀的所謂“三一律”在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中并無確切來源,恰如高乃依所論那樣:“關于地點的一致,我從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的言論中沒有發現任何指示”,這又是對于守舊派立場的致命一擊!再有就是,按照既有的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來創作的作品的不良審美效果,也從客觀上駁斥了守舊派立場的科學性。例如宗教人士不得不承認:“那種正正經經的,按照著藝術法則來編劇情的,那就只有十幾個卓識者會加賞識,其余的人都覺得莫名其妙,看不出那種編法的所以然來了。”[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文學作品的生命和價值在于審美效果的實現和傳達,一旦在作品和接受之間出現裂痕和絕緣,文學的存在也就成了問題,更遑論文類規則之有無了!所以還是莫里哀一語中的:“就我來說,我看戲只看它感動不感動我;只要我看戲看的開心,我就不問我是不是錯,也不問亞里斯多德的法則是不是禁止我笑。”[3]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所有這些就注定了守舊派必將處于論爭的下風。當然,在巨大的歷史傳統面前,主張文類規范內涵是發展的革新派也表露出些許溫和、軟弱的一面,例如,欽提奧屢次在自己立論時夾注“要常常記住,應該給亞里士多德以應有的尊重”之類的話語,甚至為了突出對于亞氏的尊重而讓觀點自我抵牾:一方面認為亞氏反對的雙線結構的悲劇,因其有快樂的收場,“本質上更能取悅觀眾”;一方面又認為自身寫作此類快樂收場的悲劇“不過是對觀眾的讓步,為了使這幾出戲在舞臺上更動人”,“與其以更壯麗的戲使觀眾不快,不如以稍差些的戲使觀眾滿足”[4]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56頁,第84頁。。既抑又揚,難求一致。又比如高乃依,一邊高舉“不必再踏古希臘人的足跡”的創新大旗,一邊又提出極富個性色彩的“容納”說,即“我們仍然可以容納亞里斯多德的見解”[5]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諸如此類,都反映出革新派在面對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傳統時態度尚不夠毅然決然,而這也是歷史必然烙在處于新舊社會轉型期的革新派身上的印跡。
二
這兩個時期另一大理論焦點則是關乎文類之間的界限問題。文類之間有無界限、界限能否逾越,又成為判定守舊派或革新派的標準之一。守舊派奉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為圭臬,強調文類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但丁從內容和語言兩個層面指出了喜劇和悲劇兩者的差異:喜劇在“內容上和悲劇不同,因為悲劇在開始時優美靜穆,而結果或煞尾則丑惡可怖,……而喜劇雖則在開頭有不愉快的糾結,但收場總是皆大歡喜,……悲劇和喜劇在語言上也各不相同,悲劇語言崇高雄偉,喜劇語言松弛卑微”[6]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又如布瓦洛提出“詩體各以其所美,來顯出它的漂亮”,故而循環歌、迭韻律詩、風趣詩、諷刺詩等文類之間各各不同;又從虛構與真實的角度,認為小說“不過供人瀏覽,用虛構使人消遣”,而“戲劇則要與精確的理性相合”,受所謂“三一律”的規約;反對田園詩與史詩的混合,即:“在一首田園詩中卻奏起鐃歌鼓吹。/直嚇得潘神聞聲逃匿到荻蘆深處”[7]布瓦洛:《詩的藝術》(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8、18頁。。
另一方面,瓜里尼、維伽、錫德尼等人則主張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中規定的悲劇和喜劇之間的界限不是不可逾越的,集中體現在對悲喜混雜劇的高度肯定上。例如,維伽在認可悲劇和喜劇存在表現對象貴賤之別的情況下,又提出寫作喜劇時,“如果有關帝王,不必顧慮”[8]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54、55-56頁,第84頁。。悲劇和喜劇的混合,雖然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個人身牛首的怪物”[9]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305-306頁,第212頁,第287頁,第259頁,第160頁,第220頁。,但是這種混合產生的多樣化因為可以引起大量的愉快而讓悲喜混雜劇顯得獨具魅力[1]關于維伽涉及此觀點的一段話,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收錄的譯文為:“把時間限于一天雖然是亞里斯多德的意見,但是這樣做是無益的;不過,我們如把悲劇體裁和卑賤的喜劇混合起來,則是對他的失敬。”(221頁)而周靖波主編《西方劇論選》(上)中的譯文為:“不必理會亞理斯多德的主張,把事情限于一天之內,因為我們如果把悲劇的語言摻和在格調卑下的喜劇里,我們早已冒犯了他老人家。”(84頁)第一個譯文里,維伽否定了亞氏的時間整一律,而肯定了亞氏的文類界限觀,反對悲喜混雜劇。第二個譯文里,維伽對于亞氏的時間整一律和文類界限觀都是持否定意見的。綜合維伽全文主旨,若按第一個譯文的意思,維伽的文類界限觀會明顯自相矛盾;第二個譯文意思和核心主旨一致,當為正譯。。錫德尼也認可悲喜混雜劇存在的合法性,他認為:“有的詩是結合了兩三種類別的——如悲劇和喜劇,而由此產生悲喜劇;……有的結合了歌頌體和田園體;但在這一點上那是全部一樣的,如果分了開來是好的,合了起來也不會壞。”[2]錫德尼:《為詩辯護》,《為詩辯護·試論獨創性作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第58頁。維伽的肯定是著眼混雜以后的審美效果,而錫德尼則是基于局部與整體的構成關系。在這方面,最典型的是瓜里尼的論述。他為了回應一些人對其悲喜混雜劇《牧羊人裴多》的批評,專門發表《悲喜混雜劇體詩的綱領》一文來正名。為了回答“是否因為不同種,就不能結合在一起來產生第三種詩”,他首先從自然和社會現實層面論證了不同文類混雜的可能性。他舉馬和驢雜交產生騾、黃銅和錫熔成青銅等為例說明混雜已有大自然的先例;又取亞里士多德之矛攻其盾,說亞氏曾經認為作為對立的寡頭政體和大眾政體,能夠混合成為共和政體,那么,“悲劇是偉大人物的寫照,喜劇是卑賤人物的寫照”,“既然政治可以讓這兩個階層的人混合在一起,為什么詩藝就不可以這樣做呢?”這就又為混雜找到了社會的范型。接著,他從藝術審美領域再次確證了悲喜混雜劇產生的理論依據。按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規范來說,悲劇或喜劇比較單純,審美效果各有弊端,即或是“拿流血死亡之類兇殘的可怕的無人性的場面來使我們感到苦痛”,或是“使我們在笑謔中放肆到失去一個有教養的人所應有的謙恭和禮儀”。而悲喜混雜劇的產生則巧妙地規避了這樣的不足,“它是悲劇的和喜劇的兩種快感揉合在一起,不至于使聽眾落入過分的悲劇的憂傷和過分的喜劇的放肆。這就產生一種形式和結構都頂好的詩”。正因為此,他進一步強調指出,“其它種類的戲劇就真不必上演,因為悲喜混雜劇可以兼包一切劇體詩的優點而拋棄它們的缺點;它可以投合各種性情,各種年齡,各種興趣,這不是單純的悲劇或喜劇所能做到的。”[3]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96-198頁。在瓜里尼眼中,悲喜混雜劇的誕生不僅可能,而且必要。當然,我們又必須得承認的是,它既昭示我們文類應該是發展變化的,又同時以悲喜混雜劇的誕生宣告了傳統戲劇文類發展的終結。
需要注意的是,錫德尼另外還提出,悲劇、喜劇打破界限的混雜,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為了混雜而混雜,而是出于內容的切實需要,因此必須杜絕和預防“偽悲喜混雜劇”。他說,“偽悲喜混雜劇”表面上也是混合著帝王和小丑這些貴賤之人,但是這種混合不是出于自然或必然,“而是硬拉著那小丑的肩頭推他進去在莊嚴的事情里擔當任務,所以結果是既不莊重,又不恰當”,所以就難以收到理想的審美效果,其原因在于“由于我們悲劇中的喜劇成分并沒有真正的喜劇,我們就只有不適合純潔耳朵的下流話或者一些愚蠢的極端表現;它們只會引起高聲哄笑,此外什么都引不起。”[4]錫德尼:《為詩辯護》,《為詩辯護·試論獨創性作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第58頁。這也恰如反對文類混雜的布瓦洛所說:“喜劇的任務也不是跑到街口/運用下流的詞句博取公庶的歡呼。”[5]布瓦洛:《詩的藝術》(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頁。這實質是在啟發我們思考作為悲劇和喜劇兩大文類的核心審美特質為何,促使我們找尋悲喜混雜劇的真正審美價值何在。簡言之,喜劇決非等同于插諢打科的簡單語言層面,悲劇與喜劇的混雜,其真正目的在于:悲劇濟以喜劇,是拓展悲劇性的廣度;而喜劇濟以悲劇,是增添喜劇性的深度。
在小學的教育階段,一個有趣的教學環境是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的。因為通過我國教育專家的研究,發現在小學階段的孩子還處于幼稚的狀態,身心發展以及心理認知都還不夠成熟,所以對于新奇的事物比較有好奇心,對于有趣的事情也是沒有抵抗力。所以針對小學生的這一發展特點,數學老師就可以創設一個有趣的教學環境,讓學生不僅可以釋放自己的天性,促進學生的發展,而且還可以很好的提高學生的學習數學的興趣,有利于小學數學高效課堂的構建。
從某種角度而言,文類界限觀也是文類發展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肯定悲喜混雜劇的合法性,就是對悲劇、喜劇兩文類自身歷史規定性的突破,就是堅持了文類的發展本性。文類之間的混雜、界限的突破,不過是文類發展觀討論的一種特殊情形而已。另外,表現對象之高下作為當初亞氏《詩學》中區分悲劇和喜劇的重要尺度之一,在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恰恰又成為解構兩者界限的主要工具和路徑。最后,瓜里尼等人的事例還表明,在反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傳統的思維特征上,他們還深受柏拉圖文類思想中“正—反—合”辯證思維的影響;自然科學的發展也為革新派提供了有益而及時的論說材料。
三
不管是文類發展觀的討論,還是文類界限觀的爭辯,結果都要落實到不同文類及其作品之上,而對它們的評價自然會與特定的發展觀或界限觀密不可分,這里就會涉及到文類等級的問題。與發展觀、界限觀相一致,凡是守舊派無一不是崇尚過去類型作品或文類的高等級地位,而凡是革新派又基本多傾向于認可新型文類的高等級地位。例如守舊派方面,明屠爾諾抬高傳統史詩的地位,認為與之相連的都是“最高尚的詩人”、“最優秀的作家”,而對新型文類的傳奇體敘事詩,認為它的發明者只有天賦而不遵守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法則,故“決不能寫出完美的作品”[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8-189頁,第261頁,第163、171-172、174頁。。宗教人士對于新型騎士文學也是如此態度,謂之荒謬絕倫而有礙讀者幸福。而守舊派人士對于莫里哀、欽提奧、瓜里尼等人作品的惡意攻擊則更不用贅述了。而與此同時,革新派則通過肯定新型文類的優越性來抬高其等級。欽提奧就認為傳奇體敘事詩因為情節頭緒多,所以比之傳統史詩會更增加讀者的快感;盡管亞氏貶低雙線結構的快樂結局的悲劇,但是欽提奧卻認為這種悲劇類型更能取悅觀眾。又如高乃依把飽受批評的己作《熙德》視為悲劇完美性原則的典型體現,他說:“我們要確立一種原則,即悲劇的完美性在于以一個主要人物為手段引起憐憫和恐懼之情,例如《熙德》。”[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8-189頁,第261頁,第163、171-172、174頁。而如瓜里尼則更是對悲喜混雜劇這種新型文類贊譽備至,竟然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在西方文論史上,恐怕這是推翻悲劇作為等級之王的第一人。可見,不論是單一文類的規范內涵上的求新,還是文類界限之間的消弭,他們都是欲借文類等級的渠道,爭取自身的身份認同。
不過,在文類等級問題上,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圍繞著悲劇和喜劇的討論或許更值得關注。在悲劇的等級問題上,可以但丁為代表。關于悲劇文類的高等級問題,并非新見,從柏拉圖到亞里士多德的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中早已有充分的論說。然而但丁之新在于,其單單是從語言層面來解釋和說明悲劇是“最高貴詩歌”的。但丁首先提出,文學語言是人為的語言,與之相對的俗語則是自然的語言,是“我們真正的元初的言語”,是“我們摹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規則就學到的那種言語”。文學語言由俗語之中派生而出,“這兩種言語之中俗語是較高貴的”,為此但丁還專門從“光輝的”、“基本的”、“宮廷的”、“法庭的”這四大特征予以了論證。其次,但丁指出,因為俗語是高貴的最好的語言,所以最好的思想要以最好的語言表現,最好的語言只適合于有知識、有天才的人。那么,最好的思想、最好的主題包括哪些呢?但丁認為“安全,愛情和美德看來是應該用最好的方式加以處理的重大主題”。最后,由于“我們稱之為悲劇的詩體是最高貴的詩體”,“悲劇帶來較高雅的風格,喜劇帶來較低下的風格”,而當“詩行的莊嚴、結構的高貴、文字的優美與題材的重量配合一致時,我們就使用悲劇體”[3]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188-189頁,第261頁,第163、171-172、174頁。,因此,最好的俗語,安全、愛情和美德等最好的主題,最高貴的文類悲劇,三者之間就自然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協調。在但丁的悲劇等級觀里,悲劇等級之高通過最好的主題為媒介而與最好的語言形式俗語緊緊相連。
我們知道,在亞氏《詩學》專章談論悲劇高于史詩時,只是從審美方式和情節特點入手,并未涉及語言層面;但是,亞氏對于悲劇文類的語言形式轉向并非是毫無意識。他在《修辭學》一書中認為:
甚至到現在,大多數無知的人,還認為詩人的語言是最為優美的語言。這是不真實的。散文的語言就不同于詩的語言。這一點,可以用今天的事實來證明。悲劇的語言已經在性質上有了改變。代替四音步,悲劇采用了抑揚格,這就因為抑揚格和散文最為接近。同時,悲劇也已經拋棄了各種不適宜于日常談話的語言。這些語言,曾經在早期被戲劇用作裝飾,現在也仍然為六音步的詩所采用。[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頁,第224頁,第219頁。
還可以借引《詩學》中的一段話作進一步說明:
……悲劇拋棄了雙四音步長短格而采取短長格。他們起初是采用四雙音步長短格,是因為那種詩體跟薩堤洛斯劇相似,并且和舞蹈更容易配合;但加進了對話之后,悲劇的性質就發現了適當的格律;因為在各種格律里,短長格最合乎談話的腔調,證據是我們互相談話時就多半用短長格的調子;我們很少用六音步格,除非拋棄了說話的腔調。[2]亞理斯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頁,第5頁,第65、67頁,第141-142頁。
然而,時過境遷,到了古羅馬時期,修辭學成為當時最為完備的人文學科,修辭學的傳授也成為最受人尊敬的職業[5]沃拉德斯拉維·塔塔科維茲:《中世紀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0頁,第111頁。,如此時代風氣使得古羅馬時期文類研究的形式化傾向異常突出。例如,賀拉斯就說過:“如果我不會遵守、如果我不懂得這些規定得清清楚楚的、形式不同的、色調不同的詩格,那么人們為什么還稱我為詩人呢?……喜劇的主題決不能用悲劇的詩行來表達;同樣,堤厄斯忒斯的筵席也不能用日常的適合于喜劇的詩格來敘述。”[6]亞理斯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5頁,第5頁,第65、67頁,第141-142頁。此時,詩格的作用已經與亞氏時期極為不同,上升為文學與非文學相區分的重要標志物,同時也構成悲劇和喜劇兩大文類界限的清晰顯示。朗吉努斯也持相近觀點,認為:“如果有哪位敢用美好莊嚴的詞匯來描述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好像給天真無邪的小孩帶上了巨大的悲劇面罩。”[7]朗吉努斯、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美學三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頁。“美好莊嚴的詞匯”似乎成為了“悲劇”的別稱。這種形式主義的傾向就是到了中世紀仍有余響,例如有神學家(如依西多爾)說:“某些人有種錯誤的興趣,喜歡傾聽智者的演講——不是為尋求真理,而是為欣賞演講技巧。他們就像詩人,關心詞語的排列更甚于真理。”[8]沃拉德斯拉維·塔塔科維茲:《中世紀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0頁,第111頁。認為詩人的工作重心只是詞語排列這樣的形式方面。總之,從亞里士多德對于悲劇語言形式變化的明確意識,到古羅馬變本加厲的文類研究的形式化傾向,為但丁將最高等級的悲劇文類與最好的語言形式俗語相關聯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源泉。
眾所周知,喜劇的等級在古典主義文類理論中不太樂觀,無法與悲劇、史詩相提并論。但是在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應守舊派與革新派之間論爭之需,喜劇的等級開始發生轉變,甚至是逆轉。可以維伽、錫德尼、莫里哀等人為代表。例如,維伽從審美效果的角度,認為自己創作的新型喜劇“如果用別的方式寫也許好些,不過它們不會這樣受到人們的歡迎;因為與合法的東西相反的東西,往往就為了這個相反,才能夠使人們的審美愛好得到滿足”[9]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頁,第224頁,第219頁。。如果這還只算是新型喜劇勝過古典喜劇的話,那么他在喜劇和歷史關系的論說中透露出的抬高喜劇等級的意識就相對比較明晰了:雖然“悲劇以歷史作為它的主題,喜劇則用虛構”,但是古羅馬著名的西塞羅曾經把喜劇稱為“風俗的鏡子,真理的活生生的形象”,這樣一來,虛構的喜劇“甚至可以和歷史并駕齊驅了”[10]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頁,第224頁,第219頁。。喜劇不僅僅是嬉笑怒罵的娛樂,而是和歷史一樣,具有別樣的認識和教育功能。這種把喜劇和歷史相提并論的做法無疑是拉近、縮小了喜劇和悲劇的等級懸殊。要說對喜劇文類的等級最為推舉的,莫過于莫里哀了。他堅決否認“全部才情和全部美麗只在正經詩里頭,滑稽戲是胡鬧東西,一點也不值得贊揚”的俗見,提出喜劇的創作難度勝于悲劇,喜劇不比悲劇等級低的觀點,他說:“發一通高貴感情,寫詩斥責惡運,抱怨宿命,咒罵國王神祗,比起恰如其分地表現人的滑稽言行,在戲臺子上輕松愉快地搬演每一個人的缺點,我覺得要容易多了。”“在正經戲里面,想避免指摘,只要話寫的美,合情合理就行;但是臨到滑稽戲,這就不夠了,還得詼諧;希望正人君子發笑,事件并不簡單啊。”同時針對“喜劇越好,為害越大”的攻擊與批評,莫里哀從人情需要的高度再次突出強調了喜劇的審美價值和等級位置:“事實上,假定虔誠的活動允許有間歇,人類也需要有娛樂,那我卻堅持說,人們怎么樣也找不到比喜劇更純正的東西。”[1]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83-284、108-109頁,第224頁。奉喜劇為世界上最純正之物,莫里哀成為西方文論史中從等級階梯上取消悲劇至高地位的第二個“瓜里尼”。
四
我們注意到,錫德尼、明屠爾諾等人還論及到文類劃分問題,布瓦洛還主張文類偏長的天賦說等等。這些觀點或承襲舊說,或無大的歷史影響和理論價值,一概從略。綜上三個方面的論述,我們以為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文類發展觀、界限觀以及等級觀其實是彼此具有邏輯相關性的有機統一體。文類發展本性的確認,為界限的破除提供理論支持,文類界限觀也可謂文類發展觀探討的一個延伸;而文類等級觀則可從對于文類發展和界限逾越的結果的評價來為它們提供實踐上的論證。也因此,大凡守舊派都固守文類永恒不變的本性,反對文類界限的抹除,自然也就對新型文類極力貶低和抵觸;而革新派則完全與之相反,大力倡導文類本質與時俱進,高度認同文類界限的混合,對新型文類的發明與創生推崇備至。上述三個大的方面在本質上都與古今觀兩相應和,互為表里。
二是古典與反古典、傳統與反傳統、固守與革新之類的論爭是文藝復興與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的主旋律、主色調,一切文類問題的討論無不入此環中。其緣由至少有四個方面:首先,各種文類的作品數量大增,客觀上帶來關注和研討各種文類寫作規范和法則的必要性。且不論上面提及的一批作品,例如維伽一人就聲稱“我已經寫了四百八十三本喜劇,……在這些劇本中,除掉六個以外,全是嚴重地犯了反對藝術之罪的”[2]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283-284、108-109頁,第224頁。,新型文類作品創作的繁盛,無疑要觸及它們的寫作規范及其與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傳統的關系等問題。其次,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學習借鑒以及闡釋之風為論爭的開展準備了理論參照和標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進入文藝復興時期,亞里士多德和賀拉斯的名字就頻繁地出現于當時的詩學著作之中,尤其是對于突然出現的亞氏《詩學》[3]亞氏《詩學》在古代就已被人遺忘,在中世紀是鮮為人知,直到文藝復興時期,G.瓦拉于1498年完成譯本后,才成為美學上通行而又有影響的一部論著。詳可參見沃拉德斯拉維·塔塔科維茲著《中世紀美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頁。的闡釋和模仿之風盛行,紛紛以亞氏和賀拉斯詩學思想為指導,重申和確立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權威地位。例如意大利文學批評家卡斯特爾維屈羅用意大利文翻譯了亞氏《詩學》,意大利文學家和批評家保羅·伯尼注釋出版亞氏《詩學》,其他諸如斯卡利格《詩學》、特里西諾《詩學》、明圖爾諾《詩的藝術》、布瓦洛《詩的藝術》等承襲亞氏和賀拉斯著作之名及其詩學思想的著作如雨后春筍般應時而生,聲勢浩大,蔚為壯觀!再次,古羅馬和中世紀詩學理論對于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時期文類理論特征形成所起的推波助瀾之力不容小覷。例如賀拉斯比亞里士多德更為曉白和直接地指出“每種體裁都應該遵守規定的用處”[4]亞理斯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42頁。,對文類界限的立場旗幟鮮明;而且在其《詩藝》開頭有這么一段話:
如果畫家作了這樣一幅畫像:上面是個美女的頭,長在馬頸上,四肢是由各種動物的肢體拼湊起來的,四肢上又復蓋著各色羽毛,下面長著一條又黑又丑的魚尾巴,朋友們,如果你們有緣看見這幅圖畫,能不捧腹大笑么?……我知道,我們詩人要求有這種權利,同時也給予別人這種權利,但是不能因此就允許把野性的和馴服的結合起來,把蟒蛇和飛鳥、羔羊和猛虎,交配在一起。[1]亞理斯多德、賀拉斯:《詩學·詩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37頁。表面是反對繪畫中不同類別物體的拼湊,若置于文類理論的知識背景中察看,其實是為否定文學作品創作中混合各種文類的做法所作的鋪墊。賀拉斯不僅僅是繼承了亞氏文類界限的觀點,而且是大為強化了文類界限觀。中世紀則通過對藝術法則的崇拜來間接宣揚文類永恒不變的發展觀。那些宗教神學家們認為“藝術具有不易的法則,它決非由人所創立”,“背離了它,就不可能產生任何適當的作品。”[2]沃拉德斯拉維·塔塔科維茲:《中世紀美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112頁。“藝術”一詞在當時就近同法則、規范之意,當藝術與法則、規則、規范緊緊相連時,恰恰與創造愈相背離。最后,文藝復興伊始的科學進步也為論爭的革新派開拓了研究視野,接受了理論指導。如果說守舊派是以機械而僵硬的藝術法則與鮮活且靈動的自然稟賦、審美經驗相對立,企圖以前者壓倒后者;那么,文藝復興時期則是以天文學、醫學為突破口,隨著科學開始消解中世紀神學世界的堅定步伐,引導民眾向豐富復雜的現實客觀世界呼吸自由新鮮之空氣,形成了一套觀察、實驗、思考的方法,吁求以客觀自然的實踐經驗代替而今已遠去的權威或法則。例如達·芬奇就曾抱怨說:“我們能完全信賴古人嗎?”“有些人自以為有充分理由責難我,他們斷言我的觀點與某些受人尊敬的人士的權威見解相反,而這些見解是脫離實際經驗的。他們未曾想到,我的作品正是出自于簡明易懂的經驗,出自于真正的權威。”[3]艾瑪·阿·里斯特編著:《達·芬奇筆記》,〔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1-2頁。復興的歷史語境決定了科學與文學一樣,同樣也面臨古今之爭的命題。倡導經驗是真正的權威,不可亦步亦趨地盲目尾隨古人,這樣的古今理念對于文學論爭中的革新派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三是我們要全面而辯證地評價歷史發展規律推動下古今文類理論之爭在西方文類理論發展史上的作用。首先,通過古今論爭有助于還原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原貌,幫助人們認清何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自身的理論遺產,何為后人的主觀臆斷、誤解強加。其次,通過古今論爭反思和沖擊了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永恒的權威地位,彰顯出發展的文類本性、可以逾越的文類界限觀以及變動不居的文類等級觀等新時期的文類理論特征。最后,通過古今論爭對于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檢討與解構的企圖,為西方詩學的發展、突破與轉型,提供了歷史契機和理論準備。因為一旦對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實現了解構,就勢必有重新創造之必要;而創造不僅意味著“破”的勇氣,更是暗含著“立”的膽識與自信。這種膽識與自信源自對于古典和自我的科學、客觀的認識和啟蒙,源自別具一格的個性與天才,源自對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是由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向現代文類理論發展、轉型的重要序幕和必要過渡。或許正是由于此歷史定位所限,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文類理論在論爭中不免顯得除舊有余而新立不足,命題還是原來的命題,眾人只是將古典主義文類理論曾經的答卷重新給出了答案,論點分散有余而集中不足,使得論爭諸個體的理論系統性、整飭性不強。諸如此類,我們當以包容和豁達的胸懷,正確對待這樣的歷史局限性。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畢竟是在反思古典主義文類理論的道路上邁開了可貴的第一步。
〔責任編輯:平嘯〕
陳軍,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225002
本文系教育部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助項目“西方文類理論史綱”(201010)成果;本文得到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NCET-12-0746)和江蘇省教育廳高校“青藍工程”(2010-2013)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