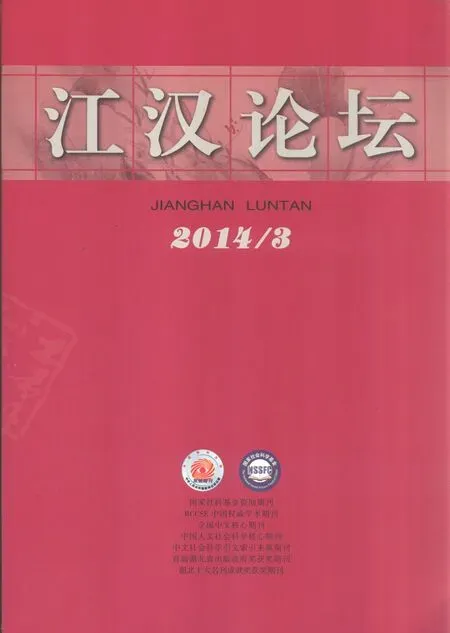集體談判中政府侵權現象研究
艾 琳
近年來,勞動關系矛盾進入了高發期和多發期,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健全勞動標準體系和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和爭議調解仲裁,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勞動關系是否和諧不但影響著經濟的發展也決定著社會的平衡。但不同利益主體的表達能力和維權能力是不同的,這就需要建立起一個利益表達機制方能達到動態平衡的市場關系、社會關系。集體談判制度的確立無疑便是一種重要的利益表達機制。
政府介入勞動關系主要是運用國家公權力,國家公權力是通過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的行使來實現的。在集體談判中,政府并不代表或者直接融入權利主體和義務主體的任何一方,而是居于勞動者和雇主雙方之上,以“裁決者”和“公正者”的身份主持社會公正,這種公正也是以保護勞動者為宗旨的勞動法的立法依據。在這種立法依據上,政府的作用就是強化一部分人的權利并限制一部分人的權利,追求法律的“實質的平等”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政府相對于勞動者是促進勞動者權利實現的義務主體,相對于雇主則是勞動者權利保障的權利主體,是一個特殊的法律關系主體。
一、政府在集體談判中的侵權現象
綜觀我國集體談判制度的運行現狀,不難發現,由于政府在自身功能定位和施政目標設置上的原因,造成了許多政府越位、缺位、錯位的現象。
(一)政績導向下的政府越位
我國的集體談判是一種由政府主導、官方工會發動、企業工會代理、地方黨政機構配合的自上而下的功能形態和推進模式,它有別于以勞動者的訴求為起點、工會作為代表、政府監督協調的自下而上的運作體制和制度安排。在自上而下的集體談判中,政府始終以主動參與、主導實施的姿態提供行政強制力的支撐,本應是談判主角的勞資關系雙方卻不能成為推進集體談判的主體力量。有學者認為,集體談判在中國的引進是一個官僚化的過程,它是由地方黨政機構推動的,而不是對勞資關系的主動回應,企業經營中的工資和雇傭條件都包含在了當地政府頒布的指導框架中。②這個有計劃、有組織的集體談判推行過程包括制發文件、分派任務、限期達標等,政府部門和工會將研究提出并經上報批準的集體談判“內容”和“要求”傳達到企業,作為企業勞資雙方討論協商的核心要求和主要參考。因此,在集體談判的過程中少有工人參與,也較少有真正的談判過程,集體談判多流于形式。③例如,2010年8月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集體合同制度實施彩虹計劃的通知》 (人社部發 [2010]32號)第二條明確規定:從2010年到2012年,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實行集體合同制度。誠然,在行政層面通過量化的指標推行集體談判制度的做法是有積極意義的,畢竟數字的增長可以部分證明進步的存在。但是如果在推進集體談判制度的出發點上不能體現對談判主體地位的尊重,不能還原集體談判的本質要求,在推進集體談判的過程中,不能夠加強對談判過程及手段運用的指導,政府就難免出于政績的考量,把完成集體合同覆蓋率指標當作集體談判的目的。以這種方式完成的集體談判,實際就會演變為“政府下達任務—工會提出要約—企業配合應約—政府部門檢查推進”的要約工作鏈。
同時,我國《集體合同規定》第五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無正當理由拒絕工會或職工代表提出的集體協商要求的,按照《工會法》及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處理。《工會法》第五十三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責令改正,依法處理。該法明確地把對集體談判義務主體侵權的救濟責任全歸于政府。毫無疑問,在勞動糾紛的處理中,政府的行政救濟確實是一種十分直接且可行的介入方式,但不應該成為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式。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行為的目的應該是把勞資雙方都納入到一定的法律制度框架之內,尊重勞資雙方的主體地位,以勞資雙方契約自治方式和制度化形態來化解、處置勞資矛盾。由此可見,在我國的集體談判實踐中,政府同時身兼運動員、裁判員兩個角色。
(二)管制導向下的政府缺位
政府介入勞動關系,要通過一系列的勞動標準立法,維持社會基本的公平與穩定④,才能起到均衡和制約的作用。政府不能通過立法來保持勞資關系雙方力量的對等均衡,不能通過立法來約束勞資關系雙方的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導致政府缺位。例如,旨在強化勞動者權益保護的《勞動合同法》對目前解決不了的問題只是暫且不作規定,或者只作原則性表述,帶來了集體談判實踐中大量依據不充分、不明確情形的存在。一般而言,引發勞資沖突特別是勞動者集體行動的普遍原因是工人權利受損,在勞資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政府更有責任通過公權力的介入來實現勞資雙方力量的相對平衡。亞當·斯密指出:工人在經濟上的維持能力總比不上老板,因此,工人的聯合或工人協會往往更具有暴力性和侵犯性。⑤這種因能力上的缺失而造成的實際危險,政府是要有所預防、消解和補償的,如果勞動者的權利長期得不到有效保障,引發涉及范圍更廣、更為激烈的勞資沖突將不可避免。在市場經濟、公民社會與法治國家共同進步的狀況下,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可以也應當形成利益制衡的格局,使有著不同利益和主張的群體能夠共生共存。勞資雙方為實現合作互利,需要法律制度進行保障;勞動者為追求自身合理權利的抗爭,也必須在法治的框架下進行。
此外,政府在勞動者權益受損時的行政救濟也同樣存在著缺位現象。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末,全國勞動監察機構共有3291個,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配備專職保障監察員2.3萬人,同期全國就業人口總數為79163萬人;到2012年末,全國勞動監察機構仍為3291個,配備專職勞動監察員2.5萬人,全國同期就業人口總數為76704萬人。⑥筆者計算,2010年,專職監察員與就業人員數量比約為1:34419,2012年數量比約為1:30681,雖然比例有所提高,但勞動監察的力量仍十分薄弱,勞動監察的效果可想而知。勞動執法力量不足也反映了對勞動者權益保護的重視不足。執法者自身缺乏權利受侵害的切膚之痛、檢查人員配備數量不足是集體談判權行權艱難的另一個方面原因,更關鍵的是如果不改變“市場轉型期的中國勞動政策變遷的基本取向是服務于企業效率和國家經濟發展”⑦的格局,那么,政府缺位的現象就不可避免。
(三)利益導向下的政府錯位
長期以來,政府習慣于以行政手段調整和控制勞資關系,但是這種方式因與雇主主導的勞資關系現實相悖,已經被證明是難以有效發揮應有作用的。政府一方面出于職責的要求,應對集體談判義務主體的侵權行為進行強力干預;另一方面出于招商引資、加快發展的政績需要,又有意無意地暗許或者放縱雇主不履行誠實談判義務,放棄了對有失公平、公正的勞資關系進行嚴格校正的責任。因此,在看到失衡的分配制度是誘致我國勞資矛盾的直接性變量的同時,還要認識到既往經濟發展模式下“親資本、疏勞工”理念對集體談判制度建立和實施的負向作用。正是因為“權力與市場的 ‘非法婚姻’,即權力與市場結合到一起,形成了權貴經濟”⑧,為了“營商環境”而無視勞動者的利益,這是極其嚴重的公權錯位,其本質是政府放棄了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責任和使命。
以轟動一時的黃埔冠星精密表鏈廠勞資糾紛為例,上千名工人進行了長達半個月的罷工行動,最后啟動集體談判事態才得以平息。回顧整個事件過程,政府錯位的現象無處不在。比如當勞動者提出集體談判要約時,廠方反對工人訴求的憑據竟是地方政府“維穩小組”的通告。可見,在現實中政府有著解釋法律的權力,當地政府的表態就是法律,而對法律的不同解讀,反而使勞資雙方本可通過集體談判解決的矛盾陷入了僵局。當工人采取罷工手段時,政府則運用行政強制力迫使工人復工。當工人被問及“在勞資沖突中,你們希望政府做什么”時,工人的回答是:“我們希望政府公正。不用向著工人,只要別向著老板就行了!”工人質樸的回答恰恰表明了本應在集體談判中受到政府保護的勞動者在政府錯位情況下的無奈與期盼。
二、政府侵權對集體談判制度的負面效應
政府在集體談判中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必然帶來集體談判的形式化、表面化,并進一步造成集體談判制度的空洞化、虛擬化,具體講就是有集體協商無集體談判、有集體合同缺集體認同。
(一)有集體協商無集體談判
我國工會既具有行政屬性又具有社團屬性,社團屬性是其表,行政屬性是其里,從這一點講,雙重代理的工會就是政府的有機構成或者職能延伸。在推進集體談判制度過程中,政府越俎代庖,宏觀上政府確定集體合同的簽訂數量和覆蓋率,微觀上從發出要約到簽訂合同都有政府的身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地方政府選擇性地施行,運用行政強制力要求企業與職工簽訂格式化的集體合同;企業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通常會識趣地配合政府的工作,很少會與政府不合作。這種默契下政府或者政府通過工會與雇主就既定內容進行協商,企業給了政府“面子”,政府照顧了企業“里子”,企業職工是有組織參加的旁觀者,卻不能通過代表自己的工會以權利主體的身份參與其中并表達意見,更遑論與雇主的談判博弈了。不論是出于對勞動者的尊重還是對于社會民主制度的需要,企業職工的自決權都是重要的,它要求雇員對關系到他們生活的決策具有發言權與參與權。⑨政府過度介入勞資矛盾、干預集體談判的結果就是勞動者難以實現本應具有的發言權、參與權,加劇了勞動者對法律的漠視和對權力的崇拜。既然權大于法,勞動者遇到勞動爭議時自然就不愿也不會運用法律武器,想到的首先是尋求政府的權力公道。對勞動者在集體談判中主體權利的“過度代表”和“包辦代替”不僅是政府的一廂情愿,以此所構建的有協商無集體談判的集體談判制度無疑也是在作繭自縛。將集體談判表述為集體合同,實質是對集體談判的否定,既在表明勞資矛盾的非對抗性,也暗含著對集體談判的控制與操縱。
(二)有集體合同缺集體認同
2010年7月,全國總工會召開的第十五屆四次執委會議要求“依法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依法推動企業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兩個普遍”的要求無疑對擴大工會組建率和集體合同覆蓋率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我們也注意到,在集體合同的覆蓋率穩步提高的同時,勞動者的生存狀況并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勞資矛盾愈發尖銳,持續高漲的勞資沖突向大規模、高頻率的方向發展,集體談判的社會“減壓閥”作用沒有實現。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推進集體協商的出發點是完成考核指標,有別于集體談判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目的。“協商與談判的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一個決策過程,而是一個咨詢過程,它強調在勞工關系中的合作而不是敵對關系。協商與談判不同,談判的結果取決于雙方能否達成一致,而在協商中,決策的最終力量總在管理者手中。”⑩用基本利益一致的“協商”替代存在一定對抗性的“談判”,提高了集體合同的原則性、通用性,但集體合同的內容也會更加一般化、空泛化和簡單化。統一規范格式和文字表述的集體合同,表達內容和方式完全法條化,從工作待遇到工作環境都是老套的最低標準,不斷增加和細化的指標是出于考核的需要而非針對解決特定企業職工的具體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簽訂集體合同對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是沒有太大實質意義的,對企業而言無非是陪著政府完成了“表演”程序,還免去了誠實履行集體談判的義務。很顯然,缺乏對勞動者權益真正關懷的以完成考核達標為主要目的的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集體“失語”了,本是權利主體的勞動者成為了政府與企業協商成果的承受者,完成了集體合同簽字確認的“畫押”。政府對勞動者權利的全面代理,蝕化了勞動者的集體談判權利,在這個形式大于內容的鏈條中,本應最有發言權的勞動者成了幫助完成集體協商套路演出的第三方。
三、對集體談判中政府侵權的救濟
第一,勞資沖突的有效解決歸根到底還是要依靠法律制度。當前政府普遍采取的救急式的短期行為并不能從根本上促成勞資矛盾解決長效機制的建立,也不利于建立各方認同、自愿參與的集體談判機制。這就需要完善集體談判制度立法、工會法立法,特別是要正視罷工權的立法。在國際勞動法律體系中,罷工權是重要構成部分,它不是一項單獨的權利,而是實現集體勞動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者之所以在集體談判中既被排斥又不得不依賴政府這一特殊主體,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罷工權保障。一般情況下,罷工權只有在雇主拒絕正當要約和談判破裂時才會啟動,是在資強勞弱的勞動關系中制約雇主不誠實談判和不承認談判的最重要且唯一的手段,在勞動者沒有這種權利作為談判的資本發起要約、平等對話時,只能任由政府這一“大家長”為其提供保護,而這種保護的代價就是虛化的集體談判和空泛的集體合同。同時,在我國一元工會的主導下,工會的主體性和獨立性明顯缺失,向政府負責的工會無法真正成為勞動者的代言人,所以,想實現罷工權的立法,加強對工會法立法的完善和改進也是立法救濟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二,行政救濟是針對集體談判中特殊主體侵權的最可行最直接的救濟,其本質在于敦促政府歸位。在集體談判中,因政府瑕疵行政行為導致勞動者集體談判權受損的,應該對其違法或不當行為進行消滅或者變更。對因政府越位而越權代理的集體合同應宣告無效,重新啟動集體談判。對已進入實質進程的集體談判應在以下四方面主動作為:一是在談判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政府要適時地進行調解、斡旋,促使談判能夠順利地進行下去。二是強化行為管控。當參與談判的任何一方不信守談判信用,過度偏離了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的原則,或者在談判之外做出單方面的施壓行為時,政府根據需要可以提出適當的強制性要求,促使其遵守談判規則。三是指導談判范疇。為了促成集體談判有效結果的取得,需要勞動者、工會能夠盡快提出明確的利益訴求,也需要雇主代表在回應這些訴求時表現出足夠的誠意。為此,政府可以結合各方面的情況提出禁止談判事項、規定討價還價幅度等,以控制的方式對集體談判有所規制。四是在集體談判結束之后,政府還應敦促勞資雙方切實履行義務,使達成的集體合同得以履行并對履行中可能出現的理解偏差和糾紛作出及時的處理。
第三,司法救濟是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救濟雖然具有巨大的公信力,但存在著成本高、周期長的不足,其“不告不理”的被動性,使其在集體勞動爭議中很難發揮作用,如果每個勞動者都按照完備的法律程序進行爭議處理,必將耗費大量的法律資源和社會資源。司法救濟可作為底線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利,在政府實施了侵權損害,又沒有通過行政救濟矯正瑕疵時,應啟動行政訴訟救濟。根據集體談判權力主體的特殊性,建議由工會或勞動者授權的律師代表,對在集體合同的簽訂程序中、在集體談判的進行中存在官商勾結、官商合謀的政府部門或工作人員,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法院審理并作出裁判。而在這一救濟中,更要側重對勞動者的傾斜保護。通過訴訟進行救濟的關鍵是舉證,在集體勞動關系中,政府作為特殊主體,占有大量的資源優勢和勞動者無法觸及的技術操作規程,勞動者無能力提供證據證明其侵權的實質,這就需要行政機關提供證據證明被訴行為的合法性,這樣才能使權利相對人得到真正的救濟。
注釋:
① 常凱:《勞權論: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頁。
② Simon Clarke,Chang-Hee Lee and Qi Li,Collective Consultation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China,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4,42(2),p.236.
③ 趙煒:《基于西方文獻對集體協商制度幾個基本問題的思考》,《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5期。
④ 李琪:《產業關系概論》,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頁。
⑤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亞楠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13頁。
⑥ 數據引自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2010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2年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⑦ 岳經綸、莊文嘉:《轉型中的當代中國勞動監察體制:基于治理視角的一項整體性研究》,《公共行政評論》2009年第5期。
⑧ 孫立平:《“權力—利益的結構之網”與農民群體性利益的表達困境》,《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5期。
⑨ 約翰·巴德:《人性化的雇傭關系——效率、公平與發言權之間的平衡》,馬振英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6頁。
⑩ 約翰·P·溫德姆勒:《工業化市場經濟國家的集體談判》,何平譯,中國勞動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