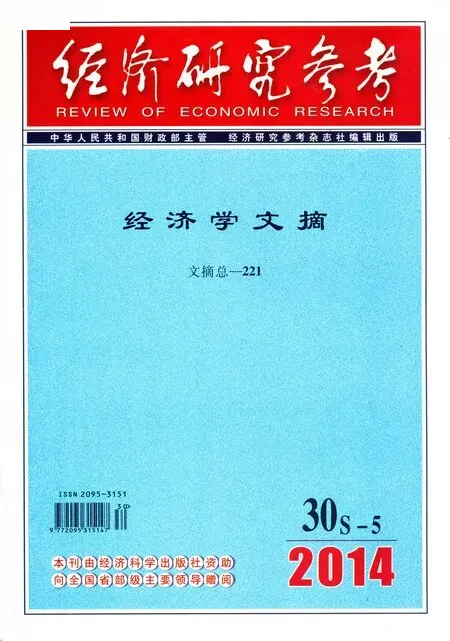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經驗教訓
智佳佳
一是通過制定“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提高國民生產積極性,拉動內需,促進消費。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指出:本計劃的最終目的是極大地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和達到完全就業;“十年后我國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國民收入為20.8萬日元,約達到現在2倍的水平”。計劃不僅深刻論述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問題,還詳細描繪實現計劃后的國民生活狀況,并列有提高程度的詳細數字,讓人們覺得經濟政策與自己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關,因此對該政策表現出極大的關心和興趣,人們對收入增長和未來生活水平的期望成為發展經濟的強大精神動力,國民高漲的生產積極性、強大的敬業精神和顯著提高的消費水平,為日本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目前,中國居民儲蓄率高,消費意愿低,內需嚴重不足,經濟發展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只有讓居民對未來經濟發展充滿希望和信心,認為自己預期收入會大幅增加,有錢可花,才會樂意把錢從銀行取出來消費,從而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投資、消費和出口協調發展。人民整體富裕,形成龐大、穩定的中產階級隊伍,有利于消除危機隱患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二是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不是單純的居民收入增加,更是一項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日本“收入倍增計劃”是一項涵蓋財稅、產業、區域、投資規劃在內的、系統的促和諧工程,本質上首先是經濟增長計劃,其次才是收入增長計劃。“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國民收入,不僅指向居民收入水平,而且是指國民生產總值減去固定資本折舊和生產稅凈額外的值,包括勞動者報酬、非企業財產性收入、企業在獲取投資紅利和向外支付紅利之后的所得。
在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期間,日本國民收入大幅增長,整個社會福利體系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全面發展,日本即使在經歷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和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后,仍然能保持穩定繁榮。我國可以借鑒日本經驗通過找準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勞動生產率,積極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穩定價格體系,提高勞動者的勞資對話權,發展壯大中小企業,保障國民充分就業,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等政策手段,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穩健發展。
三是中國目前形勢與日本當時情況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地方,借鑒經驗應靈活多樣,不能生搬硬套。中國推出收入分配改革時機與日本當時情況有所類似,如人口紅利即將過去,國民消費水平低,內需不足,城鄉差距明顯等。但與日本當時情況也有很大不同。
例如,當時的日本以美國為保護傘,通過《日美安全條約》謀得美國軍事保護而得以全力以赴發展經濟,當時日本軍事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不足1%。國際上倡導自由貿易,又恰逢第三次科技革命進入高潮,以原子能、微電子、半導體為中心的新科技,帶動石油化工、合成纖維、機器制造和金屬冶煉等領域的技術革新,為日本低價購入原料,引進科學技術,加速技術進步,擴大貿易順差提供非常有利的國際環境。
目前,中國城鎮化低于日本1960年的水平,城鄉收入差距較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為防止中國“崛起”而進行各種牽制,人民幣升值壓力大,國際能源供應緊張,價格上漲,面臨的國際環境遠比日本當時所處的環境艱難。
四是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值得反思。日本“收入倍增計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造成很多矛盾。10年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78倍,但國民工資實際上只增長0.94倍,并沒有和經濟增長完全同步;收入倍增計劃推出后,出現劇烈的通貨膨脹,引起民眾恐慌和不安,不利于社會安定;“公害”沒有得到治理,反而更加嚴重,日本國會甚至被國民稱為“公害國會”;環境污染嚴重,四大公害病中有三起和重金屬污染有關,空氣和水污染嚴重,給民眾健康造成很大隱患。
日本對人才培養過于重視科技,但忽視人文教育,導致人才思維過于機械化;一些大企業和土地投機商搶購土地造成地價暴漲,暴發戶層出不窮,使一般公民對社會的公正合理失去了信心,日本謀求通過分散財富和人口,實現國土均衡開發的主題并沒有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