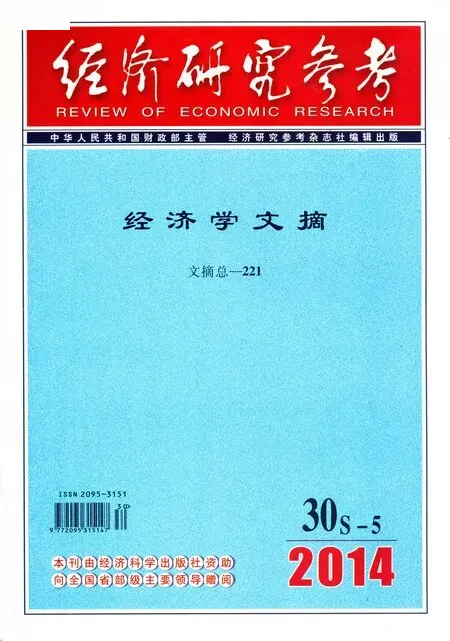宏觀調控要從總量調控為主轉向結構調整為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 鄭新立
2013年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制定了“穩中求進”的經濟發展總基調,而“十二五”規劃提出的長遠發展目標是把轉變發展方式作為主線。年度確定的“穩中求進”總基調和中長期的轉變發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是不是產生了矛盾?最近,美國經濟學家斯蒂夫·羅奇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宏觀調控的中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自相矛盾。羅奇先生長期跟蹤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常有真知灼見。羅奇先生的擔憂是,中國在年度目標中過分地強調了“穩中求進”,強調穩增長,可能會因為對速度的重視而犧牲結構調整。他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怎么解決羅奇先生擔憂的這個問題?這恰恰是今年的宏觀調控需要改進的重點,也就是宏觀調控要從總量調控為主轉向結構調整為主,這樣宏觀調控的措施就能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在結構調整中實現穩增長,而不是單純靠放松銀根、擴大需求來實現經濟增長。通過經濟結構的優化、經濟質量的提高來實現穩增長,而不是回到過去通過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來實現高增長的老路上去。
圍繞著宏觀調控為什么要從總量調控為主轉向結構調整為主,怎樣實現從總量調控為主向結構調整為主的轉變,我提出四個觀點。
第一,當前價格穩定為實現宏觀調控從總量調控為主向結構調整為主轉變提供了外部環境。從去年全年物價走勢看,基本上是穩定的,今年年初走勢也很穩定,這就為宏觀調控從總量為主轉向以結構為主提供了前提條件。我們不僅要通過貨幣政策的調整繼續保持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大體平衡,而且更要運用各種調控杠桿,把調控的著力點放在引導結構優化升級和發展方式轉變上來。
第二,通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來實現穩增長,需要宏觀調控加大對結構調整的引導力度。轉變發展方式最重要的是三個方面的轉變:一是經濟增長要由過去的投資、出口拉動為主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二是要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提高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三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通過自主創新帶動產業優化升級,改變過去主要靠增加物質消耗來實現經濟增長的局面。實現這三大轉變,必須有宏觀政策的引導,運用各方面的經濟杠桿來引導資金投向。如果宏觀調控僅局限在總量調控上,靠貨幣政策來調控總量變化,很難對結構調整產生作用,需要運用經濟杠桿來引導資金投向,加快結構轉型升級。所以,發展方式轉變不是一個自發的過程,而是一個宏觀經濟引導下充分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過程。如果僅靠市場的作用,沒有宏觀政策的引導,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曠日持久,所以一定要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來引導資金配置,同時在宏觀政策引導下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才能夠有效地推動發展方式轉變。
第三,實行以結構調整為主的宏觀調控,需要計劃、財稅、金融這三大調控杠桿形成合力。現在這三大杠桿配合得還不是很協調,應當有計劃提出需要調控的方向、目標、重點,主要運用財稅杠桿,包括貼息、資本金補助、降稅等手段來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特別是引導銀行貸款投向。在宏觀調控轉向結構調整為主的時候,要更多地發揮財稅杠桿的作用,因為金融杠桿主要是管總量的,財稅杠桿主要是管結構的。計劃、財稅和金融這三大杠桿要密切配合,圍繞發展方式轉變形成一個強大合力。
第四,結構性調整的政策要從選擇性的調整政策轉向功能性的調整政策。所謂選擇性結構調整政策,就是挑選幾個產業,給予一定優惠政策,支持其發展。這樣的政策應當越來越少,要更多地發揮功能性結構調整政策的作用。比如,目前實施節能減排,改善生態環境,降低污染物排放是重要目標,所有能夠實現這個功能的投資都應當享受國家優惠政策,不管是從事哪個行業,即使是傳統的能源行業,如果能夠實現節能減排目標,同樣應當得到政策支持。所以,要從選擇性的結構調整政策向功能性的結構調整政策轉變。
我國現在正處在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而且我們的結構轉型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經濟結構已經實現了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而且企業競爭力較強,市場供求也已經大體平衡,所以,通過總量的調控就能夠達成一些戰略目標。我們現在正處于趕超時期,處于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等收入國家邁進的時期,應該把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放在結構調整優化上,一味照抄照搬發達國家的總量調控為主的政策,只會延誤我們發展方式轉變的進程。現階段,特別是今年,宏觀調控政策的著力點應由總量調控為主向結構調控為主轉變,這樣就能夠在轉變發展方式中實現穩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