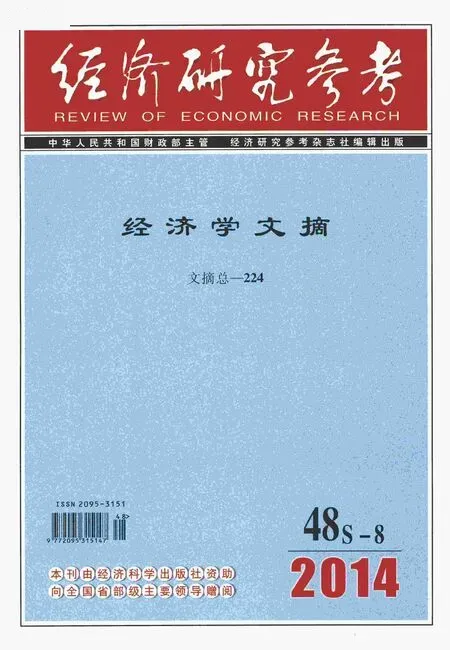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tái)利益分配的失衡格局
高 艷 王 緯
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tái)利益分配的失衡格局
高 艷 王 緯
一、利益分配在主體間的不均衡。
各利益主體從平臺(tái)投融資中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政府得到了經(jīng)濟(jì)和政治利益,金融機(jī)構(gòu)和平臺(tái)獲得了利潤(rùn),民眾獲得了公共產(chǎn)品。但是比較各主體收獲利益的種類和大小,政府不僅獲得經(jīng)濟(jì)利益,還能獲得政治利益,地方政府直接獲得的經(jīng)濟(jì)利益和政治利益是高于中央政府的,但是從地方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下屬來(lái)說(shuō),地方政府所獲得的一切利益都?xì)w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所獲利益的最終獲益者。平臺(tái)投融資操作的利潤(rùn)一部分以稅收方式上繳給地方政府,一部分以利息和股息的方式繳給金融機(jī)構(gòu),因?yàn)槠脚_(tái)大多從事的是非營(yíng)利性和半營(yíng)利性公共產(chǎn)品,利潤(rùn)分配后往往自己所得不多。民眾是從平臺(tái)運(yùn)作中獲益最少的主體,獲益少的結(jié)論主要是依據(jù)成本收益比較得來(lái)的:我們知道所有的政府資源尤其是經(jīng)濟(jì)資源是取之于民的,不僅國(guó)有資產(chǎn)是全民所有,而且政府財(cái)政收入的主要來(lái)源也是民眾,所以對(duì)于民眾來(lái)講,平臺(tái)投資也不過(guò)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從理論上講,民眾從中獲得的利益應(yīng)該等于或大于所支付的成本,但是實(shí)際上,平臺(tái)資金部分投向盈利性產(chǎn)品、投融資過(guò)程中存在的資源損耗以及腐敗現(xiàn)象等因素都導(dǎo)致民眾的最后獲益低于其支付的成本。所以從凈收益上來(lái)說(shuō),民眾是獲益最少的。而政府、平臺(tái)、金融機(jī)構(gòu)本質(zhì)上是資源的中介,通過(guò)操控各種資源的流動(dòng)從中獲益。
二、利益分配失衡與風(fēng)險(xiǎn)惡化。
平臺(tái)投融資能給各主體帶來(lái)不同的利益,因而獲益較多的主體尤其是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強(qiáng)烈的投融資沖動(dòng),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同樣面臨來(lái)自行政體系和市場(chǎng)領(lǐng)域的約束。從本質(zhì)上看,這些約束都來(lái)自于平臺(tái)的利益相關(guān)者:金融機(jī)構(gòu)作為平臺(tái)信貸的主要來(lái)源,為了保障資金安全會(huì)依據(jù)市場(chǎng)規(guī)則約束平臺(tái);當(dāng)?shù)孛癖娮鳛槠脚_(tái)提供的公共品受益者和平臺(tái)資本金的最終來(lái)源方,理論上對(duì)地方政府及其平臺(tái)的舉債行為有一定的約束力;中央政府作為地方政府的委托人,為地方政府債務(wù)提供了正規(guī)或隱性的擔(dān)保,所以中央政府也會(huì)對(duì)地方政府舉債起到重要的約束作用。前兩者屬于市場(chǎng)約束機(jī)制,后者則屬于行政機(jī)制,在實(shí)際境況中,行政約束的效力往往大于市場(chǎng)約束的效力。
在融資約束機(jī)制和利益激勵(lì)機(jī)制的交互作用下,平臺(tái)發(fā)展處于平衡態(tài)勢(shì),地方政府債務(wù)風(fēng)險(xiǎn)也一直處于穩(wěn)定可控狀態(tài)。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jī)導(dǎo)致的“恐慌政治”打破了這種平衡,主要利益相關(guān)者在全球化風(fēng)險(xiǎn)面前,急于找到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的出路,放松了約束,加大對(duì)平臺(tái)利益的追求,導(dǎo)致了平臺(tái)債務(wù)失控風(fēng)險(xiǎn)凸顯。
正如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理論所指出,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的驅(qū)動(dòng)力是“我害怕”。雖然適度的恐懼有助于人類集中注意力面對(duì)各種風(fēng)險(xiǎn),但是過(guò)度恐慌會(huì)使整個(gè)社會(huì)陷入對(duì)各種危險(xiǎn)來(lái)臨景象的想象之中,即便采取行動(dòng)也容易喪失理性。始于2008年年底的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給全球經(jīng)濟(jì)發(fā)展形勢(shì)蒙上了一層陰影,許多國(guó)家都陷于風(fēng)險(xiǎn)恐慌中。各國(guó)積極采取救市行動(dòng),我國(guó)也出臺(tái)了4萬(wàn)億元的投資救市計(jì)劃。自此,國(guó)際金融危機(jī)成為中央政府默許并推動(dòng)、金融機(jī)構(gòu)推波助瀾、地方政府大力發(fā)展平臺(tái)融資的催化劑;4萬(wàn)億元政府投資計(jì)劃下的配套資金給地方政府帶來(lái)了資金壓力,進(jìn)一步誘發(fā)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動(dòng)機(jī)和行為;“保增長(zhǎng)”目標(biāo)極大強(qiáng)化了政績(jī)合法化建設(shè),加大了對(duì)地方政府政治利益追求的激勵(lì)強(qiáng)度;對(duì)國(guó)際金融風(fēng)險(xiǎn)的擔(dān)憂讓中央政府放松了對(duì)地方政府的行政約束,一定程度上放縱了地方的融資沖動(dòng)和大規(guī)模投融資行為。
地方政府在財(cái)政壓力和政績(jī)激勵(lì)刺激下尋求體制外籌資渠道建立平臺(tái),銀行正在為流動(dòng)性過(guò)剩下的金融資本尋找利潤(rùn)。地方政府和銀行一拍即合,借助融資平臺(tái)這個(gè)媒介,大規(guī)模地開(kāi)展信貸合作,以圖實(shí)現(xiàn)各自的利益訴求。最終,地方政府的融資沖動(dòng)被徹底激發(fā)了,平臺(tái)數(shù)量膨脹,債務(wù)累積,風(fēng)險(xiǎn)迅速擴(kuò)大。
(成林摘自《地方財(cái)政研究》2014年第7期《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tái):利益相關(guān)者與分配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