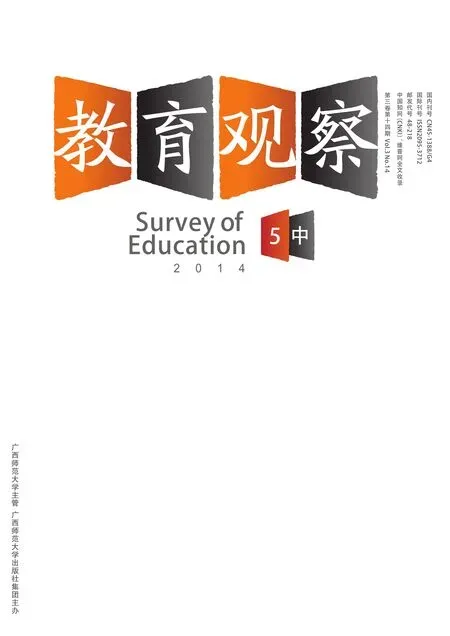談馬克思主義合力思想內涵的認識
馮曉玲
(廣西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廣西南寧,530023)
馬克思主義合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時期,從不同角度對合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與分析而形成的重要理論思想。
一、馬克思的合力思想
馬克思的合力思想源自于人類生存發展最基本的物質生產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與分析。在馬克思物質生產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和分析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合力思想,并對合力理論進行了深刻闡述。
(一)生產合力實質上是集體力
生產合力是社會合力的根和本。馬克思在闡述生產過程中的合力問題時指出:“單個工人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抬重物等)時所發揮的機械力在質上是不同的。協作直接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實質上是集體力。”在這里,馬克思所說的集體力就是指生產的合力,認為生產合力實質上是集體力。
(二)生產合力源自于協作
關于協作問題,馬克思指出:“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在這里,馬克思闡明了協作含義,并通過深入分析生產協作形式闡述了合力的本質特性。馬克思指出:“一個騎兵連的進攻力量或一個步兵團的抵抗力量,與單個騎兵分散展開的進攻力量的總和或單個步兵分散展開的抵抗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同樣,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么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么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且不說由于許多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而產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數生產勞動中,單是社會接觸就會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每個人的個人工作效率。”從上述馬克思關于集體力的論述和關于協作含義的闡釋分析可知,協作的本質特性在于“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即在于人自覺地、有目的、有意識地一起共同完成同一預定的工作目標任務。其中,協同主要是指在計劃指導下“同時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協同是協作的基礎和形式,在協作中起聯結紐帶作用;而計劃則是“協同的計劃”,意指根據協作各方的實際需要,確定共同的奮斗目標,經過有效的資源整合,包括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而獲得最佳的經濟和社會效益。特別是從馬克思闡述協作是“許多人在同一生產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聯系的生產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的這句話的含義分析來看,“同時共同”是服從于“同一”,即“協同的計劃”,其核心是協同組織的目標,這才是協作真正不可分割的,才是協作實際意義上必須“同時共同”要完成的。也就是說,在這里,實際上馬克思已經告訴我們,協作的關鍵在于相互之間是否有共識,是否確立了共同的奮斗目標和具有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和科學可行的行動方案。可見,“協同的計劃”具有建立在共同利益訴求基礎上,以實現共同發展為目標的“同一”社會屬性,“同一”對協作來說才是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協作的根本和發展方向,協作往往是以計劃的組織性和目標的有效性來凝聚力量,推動發展的。而以協作促進各方在“結合勞動”的“社會接觸”中,進行內部各種要素的必要重組與資源整合,使許多力量融合成為一個總的力量,并在這一過程中使得協作各方的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激發出來,特別是把各方面的創新能力激發出來,才能形成一種與“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有了質的區別的一種新的力量;這是一種不僅使個人生產力得到了提高,而且還創造了一種生產力的力量;這是一種有組織的執行,既有利于個人,又有益于社會,具有高度自覺性和創新精神的力量,馬克思把這種力量叫做集體力。
從上可見,馬克思通過分析物質生產過程,闡述了合力的實質、來源途徑、本質特征、發展動力及其產生過程中所涉及的分工與協作關系等重要思想內涵,指出合力實質上是集體力;源于協作;具有以共同利益訴求為基礎,以共同發展愿望為目標的 “同一”的社會屬性;是由協作內部各要素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種計劃性、目標性強,具有高度自覺性和創造性的社會活動力量。
二、恩格斯的合力思想
恩格斯的合力思想直接來自于對社會歷史及其發展規律的研究,是對馬克思合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恩格斯主要從內容構成、運動規律、實現機制及其價值訴求等方面對合力問題進行了深入闡述。
恩格斯在闡述社會歷史及其發展規律中指出:“無論歷史的結局如何,人們總是通過每一個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在這里,恩格斯首次使用了“合力”這一概念,并明確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人類能動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歷史,也就是合力發揮作用的歷史。從恩格斯上述合力含義的表述可以看出,在合力內涵問題的認識上,恩格斯與馬克思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認為合力是社會有機體內部各要素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種具有很強的組織計劃性、目標性,以及高度自覺性和創造性的社會活動力量,并進一步指出:“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在這里,恩格斯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唯物辯證地闡明了影響社會歷史發展,形成合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合力運動是有規律的觀點,指出社會歷史是由和人的切身利益攸關的經濟問題,即滿足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實踐活動決定的,這是社會歷史發展最根本的力量,也是人認識歷史發展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恩格斯提出應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復雜性,懂得社會歷史發展總會受到政治、傳統等上層建筑各種因素的影響,認為就是這些社會生產的現實條件和各種社會存在,包括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制約著人們創造歷史,影響著社會發展進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不能隨心所欲,然而,這決不能由此而否定人創造歷史的基本事實,更不能由此而忽視人類作為社會歷史主體在合力推動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為此,恩格斯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在這里,恩格斯唯物辯證地分析了人的主觀意志在合力推動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雖然不是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但并不等于說人無所作為。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對社會發展有影響的各種因素作用的發揮無不是通過各種不同的個人主觀意志的沖突表現出來,并形成不同力量的博弈與較量,但最終并不是以“任何一個人的愿望”的達成為終結,而是由蘊藏在各種不同利益訴求和發展愿望中有益于各方成長,并使得各方利益不斷得到平衡的“共同的利益”。恩格斯把它喻為“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現時我們則把它稱之為各方尋求的“最大公約數”筑就的。正因為如此,恩格斯指出:“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然而“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
(一)合力就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社會發展力量
正如上述恩格斯所指出的一樣,盡管人們看到社會歷史發展中反映得最激烈、表現得最活躍、作用得最直接的是個人,甚至表現得最突出的是某一些個人。但是,從“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的最終結果來看,最終能夠恒久地立于人類歷史舞臺上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持續不斷地得到生長的是那些維護了各方根本利益,反映了各方共同發展夙愿,而把大家聯結在一起,融合為一個各方都能夠共同參與、并在其中有所作為的社會利益共同體和有利于這一利益共同體發展的社會變革力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無論人類社會經歷過什么,也不管經歷的過程有多么的曲折、尖銳、艱難,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即認為是合力同一運動規律,把人們聯結在一起來,推動著社會向前發展,合力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強大動力。
(二)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是合力應有之意
這是恩格斯合力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及其提出判斷人生價值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恩格斯對馬克思合力思想的一大發展,提出 “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的合力價值訴求及其評價標準是社會合力“同一運動規律”的必然要求。即認為,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進程中,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斗爭、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以及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更迭、人類歷史不斷地從低級向高級形態的遞進,無不是人類社會內部同一運動規律作用的結果,認為是合力同一運動規律,促進了不同利益矛盾沖突由激烈走上緩和,并促進不同矛盾紛爭的逐步消解。人類社會總體上日趨平和有序,而認識和把握合力同一運動規律,積極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或發揮人的自覺能動作用,對合力推動社會發展做出應有貢獻,這是合力應有之意,也是協作各方應有責任和自身價值所在。
總而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力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馬克思主義合力思想蘊含著極其深該而又豐富的內涵,并揭示了合力的實質、來源途徑、本質特征、發展動力、運動規律、實現機制及其價值訴求;揭示了社會有機體中各種因素、各種關系、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和非平衡發展規律;揭示了歷史創造過程中主體能動性與歷史發展規律之間的關系。特別是通過闡述集體力、協作、同一、融合、創造、貢獻之間的內在聯系,闡明合力的同一本質特性及其運動規律,從而認識到合力的最大價值就在于它在反映共同利益訴求,實現共同發展夙愿的同一運動規律的作用下,以高度的組織能力凝聚共識,團結力量,整合資源,完成了一個又一個預定的工作目標,踏上了一步一個臺階的人類文明發展康莊大道。
[1]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王和強.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論——思想政治教育說理方法的哲學思考[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