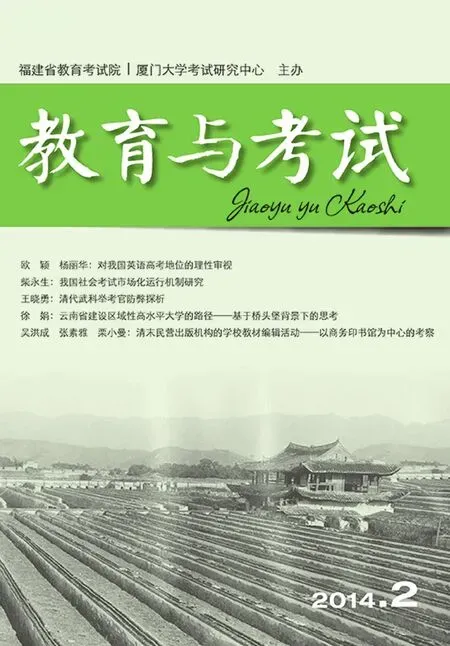清代武科舉考官防弊探析*
王曉勇
在“官本位”的清代,科舉制度無疑有著極大的吸引力,不少士子為了能夠順利通過考試,采用各種舞弊手段,由此滋生很多弊端,由于考官在取士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發揮著極大作用,因此針對武科舉考試的考官群體制定各種防弊規定,就顯得尤為重要。對于武科舉中考官的科場防弊,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考官的回避
武科舉在防止考官作弊方面,最主要的是對武科舉考官的籍貫和家庭的情況,并有針對性地限制其主持考試時出現本家族或者本省內武科士子的情況,將家庭和籍貫作為任命武科舉考官的一個重要約束手段。這種做法符合中國的國情,作為一個人情社會,中國的家族和親緣關系相當牢固,甚至同鄉同省的情誼也會在很多場合產生強烈的影響〔1〕。這種牢固的感情和鄉情在科舉考試中容易產生一些弊病,包括出現“科甲朋黨”或者取士過程中為了照顧親情和鄉情而不秉公校閱,這也是長久以來對科舉考試公平公正性沖擊的諸多力量中最不可忽視的力量之一。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的出現,早在唐、宋、元、明時期,就開始出現科舉考官的回避制度,到清代這種回避制度的規定更為嚴格。在武科舉考試中,與內外簾官員有親緣或者地緣關系的應試舉子,或者與應試舉子有著親緣或者地緣關系的官員都要在科考中盡量回避,以免出現錄取不公的現象。武科舉考官的回避主要包括親屬回避和籍貫回避兩大類。
首先是親屬回避。為了防止考官因自身或者同僚親屬參與科舉考試而導致舞弊現象,對武科舉的考官及其同僚提出了姻親回避的規定,主要有以下三類情況:
有親屬參加考試的官員不能獲得出任鄉會試主考、同考和監試官的資格。嘉慶五年九月軍機大臣就考官問題會同兵部議奏:“開列武鄉會試主考、同考官及監試御史、提調、收掌等官時,各處應送人員,如有本族及有服姻親考試者,即自行呈明不必開送。”〔2〕送交審核備選的考試官員“均于文內聲明并無應行回避之人,始列入本內。”〔3〕如果出現因為考官本人沒有自行呈明卻經皇帝欽點入場主持考試,最終出現本“應行回避之人因而中式者”的情況,則“照例將本官革職,該生褫革。 ”〔4〕
對武鄉會試的部分考試官員規定限制參加武科舉考試的親屬范圍。在武會試和順天武鄉試中“內場主考、監試、知武舉、提調、收掌等官及場內辦理供給之順天府治中、通判,其子弟姻親俱令回避。”〔5〕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考官的姻親回避要求并非針對所有參與武鄉會試的考官,主要是針對主考、監試、提調、同考等官員。之所以劃定這些考官,是因為他們“均有承辦試卷之責”〔6〕,如果允許其子弟姻族入場應試,容易出現“字句舛錯而代為改竄、甚至代人傳遞”〔7〕等關照之事。而對于非主持考試的官員則沒有要求,如“兩翼副都統、參領、章京等官及順天府所委巡綽等官之子弟姻親俱不回避。”〔8〕此舉屬于一種盡量降低科場回避章程給考官親屬帶來負面影響的辦法之一。
對各省官員子弟參加武科舉作出限制。清代早期規定較為嚴格,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御史段曦就上奏表示各省武鄉試起送兵丁參加考試時“務查果系兵丁實在行間効力之人會同文職官員公同出具印結保送”,“各省武闈凡本省文武官員子弟不準頂食兵糧入場考試”,〔9〕如果出現“現任本省官員子弟臨期頂食兵糧冒濫入場”的現象,則將“入場中式者察出”、“保送出結官會同吏部照例議處。 ”〔10〕奏議得到康熙帝批準并遵照施行。到清中期乾隆年間,規定有些松動,“籍隸他省官員隨任子弟,概不準就現任本省應試,并不準其入伍食糧有占該省兵額”,而對“籍隸本省員弁游擊都司系五百里以外”者和“籍隸本省的守備系隔府別營”〔11〕者,允許其弟子“令各歸本縣”應試。
其次是籍貫回避。主要指參與武科舉鄉試的考官,其籍貫應當在自己所參加的武鄉試所在省份之外。在文科鄉試中,要求主考官回避本省,同考官也要嚴格遵循地區回避政策。〔12〕在武科鄉試中,不僅負責內簾的主考官和同考官需要遵守不能回歸本省主持考試的規定,對于其他一些考官,如統領武鄉試考務的監臨官、主要負責外簾考務的監試官和提調官等,均同樣需要執行嚴格的地區回避政策。
清代各個直省的武鄉試中,所有監臨官、主考官和同考官、提調官等考務官員,除了部分由滿洲和蒙古人員擔任外,其余均由其它省份人員充任,可見對于考官籍貫的地域回避管理相對嚴格。除各省武鄉試外,還有一個地位較為特殊的武鄉試,即地處京畿重地的順天武鄉試。從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起,對武鄉試主考官和同考官作出一項特殊規定:“順天武鄉試內場,于開列主考官及同考官名單內,將直隸人員扣除。”〔13〕由于直隸在清代一直是武科舉大省,士子的整體水平較高,從地理位置上看,直隸環繞在順天周圍,因此,負責順天武鄉試的主考官籍貫排除直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直隸士子因地緣關系而獲得特殊照顧的可能性。
由此可見,對于考官的回避問題,清代所有武鄉試中無論順天還是各個直省,都嚴格遵照執行。而在武會試中,由于武會試的應試者是全國各省的武舉人,因此難以像武鄉試一樣作出嚴格的考官籍貫回避制度,但仍參照文科會試,保留了“本省人不看本省卷”〔14〕的慣例。
二、考官的約束
考官的回避規定主要是各級武科舉考官選擇之前的防弊舉措。在考官確定之后,對于考官及其隨從吏員的約束也有著比較詳盡的規定,這些規定又可以細分為外在約束與內在約束兩種。
首先是對考官的外在約束。主要指通過諸多規定約束考官行為,客觀上使其避免泄露考試信息和發生考試舞弊行為。外在約束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對武科舉考官本身進行約束。符合條件的官員在得到任命之后,雖然有不得事先宣布通過考差的各省內外簾工作崗位和人物情況的規定,但由于科考關系重大而考官在取士中又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被任命的考官會不可避免地成為各方試圖作弊者的渴望結交的對象。對這些考官從“待人接物”上進行嚴格控制就顯得十分必要。
所謂的“待人”是指考官和其他非考務人員的接觸。在考官確定工作職責后,要盡量隔絕他們與外界的聯系,尤其是避免接觸到參加考試的士子。其中關鍵一點在于考官的住宿安排,清代前期對于出任武科舉考官的官員住宿并無明確規定,乾隆七年(1742年)十一月甲申御史薛澄就曾指出其弊端所在,表示“外場考官應行關防也。凡武鄉會試,首重外場,乃向來惟內闈考官嚴行關防,而外闈考官謝恩后各回私家,次日始行赴闈,兼有衙門畫題事件,不惟酬應紛繁,于考校之事未能從容,且恐啟夤緣請托之弊。”〔15〕為了使考官能夠處于更嚴密的監視和管束之下、杜絕因為考官歸私宅而出現和士子協商暗通關節的現象,乾隆四十年(1775年)覆準兵部供役人等具交提調官嚴格管束〔16〕,乾隆四十八年(1782年)起清廷又采納御史李廷欽的建議,對考官的住宿情況提出特殊要求,“武會試監射大臣及兵部堂官宣旨后,即不準歸私宅”,不僅如此,還不準在外圍附近武舉之處居住。為了考官能夠處于遠離士子的位置而不容易被打擾,要求考官“俱于城內距外圍稍遠之處住宿”,并且將這一規定試用范圍擴展到武鄉試,除了對考官居住條件作出規定外,還嚴禁考官的幕友子弟等出入往來。如果出現士子私通關節等事,即由該督撫嚴參究辦。
所謂“接物”是指考官接受各種場外物件。為防止有人利用考官請家人取物品而進行賄賂的行為,乾隆四十年(1775年)規定,順天及各省鄉試考官入場后,凡衣服等物未能攜帶完全,允許在規定時間“補行家取”,但“舉子進場后,不得仍向家中索取什物,并令巡察各官,遇有考試官自家中送到什物,即全行駁回,不準放進”〔17〕。通過限制考官接收物品來起到防止考官家人私遞關節條子的現象。
無論限制考官接觸人員,還是禁止考官接受物品,都是對武科舉考官行為的嚴格限制。這種限制雖然給考官帶來生活上的諸多不便,卻是杜絕交通賄賣之弊所必須采取的舉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無論是主持武鄉試或者武會試,每一科的考官數量相對有限,因此目標十分明顯〔18〕,很容易成為各色人等交通賄買的對象,而清代對于科場違紀的處罰十分嚴厲,輕則官丟,重則身隕,這種對考官的限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其實施的一種有效保護舉措。
對考官隨從人員也有相應約束。要使對考官的約束產生效力,僅僅將關注點放在監試御史、主考官等考官身上是不夠的,這些官員很少獨自一人參與科考,絕大多數都會有一些輔佐的吏員和跟役等隨從人員,而這些人員正是科場舞弊的人群。為防止這些人員成為溝通考生和考官的橋梁,需要對其嚴加約束。乾隆四十年(1775年),規定監射大臣勿得隨帶多人,“各闈箭冊俱系大臣等自行登記,毋庸假手官員,不得隨帶官員,隨帶跟役概不得過四名。兵部供役人等俱交提調嚴行管束。”〔19〕在受卷、彌封二所書手、皂役安排方面,由于“武會試人數較文場甚少,受卷彌封二所經辦之事亦簡”,僅需數人而已,卻設置三十名書手專司繕寫,由于人員“閑冗既多”,導致弊端滋起,因此乾隆十六年(1751年)采納兵部侍郎裘曰修的建議改為“受卷所酌留書手四名,彌封所稍繁酌留書手六名,其余二十名裁去。”同時這兩所各添設皂役四名以應對“啟閉彈壓之事。”〔20〕在跟役和吏員進入考場方面,為避免其串通參加考試的武士子進行舞弊活動,“武鄉會試入闈官員之跟役及執事人等,入場時概行嚴加搜檢。”如果出現“串通士子代為懷挾情弊”則教送“該管衙門從重治罪”,同時還追究考官本人的連帶責任“官照失察家人犯贓例議處。”〔21〕在出考場方面,起初并無明確規定,執事人員所帶吏胥,向于受卷、彌封之后就可以放出。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采納兵部左侍郎蔣檙的建議,吏員不得先期出場,需要等到榜發之后,才能逐名點放,以此杜絕與考場外士子互相交流、串通作弊的現象。
其次是對考官的內在約束。內在約束主要是指對考官在主持考試過程中取士態度的控制,通過對濫用職權隨意選拔士子導致取士質量堪憂的考官進行相應的懲處,來督促考官取士時用心校閱。外在約束僅為武科舉考官拔取真才提供了一個基礎條件,能否真正夠抵御各種舞弊現象的侵襲拔取真才,則需要依靠考官內心的抉擇。在各個級別武科舉考試中用以督促考官取士行為的內在約束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對武童試考官的約束,雍正十一年(1733年)曾下令“府州縣官考試武童,倘不悉心校閱濫行錄送”以至于如果再武童試中出現弓馬平庸、文理不通之人混入內場,越號、換卷、傳遞、代筆、賄囑、倩代的行為,或者府、州、縣考試時考官希望廣收博取市寬大之名,無論騎射優劣悉行錄送,導致技藝不堪漢仗猥頊之輩混入內場的情況,都由學政題參議處。學政在閱外場時尤當加意選擇,如果將平常懦弱之人,濫列好字號入場取中,亦著督撫查參。雖然有此規定,武童考試中考官不悉心校閱、放松管理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如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謝階樹上奏“湖南省考試武童,經該學政查出重名者,寶慶、永州二府屬各有一千數百余名之多、桂陽、郴州、衡州所屬,每縣亦各有數百名。此外冒考者竟有僧人、屠戶、皂役、腳夫等項雜流之人,并匿喪頂替各弊,不一而足。”〔22〕皇帝閱奏后震怒,“傳旨嚴行申飭。該撫即會同該學政實力整頓。其查出冒考、匿喪一干人犯,均提案審明,照例分別治罪并通飭所屬,嗣后考試武童,務嚴行甄別,如有仍前作奸犯科者隨時懲辦,以除積弊。”〔23〕道光年間針對武童試中因為應考人數,動輒以技藝羸弱之人取充學額的現象,專門下詔要求“取士必嚴初進”,令各省武童試考官“考試武童宜慎重遴選、嚴加選擇,如人數不敷即行缺額,毋得濫竽充數。 ”〔24〕
第二是對武鄉試考官的約束。在武鄉試中規定“考試另編好字號,并分別雙單另入內場,再考試文藝比較取中。”〔25〕通過對外場不同成績士子的區別編號,督促考官將人材壯健、技勇兼優者選拔入內場,杜冒濫進諸項弊端,完成選俊儲材的任務。如果武鄉試考官不悉心校閱,將弓馬平庸、文理粗通之人,濫列好字號使之混入內場,出現“赴號換卷,傳遞代筆,賄矚代倩”〔26〕等作弊行為,則將考官黜革議處。在清代武鄉試中確實存在一些因武鄉試考官主觀因素而出現的舞弊事件,這些考官受到了較為嚴重的懲罰。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山西武鄉試中,武生劉際昌等賄賂監鼓官捏報中箭數量,乾隆帝傳諭對山西巡撫嚴切審究后獲得賄囑確情:“參將德成監視箭靶,漫不經心,使擂鼓兵丁受賄舞弊卻又無覺察”,責令嚴加議處,此外失察之提調、監試道員費淳、方應清,參將韓正國著一并被議處,同時督促各省督撫等嗣后辦理武闈事宜時務須留心查察,不得存姑息了事。除了在武鄉試中約束考官取士行為外,在更高一級的武會試中,還通過對武舉的考核來判斷武鄉試考官是否盡力拔取人才,如雍正七年(1729)議準,舉行武會試時。如各省所送武舉弓馬人材皆不堪者,將“鄉試取中之監試各官,照文場例處分”〔27〕。
第三是對武會試考官的約束。通過在殿試之前安排測試可以考察武會試考官是否用心校閱,對于會試中技藝不佳的士子,追究會試考官的責任。康熙四十年(1701年)規定“殿試之前將六部滿漢堂官開列,奏請欽點二三員,傳集中式武舉,按照會試原冊弓刀石斤重號數,令其逐一演試,如有前后參差者,即行參奏,原挑之監射大臣,交部議處。 ”〔28〕乾隆四十年(1775年)規定“中式武舉殿試前奏派大臣按會試原冊,所填弓刀石斤重號數,令該武舉逐一演試,有前后參差者,照文會試磨勘處分,并將原挑之監射大臣議處。”〔29〕除武殿試前安排的測試外,在武殿試舉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士子開弓違式技藝平常的現象,則將武會試“原闈監射、較射大臣議處,覆試王大臣察議。 ”〔30〕如嘉慶十年(1805年)武殿試時“湖南省武舉諶思棠,廣東省武舉鄧天保二名,照所注弓力試看,俱不能開。”皇帝認為“武會試掄才大典,監試覆試均應認真校閱,其技藝平常者,豈應濫行與選?此技藝庸劣,前此會試及覆試時如何閱看?殊屬草率。”因此做出嚴厲的懲罰措施,下令將“初次派令覆試”的二阿哥由軍機大臣“面行傳旨申飭”,〔31〕將其余武會試考官中校看武舉諶思棠和鄧天保的“莊親王綿課、尚書明亮、尚書鄒炳泰”以及派出覆試的“成親王、定親王綿恩、協辦大學士費淳、尚書長麟”等人,交與“宗人府、吏部、都察院分別察議”,〔32〕并從此規定“嗣后武會試覆試派出之王大臣若不認真校看”〔33〕則一并交部議處。 到咸豐九年(1859年)又作出補充規定“自庚申恩科為始,將較射大臣處分添入武場條例”。〔34〕
三、考場環境和取士過程中的防弊
除了針對考官的回避、內在外在約束等防弊舉措外,在武科舉考試中,還包括考場環境和錄取過程中針對考官的各項防弊舉措。
首先是考場環境的防弊舉措。在武科舉考試中,最重要的考試環境莫過于科舉考試的專用考場——貢院,貢院又稱貢闈、貢場、闈場,是科舉考試最為有形的一種體現。在文科舉中,它是進行鄉會試考試唯一的場所,在武科舉中,它是進行內場考核的重要場所。清代科舉考試大約三年舉行一次,平時貢院處于停用狀態,由于風雨侵蝕或者人為損害,使貢院年久失修出現破敗不堪的景象。貢院圍墻低矮,而武科應考士子由于大多身體條件出色,很容易翻墻入場進行作弊的現象,如乾隆年間武會試就出現山東武舉周鼎等逾號底墻希圖換號的案件。因此,乾隆七年(1742年)御史薛澄條奏建議“將鄰號院墻增高數尺,并照外圍墻一體加之荊棘”〔35〕,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內兵部侍郎歸先光也主張:“順天府修葺頁院之時,將號底墻垣加高數尺,上插枳棘與外圍墻并峙,以除越墻亂號之弊”。修葺貢院的建議很快得到采納,順天府在武會試及順天武鄉試舉行前修葺貢院時都注意將內場貢院墻垣增高,并上加荊棘。除此之外還“仿照外墻之制在貢院四角各建一樓”,以防士子越墻出舍。在進行考試時,“每樓派委首領官一員(即瞭望官),帶役數名專門負責瞭望稽察。”〔36〕如果該員有徇縱等弊端,則交由知貢舉、監試官參究處治。
除了對貢院進行整修和添設專員外,士子進行外場考試時,也有專門官員負責領取箭矢和內場考試座位安排中的防弊活動。在外場領取箭矢方面,武會試和順天武鄉試的外場及覆試,由兵部“先期行文順天府每闈在馬道適中及步箭落箭之處各搭蓋收箭棚廠一座,步軍統領衙門每闈委派營弁五員,揀派兵丁十五名。馬射時在頭二三靶處各擬派營弁一員,兵丁三名、步射時在落箭處,派撥營弁二員,兵丁六名專司打箭送往棚內。”〔37〕參加考試的武生武舉“各于箭枝上書寫姓名,射畢后親身赴棚報名領取”,未經考生領取的箭枝著派營員按名送交提調司員查收。對于考試期間“有間雜人等在落箭處及收箭棚附近處,窺伺希圖打箭者”將其“立即鎖拏枷號在本闈示眾。”如果“該營員營轄不能嚴肅,致有間人滋擾,即行參辦。”〔38〕在內場考試座位安排方面,考試之前的武會試及順天武鄉試外場棚座由兵部先期仰委托大興、宛平兩縣照例備辦,提調官親赴外圍查驗棚座。由于清代武科舉對士子的外場成績相對重視,一般外場成績好的士子會優先得到選拔,為了防止外場成績不佳的士子混入內場協助其他考生作弊的現象,雍正七年(1729年)特別作出外場成績不同分別安排內場號舍的規定:“順天武鄉試及武會試,頭場、二場試弓馬技勇人材,分別雙好、單好字號。將雙好字好號人。編入東文場坐號。單好字號之人,編入西文場坐號,歸號之后,令巡綽官按號查對,倘有不符,立即詢究。 ”〔39〕
其次是錄取過程中考官的防弊舉措。清代武科舉首先進行外場馬步射的考試。康熙年間對于外場成績合格的考生于“面上用印記”,同時在“空白印冊”上填寫本人親供,由內簾官員負責驗明身份入闈,“以杜代倩頂替之弊”。因武鄉會試首場考試與三場考試持續時間“為期將及經旬”而對士子“左右兩頰用以印記,士子保護維艱,日則不能盥洗,夜則難以就枕,且觀瞻不雅。”后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改為“合式戳記引武生武舉左右小臂。”〔40〕在考官記錄外場成績箭冊方面,規定“考試騎射、技勇,考試官及兵部堂官、監試御史各持冊一本記注,考試畢,公同密定雙單好字后,三冊封固,兵部同御史冊各攜入貢院,查對編號。”〔41〕起初這些考官冊由主持考試的官員各自攜帶回家。到乾隆七年(1742年)考慮到此舉于防弊不利,“或啟家人漏泄撞騙之弊”,規定“外場考試官號冊一并封固入箱帶入貢院”。〔42〕為進一步加強防范以昭慎重,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對裝載箭冊的冊箱做出規定:武鄉會試中每闈各備一箱,每晚將“冊箱封鎖后交提調官收掌……箱鑰交與監試之員”,次日公同取出,“校閱外場事畢,打完雙單好字號后,公同封固,送入內場。箱鑰交與監試御史帶入內場。 ”〔43〕
在內場考試中同樣存在很多防弊舉措。在內場試題的命制上,為防止試題泄露,嘉慶六年(1801年)規定 “武科密擬試題,試題由讀卷大臣密擬武經一段約百余字,欽定后在考試前一日齊交內閣刊刻題紙”,同時由“兵部奏請欽派護軍統領一員,帶領護定軍校等,在內閣前后門外,嚴密稽察。”〔44〕在內場考試舉行時,由監試御史發給試卷,各闈御史在“點名時各認其考試之人,倘有頂替代倩作奸之徒則立即拏究照例治罪。”〔45〕在士子完成內場考核交卷時,內簾考官將原冊所填的馬、步射和技勇成績逐一詢問,士子如能應對相符,則可以獲準“給籤放出”,如果回答與原填馬步射技勇成績全不相符,則確“系頂冒,由考官照例查究。”內場考試完成之后,由監試官、提調官會同受卷官和彌封官在至公堂上親自分卷并親用號印在卷面蓋戳,禁止“假手書吏”以防滋生弊端。在對試卷的進行彌封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奏準“武闈內場彌封,將卷面折疊,外用厚紙兩層封固以昭慎重”。嘉慶十六年(1811年)御史吳椿奏曾奏請 “武闈鄉會試卷糊名之處照文鄉會試一律加厚。”到光緒九年采納御史曾培祺的建議:“武闈內場試卷,彌封白紙再行加厚,仿照禮部彌封之式,將姓名籍貫,由上下卷角,斜疊數層,嚴密封固”,同時“鈐蓋關防,以昭慎重”。〔46〕在內場考官閱卷時,對用筆的顏色進行嚴格區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規定“覆準武闈鄉會試內簾閱卷房考官定以紫筆,主考官定以藍筆”,由于士子答題時用的是黑筆,閱卷考官使用有別于考生答題顏色的筆判卷,有效降低其利用職務之便替考生修改試卷的潛在危險,如果試卷中有“紫筆添改”痕跡,則將房官議處,如果試卷中有“藍筆添改”痕跡,則將主考議處。后因為“主考官專用藍筆,易滋脫落洗改之弊”,將之后閱卷改為“房考官定以紫筆,主考官定以赭黃筆”,其他“印卷戳記,及一切應用藍筆之處,具照文闈之例,改用紫色。”〔47〕考官用筆顏色的規定,使得試卷上的文字顏色沒有互相的交叉和重疊,既能夠起到防止考官修改士子考卷的作用,也使卷面比較清晰明快,同時不同顏色來自不同的考官,也有利于責任的判定。
四、結語
武科舉考官的科場防弊,是清代整個考場官員場務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清代武科舉考官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考官的籍貫、家庭和地域回避政策,還是對考官的各種內、外在約束,或是對考場環境的控制和取士流程中種種防弊的監控舉措,都體現出了清代作為科舉制度的完備時期,在科場舞弊管理中的成熟與嚴密,對科場舞弊起到了較好的防范與威懾作用,對保證武科舉的客觀、公平、公正收到了一定的實效。
〔1〕姜傳松.清代江西鄉試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38.
〔2〕〔3〕〔4〕〔5〕〔6〕〔7〕〔8〕〔9〕〔10〕〔11〕〔19〕〔20〕〔21〕〔24〕〔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欽定武場條例.四庫未收書輯刊玖輯玖冊〔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9-385.
〔12〕郗鵬.試論清代前期科舉回避制度〔J〕.南開學報哲社版,2004(3):31-36.
〔13〕〔14〕〔16〕〔27〕〔47〕(清)崑岡.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七百十八〔M〕.臺北:新文豐書局,1976:14381,14381,14381,14278,14290.
〔15〕王澈.乾隆朝武科史料選編〔J〕.歷史檔案,1995(4):26-30.
〔17〕沈云龍主編.欽定科場條例,卷二七,考官士子關防〔M〕.文海出版社,1973:1939-1940.
〔18〕姜傳松.清代江西鄉試研究〔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38.
〔22〕〔23〕林鐵鈞本卷編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第7卷)嘉慶朝〔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784,785
〔25〕〔26〕〔28〕〔29〕清高宗敕. 清朝通志,卷七十二,選舉一〔M〕.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7:7181,7181,2137,7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