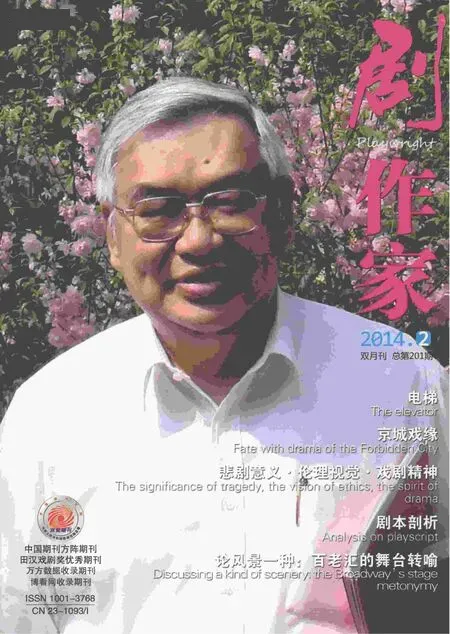淺析鄂倫春民族傳統說唱藝術“摩蘇昆”起源與傳承
李秀珍 溫慶民
鄂倫春民族是我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是一個自古以來以狩獵采集為基本經濟形態,兼有漁業、農業和少量手工制作業的勇敢強悍的北方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國東北地區的黑龍江沿岸和大小興安嶺一帶。與生活在這一地區其他兄弟民族一起,保衛、開發、建設、發展祖國美麗的北疆。同時,鄂倫春民族也以反映本民族獨特生活習俗的十分發達的口頭文學豐富和發展了北方民族文化,為我國的傳統文化增添了極具韻味的色彩。說唱藝術“摩蘇昆”就是其獨具特色的鮮明代表。
一、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摩蘇昆”的由來
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通俗地講就是說唱故事,是其口頭文學、口頭藝術的一個種類,具有古老的歷史,主要流傳于鄂倫春民族主要聚集地之一的黑龍江省遜克縣新鄂鄂倫春族鄉,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一直鮮為人知。在此之前,國內正式公開出版的多種有關鄂倫春民族的調查材料和論著中,雖對鄂倫春族的口頭文學、口頭藝術有所涉獵,卻獨獨不見鄂倫春民族的說唱藝術的有關章節和文字。可見,學術界、文學界對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一直是個空白。
1986年,黑龍江省民研會內部出版的《黑龍江民間文學》第17集、18集,先后發表了10部(篇)長短不一的鄂倫春說唱故事,引起了學術界、文學界的極大關注,使人們對鄂倫春民族的說唱文學藝術的存在不再產生懷疑。這些說唱故事的民族歌手李水花、莫寶鳳、孟德林、魏金祥、初溫特、莫海亭、孟興全等人均為黑龍江省遜克縣新鄂鄂倫春族鄉的鄂倫春族人,他們的說唱故事有的講述了英雄戰勝蟒猊的偉大業績,有的講述了民族中流傳的神奇、美麗、動人的傳說,有的則是一些廣泛流傳于民間的社會生活故事的說唱化處理。
在發表10部(篇)鄂倫春說唱故事的同時,《黑龍江民間文學》第17集上還發表了說唱故事采集者——孟淑珍的兩篇重要的調查報告,在題為《新鄂鄉鄂倫春族“摩蘇昆”、“堅珠恩”調查報告》的長文中,作者就畢拉爾地區鄂倫春民族的歷史、語言、民俗、民間口頭文學的狀況,尤其是說唱故事“摩蘇昆”和敘事詩“堅珠恩”的流傳范圍、傳播形式、傳承概況、作品采集的情況、整理的方法、作品的藝術特點等一系列問題驚醒了描述和初步的探討。正是在這篇調查報告中,孟淑珍將流傳于黑龍江省遜克縣新鄂鄂倫春族鄉一帶的說唱故事,按照當地鄂倫春族人的說法命名為“摩蘇昆”。在同一集中還發表了著名民族問題研究學者馬名超的論文《古老語言藝術的“活化石”——論鄂倫春史詩“摩蘇昆”》。自此,在學術界人們普遍把鄂倫春民族說唱故事定名為“摩蘇昆”,一直延用至今。
二、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摩蘇昆”的起源
鄂倫春民族的說唱藝術“摩蘇昆”是古老語言藝術的“活化石”,對于這一點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已經形成一個共識。但是,對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摩蘇昆”起源于何時至今沒有定論,只能從其藝術形態、故事內容、傳播范圍、表現的文化特征來分析、研究,探索其古老的歷史淵源。從已經采錄到的10篇鄂倫春說唱故事來看,它們篇幅長短不一,音樂不一樣,內容上也表現為互有差異的不同類型,結合其中各種文化藝術特點綜合考察、研究,這些說唱故事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起源。
從說唱故事的母題分析來看,在新鄂鄂倫春族鄉一帶的說唱故事,其中不少情節母題就時間的古老而言,可以追溯到遙遠的神話時代。通過母題分析不難看出鄂倫春民族的口頭文學、口頭藝術與通古斯——滿語語族的其他民族的口頭文學存在著深刻的內在聯系,而且還可以看出它同相鄰相近的突厥蒙古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系。《英雄格帕欠》是最典型的一篇。格帕欠的父母被兇惡的蟒猊捉去釘在門洞上,是英雄長大后將他們救出,蟒猊被英雄殺死。這樣的血親復仇母題在通古斯民族的長篇說唱故事中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若隱若現、若有若無的情節框架。英雄神異誕生、神異成長,英雄功業、婚姻都在征程中得以實現,英雄結拜、并肩奮戰等等,這同突厥蒙古、赫哲等民族的英雄故事中的英雄所作所為、所經所歷如出一轍。
從說唱故事的內容、人物形象分析,在新鄂鄂倫春族鄉一帶的說唱故事,其中不少內容、人物形象也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古代。在我們接觸到的十部(篇)鄂倫春民族說唱故事中,神幻的情節占有一席之地,如死而復生、體外靈魂、變形、飛騰的寶馬、神人的眷佑和反面形象蟒猊、妖鷹等。英雄在戰勝蟒猊、妖鷹的激烈戰斗中,英雄的寶馬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目前已有的史料看,17世紀以前的鄂倫春人主要是役使馴鹿而非馬匹。但在這些說唱故事中,卻未發現使用馴鹿的故事。這里只能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些說唱故事起源更早,還沒有開始役使馴鹿;另一種可能就是同突厥蒙古民間文學相關。
薩滿文化對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摩蘇昆”的產生,具有深刻的影響。在鄂倫春族說唱故事中,薩滿的形象引人注目,薩滿文化無處不在。鄂倫春族說唱故事同薩滿文化的關系,遠不止故事中那幾處薩滿形象的出現,薩滿文化對說唱故事的影響是多種多樣的,它表現在母題、情節、人物形象、細節描寫等各個方面,隨處可見。但是,細細分析,可以歸納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故事中描述了不少屬于薩滿文化范疇的可見行為,如尼遜薩滿的跳神儀式,鄂得薩滿的請神儀式,鄂得薩滿在請神時所唱的請神詞,英雄死而復生時躲避日光、月光、星光的禁忌等;另一方面,故事中還曲折地表現出屬于薩滿文化的許多觀念,薩滿文化的某些母題,如血親復仇等。薩滿文化觀念的流露,在鄂倫春族說唱故事中則顯得更為普遍,具有更為直接廣泛的生活基礎。
三、鄂倫春民族說唱藝術“摩蘇昆”的傳承
鄂倫春民族無文字,鄂倫春語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滿語語族的北支,即通古斯語支,目前,除少數老年人尚使用鄂倫春語外,絕大多數鄂倫春族人均使用漢語。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鄂倫春族的說唱藝術傳承受到限制,只能是“口傳心授”。鄂倫春族是一個游獵民族,在其漫長的歷史中,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壓迫,沒有固定的聚集地,分散生活在廣袤的大小興安嶺地區,出沒于崇山峻嶺之間,也使得這個說唱藝術的傳承更加受到局限。
鄂倫春族說唱藝術“摩蘇昆”主要流傳于鄂倫春民族主要聚集地之一的黑龍江省遜克縣新鄂鄂倫春族鄉,是黑河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孟淑珍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懷著搶救本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高度責任感,憑借她同歌手們生活在一起又懂鄂倫春語的得天獨厚的條件,用近五年的時間,經過采集、挖掘、整理,才使這一民族瑰寶得以重見天日。她通過廣泛的調查了解,對畢拉爾地區鄂倫春族的歷史、社會、民俗、宗教、民間文學藝術等各方面情況進行研究,重點是說唱故事。長期的調查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就是流傳于該地區的十部(篇)鄂倫春民族說唱故事得以發表,填補了鄂倫春族口頭文學樣式的空白,引起了國內民間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和認可。
1988年5月,《鄂倫春族文學》的作者隋書金、龐雨天再赴北京、呼和浩特、海拉爾、鄂溫克族自治旗南屯、鄂倫春族自治旗阿里河、大興安嶺地區加格達奇等地調查時,曾就孟淑珍所發現的“摩蘇昆”問題,訪問過長期從事鄂倫春族民族狀況研究的秋浦、招撫性、巴圖寶音、白杉、鄂倫春族作家敖長福、鄂倫春族民間故事家鄂爾登桂等人,他們一致認為在內蒙古地區的鄂倫春民族中確有“說一段,唱一段”的說唱故事在流傳。他們中間有些人還曾經在各種場合親耳聆聽過鄂倫春族中的“說一段,唱一段”的故事。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當時未能記錄下來,時過境遷,后來無法拿出相關的資料,也沒有形成相應的文字材料。只是他們對“摩蘇昆”這個名稱不敢肯定。在此之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一些研究鄂倫春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學者在黑龍江省的呼瑪、塔和等地搞社會調查時,也曾聽過“說一段,唱一段”的說唱故事,同樣遺憾的是他們也不曾將其采錄下來。
從以上的文獻資料和歷史來看,鄂倫春族的說唱故事不僅在黑龍江省遜克縣新鄂鄂倫春族鄉流傳,在其他鄂倫春族生活、棲息的地區也曾經出現、流傳。應該可以證明兩點:一是“摩蘇昆”這個說唱藝術,是鄂倫春族祖先留傳下來,并曾經在其各個部落都普遍流傳,雖然名稱不能肯定,但是表現形式均為“說一段,唱一段”的故事,故事內容也極為相似,都表現英雄、愛情等。二是由于受到生存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等諸多影響,加之,鄂倫春族沒有文字,“摩蘇昆”這門藝術同鄂倫春族其他很多民間藝術一樣,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和保護,以至于在一些鄂倫春族的聚集地失散、失傳。
談到鄂倫春族說唱藝術的傳承,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當年,在孟淑珍采錄、整理“摩蘇昆”時,歌手就不多,年齡均在35歲以上,而且,能夠成篇演唱的人也是寥寥無幾,如今更是寥若星辰,亟待我們投入更大人力物力去拯救、保護、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