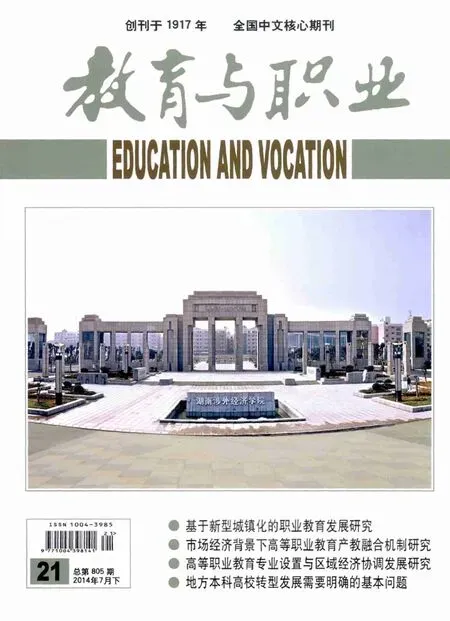醫學生生死觀教育研究
張麗紅 姜淑蘭 金雪蓮
人類自有了理性思維能力,就有了對生與死的深入思考。為何而生?如何面對死亡?人們不斷追索答案,人類歷史上積累了關于生命和死亡的各種思想資源,如宗教解讀的生死觀、無奈的宿命論、樸素唯物主義的生死觀及辯證唯物主義的生死觀等。由對生死的自為性思考發展為自覺性的生死觀教育,并日益得到社會和院校的重視。醫學生因其專業學習及未來職業的特殊性,對其開展生死觀教育具有更加特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生死觀教育概述
生死觀就是人們對生與死的根本看法和態度。“教育中不必回避死亡,因為意識到死,才能自覺的生,死亡的追問就是對生命意義的解讀。”①開展生死觀教育的主要意義就在于引導人們走出生命觀的誤區。在現實生活中,不珍惜生命、不尊重生命、甚至用犯罪的手段侵害他人生命的現象已經不是偶發事件。表現在青少年身上,由于心理脆弱,生命意識差,人生觀、價值觀不成熟,往往出現激情殺人犯罪及自殺等現象;成年人通常表現為因工作壓力問題、婚姻家庭問題而情緒低落,失去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也會導致傷害個人或他人生命的行為;即使老年人也會因身體健康問題、孤獨問題而產生傷害生命的行為;還有為數不少的人人生態度消極,沒有人生目標,缺乏追求,生活中表現頹廢落后。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死亡悲劇,并不是先從生理意義上剝奪了生命,而恰恰是因為對死的恐懼而先在心理上摧毀生的希望。
美國早在20世紀50年代開始開設死亡教育課程,其他國家如澳大利亞、英國等國家也相繼設立生命教育中心,以生存和死亡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致力于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我國傳統文化重視生避諱死,生命價值教育內容較為豐富,死亡教育則是生命教育的禁區,也是空白地帶。即使是有關生命觀教育的內容也主要呈現于思想政治教育、倫理教育、心理教育等諸多課程中,系統獨立的生命觀及生死觀教育還沒有形成。我國的臺灣地區生死觀教育起步較早,傅偉勛先生對臺灣地區生死觀教育的產生和發展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目前臺灣的小學生就開始接受生死觀教育,中學則有系統化的教育內容。香港地區的生死觀教育開展得也比較早,2009年香港大學推行正視生死的“善美生命計劃”,已經將生死特別是死亡教育向全社會推廣。我國大陸地區的生死觀教育出現較晚,在教育界及其他學科領域學者們的呼吁下,逐漸受到重視,有些高校成立了相關機構,開展了生死觀教育的嘗試,如北京師范大學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0年,已經成功舉辦了兩次(2011年和2012年)“大學生生命教育高峰論壇”會議,在生命教育研究和推廣方面積累了相關經驗。但仍然是采用“生命教育”的提法,而未有“死亡教育”提法,用“生命教育”包含“死亡教育”。當前,應當摒棄重視生而忌諱死的傳統觀念,借鑒已有的經驗,通過開展馬克思主義生死觀教育,促使人們認識生命、熱愛生命、正確對待死亡,培養其追求生命意義的自覺性,樹立積極向上的生命觀,激發生命潛能,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二、目前醫學院校生死觀教育現狀及原因
目前我國的醫學院校,這一最急需生死觀教育的教育領域較之其他類別的教育機構,生死觀教育幾乎就是空白。據筆者調查,吉林省主要的幾家醫學類院校(吉林大學醫學部、長春中醫藥大學、延邊大學醫學部、北華大學醫學院、吉林醫藥學院)幾乎都沒有專門的生命教育課程或死亡教育課程的安排。總結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生死觀教育作為新鮮事物,還沒有受到醫學教育者的重視。醫學院校的專業教育是重中之重,教師壓力、學業壓力及就業壓力集中體現在繁重的教學任務安排上。不管是生死觀教育還是其他非醫學類教育,統統要給醫學專業教育讓路。這一點從醫學院校的課時安排上可見一斑,只有在專業課排定之后,其他“無關緊要”的課程才能見縫插針地安排。
2.醫學院校缺乏綜合類大學豐富多彩的人文課程資源和人文環境。同綜合性大學相比,醫學院校過于專業化,師資隊伍以專業教師為主,對學生的人文文化熏陶相對較少。生死觀教育的價值取向偏重哲學,包含一定的生命自然科學知識、心理學知識、倫理知識及社會學知識,更是充滿對生命和死亡問題的思考,從內容上無疑屬于人文文化教育。在人文文化相對缺乏的醫學院校,生死觀教育的缺失也就不難理解了。
3.即使有些院校已經意識到對醫學生進行生死觀教育的重要性,但專業知識的替代性思維阻礙了獨立生死觀教育的產生。生死觀教育中確實包含一定的生命自然科學知識,這就使得醫學院校的教育者們認為,通過專業教育,生與死對醫學生來說不會像普通人那樣神秘,醫學生面對死亡時比一般人要沉著冷靜。事實上,當醫學生在未來工作中,面對越來越多的死亡病例時往往會沉著冷靜,但也不排除是麻木的沉著,隱含在生與死生理現象背后的意義并未被察覺,其正確的生死觀也沒有樹立。專業知識替代性思維使得本來具備開展生死觀教育優勢的醫學院校,當前卻在這個領域呈現出一片空白。
綜上所述,醫學院校有條件且能做好生死觀教育,醫學生這個特殊的大學生群體也迫切需要生死觀教育的指導。
三、醫學生生死觀教育的必要性
醫學生是大學生中的特殊一群,其特殊性既在于他們的專業學習與未來職業,同時也與社會對他們的期待相關。生死觀教育對醫學生來說,具有特別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1.生死觀教育可以培養醫學生的醫學人文精神。醫學人文關懷是指在醫護過程中,除了為病人提供必須的診療技術服務之外,還要為病人提供精神、文化、情感的服務,以滿足病人的健康需求。醫學人文關懷在診療過程中的重要性不亞于純醫學技術服務,醫務工作者在接受專業教育時,由于其人文知識的匱乏、對人文類課程的忽視,且在實際工作中,醫務工作者過分重視經濟效益、不重視與病患的交流和溝通,醫學人文關懷往往被忽略。要切實樹立醫護人員的醫學人文關懷精神,應當從在校醫學生開始進行教育,特別是通過生死觀教育,使他們將生命神圣、生命價值等觀念根植于心底,教育和引導醫學生對生命的重視和理解,充分認識到患者首先是人,是有生命尊嚴和價值的人,而不僅僅看到疾病本身,從而真正踐行“以患者為中心”的工作作風。
2.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確立要求對醫學生進行生死觀教育。1977年美國學者恩格爾提出應以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逐漸取代單純生物醫學模式,從此,醫學界及醫學教育界便一直致力于“新醫學模式”的構建。很顯然“新醫學模式”在診療中,既要考慮生物因素,又更加重視心理、社會因素產生的病因及治療方法。這就要求在醫學人才的教育中要培養學生對患者心理、生活、工作環境分析的能力。這種分析能力的培養最根本的途徑是從更深層的生命與死亡觀念的樹立中去培養,醫學生自己首先理解了生命或生的意義,懂得死亡是人類生命不可逆轉的生物學現象,克服對死亡的恐懼感,能夠從容面對死亡,才能在未來的工作中真正應用新醫學模式于患者,更容易走近患者,產生共鳴,深入了解患者,找到真正的病因。
3.未來職業特點及自身需要決定了醫學生生死觀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醫學生未來職業將經常面臨患者的三種狀態,即生、傷、死,其中死亡事件將會是最常遇到的事件,沒有哪一種職業像醫護人員這樣頻繁而又近距離地接近“死亡”。同其他大學生一樣,受傳統重生輕死教育的影響,他們同樣恐懼死亡,大多表現為對死亡的無知與困惑,又因為不同于其他專業學生的壓力,醫學生群體是心理問題與疾病的高發人群,因此醫學生中輕率對待生死的事件并不鮮見。通過死亡教育能夠使醫學生解除對死亡的神秘感,更加深入地理解死亡,明白死亡的意義,直面死亡,深入了解生命存在的意義,從而珍惜生命、坦然面對死亡;在未來工作中能夠推己及人,尊重他人生命,真正實踐“醫者父母心”的信條,既要努力延長患者的生命長度,更要人道地關懷他人、重視生命質量。
4.塑造良好的醫患關系要求有效的醫學生生死觀教育。
如前所述,切實有效的生死觀教育不僅有利于醫學生個人的成長,對其未來從事的職業同樣大有裨益。特別是在目前醫患關系仍然較為緊張的形勢下,生死觀教育作為職業道德教育的補充,對改善醫患關系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醫患間缺乏溝通、醫院的商業化運作模式是導致醫患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醫生視患者為勞動對象與效益的來源,將患者排除在專業領域之外,導致患者置身醫療過程之外,逐漸產生了醫患間的對立。通過生死觀教育使醫學生對生命產生敬畏之心,未來職業中自然會恪盡一名醫護人員的職守,尊重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權利;因為對死亡必然性的理解,對患者的生、傷、死會產生感同身受的體驗,從而真正做到以人為本,關心、關懷每一位患者。這必然能夠緩解醫患的緊張關系,逐漸使對立的雙方走向目標一致的統一。
系統的生死觀教育在我國是一個老話題、新任務,應當借鑒比較成熟的教育理念與教育體系,對于大學生來說無法補上兒童、少年時期的缺課,但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關鍵期加強生死觀教育,對其今后走向社會為時未晚。對醫學生來說,無論從其自身發展的角度還是從未來職業要求的角度來看,都應當能夠接受有效的生死觀教育。醫學院校相較于其他院校擁有開展生死觀教育的優勢,應當及時、系統地安排生死觀教育課程,為其他院校及社會上開展生死觀教育提供有益借鑒。
[注釋]
①宋曄.一個亟待關注的課題:生死教育[J].上海教育科研,200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