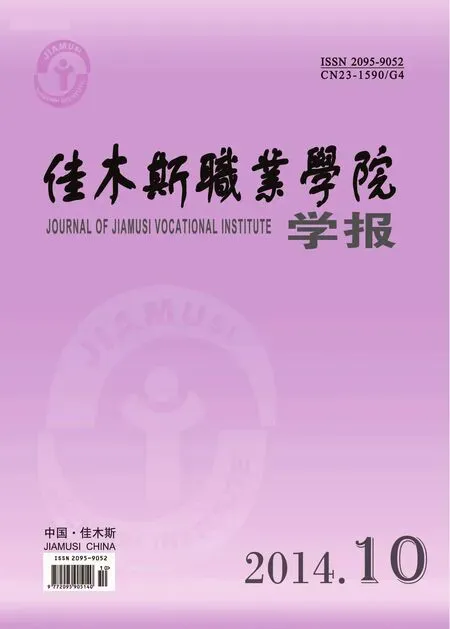疏離者的悲歌
——麥爾維爾《白鯨》主題解析
李艷紅
(吉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吉林四平 136000)
疏離者的悲歌
——麥爾維爾《白鯨》主題解析
李艷紅
(吉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 吉林四平 136000)
《白鯨》是19世紀美國重要作家赫爾曼·麥爾維爾的代表作,是美國文壇及世界文學史上的一部不朽的經典作品。該作品似史詩般宏大,充滿悲劇的色彩,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主題思想。
《白鯨》;主題;悲劇
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是19世紀美國后浪漫主義時期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一生創作的作品包括小說、短篇故事和詩歌。但其生前并不被人重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他創作的偉大之處才被重新發現。其代表作《白鯨》(Moby Dick,1851)也被重新界定為美國文壇及世界文學史上的一部不朽的經典作品,被《劍橋文學史》稱之為“世界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海洋傳奇小說之一”。
《白鯨》是敘述者以實瑪利(Ishmael)講述的一次海洋捕鯨探險的經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艘名為“裴廓德號”(Pequod)捕鯨船的船長亞哈(Ahab),他因為被一只名為莫比·迪克(Moby Dick)的大白鯨咬斷了一條腿而展開了對后者的復仇。亞哈船長帶領整艘捕鯨船與莫比·迪克較量的結局是兩敗俱傷,整艘捕鯨船連同船員覆沒在大洋中,只有以實瑪利被路過的船只救起而幸存下來。故事線索清晰,跌宕起伏,史詩般的宏大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主題思想。
一、無所畏懼的冒險精神
翻開《白鯨》,字里行間透露著冒險精神的主題。以實瑪利一開始就告訴讀者,到茫茫海域上才能治愈他的憂郁,如果他再不出海,就會用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而面對海上不可預知的種種兇險,他卻毫無怯意,求之不得,視為理想追求。在主人公亞哈船長身上,毫無畏懼的冒險精神體現的更為突出,雖被咬斷了一只腿,卻依然率領著捕鯨船向茫茫海洋出發,在危險隨時到來的情形下卻依然朝向復仇的目標前行,不惜付出生命。船上其他的船員和捕鯨手無一不體現出無畏和冒險。
這種無所畏懼的冒險精神在筆者看來有著更深的寓意。回顧美國歷史,美國民族特質的形成就源于冒險精神,最初北美大陸被發現是因為哥倫布的冒險,隨之不斷有來自歐洲的冒險者登陸到這片土地,其中盎格魯撒克遜一族尤為強大,在他們冒險精神中匯集了樂觀務實的態度,最終成為這片新大陸的主宰,締造了新的美利堅民族。冒險、樂觀、務實也成為美國民族精神,推動著美國的發展與壯大,到麥爾維爾時期,已使美國疆域由東海岸的新英格蘭區推進至中西部并直達西海岸。可見,《白鯨》中的無所畏懼的冒險精神正是美國民族精神的寫照。但從亞哈船長的命運結局的安排上,麥爾維爾似乎在向讀者透露他的警示,追求過度瘋狂的冒險會招致惡果,進而反映出作者對19世紀美國資本主義迅速擴張的擔憂之情和悲觀看法。
二、自取滅亡的極端個人主義
小說中的主人公亞哈船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個人英雄主義者,他聰明、智慧、獨立、有堅強的意志和征服一切的勇氣。以實瑪利視他為“神”,捕鯨船上的其他船員更將他奉為“王”,而亞哈船長也自詡為不凡神圣之人,船上的一切都由其主宰,只有他的意愿才是至高無上而不可違背的。正是這樣的極端個人主義,才使得亞哈船長聽不進大副斯達巴克(Starbuck)勸說,一意孤行,為滿足個人復仇的一己私欲,執意帶領已完成出海任務的捕鯨船向充滿危機的深海進發。在與大白鯨莫比·迪克正面交手的三天過程中,亞哈船長無視白鯨用兩天相繼掀沉兩條小艇的警告,固執地繼續實施他的復仇行動,不顧船上其他人的生死,最終將“裴廓德號”捕鯨船及全體船員至于萬劫不復之地。
亞哈船長的遭遇體現了麥爾維爾對于個人主義的看法,他認為極端個人主義所要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的,懷著極端個人主義思想的人最終只會走向自取滅亡的悲劇結局。
從更深層次上來看,麥爾維爾對個人主義的態度是對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思想的解構。
三、對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解構
以愛默生思想為主的新英格蘭超驗主義的特征之一是尊崇個性,強調人性中的神性和個人的重要性,認為社會的主要構件是個人而非群體。理想的人是自我依靠的人,要“相信你自己”。
對照《白鯨》中亞哈船長的人物個性的塑造,不難看出,麥爾維爾對愛默生的關于個人主義的超驗思想是持否定態度的。他認為愛默生的個人主義理念太過樂觀,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沒有意識到對個人主義過于理想化的追求最終勢必導致極端個人主義。如同亞哈船長一樣,不僅沒能通過自我依靠發展成為理想的人,相反卻成為“裴廓德號”捕鯨船上的邪惡化身,給捕鯨船帶來覆滅的結局。
不僅如此,麥爾維爾在《白鯨》中還解構了超驗主義的另一個思想。愛默生等超驗主義者認為自然是超靈(上帝)的象征,并不完全是物質的,是有生命的,是超靈的外衣,可以凈化人的心靈,人融入自然可以使思想向健康的方向發展。在《白鯨》中,麥爾維爾解構了這一思想。小說中的大白鯨莫比·迪克理所當然是自然的代表,可當人們談起它時卻總是心生畏懼,透著神秘,對海上過往的船只充滿了敵意,亞哈船長與之打交道先是被咬掉了一條腿,而后在心中燃起復仇之火,心靈不僅未得到凈化,反而走向邪惡。因此,自然對人是漠視的,并存在敵意,人面對自然是渺小的,力量是有限的。
麥爾維爾透過《白鯨》解構新英格蘭超驗主義思想旨在讓人類思考一個更為宏大的問題,即,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應時刻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該如何和諧發展。
四、對人類文明的反思
“裴廓德號”捕鯨船在大洋上就如同人類社會處于自然界中,象征著人類文明進程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這艘捕鯨船出海的主要目的是捕殺鯨魚制作鯨魚產品,是人類社會向自然界索取滿足其發展所需的縮影。縱觀人類文明化的進程,我們不難發現,伴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類活動的范圍也越來越大,對自然的吞噬與攫取的也越來越多的,同時自然對人類的回應也在發生著變化。最初,人類文明程度不高,在農耕時代只要自然界提供維持生存的產品就好,這時自然對人類是寬容的;隨后,人類進入到工業文明發展的時代,人類已不再滿足于基本生存的狀態,向自然界要求的不再局限于谷物棉麻,不斷地使用轟鳴的機器瘋狂地毀掉荒野叢林,挖掘礦山土地,攪動瀚海湖泊,同時向自然界拋去廢物垃圾,這時自然被惹惱了,不斷地用洪水、干旱、風沙、霧霾來教訓人類,就像大海和白鯨對待捕鯨船一樣。
如果“裴廓德號”捕鯨船在完成捕鯨任務就返航回到陸地,不再向大海進一步索取大白鯨莫比·迪克,結局又會是怎樣能?為什么只有以實瑪利幸存下來呢?僅僅是要他來講故事嗎?顯然,麥爾維爾是在通過以實瑪利這一人物的書寫指導讀者正確反思。以實瑪利從一開始對待大海和白鯨的態度就是懷有憧憬、探索和敬畏的,在他對鯨魚及鯨魚產品加工知識的介紹中,還透漏著熱愛、尊重與崇拜。大概是大海感知到了以實瑪利的情懷,并回饋以肯定,才沒有淹沒他。這不禁讓現代的讀者驚嘆麥爾維爾的偉大與思想的深邃,他透過美國19世紀上半葉的發展趨勢,已經預知了未來人類社會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將導致人類與自然之間出現怎樣的摩擦,他在提醒整個人類社會要認真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對自然要敬畏、熱愛、維護,自然才會繼續無私地用陽光雨露供養人類,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才是文明的真諦。
五、疏離異化
疏離異化是麥爾維爾通過《白鯨》這部作品向讀者揭示的另一深刻主題。主人公亞哈船長為追捕大白鯨莫比·迪克的做法并不受歡迎,然而他拒絕接受大副斯達巴克的勸說,而用盡一切手段強行實施自己的計劃,他雖成功脅迫捕鯨船跟隨自己去復仇,但并未獲得理解;當另一艘捕鯨船的船長懇請他幫忙搜救被白鯨傷害的兒子時,他無情地拒絕。這些都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閡。亞哈船長拋掉家庭終日在海上漂泊,以實瑪利無法忍受陸地生活,捕鯨船遠離陸地不斷向深海挺近,這一系列的描寫透視出的是人與社會的疏遠。而影射人類社會的“裴廓德號”捕鯨船在海上與自然界代表白鯨的廝殺則反映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疏離。這三個層面的疏離最終帶來的是相同的結局——覆滅。
麥爾維爾透過《白鯨》這一鴻篇巨制演唱了一曲疏離者的悲歌,震撼著生活在全球化今天的當代人,發人深省。
[1]Baym, Nina.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98.
[2]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論自然[M].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0.
[3]常耀信.美國文學簡史[M].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An Analysis of the Themes in Moby Dick
Li Yan-h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Jilin, 136000, China)
Herman Melvil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riter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whose masterpiece Moby Dick is known a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works. It is tragic work which is full of profound themes.
Moby Dic; theme; tragedy
I106.4
A
1000-9795(2014)010-000032-02
[責任編輯:劉 乾]
李艷紅(1972-),女,吉林榆樹人,副教授,從事英美文學研究。